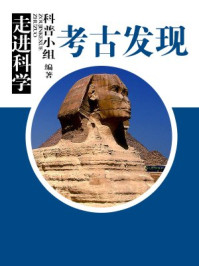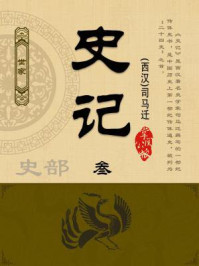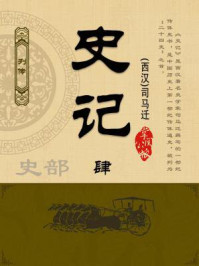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 Porphyrogennetos,Κωνσταντ
 νος Ζ' Πορφυρογ
νος Ζ' Πορφυρογ
 ννητος
ννητος
 ,生于905年5月,卒于959年11月9日,享年54岁)是马其顿王朝第四位皇帝,出生当年便被父皇利奥加冕为共治皇帝,913—920年和945—959年两度登基,共在位21年。
,生于905年5月,卒于959年11月9日,享年54岁)是马其顿王朝第四位皇帝,出生当年便被父皇利奥加冕为共治皇帝,913—920年和945—959年两度登基,共在位21年。
君士坦丁七世出身于皇室,幼年继位,经历大臣辅政、母后摄政,岳父罗曼努斯一世篡位,直至945年才重新夺回帝位,历经重重政治动荡。君士坦丁七世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磨难。他幼年失去父亲,母亲邹伊的合法地位一直备受质疑,而且在其叔叔亚历山大统治时期,邹伊被遣送至修道院,母子长时间分离,使得他的成长缺乏至亲陪伴。在被推上皇位后,他亲眼看见多次残酷的宫廷动荡,后又在其岳父罗曼努斯一世的监控下生活,其早期宫廷生活十分艰辛。由于长期被排斥在帝国政治核心圈之外,君士坦丁七世有充裕的时间潜心学习写作,对学问表现出广泛的兴趣。现流传下来的君士坦丁七世的著作主要有四部,分别是《礼仪书》《论帝国政府》《君士坦丁七世关于军队远征的三篇手册》《瓦西里一世传》。
913年6月,亚历山大去世后,年仅七岁的君士坦丁七世继承皇位,由尼古拉为主的七位大臣辅政。这个摄政团体成立不久,即面临着内外困局的挑战,权力斗争导致摄政者的更迭。君士坦丁·杜卡斯,这位在地方掌握重兵的将军,秘密潜入首都后,意图谋反篡位,但是很快被摄政大臣之一的约翰·艾拉达斯(John Eladas)平叛。参与这次反叛的人受到了严酷惩处,杜卡斯本人在反叛中被杀。杜卡斯的岳父格里高利在反叛失败后躲入圣索菲亚大教堂避难,但仍然被艾拉达斯从教堂拖出,并被关入修道院。部分反叛者受到鞭刑,并被游街示众,或者被弄瞎双眼,遭到流放。
 摄政者对于反叛者毫无怜悯,处罚严厉,以震慑觊觎者,树立皇家权威。而来自保加利亚人的入侵,也考验着新成立的摄政团体,甚至导致了尼古拉的下台。此前,由于亚历山大拒绝继续履行与保加利亚人的和平协议,保加利亚国王西米恩以此为借口,再次入侵拜占庭帝国,并很快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以尼古拉为首的摄政者们力主和平,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当代拜占庭学家朗西曼认为,尼古拉的和平政策是出于教会控制权方面的考量,是为了牢牢把握住对保加利亚教会的控制权。此前君士坦丁堡教会在与罗马教会争夺保加利亚教会控制权中胜出,尼古拉担心战争会引发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甚至会倒向罗马教会,因此,即使在双方作战期间,他依然试图通过书信说服保加利亚宫廷接受和平协议。
摄政者对于反叛者毫无怜悯,处罚严厉,以震慑觊觎者,树立皇家权威。而来自保加利亚人的入侵,也考验着新成立的摄政团体,甚至导致了尼古拉的下台。此前,由于亚历山大拒绝继续履行与保加利亚人的和平协议,保加利亚国王西米恩以此为借口,再次入侵拜占庭帝国,并很快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以尼古拉为首的摄政者们力主和平,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当代拜占庭学家朗西曼认为,尼古拉的和平政策是出于教会控制权方面的考量,是为了牢牢把握住对保加利亚教会的控制权。此前君士坦丁堡教会在与罗马教会争夺保加利亚教会控制权中胜出,尼古拉担心战争会引发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甚至会倒向罗马教会,因此,即使在双方作战期间,他依然试图通过书信说服保加利亚宫廷接受和平协议。
 西米恩在攻城无果之后,接受了尼古拉的协议,并获得了两国联姻的提议,有望成为君士坦丁七世的岳父。
西米恩在攻城无果之后,接受了尼古拉的协议,并获得了两国联姻的提议,有望成为君士坦丁七世的岳父。
虽然在亚历山大选定的摄政七大臣中,尼古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权力斗争的加剧,摄政者面临新一轮的更迭。君士坦丁七世的母亲邹伊,虽然其皇后身份长期得不到承认,被排斥在政治核心圈之外,但是从未放弃对权力的觊觎。由于君士坦丁七世年幼无知寻找母亲,邹伊得以重返宫廷,之后她加快培植亲信,摄政大臣之一的约翰·艾拉达斯成为其重要助手。在艾拉达斯的建议下,邹伊罢免了亚历山大的宠臣,并计划召回优西米乌斯替换尼古拉,但是遭到优西米乌斯的拒绝。不久,艾拉达斯也去世了,邹伊不得不答应与尼古拉共同执政,但她警告尼古拉管好自己的事(教会的事)。
 邹伊摄政期间,非常倚重宦官君士坦丁。
邹伊摄政期间,非常倚重宦官君士坦丁。
在她摄政初期,帝国最大的外部敌人还是保加利亚人,西米恩带领军队侵占色雷斯地区,邹伊向大臣们询问如何能够有效地解决西米恩的入侵,约翰·博加斯(John Bogas)自我举荐,如果能获得贵族头衔,他可以说服帕齐纳克人攻打保加利亚人。在得到封赏后,博加斯前去与帕齐纳克人签订协议,后者同意越过多瑙河打击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的进攻因此得到暂时遏制。然而,邹伊无法忍受保加利亚人连续不断的侵扰,决意主动进攻以绝后患,为此,她进行了精心的战前准备。她与萨拉森人签订和约,以便于集结东、西部所有军队对付保加利亚人。邹伊任命利奥·福卡斯(Leo Phokas)为征讨保加利亚人的主帅,所有部队集结于迪阿巴斯(Diabasis),参与此次出征的将领还包括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等
 ,军队中招募了大量亚美尼亚人士兵。917年8月6日,拜占庭人与保加利亚人在阿彻鲁斯(Achelous)要塞附近交战,战争之初,拜占庭军队占据优势,但之后局势出现逆转,西米恩率领保加利亚人反击成功。关于造成战场形势改变及拜占庭军队溃败的原因,斯基利齐斯记载了两个版本,其主要区别在于对罗曼努斯一世的描述。第一个版本只字未提罗曼努斯一世,将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利奥·福卡斯的粗心大意,进而引起一连串的溃败。而第二版本则提及罗曼努斯一世负责运输帕齐纳克人增援大部队,但是在途中与博加斯争执不下,导致帕齐纳克人中途折返,利奥·福卡斯失去重要的外援而兵败。更为重要的是,利奥·福卡斯听到传闻说罗曼努斯一世意图谋反,遂不顾战争有利的情况,迅速下令撤退,引发不明就里的士兵混乱,西米恩趁机反攻,并获得胜利。罗曼努斯一世在战后也被指控渎职,只是因为友人的帮助才免于重刑受罚。
,军队中招募了大量亚美尼亚人士兵。917年8月6日,拜占庭人与保加利亚人在阿彻鲁斯(Achelous)要塞附近交战,战争之初,拜占庭军队占据优势,但之后局势出现逆转,西米恩率领保加利亚人反击成功。关于造成战场形势改变及拜占庭军队溃败的原因,斯基利齐斯记载了两个版本,其主要区别在于对罗曼努斯一世的描述。第一个版本只字未提罗曼努斯一世,将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利奥·福卡斯的粗心大意,进而引起一连串的溃败。而第二版本则提及罗曼努斯一世负责运输帕齐纳克人增援大部队,但是在途中与博加斯争执不下,导致帕齐纳克人中途折返,利奥·福卡斯失去重要的外援而兵败。更为重要的是,利奥·福卡斯听到传闻说罗曼努斯一世意图谋反,遂不顾战争有利的情况,迅速下令撤退,引发不明就里的士兵混乱,西米恩趁机反攻,并获得胜利。罗曼努斯一世在战后也被指控渎职,只是因为友人的帮助才免于重刑受罚。
 很明显,在第二个版本中,虽然战争失利要归咎于利奥·福卡斯,但是罗曼努斯一世也要承担相应责任。相比较而言,第一个版本对罗曼努斯一世避而不谈,更像是对其不光彩历史的遮掩,毕竟罗曼努斯一世之后篡位成功,登基做了皇帝。
很明显,在第二个版本中,虽然战争失利要归咎于利奥·福卡斯,但是罗曼努斯一世也要承担相应责任。相比较而言,第一个版本对罗曼努斯一世避而不谈,更像是对其不光彩历史的遮掩,毕竟罗曼努斯一世之后篡位成功,登基做了皇帝。
对保加利亚人作战失利,不仅未能清除宿敌,也极大降低了邹伊的威望。外事未平,内忧又起,利奥·福卡斯与宦官君士坦丁勾结,意图篡位自立,君士坦丁七世的老师塞奥多利向罗曼努斯一世寻求援助,希望这位海军司令带领舰队护驾。利奥·福卡斯以清君侧的名义反叛,但迅即被揭穿,罗曼努斯一世派人将君士坦丁七世的诏令传于利奥·福卡斯的军营:“皇帝陛下认为罗曼努斯一世能力卓越、忠心耿耿,他会像父亲般守护臣民们……利奥·福卡斯总是心怀叵测,不满于皇帝的统治,如今更是显出隐藏已久的敌意。他失去了作为臣民的资格,只是篡位者、反叛者。”
 参与反叛的军队将士在得知真相后军心大乱,溃败逃散。利奥·福卡斯的反叛以失败告终,但是它给罗曼努斯一世的上台提供了机遇。此后,罗曼努斯一世将女儿海伦娜嫁给小皇帝,他本人不仅成为君士坦丁七世的岳父,还被加冕为共治皇帝,进而取代君士坦丁七世成为执政者,而邹伊再次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赶出皇宫,结束了其皇后摄政生涯。
参与反叛的军队将士在得知真相后军心大乱,溃败逃散。利奥·福卡斯的反叛以失败告终,但是它给罗曼努斯一世的上台提供了机遇。此后,罗曼努斯一世将女儿海伦娜嫁给小皇帝,他本人不仅成为君士坦丁七世的岳父,还被加冕为共治皇帝,进而取代君士坦丁七世成为执政者,而邹伊再次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赶出皇宫,结束了其皇后摄政生涯。
君士坦丁七世在位初期,经历了大臣摄政、皇后摄政和皇位遭到篡夺多次磨难,这暴露了皇权血亲世袭制度存在的风险。血亲世袭继承虽然降低了帝国最高权力交接中的社会成本,但是其制度性的不足也不容忽视。继任者所拥有的制度化权力与实际的执政能力并不一定对称,这种矛盾尤其体现在幼帝继位时。年幼的皇帝在各个方面还处于他人照料阶段,并不具备执掌帝国内外军政大权的能力,很容易出现最高皇权空虚的状态,为篡位者提供可乘之机。即便拜占庭帝国也出台了相应的摄政制度以作辅助,但是由于摄政者自身政治能力、政治野心及政治环境的不同,摄政权力也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很难保障皇权的正常运行。围绕着虚位的最高权力,必定形成多种势力的博弈,通常会酿成血腥的宫廷内讧。幼帝继位,皇帝成为象征,皇权则变为军事强人和大贵族争夺的目标,其与实际统治权相分离的状态必然形成权力真空,而摄政权的不稳固为篡位者提供了机遇。君士坦丁七世继位后,围绕摄政权的斗争是帝国政局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也为罗曼努斯一世参与权力角逐提供了机遇。成为国丈后,罗曼努斯并不满足,他企图建立自己的王朝,不仅将其子加冕为共治皇帝,而且处处压制小皇帝。不幸的是,他的企图被自己的儿子们破坏了,他们发动政变将父皇废黜。
944年12月16日,罗曼努斯一世被自己的儿子斯蒂芬、君士坦丁赶下台,并被流放至普罗特。斯蒂芬与君士坦丁开始联合执政,君士坦丁七世的复位计划也在悄然进行中。945年1月27日,君士坦丁七世召集旧部,将斯蒂芬、君士坦丁流放,在权力角逐中胜出,年近40岁开始真正独立执掌政权,帝国的统治再次回到瓦西里一世的血亲后代中。君士坦丁七世独立执政前已迎娶皇后,当时,年幼的他也并无太大选择权。919年,14岁的君士坦丁七世迎娶了罗曼努斯一世的女儿海伦娜,共育有七个子女,儿子罗曼努斯二世出生于939年,并在君士坦丁七世复位后的945年被加冕为共治皇帝,五个女儿为邹伊、塞奥多拉、阿加莎、塞奥法诺、安娜,在罗曼努斯二世继位后,被流放至修道院。此外,他还有一个儿子利奥,不幸早逝。
关于君士坦丁七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斯基利齐斯认为君士坦丁七世算不上合格的统治者。“一旦独自掌权,人们期待他成为一个能力卓著、精力充沛、全身心地投入国家事务中的统治者。但事实上,他比预期的要弱,几乎未完成人们期待的任何事。他喜欢饮酒、耽于享乐……他对错误难以容忍,并冷酷无情地施以惩罚。他对官员的提拔毫不关心,不愿意根据出身或功绩来任命或提拔他们。他委任官员时,无论是军事或民事的,往往不加选择,随意给予那些在场的人。因此这样的情况一再出现,一些卑鄙、可疑的人被任命为最高的民事官员……他的妻子海伦娜过多地干预他,还有瓦西里,他们要对买官鬻爵的事情负责任。”
 约翰·沃特利(John Wortley)认为斯基利齐斯对君士坦丁七世一味否定的评价明显有失公允。詹金斯认为关于君士坦丁七世的种种评价,并不矛盾。君士坦丁七世往往被描述为软弱的、孤僻的、高傲的、专心的、勤奋的。“他大量饮酒,只是为了缓解害羞。如果说他有些严格,甚至残酷,这只是他性格内向的另一面。他爱好学术,很像他的父亲,这在他被幽禁时期更为明显。他缺乏自信,是因为长期受制于罗曼努斯一世。不过在这些年中他掌握了大量历史学、古文物的知识,这些知识积累成为他创作各式手册及历史研究的基础,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组织机构。而且他在文化领域成就非凡,他支持典籍编撰,鼓励学术研究。”
约翰·沃特利(John Wortley)认为斯基利齐斯对君士坦丁七世一味否定的评价明显有失公允。詹金斯认为关于君士坦丁七世的种种评价,并不矛盾。君士坦丁七世往往被描述为软弱的、孤僻的、高傲的、专心的、勤奋的。“他大量饮酒,只是为了缓解害羞。如果说他有些严格,甚至残酷,这只是他性格内向的另一面。他爱好学术,很像他的父亲,这在他被幽禁时期更为明显。他缺乏自信,是因为长期受制于罗曼努斯一世。不过在这些年中他掌握了大量历史学、古文物的知识,这些知识积累成为他创作各式手册及历史研究的基础,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组织机构。而且他在文化领域成就非凡,他支持典籍编撰,鼓励学术研究。”

君士坦丁七世崇尚学术与教育,促成了古典学的复兴。他也提倡教授实践知识,传递经验的智慧。但是,他所在的时代这方面的书籍十分匮乏,于是他致力于此类书籍的编撰,并系统化地完成工作,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撰选集、百科全书,并汇总商业和政府管理方面的实用信息整理成册。
 君士坦丁七世在位期间,积极推动算术、音乐、天文学、几何学等古典学术的复兴,聘请各领域的专家为教师,并大力奖赏勤奋努力之人。同时君士坦丁七世也亲自参与著书立说,为马其顿王朝的文化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君士坦丁七世在位期间,积极推动算术、音乐、天文学、几何学等古典学术的复兴,聘请各领域的专家为教师,并大力奖赏勤奋努力之人。同时君士坦丁七世也亲自参与著书立说,为马其顿王朝的文化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君士坦丁七世著有《礼仪书》,内容包括帝国的宫廷礼仪与友邦的外交礼节等。这部著作的内容十分庞杂,涉及宗教传统节日的流程细节,如圣诞节、主显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耶稣升天节等;帝王的仪仗队从皇宫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路线、具体要求等;皇帝参与非固定的宗教宴会的仪式;皇帝的加冕、皇后的加冕需要穿着的服装、必要的盛典仪式;皇帝接见帝国官员、外国使臣的仪式;帝国官员任命的仪式;皇帝在大竞技场观看蓝、绿、红、白车队的比赛等。君士坦丁七世充分肯定了帝国礼仪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维护帝王权威的重要手段。同时,他编撰这部书籍,也是为了使重要的礼仪要求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遗忘。目前存世的君士坦丁七世《礼仪书》的最早版本保存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是尼基弗鲁斯二世时期的手抄本,也是现存唯一易辨认的版本。在最初的手抄本中,这部著作的名称十分简单,即《皇帝汇编本》
 ,直至18世纪中叶的学者莱克(Leich)在编订过程中以拉丁语“De cerimoniis aulae Byzantinae”为其命名,这个名称与著作的第一部分内容相符合,现代学者沿用了这个名称,即《礼仪书》。
,直至18世纪中叶的学者莱克(Leich)在编订过程中以拉丁语“De cerimoniis aulae Byzantinae”为其命名,这个名称与著作的第一部分内容相符合,现代学者沿用了这个名称,即《礼仪书》。

君士坦丁七世还为其祖父立传《瓦西里一世传》,以歌颂这位马其顿王朝第一任皇帝的丰功伟绩。君士坦丁七世在作品中表达了著书立说的初衷,“一直以来我便希望将政府管理的经验、认知传给优秀的人,通过可记忆的、长久的历史记述这种方式。我打算详细记下罗马人统治拜占庭时期的显著成就——假设我能做到的话——皇帝的功绩,服务于他们的官员、将军、副官们的作为。但是这需要大量时间,全神贯注的投入,参阅众多的典籍,并从日常的繁杂事务中抽出身来,这些对我来说不太可能,我只能退而求其次:目前写下关于一位皇帝一生的事情……他做了很多有益于罗马帝国的事。通过这种方式,子孙后代才不会忘记帝国的根基、最初的样子,这样也为后代们立下标准——可供模仿的楷模”
 。君士坦丁七世的《瓦西里一世传》保存在《塞奥法尼斯编年史续》中。11世纪时,一位匿名者将一些历史文本编辑成册,这些文本包括813—961年间的史事,分为四卷,其内容独立,形式各异,贝克(Bekker)的伯恩版本称其为“塞奥法尼斯编年史续”。第一卷的作者匿名,涉及813—867年的历史,他自称为忏悔者塞奥法尼斯的后继者,但是其作品的体裁未采用编年体,而是皇帝列传的形式。第二卷的作者即君士坦丁七世,他专门为其祖父瓦西里一世做传。第三卷非常接近大法官西米恩的作品。最后一卷明显写作于963年以前,作者可能是塞奥多利。
。君士坦丁七世的《瓦西里一世传》保存在《塞奥法尼斯编年史续》中。11世纪时,一位匿名者将一些历史文本编辑成册,这些文本包括813—961年间的史事,分为四卷,其内容独立,形式各异,贝克(Bekker)的伯恩版本称其为“塞奥法尼斯编年史续”。第一卷的作者匿名,涉及813—867年的历史,他自称为忏悔者塞奥法尼斯的后继者,但是其作品的体裁未采用编年体,而是皇帝列传的形式。第二卷的作者即君士坦丁七世,他专门为其祖父瓦西里一世做传。第三卷非常接近大法官西米恩的作品。最后一卷明显写作于963年以前,作者可能是塞奥多利。

君士坦丁七世著有《论帝国政府》,是写给他的儿子罗曼努斯二世的,希望将外交及军事方面的经验传授给他,培养罗曼努斯二世成为英明的君主。他在前言中写道:“我为你留下一份集知识与经验的手册,你以后将不会在好的建议及公共利益方面犯错:首先,哪个民族能够使罗马人获益,哪个民族会伤害罗马人?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可以在战场上分别遇到其他民族并征服他们?其次,考虑到他们的贪婪、无法满足的胃口以及过度要求的礼物;之后考虑到不同民族的差异,他们的起源、习俗及生活方式,他们生活所在地的位置、气候,它的地理描述、测量,此外,考虑到不同时期罗马人与不同民族所发生的事情;因此,什么样的改革一直被引入我们的帝国,并贯穿罗马帝国始终。以上我通过个人的才智所了解的事情,希望未来都可以传达给你,我钟爱的儿子,因此你可以了解到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如何对待及安抚他们,或向他们开战并反击他们。”

君士坦丁七世的这部著作,最初并无标题,直至迈尔修斯(Meursius)为其标注拉丁语的名称“De Administrando”。据学者推测,这部书大致完成于948—952年间。该著作的内容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论及外交政策的核心,主要针对最为危险、最复杂的北方民族和斯基泰人。第二部分总结外交教训,主要针对这一地区民族。第三部分,也是最长的部分,是关于帝国周边民族的历史、地理信息,从萨拉森人开始,到东南部的民族,环地中海、黑海各族群,直至亚美尼亚人。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帝国境内的历史、政治、组织机构的概述。君士坦丁七世这部著作的很多内容,是根据更早的古代作品改写的。
《论帝国政府》被完整翻译出版的译本共有四个,两个为拉丁语译本,一个为俄语译本,一个为克罗地亚译本。第一个拉丁语译本由迈尔修斯翻译,1611年出版,并在1617年进行了再版(未进行修改),采用的皆为拉丁语与希腊语的对照版。拉米在编撰迈尔修斯作品集时,将他的译本放在附录部分出版。安塞姆·班杜拉(Anselm Bandur)对迈尔修斯的译本进行了重大修正及补充,于1711年出版,1729年这一重修的版本在维也纳再版。拉米编撰的迈尔修斯作品集中,同样收录了班杜拉的重修本,并与希腊本相对照。贝克的1840年版本与米涅的1864年版本同样收录了这一译本。之后,《论帝国政府》相继被翻译成俄文、克罗地亚文等语言。关于《论帝国政府》的选编,被收录及被翻译的语种更为丰富,除了拉丁文、俄文,还被翻译成法文、德文、英文等。

《君士坦丁七世关于军队远征的三篇手册》主要是关于帝国军队在远征之前的准备及组织,也被认为是君士坦丁七世对罗曼努斯二世的经验传授。第一篇最为简短,列举了参与远征的军队名册以及各省区军队及其将领与皇帝汇合的地点。首先便是对各个军区的集结命令,列举了亚美尼亚(位于小亚细亚地区的东北部)军区的六个主要基地:马拉基纳(Malagina)、多里利昂、卡伯肯(Kaborkin)、科洛尼亚(Koloneia)、凯撒里亚、达兹蒙。之后便是对各个军区的集结命令。

第二篇讲述皇帝在出征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在征战方面,有两位值得学习的楷模——君士坦丁一世皇帝与凯撒大帝。也有学者认为不可能是他们,因为存在时代错误,凯撒大帝不可能是基督徒。这只是为了遮掩,实际上描述的是另外两位皇帝,即毁坏圣像运动时期的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书中详细记述了君士坦丁大帝在出征前的一系列流程,他对于是否开战十分谨慎,要询问相关人士的意见,决定出征时间、地点,充分了解敌情,并安排各级将领的职责。
 除此之外,君士坦丁大帝在出征前,会指定摄政人,在其离开首都期间注意护卫首都安全,以保障后方的稳固。
除此之外,君士坦丁大帝在出征前,会指定摄政人,在其离开首都期间注意护卫首都安全,以保障后方的稳固。

君士坦丁七世在第三篇中直接表明是写给罗曼努斯二世的,作为父亲留给儿子的重要遗产。君士坦丁七世同样以先辈们作为榜样,分别是米哈伊尔三世、瓦西里一世、塞奥菲鲁斯。君士坦丁七世十分详细地列举了战争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收缴传统捐税(帝国各级官员、主教、修道院应缴纳的标准)、宴会上用的牺牲、帐篷、驮畜、衣物、作为礼物送予外邦的衣料等,之后还讲述了皇帝远征归来应做的事情,并以瓦西里一世、塞奥菲鲁斯的凯旋为例。第一篇及第三篇手册主要涉及小亚细亚地区,特别是叙利亚,这表明此时帝国对外战争的重点发生转移,也验证了在君士坦丁七世时期,帝国向东部地区收复失地的活动在逐步展开。
这三篇手册目前唯一的版本,是莱克和瑞斯克(Reiske)在1751—1754年间整理《论帝国政府》时,收在附录中的文本。
 三篇手册各自独立,有很大区别。第三篇手册写作的时间最靠后,大约开始于1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君士坦丁七世时期似乎并未完成,后继的编辑者又补充进许多君士坦丁七世时期的资料。第二篇手册写作于903—912年间,主要参考了利奥·卡塔凯拉斯(Leo Katakylas)的作品。
三篇手册各自独立,有很大区别。第三篇手册写作的时间最靠后,大约开始于1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君士坦丁七世时期似乎并未完成,后继的编辑者又补充进许多君士坦丁七世时期的资料。第二篇手册写作于903—912年间,主要参考了利奥·卡塔凯拉斯(Leo Katakylas)的作品。
君士坦丁七世在位期间,还颁布了保护军役土地的法令,这是拜占庭帝国第一部关于军役土地的成文法。君士坦丁七世强调:“军队之于国家,正如大脑之于身体,当它们发生改变,整体也会随之变动。如果不关注这些变化,就是罔顾自身安全,更不要说国家的安危。军役土地自创建之初,便是士兵生存、生活的根基,但是现在遭到了破坏,而且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皇帝受命于上帝,要恢复并改善它们,这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

拜占庭帝国自中期以来,进行军饷制度改革,军役土地与士兵的供给、军役的履行密切关联,重要性日益突出。“由于6世纪晚期黄金储备的急剧下降,国家被迫开始部分以铜币而非金银来支付士兵的军饷。当然在贵金属有限的基础上,黄金依然用于支付,特别是用于捐赠。但是从7世纪40年代早期,国家提供给军事附加的捐赠只有通常的三分之一,国家的财政似乎已接近崩溃的边缘。维持军队供给的方式似乎从这一时期开始。”
 通过向帝国外籍士兵授予土地,使其通过土地收入来维持个人的生活与作战,可以有效缓解帝国财政的困境。同时,拜占庭资料也显示被授予土地的农兵成为帝国的重要兵源。
通过向帝国外籍士兵授予土地,使其通过土地收入来维持个人的生活与作战,可以有效缓解帝国财政的困境。同时,拜占庭资料也显示被授予土地的农兵成为帝国的重要兵源。
君士坦丁七世的这部法令并无明确时间,麦克杰尔推测为其继位的初期,他认为这则法令是君士坦丁七世登基之初进行军事整顿政策的一部分
 ,也是君士坦丁七世力图消除腐败、裁撤不称职官员行动中的一部分。据《塞奥法尼斯编年史续》载:“让皇帝记忆犹新的是,在罗曼努斯时代(君士坦丁七世的岳父),悲惨、不幸的小农在军区将军、副官、士兵、骑兵手里遭受的不公及损害。那时他派遣正直及诚实的人前去减轻施加在备受折磨的小农身上的过分勒索造成的巨大压力。他派罗曼努斯·萨洛尼提斯(Romanos Saronites)前往安纳托利亚军区,派罗曼努斯·穆瑟勒(Romanos Mousele)前往奥普斯金军区,派弗提乌斯前往色雷斯军区,派利奥·阿格拉斯图斯(Leo Agelastos)前往亚美尼亚军区,派其他人依次前往剩余的军区。在皇帝的命令下,他们为小农减去了一些痛苦。”
,也是君士坦丁七世力图消除腐败、裁撤不称职官员行动中的一部分。据《塞奥法尼斯编年史续》载:“让皇帝记忆犹新的是,在罗曼努斯时代(君士坦丁七世的岳父),悲惨、不幸的小农在军区将军、副官、士兵、骑兵手里遭受的不公及损害。那时他派遣正直及诚实的人前去减轻施加在备受折磨的小农身上的过分勒索造成的巨大压力。他派罗曼努斯·萨洛尼提斯(Romanos Saronites)前往安纳托利亚军区,派罗曼努斯·穆瑟勒(Romanos Mousele)前往奥普斯金军区,派弗提乌斯前往色雷斯军区,派利奥·阿格拉斯图斯(Leo Agelastos)前往亚美尼亚军区,派其他人依次前往剩余的军区。在皇帝的命令下,他们为小农减去了一些痛苦。”
 君士坦丁七世颁行军役土地与这一行动相呼应。
君士坦丁七世颁行军役土地与这一行动相呼应。
君士坦丁七世首先设定了军役土地不可转让的最低值,以保障军役土地的安全。“士兵(στρατι
 της)不得出售军役(στρατεíα)土地
[1]
,每个负有军役的骑兵至少要持有价值4磅金币的土地。爱琴海、萨摩斯岛(Samos)、西比莱奥特舰队海员要自备装备,履行划桨水手的职责,还要承担沉重的劳役,因此我们规定他们持有的土地,要以此为参照。海员要承担帝国海军及其他海员的开支,长期以来,根据习惯法每份军役至少要有价值2磅金币的土地做保障。我们认为这是足够的。”
της)不得出售军役(στρατεíα)土地
[1]
,每个负有军役的骑兵至少要持有价值4磅金币的土地。爱琴海、萨摩斯岛(Samos)、西比莱奥特舰队海员要自备装备,履行划桨水手的职责,还要承担沉重的劳役,因此我们规定他们持有的土地,要以此为参照。海员要承担帝国海军及其他海员的开支,长期以来,根据习惯法每份军役至少要有价值2磅金币的土地做保障。我们认为这是足够的。”
 此外,法令肯定了军役土地可以通过遗产继承进行转移,但是明确土地与军役密不可分。“那些入军籍并拥有这个数量土地的士兵,未进行过出售,将它们保留了下来,可以依法将这些土地及其连带的义务传给子孙们,当然——不管继承到土地的人是多了或少了,是否是旁系亲属,不管这个遗产是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被平均分配成几份,或按照遗嘱由法律上的、亲缘上的或毫无关系的继承人分别获得大小不等的份数(我们禁止那些权贵染指这些继承),我们规定需要履行的义务与得到的遗产份额相关。”
此外,法令肯定了军役土地可以通过遗产继承进行转移,但是明确土地与军役密不可分。“那些入军籍并拥有这个数量土地的士兵,未进行过出售,将它们保留了下来,可以依法将这些土地及其连带的义务传给子孙们,当然——不管继承到土地的人是多了或少了,是否是旁系亲属,不管这个遗产是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被平均分配成几份,或按照遗嘱由法律上的、亲缘上的或毫无关系的继承人分别获得大小不等的份数(我们禁止那些权贵染指这些继承),我们规定需要履行的义务与得到的遗产份额相关。”
 君士坦丁七世严禁权贵对军役土地的染指:“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购买,尤其是有名望的人,有尊贵头衔的人,大主教、教士、修道院长,或任何一种宗教机构,上至权贵下至普通官员,(如果他们被发现违反了法律)他们将不得要求归还购买的钱款、投入的花费,即使他们正好投入了大量的钱款用于所购土地的开发。他们可以带走原料,但是不能影响到土地现有的状况。”
君士坦丁七世严禁权贵对军役土地的染指:“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购买,尤其是有名望的人,有尊贵头衔的人,大主教、教士、修道院长,或任何一种宗教机构,上至权贵下至普通官员,(如果他们被发现违反了法律)他们将不得要求归还购买的钱款、投入的花费,即使他们正好投入了大量的钱款用于所购土地的开发。他们可以带走原料,但是不能影响到土地现有的状况。”

此外,君士坦丁七世针对军役土地的转让,制定了优先权(Protimesis,προτíμησις)顺序,规定“那些登记在册的士兵的继承人,或是卑亲属,或是尊亲属,或是旁系亲属,根据亲缘关系拥有优先购买权,并被允许收回士兵不慎转让以及权贵霸占的土地。只有亲缘比较近的亲属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收回土地时,更远一些的亲属才被允许。如果所有的亲属以及那些姻亲关系的亲属都没有可能,那么他们在军队中关系密切的纳税人或战友也可以,如果他们也未出现,那么同一税区的更为贫困的士兵,可以通过这些土地来自给自足。如果这些人也未出现,那就有必要召集同一税区未入军籍的纳税人,以保障这份税收可以征集上来”
 。
。
君士坦丁七世在法令最后再次谴责权贵对军役土地的侵占,明确指出“当权贵们急切地搜刮土地,并将不幸的农民纳为农奴时,他们并未想到会受到谴责,而当别人的贪婪超过自己时,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对待。这是邪恶的大范围扩散。灾难不仅没有止于权贵,而且开始往下蔓延,因为通常权贵的习惯会影响到民众。那些受命领导军队的人——虽然根据法律,将军也属于这类人——带领着士兵去往各处,他们收到礼物后就会免役。他们是些收受贿赂的家伙,玩忽职守,不喜战争,比蚂蚁还要卑鄙,比狼还要贪婪。由于这些原因,他们无法从敌人那获取贡金,便从我们的子民那盘剥钱财,结果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他们的好逸恶劳给帝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君士坦丁七世的这则法令,综合了各种不成文法、案件的处理结果等,是第一部关于士兵及其土地的成文法,为之后的军役土地法令提供了范例。
。君士坦丁七世的这则法令,综合了各种不成文法、案件的处理结果等,是第一部关于士兵及其土地的成文法,为之后的军役土地法令提供了范例。
此外,君士坦丁七世还颁行了947年土地法令,进一步完善解决土地归还过程中的偿付问题,并对“贫困者”进行了界定。君士坦丁七世在947年法令中规定,“如果购买者是一位权贵或与权贵相熟,不论是世俗或宗教方面的(或许是一位教士),而出售者十分贫寒,资产少于50诺米斯玛,将被免除偿还购买土地的钱款。如果(出售者)资产超过50诺米斯玛,可以(从购买者那得到缓期),在三年之后偿还购买的钱款,作为村社的一员享有同样的权利,即使他是位官僚体系中的将军或官员”
 。
。
君士坦丁七世在军事方面,继承了罗曼努斯一世的东扩政策,并且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君士坦丁七世继位后不久,便起用了将军巴尔达斯·福卡斯,随即开始对西西里、叙利亚、克里特等地展开攻势,但总体而言,君士坦丁七世时期的对外战争并不十分成功。莫里斯认为帝国军队在这一时期遇到的军事失利,是皇帝君士坦丁七世颁布军役土地法令的直接原因。

帝国军队在950年前后遭遇了重大打击。莫里斯认为,帝国军队此时身心均受到重创,10世纪末来自拉特洛斯(Latros)的圣保罗的传记,以绝望的口吻写到君士坦丁七世对圣徒预言视而不见,他们预言克里特即将发生厄运。
 949年,君士坦丁七世计划从萨拉森人手中夺回克里特岛,以平息他们对帝国的侵扰。此次行动,君士坦丁七世吸取了911年克里特岛战役的教训,策划了耗资更少、兵源更为精简、更为谨慎的攻占计划。他派遣舰队防护爱琴海及地中海区域,远至西班牙的后倭马亚、北非的法蒂玛(Fatimid)的海区,剩下的海军则有4 100名,前往克里特。
949年,君士坦丁七世计划从萨拉森人手中夺回克里特岛,以平息他们对帝国的侵扰。此次行动,君士坦丁七世吸取了911年克里特岛战役的教训,策划了耗资更少、兵源更为精简、更为谨慎的攻占计划。他派遣舰队防护爱琴海及地中海区域,远至西班牙的后倭马亚、北非的法蒂玛(Fatimid)的海区,剩下的海军则有4 100名,前往克里特。
 但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用人不当,导致了帝国军队的再次失利。
但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用人不当,导致了帝国军队的再次失利。
克里特岛战役的主帅,是毫无战争经验的宫廷宦官贡戈利奥斯(Gongylios),他对营地的安全掉以轻心,给予敌人可乘之机。
 帝国军队在阿拉伯人的突袭下很快溃不成军,只有主帅贡戈利奥斯及少数随从得以逃脱。克里特岛的失利很快激起了周边民族对帝国的侵扰,君士坦丁七世的军事压力日益沉重。哈姆丹王朝(Hamdan dynasty)的赛义夫·道莱(Saif al-Daulah)率军从利堪多斯(Lycandus)侵入拜占庭领土,在查尔西农军区大肆破坏。在亚美尼亚东部的莱库斯(Lycus)谷底,他击败了拜占庭将领巴尔达斯·福卡斯。不过当赛义夫返归时,在利堪多斯与日耳曼尼基亚之间的隘口处受到帝国将军利奥·福卡斯的伏击,损失8 000名士兵。
帝国军队在阿拉伯人的突袭下很快溃不成军,只有主帅贡戈利奥斯及少数随从得以逃脱。克里特岛的失利很快激起了周边民族对帝国的侵扰,君士坦丁七世的军事压力日益沉重。哈姆丹王朝(Hamdan dynasty)的赛义夫·道莱(Saif al-Daulah)率军从利堪多斯(Lycandus)侵入拜占庭领土,在查尔西农军区大肆破坏。在亚美尼亚东部的莱库斯(Lycus)谷底,他击败了拜占庭将领巴尔达斯·福卡斯。不过当赛义夫返归时,在利堪多斯与日耳曼尼基亚之间的隘口处受到帝国将军利奥·福卡斯的伏击,损失8 000名士兵。
巴尔达斯·福卡斯出身军事贵族,他的家族几个世纪以来驻守在小亚细亚边境地区,战斗在抗击阿拉伯人的前线。他曾在941年击退罗斯人的战争中一战成名,并助力君士坦丁七世击败雷卡平兄弟,成为君士坦丁七世复位中的功臣。巴尔达斯·福卡斯也获得相应回馈,他被任命为皇宫近卫军军团司令,他的儿子尼基弗鲁斯、利奥、君士坦丁分别被任命为安纳托利亚、卡帕多西亚、西里西亚军区将军。
 福卡斯家族的势力日渐强大,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之后篡位成为又一个帝王,此为后话。
福卡斯家族的势力日渐强大,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之后篡位成为又一个帝王,此为后话。
巴尔达斯·福卡斯上任之后,帝国在军事上不断受挫。斯基利齐斯对巴尔达斯·福卡斯的评价十分负面,认为他在别人的领导下,还可以做个合格的将军,一旦自己成为主帅,需要独立判断,便对帝国毫无益处。
 据记载,当巴尔达斯·福卡斯遇到哈姆丹部队时,他的军队很快逃散,他本人只是由于随从拼死救护才不至于沦为俘虏。他的前额受伤严重,伤疤直至他临终也未痊愈。
据记载,当巴尔达斯·福卡斯遇到哈姆丹部队时,他的军队很快逃散,他本人只是由于随从拼死救护才不至于沦为俘虏。他的前额受伤严重,伤疤直至他临终也未痊愈。
 他的儿子君士坦丁·福卡斯不幸被俘,并被杀害。不过巴尔达斯·福卡斯未竟的事业,由他两位儿子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和利奥·福卡斯继承,他们在罗曼努斯二世统治时期逐渐崭露头角,并获得赫赫军功。
他的儿子君士坦丁·福卡斯不幸被俘,并被杀害。不过巴尔达斯·福卡斯未竟的事业,由他两位儿子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和利奥·福卡斯继承,他们在罗曼努斯二世统治时期逐渐崭露头角,并获得赫赫军功。
总之,君士坦丁七世一生命运多舛,因为母亲而长期受到他人对其皇储资格的质疑,一生深陷宫廷争斗的腥风血雨,恐惧和猜忌伴随始终。他的人格缺陷与生俱来,只能沉迷于知识的海洋,痴迷于对学问的追求。显然,他对基督教神学并不感兴趣,而对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十分热爱,这种偏好世俗文化的特质显然有其父亲的遗传,与拜占庭历史上其他“文人”皇帝区别明显。他是个学究,而非智者,读书做学问是把好手,但治国理政、运筹帷幄的能力非常欠缺。如果说,他是个非凡的学者,那么他也是个糟糕的帝王,在拜占庭帝国治理上毫无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