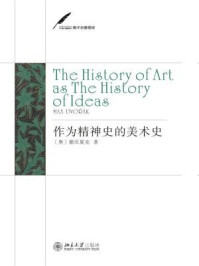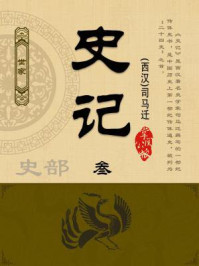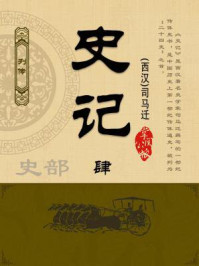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Ⅲ,Μιχα
 λ Γ',生于840年1月19日,卒于867年9月24日,享年27岁)是阿莫里王朝的第三位皇帝,也是该王朝末代皇帝,842年1月20日至867年9月24日在位25年半。
λ Γ',生于840年1月19日,卒于867年9月24日,享年27岁)是阿莫里王朝的第三位皇帝,也是该王朝末代皇帝,842年1月20日至867年9月24日在位25年半。
米哈伊尔三世的父亲是塞奥菲鲁斯,母亲是塞奥多拉,有一个哥哥君士坦丁,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死去,有五个姐姐,分别是塞克拉、安娜、阿纳斯塔西娅、帕尔切里亚和玛丽亚。妻子是欧多基娅·迪卡波利提莎(Eudokia Decapolitissa),没有子嗣。米哈伊尔三世还有一个情妇,名为尤多奇亚·伊格琳娜(Eudocia Ingerina),为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利奥。

米哈伊尔三世的统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他年幼时,皇太后塞奥多拉摄政,待他成年后,开始独自统治。在这两个阶段中,拜占庭帝国都具有较高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
842年1月20日,塞奥菲鲁斯病死,两岁的米哈伊尔成为帝国的皇帝。遵照塞奥菲鲁斯的遗愿,皇太后塞奥多拉摄政。同时还有几位帝国朝廷重要的辅政大臣,包括塞奥多拉的两位兄弟佩特洛纳斯和巴尔达斯,以及曼努埃尔和路政大臣塞奥克提斯图斯。他们在塞奥菲鲁斯统治时期便是皇帝极为信赖的大臣,而此时,他们承担着辅佐小皇帝继续统治的角色。其中,塞奥克提斯图斯尤为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宦官身份,这样的宠臣更方便协助皇太后执政而不会产生任何绯闻和谣言,同时也不存在觊觎皇位的嫌疑。
 正因如此,在诸多摄政大臣之中,塞奥克提斯图斯非常受到皇太后塞奥多拉的青睐,权势最大。然而,这个摄政群体并非团结一心,不久,权势最大的塞奥克提斯图斯便开始排挤曼努埃尔。二人原本共同住在皇宫中,齐心协力为皇帝和太后出谋划策,但塞奥克提斯图斯无端暗示指控曼努埃尔在策划叛乱,迫使后者搬离皇宫。
正因如此,在诸多摄政大臣之中,塞奥克提斯图斯非常受到皇太后塞奥多拉的青睐,权势最大。然而,这个摄政群体并非团结一心,不久,权势最大的塞奥克提斯图斯便开始排挤曼努埃尔。二人原本共同住在皇宫中,齐心协力为皇帝和太后出谋划策,但塞奥克提斯图斯无端暗示指控曼努埃尔在策划叛乱,迫使后者搬离皇宫。
 事实上,在塞奥多拉摄政时期,塞奥克提斯图斯一直是帝国朝廷最有权势的重臣,而且他很有才能,此时也在辅助塞奥多拉摄政的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
事实上,在塞奥多拉摄政时期,塞奥克提斯图斯一直是帝国朝廷最有权势的重臣,而且他很有才能,此时也在辅助塞奥多拉摄政的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
米哈伊尔三世即位后,塞奥多拉最为担心的是皇权不稳,朝中显露出阴谋叛乱的倾向。因此,他们采取了两项措施宣扬皇位继承的正统性。一方面,塞奥多拉安排曼努埃尔前往大竞技场,召集士兵和民众,向他们强调阿莫里王朝皇帝们向他们赐予的恩惠、保护以及对他们的关心,进而要求他们履行责任,公开表示忠心,全部口头宣誓效忠皇帝。士兵和民众遵从指示,承认米哈伊尔三世的皇位继承人身份。
 另一方面,塞奥多拉铸造新版的金币,金币的正面图案是新任皇帝米哈伊尔三世和长姐塞克拉分列十字架的两侧,背面则是皇太后塞奥多拉。通过金币的发行,塞奥多拉向帝国各阶层民众,以及帝国的盟友、邻邦宣布拜占庭帝国更换了统治者,特别是新任皇帝米哈伊尔三世即位。这既是公开宣告新即位皇帝的皇权,也是警告任何觊觎皇位的野心家不要轻举妄动。
另一方面,塞奥多拉铸造新版的金币,金币的正面图案是新任皇帝米哈伊尔三世和长姐塞克拉分列十字架的两侧,背面则是皇太后塞奥多拉。通过金币的发行,塞奥多拉向帝国各阶层民众,以及帝国的盟友、邻邦宣布拜占庭帝国更换了统治者,特别是新任皇帝米哈伊尔三世即位。这既是公开宣告新即位皇帝的皇权,也是警告任何觊觎皇位的野心家不要轻举妄动。
 事实上,在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时期,帝国大臣们对阿莫里王朝非常忠心,除了最终被马其顿王朝开创者瓦西里(一世)篡权,在此之前,帝国并没有出现针对皇位的叛乱和阴谋。
事实上,在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时期,帝国大臣们对阿莫里王朝非常忠心,除了最终被马其顿王朝开创者瓦西里(一世)篡权,在此之前,帝国并没有出现针对皇位的叛乱和阴谋。
塞奥多拉确立摄政权后,着手解决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彻底结束毁坏圣像运动。塞奥多拉如同多数基督教女性信徒一样,是一位坚定的崇拜圣像者。即便皇帝塞奥菲鲁斯坚决执行毁坏圣像政策,塞奥多拉仍然背着丈夫在皇宫自己的闺房中藏有圣像,私下进行个人崇拜。
 因此,当塞奥多拉获得摄政权之后,她很容易将自己类比于伊苏里亚王朝的伊琳妮,因为后者也在皇帝君士坦丁六世统治时期担任摄政,并因此而召开第七次大公会议,否定了毁坏圣像运动,恢复了圣像崇拜。塞奥多拉决定效仿伊琳妮,彻底结束圣像争端,为帝国的宗教生活带来安定。
因此,当塞奥多拉获得摄政权之后,她很容易将自己类比于伊苏里亚王朝的伊琳妮,因为后者也在皇帝君士坦丁六世统治时期担任摄政,并因此而召开第七次大公会议,否定了毁坏圣像运动,恢复了圣像崇拜。塞奥多拉决定效仿伊琳妮,彻底结束圣像争端,为帝国的宗教生活带来安定。
 除了皇太后塞奥多拉积极谋划恢复圣像崇拜之外,曼努埃尔也在积极推动。根据史料记载,曼努埃尔患了一种重病,日益憔悴,气若游丝,濒临死亡。这时候斯图迪特派的一些修士到访,告诉曼努埃尔只要他向上帝承诺将会恢复圣像崇拜的传统,那么他就会重获新生。这些修士离开后,曼努埃尔的身体逐渐获得康复,于是对他们的话确信无疑,并开始坚定地推动恢复圣像崇拜。
除了皇太后塞奥多拉积极谋划恢复圣像崇拜之外,曼努埃尔也在积极推动。根据史料记载,曼努埃尔患了一种重病,日益憔悴,气若游丝,濒临死亡。这时候斯图迪特派的一些修士到访,告诉曼努埃尔只要他向上帝承诺将会恢复圣像崇拜的传统,那么他就会重获新生。这些修士离开后,曼努埃尔的身体逐渐获得康复,于是对他们的话确信无疑,并开始坚定地推动恢复圣像崇拜。

但塞奥多拉仍然存在几大顾虑。其一,自己的丈夫塞奥菲鲁斯是坚定的毁坏圣像者,恢复圣像崇拜是对塞奥菲鲁斯政策的彻底背离,这对丈夫和阿莫里王朝的声望都非常不利。
 其二,现行的帝国统治秩序中,不管是世俗的行政官员,还是教会内部的牧首、主教等,全都是毁坏圣像者,他们人数众多,如果召开宗教会议恢复圣像崇拜,可能会遭遇很大的阻力。其三,帝国军队中拥护毁坏圣像的将士占绝大多数,贸然背离前任皇帝的政策,必定将严重影响帝国武装力量的士气,甚至还可能像伊琳妮当年那样遭到军队的公开反对。
其二,现行的帝国统治秩序中,不管是世俗的行政官员,还是教会内部的牧首、主教等,全都是毁坏圣像者,他们人数众多,如果召开宗教会议恢复圣像崇拜,可能会遭遇很大的阻力。其三,帝国军队中拥护毁坏圣像的将士占绝大多数,贸然背离前任皇帝的政策,必定将严重影响帝国武装力量的士气,甚至还可能像伊琳妮当年那样遭到军队的公开反对。

塞奥多拉用一年多的时间先行解决了这几个问题。一方面,塞奥多拉进行舆论宣传,设法原谅塞奥菲鲁斯对毁坏圣像运动的支持,引导教会放弃对塞奥菲鲁斯的谴责。皇太后塞奥多拉借助其身份制造舆论,从皇宫中传出塞奥菲鲁斯临死前接受了圣像崇拜的传闻。根据这些消息,塞奥菲鲁斯在死前每日遭受煎熬和苦恼,经常梦见自己被鞭打的噩梦,清醒时则身体痛苦,哀号不断。有一天,当塞奥克提斯图斯前来探望时,他佩戴的项链中有一枚特别精致微小的圣像引起皇帝注意,病痛中塞奥菲鲁斯突然抓住链子上的圣像,放到嘴边亲吻。这时他受到的折磨停止了,终于得以安然入睡。通过这些杜撰的故事,塞奥多拉希望帝国上下相信,皇帝塞奥菲鲁斯在死前已经真正忏悔、并皈依了正统信仰,因此他不应该遭受诅咒。
 但塞奥多拉仍然担心,教会人士日后会召开宗教会议,重新追究塞奥菲鲁斯的责任。为此,在正式恢复圣像崇拜之前,塞奥多拉对正教神职人员发表演讲,恳求他们谅解塞奥菲鲁斯。最终正统派教士出于对塞奥多拉的敬重和对恢复崇拜圣像的渴望,共同投票表决,同意塞奥菲鲁斯将得到上帝谅解,而他们会签署书面誓言,对此作出保证。
但塞奥多拉仍然担心,教会人士日后会召开宗教会议,重新追究塞奥菲鲁斯的责任。为此,在正式恢复圣像崇拜之前,塞奥多拉对正教神职人员发表演讲,恳求他们谅解塞奥菲鲁斯。最终正统派教士出于对塞奥多拉的敬重和对恢复崇拜圣像的渴望,共同投票表决,同意塞奥菲鲁斯将得到上帝谅解,而他们会签署书面誓言,对此作出保证。
 于是,皇太后实现了自己的计划,首先使塞奥菲鲁斯免除了教会的谴责。在恢复崇拜圣像的正统信仰之后,塞奥多拉还设宴款待正统的崇拜圣像者,与士麦那的塞奥法尼斯等被迫害者交谈,再次恳请他们原谅塞奥菲鲁斯。
于是,皇太后实现了自己的计划,首先使塞奥菲鲁斯免除了教会的谴责。在恢复崇拜圣像的正统信仰之后,塞奥多拉还设宴款待正统的崇拜圣像者,与士麦那的塞奥法尼斯等被迫害者交谈,再次恳请他们原谅塞奥菲鲁斯。

另一方面,考虑到帝国内既有的绝大多数主教都是毁坏圣像者,塞奥多拉并没有按照教会传统,通过召开宗教会议来变更教义。相反,她召集挑选出来的心腹官员和正统教士,命令他们在塞奥克提斯图斯的府邸集结。他们并没有召开宗教会议,而是以小型会议的方式,再次公开接纳了787年第七次大公会议的决议,进而设计结束了毁坏圣像运动。
 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试探性地触及军队中反对派的底线。一切如愿,由于她前期的细致努力,军队中没有太强烈的反应。于是,843年3月,塞奥多拉颁布敕令,恢复圣像崇拜,将崇拜圣像者从流放地和监狱全部召回。大多数主教选择了接受,改变态度,回归崇拜圣像神学和礼仪,对于坚持毁坏圣像者,皇太后只是将其流放而不做处罚。与此同时,塞奥多拉下令罢免现任牧首“语法学家”约翰,选任长期被囚禁的崇拜圣像修士美多迪乌斯继任。根据史料记载,美多迪乌斯身上满是为坚持崇拜圣像信仰遭受到的不公待遇的印记,他由于长期被囚禁在肮脏的小牢房里,所以失去了头发,他认为自己的谢顶就是上帝给他的嘉奖。由于毁坏圣像运动的结束和美多迪乌斯继任牧首,崇拜圣像者从帝国各地齐聚到首都,在任命当天举行了集会,所有人都欢呼圣像崇拜的胜利。
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试探性地触及军队中反对派的底线。一切如愿,由于她前期的细致努力,军队中没有太强烈的反应。于是,843年3月,塞奥多拉颁布敕令,恢复圣像崇拜,将崇拜圣像者从流放地和监狱全部召回。大多数主教选择了接受,改变态度,回归崇拜圣像神学和礼仪,对于坚持毁坏圣像者,皇太后只是将其流放而不做处罚。与此同时,塞奥多拉下令罢免现任牧首“语法学家”约翰,选任长期被囚禁的崇拜圣像修士美多迪乌斯继任。根据史料记载,美多迪乌斯身上满是为坚持崇拜圣像信仰遭受到的不公待遇的印记,他由于长期被囚禁在肮脏的小牢房里,所以失去了头发,他认为自己的谢顶就是上帝给他的嘉奖。由于毁坏圣像运动的结束和美多迪乌斯继任牧首,崇拜圣像者从帝国各地齐聚到首都,在任命当天举行了集会,所有人都欢呼圣像崇拜的胜利。
 在四旬斋(Lent)第一个周日的前一天晚上,牧首美多迪乌斯带领修士群体,举行了守夜祈祷。转天早晨(843年3月11日),皇帝米哈伊尔三世和皇太后塞奥多拉,以及朝廷官员,从皇宫中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所有人都手举十字架、圣像和蜡烛,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庆祝拜占庭教会恢复圣像崇拜。
在四旬斋(Lent)第一个周日的前一天晚上,牧首美多迪乌斯带领修士群体,举行了守夜祈祷。转天早晨(843年3月11日),皇帝米哈伊尔三世和皇太后塞奥多拉,以及朝廷官员,从皇宫中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所有人都手举十字架、圣像和蜡烛,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庆祝拜占庭教会恢复圣像崇拜。

但毁坏圣像派并未立刻偃旗息鼓,也没有放弃抵抗。牧首“语法学家”约翰在得知被罢免后,立刻采取措施,装扮成弱者和被迫害者的形象,博取教会人士的同情。他割伤自己的肚子,弄出不致命的伤痕,好像自己受到了折磨,然后宣称自己遭到了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而那些迫害者就是崇拜圣像的修士。塞奥多拉派遣巴尔达斯前去查证,发现伤口很轻。这时约翰的仆人告发他自我伤害,并嫁祸于人,而作案工具的小刀也被发现。于是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约翰因为造假欺骗而颜面尽失,立刻被驱逐出教会,流放到远方一个修道院。
 那里有一幅圣像,约翰命令自己的随从将圣像中人物的眼睛全部除去。塞奥多拉获悉此事后,下令也挖出他的眼睛,以便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但后来在其他人恳请下,她善心大发,放弃这一刑罚,但仍然下令对他鞭打200下,以示对毁坏圣像者的警示。
那里有一幅圣像,约翰命令自己的随从将圣像中人物的眼睛全部除去。塞奥多拉获悉此事后,下令也挖出他的眼睛,以便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但后来在其他人恳请下,她善心大发,放弃这一刑罚,但仍然下令对他鞭打200下,以示对毁坏圣像者的警示。
 皇太后先以舆论开道,争取民心在前,而后低调进行实质性操作,将计划变为既定事实,最后确立皇家主调,严厉打击反对派,却宽容对待多数人。她心思缜密,治国手段和处理难题的能力超越常人。其有步骤分阶段地结束毁坏圣像运动,特别是在具体实施中注意只能做不能说的措施落实效果,取得了最终胜利。
皇太后先以舆论开道,争取民心在前,而后低调进行实质性操作,将计划变为既定事实,最后确立皇家主调,严厉打击反对派,却宽容对待多数人。她心思缜密,治国手段和处理难题的能力超越常人。其有步骤分阶段地结束毁坏圣像运动,特别是在具体实施中注意只能做不能说的措施落实效果,取得了最终胜利。
毁坏圣像者虽然也进行反扑的尝试,但很快遭到打压。同时,皇太后吸取前人教训,并没有继续展开对毁坏圣像派的大规模迫害,而是采取更为宽容的政策,从而降低了长期进行毁坏圣像运动在社会层面的破坏烈度。至此,皇太后的宗教宽容政策平息了长期的争端,拜占庭教会终于恢复对圣像崇拜的统一态度,毁坏圣像运动的时代宣告结束。这一运动在拜占庭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在东正教教会中仍发挥着作用。
除此之外,在塞奥多拉摄政时期,帝国基本沿袭塞奥菲鲁斯的改革,继续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然而,随着米哈伊尔三世逐渐成年,其顽劣昏庸愈加放纵,开始使帝国朝廷出现一些混乱,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米哈伊尔三世自幼为帝,皇太后日理万机忙于政务,对他缺乏严厉管教,而众多大臣摄政对这个小皇帝缺少正确的引导,致使他从小骄横跋扈,任性妄为,不仅对帝国军政大事管理缺乏兴趣和能力,还沉迷于酗酒、赛车比赛和种种非常耗费钱财的娱乐。他向自己的玩伴慷慨赠送礼物,每人赠送30—50镑黄金。他还答应成为一名玩伴孩子的教父,于是赠送100镑黄金。他对马车比赛充满热情,在短时间内便浪费了大量钱财。皇太后塞奥多拉对已经恶习缠身的小皇帝也无奈,不得不求助于元老院,将帝国财政数字完全告知元老院,帝国的财政大臣证实了相关数字的真实性。塞奥多拉此举是在表明,皇帝米哈伊尔三世铺张浪费、开支奢靡、不受管控,元老院如若可能,应当阻止其无端消耗帝国财政的荒唐行为。

其次,在米哈伊尔三世的婚姻问题上,任性的皇帝和母亲塞奥多拉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塞奥多拉希望能够通过婚姻,使得米哈伊尔三世克服缺点,纠正恶习,正常成长起来,于是便按照习俗安排了新娘秀。但此时花天酒地的米哈伊尔三世已经有了一名情妇尤多奇亚·伊格琳娜,还对这个风尘女子感情深厚。在选秀时,塞奥多拉虽然允许她参加,却出于其已经失去贞洁的因素而将其排除在最终入围的秀女之外。塞奥多拉建议皇帝选择欧多基娅·迪卡波利提莎为妻。米哈伊尔三世对这桩婚事非常反感,考虑到既然情妇不能变成妻子,那么选择谁成为皇后就不重要,因此接受了塞奥多拉的婚事安排。从此,母子二人形同陌路,皇帝对皇太后怀恨在心。米哈伊尔三世私下里不仅牢骚满腹,而且开始联合塞奥多拉的弟弟巴尔达斯暗中密谋,准备推翻塞奥多拉的摄政,摆脱母亲的管束
 ,从而将王朝置于危险的境地。此时,母子争端就不再是皇帝的家事,而是决定帝国政治秩序走向的国家大事了,特别是在大权在握的皇帝培养问题上出现的失误便成为危害帝国前途的重大失误了。
,从而将王朝置于危险的境地。此时,母子争端就不再是皇帝的家事,而是决定帝国政治秩序走向的国家大事了,特别是在大权在握的皇帝培养问题上出现的失误便成为危害帝国前途的重大失误了。
第三,母子反目后,米哈伊尔三世开始要求真正的执政权。这并非源于他的政治抱负,而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大的权力为所欲为。作为小皇帝的舅舅,巴尔达斯原本应该教育规劝不成器的外甥,但他受到皇帝的青睐后,肮脏的心理促使他希望获得更大的权力。他清楚挡在自己攫取更大权力的障碍是塞奥克提斯图斯,因此要能够取代塞奥克提斯图斯成为帝国内最有权势的大臣,就必须击败这个重臣。他顺着小皇帝的意愿说话,进一步加剧了皇室内政局的动荡。皇帝米哈伊尔三世有位不学无术、品行不端的老师,总是变着法子满足小皇帝的要求,皇帝想给予他更高的头衔和官职,但塞奥克提斯图斯并不同意。巴尔达斯借机宣传塞奥克提斯图斯对皇帝的威胁,让皇帝产生一种错觉:虽然他是皇帝,但他并没有帝国的权势,而塞奥克提斯图斯可能正在谋划剥夺皇帝的统治权。于是米哈伊尔三世和巴尔达斯准备将塞奥克提斯图斯谋杀或者放逐。塞奥克提斯图斯作为路政大臣,需要时常出入皇帝的会客厅,而巴尔达斯则埋伏在那里。当塞奥克提斯图斯毫无防备的时候,巴尔达斯冲了上去,皇帝安排的一些士兵前去协助,最终将塞奥克提斯图斯手刃。皇太后塞奥多拉得悉此事,蓬头垢面冲了过去,她指责皇帝的所作所为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
 母子之间的矛盾越发不可调和。这里,笔者不得不说,精明的皇太后以为只有帝国事务才是大事,而忽视了对小皇帝的管教,却不知道在皇帝专制的帝国,后者也是关乎王朝命运的大事。只是母亲对过早失去父亲的儿子溺爱过头,从小宠爱过度,母子之爱冲昏了头脑,不仅放任孩子的任性,还错误地为小皇帝找错了老师和玩伴。待到她明白其中的道理时,一切都晚了。
母子之间的矛盾越发不可调和。这里,笔者不得不说,精明的皇太后以为只有帝国事务才是大事,而忽视了对小皇帝的管教,却不知道在皇帝专制的帝国,后者也是关乎王朝命运的大事。只是母亲对过早失去父亲的儿子溺爱过头,从小宠爱过度,母子之爱冲昏了头脑,不仅放任孩子的任性,还错误地为小皇帝找错了老师和玩伴。待到她明白其中的道理时,一切都晚了。
米哈伊尔三世对母亲的摄政无法容忍,最终决定利用手中的皇权取消其摄政权,于是派人前去抓捕塞奥多拉和她的女儿们,强行削去她们的头发,没收她们的财产并据为己有,并将她们全部驱逐出皇宫,把她们关入加斯特里亚修道院,过着修道生活。不久后,塞奥多拉伤心过度,绝望离世,尸骨被草草地埋葬在这所修道院。 [3] 856年年初,米哈伊尔三世宣布自己为唯一的皇帝。巴尔达斯成为皇帝的心腹,被擢升为凯撒,扮演着塞奥克提斯图斯在塞奥多拉摄政时期的角色。在其大权在握的十年里,凭借前任皇帝打下的基业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帝国仍然平稳运行,在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也取得了些许成就。
在米哈伊尔三世亲政时期,巴尔达斯在玛格纳乌拉皇宫中建立了一所公立学校,用于教授世俗知识。“哲学家”利奥曾被塞奥菲鲁斯安排为塞萨洛尼基大主教,但在毁坏圣像运动结束之后也被免去职务。巴尔达斯令其掌管这所学校的运转。利奥本人教授哲学,他的一些学生则负责几何学、天文学、语法等。帝国为他们提供高额的皇室薪俸,以确保他们能够对教学事业兢兢业业。巴尔达斯也会经常前去参加他们的课程,考察学生的培养质量。
 拜占庭帝国的世俗文化因此得到极大的推进和发展。
拜占庭帝国的世俗文化因此得到极大的推进和发展。
在宗教领域,巴尔达斯与牧首伊格纳提乌斯发生了冲突。伊格纳提乌斯在847年美多迪乌斯死后继任牧首。他对于米哈伊尔三世、巴尔达斯谋杀塞奥克提斯图斯以及强迫塞奥多拉进入修道院等事颇有微词。加之857年时巴尔达斯与守寡的儿媳妇有染的丑闻传出,伊格纳提乌斯禁止他参加基督教圣礼和领圣餐礼。巴尔达斯被处罚后,含恨在心,决意报复。他粗暴地将伊格纳提乌斯驱逐出教堂,然后将其抓捕,百般折磨之后,将其锁在地下皇陵之中,让他赤身露体地待在石棺中。而后,巴尔达斯将其放逐到莱斯沃斯岛。

858年,巴尔达斯委任大学者弗提乌斯(Photius)成为新任牧首。不久,他们便在圣使徒教堂召开宗教会议,免除了伊格纳提乌斯牧首之职。但弗提乌斯这一任命本身就争议不断,因为弗提乌斯虽然因为知识渊博在世俗世界闻名遐迩,但他并非教士,只是个普通信徒,缺乏教士身份的普通信徒被直接任命为牧首是有违教规的。因此,这导致拜占庭教会内部分裂为两派,分别拥护前后两任牧首。伊格纳提乌斯的支持者将这一争议事件提交给罗马教宗,希望罗马新任教宗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858—867年在任)能够进行仲裁。863年,尼古拉一世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宣布罢免弗提乌斯,重新任命伊格纳提乌斯为新任牧首。罗马教宗的决议导致拜占庭教会内部争端加剧。

君士坦丁堡牧首任职问题,实际上折射了这一时期东、西方教会之间的激烈冲突。事实上,双方围绕传教势力范围的争夺,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这集中体现在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事件上。根据史料记载,在塞奥多拉摄政时期,拜占庭帝国与保加利亚之间交换了一位重要战俘,即保加利亚君主伯利斯(Boris)的姐姐,她此时得以回到保加利亚。但她已经在拜占庭皇宫待过很长时间,学习识字,皈依了基督教希腊正教,因此在回国后,努力将这种信仰灌输给伯利斯。但伯利斯并不接受。只是不久之后,保加利亚境内遭遇各种灾难,伯利斯无奈之中祈求上帝救助。当保加利亚人度过危机后,伯利斯改信了基督教,并以拜占庭皇帝的名字米哈伊尔为自己重新命名,并诚请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三世成为其教父。

事实上,在保加利亚人选择拜占庭教会之前,也曾在东、西教会之间游移不定,难以抉择。而拜占庭教会做出重要举措,于863年派遣两位学识渊博的教士,即君士坦丁(后改名为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前去保加利亚邻国摩拉维亚公国,向斯拉夫人传教。他们是塞萨洛尼基本地人,自幼熟知斯拉夫人的语言,甚至有学者考证他们的母系有斯拉夫血统。他们以希腊语字母和语法,为斯拉夫语言创造了最初的斯拉夫文字体系,并开始将基督教经典作品翻译成斯拉夫语,从而将斯拉夫人纳入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范畴之中。
 这一举措客观上促进了保加利亚人的选择,进而被接纳进拜占庭教会。拜占庭教会成功在保加利亚人传教,加剧了东、西教会之间的矛盾。但弗提乌斯的后续举动进一步激化了双方之间的冲突。867年夏末,弗提乌斯召开宗教会议,反击罗马教会在861年的决议,宣布罢免教宗尼古拉一世,指控西部教会多年的行为都是异端行为;他还特别谴责了罗马教会一直坚持的“和子”神学主张,由此打击了整个西部教会。
这一举措客观上促进了保加利亚人的选择,进而被接纳进拜占庭教会。拜占庭教会成功在保加利亚人传教,加剧了东、西教会之间的矛盾。但弗提乌斯的后续举动进一步激化了双方之间的冲突。867年夏末,弗提乌斯召开宗教会议,反击罗马教会在861年的决议,宣布罢免教宗尼古拉一世,指控西部教会多年的行为都是异端行为;他还特别谴责了罗马教会一直坚持的“和子”神学主张,由此打击了整个西部教会。
 弗提乌斯的诸多措施不仅加剧了东、西教会的矛盾,也导致拜占庭教会内部动荡。
弗提乌斯的诸多措施不仅加剧了东、西教会的矛盾,也导致拜占庭教会内部动荡。
巴尔达斯大权在握,自以为是皇帝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做事越来越张狂,甚至不把自己的外甥皇帝放在眼里,对朝政指手画脚,自然成了皇帝新的威胁。为了摆脱巴尔达斯的控制,米哈伊尔三世笃信皇室之外的亲兵更为可靠,听信了掌握兵权的马其顿人瓦西里[即马其顿王朝的创始人瓦西里一世(Basil Ⅰ,867—886年在位)]的建议,开始计划除去巴尔达斯。866年春季,米哈伊尔三世和瓦西里一起远征克里特,途中在色雷斯军区登陆。他们在一个叫柯坯(Kepoi)的地方安扎营帐。皇帝私下拉拢了巴尔达斯的女婿,指使后者为皇帝执行谋杀计划。于是他暗地里安排刀斧手埋伏在大营后,当他进入营帐时,皇帝和巴尔达斯正在场商议出征问题,等待他汇报远征开支情况。当他离开营帐时,按照预先约定在身前画了十字,这是执行谋杀的信号,于是躲在营帐后角落中的刀剑兵冲了进去,在皇帝面前将巴尔达斯杀死。

皇帝立刻给牧首弗提乌斯去信,称已确认巴尔达斯叛国,并被处死。弗提乌斯在回信中,恭喜皇帝躲过一劫。但他在信中同样表达了对瓦西里的怀疑,因为他称:“陛下您的品德和仁慈,禁止我去怀疑这封书信是被伪造的,或者去怀疑巴尔达斯的叛乱另有隐情。”弗提乌斯成为牧首,得益于巴尔达斯,而瓦西里的精明算计,众人皆知,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唯有皇帝一心除掉他的舅舅。他可能担心瓦西里图谋不轨,因此,在信的结尾,弗提乌斯请求皇帝,立刻返回首都,称这是元老院和民众的意愿。于是远征克里特的军事行动作罢,米哈伊尔三世回到首都。

返回首都后,米哈伊尔三世将事事顺从自己的瓦西里收为义子,成为辅帝。米哈伊尔三世此举,实际上有自己的考虑。866年年初,皇帝发现自己的情妇尤多奇亚·伊格琳娜怀孕了。皇帝不希望像君士坦丁六世那样被教会指责犯有通奸罪,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背负私生子的名声,于是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选择。他让瓦西里离婚,然后和尤多奇亚·伊格琳娜结婚,缔造一场名义上的婚姻。这样,米哈伊尔三世仍然可以和尤多奇亚·伊格琳娜保持情妇关系,而为了补偿瓦西里,皇帝将自己的大姐塞克拉送给瓦西里做情妇。米哈伊尔三世和原配妻子并无子嗣,因此,他将瓦西里收为义子,以便瓦西里名义下的儿子(其实是米哈伊尔三世的儿子)可以获得合法继承皇位的权利。

但这一行为也给予瓦西里合法继承皇位的机会,为米哈伊尔三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隐患。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发现,在参加宗教仪式时,需要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并列摆放两张皇座;在游行队列中,瓦西里和皇帝并肩而行。
 此后,瓦西里掌控帝国大权,而米哈伊尔三世继续花天酒地,沉迷于赛马比赛之中。有一次,米哈伊尔三世骑马正准备参加比赛,皇帝侍卫突然上前来禀报,称烽火预警系统显示,有外敌正在入侵。皇帝非常担心,但担心的不是外敌,而是担心观众受此消息影响,无心观看他的比赛。于是他下令废除烽火预警系统。其荒唐行为遭到民众的憎恨、政教官员们的嫌弃。
此后,瓦西里掌控帝国大权,而米哈伊尔三世继续花天酒地,沉迷于赛马比赛之中。有一次,米哈伊尔三世骑马正准备参加比赛,皇帝侍卫突然上前来禀报,称烽火预警系统显示,有外敌正在入侵。皇帝非常担心,但担心的不是外敌,而是担心观众受此消息影响,无心观看他的比赛。于是他下令废除烽火预警系统。其荒唐行为遭到民众的憎恨、政教官员们的嫌弃。
 而且米哈伊尔三世铺张浪费,导致国库亏空。为了给军队支付军饷,他被迫将塞奥菲鲁斯用于装饰皇宫的金树、金制狮子、纯金打造的格里芬雕塑等全部熔化,铸造成金币,以解燃眉之急。这很可能是在处死巴尔达斯之后,米哈伊尔三世更加无拘无束奢侈地胡乱花钱,导致财政困难,因为在巴尔达斯大权独揽时,并没有史料表明帝国财政紧缺。
而且米哈伊尔三世铺张浪费,导致国库亏空。为了给军队支付军饷,他被迫将塞奥菲鲁斯用于装饰皇宫的金树、金制狮子、纯金打造的格里芬雕塑等全部熔化,铸造成金币,以解燃眉之急。这很可能是在处死巴尔达斯之后,米哈伊尔三世更加无拘无束奢侈地胡乱花钱,导致财政困难,因为在巴尔达斯大权独揽时,并没有史料表明帝国财政紧缺。

米哈伊尔三世和瓦西里共同执政一年半左右。在这期间,米哈伊尔三世意识到官员更加听从瓦西里的指示,因此对瓦西里开始提防,意欲将其除去。于是皇帝安排其去狩猎,暗中指使狩猎者使用长矛去射杀野兽,但实际上是为了借机造成失手杀害瓦西里的假象。皇帝安排的士兵在将长矛掷向瓦西里的时候并未击中目标,瓦西里侥幸逃出劫难,于是私下里积极准备反击。因为瓦西里深知皇帝的恶劣秉性,他连自己的母亲和舅舅都不放过,感到不满就残忍杀掉,他这个外姓人,早晚成为皇帝的刀下鬼。于是他先下手为强,于867年9月24日,趁着米哈伊尔三世喝醉之机,带领一群亲信闯入皇帝的卧室,将其残忍杀害。阿莫里王朝由此终结。

在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时期,帝国在对外关系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当然这主要得益于塞奥多拉摄政时期的重臣塞奥克提斯图斯和曼努埃尔,以及皇帝亲政时期的亲信巴尔达斯和佩特洛纳斯。由于他们的精心周旋,保加利亚人与帝国保持和平关系。在塞奥多拉摄政时期,伯利斯曾扬言要入侵拜占庭领土,但塞奥多拉命令大军集结到边境,虚张声势,引而不发跃如也,伯利斯受到震慑,选择和平。据说塞奥多拉去信称:“即便你们击败一个女人,你们也毫无吹嘘之处。但如果你们失败了,你们的败绩将会被所有人耻笑。”
 864年,巴尔达斯和米哈伊尔三世对保加利亚人发起海、陆两路大军远征,收复了梅塞布里亚,保加利亚君主伯利斯被迫接受拜占庭教会的传教,并于次年受洗。
864年,巴尔达斯和米哈伊尔三世对保加利亚人发起海、陆两路大军远征,收复了梅塞布里亚,保加利亚君主伯利斯被迫接受拜占庭教会的传教,并于次年受洗。
 拜占庭人还试图收复克里特。塞奥多拉在摄政期间,派遣塞奥克提斯图斯和塞尔吉乌斯·尼基提亚提斯(Sergius Nicetiates)远征克里特。拜占庭军队进展顺利,不仅安全登陆,而且围攻重创了阿拉伯人,随后建立克里特军区。但塞奥克提斯图斯听到都城动乱的谣言,匆匆返回。此后不久,克里特岛上的阿拉伯人开始反击,杀死了塞尔吉乌斯,粉碎了拜占庭的远征计划成果。拜占庭人收复克里特的行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这同时也表明拜占庭海军实力得以恢复,海军正常运转。
拜占庭人还试图收复克里特。塞奥多拉在摄政期间,派遣塞奥克提斯图斯和塞尔吉乌斯·尼基提亚提斯(Sergius Nicetiates)远征克里特。拜占庭军队进展顺利,不仅安全登陆,而且围攻重创了阿拉伯人,随后建立克里特军区。但塞奥克提斯图斯听到都城动乱的谣言,匆匆返回。此后不久,克里特岛上的阿拉伯人开始反击,杀死了塞尔吉乌斯,粉碎了拜占庭的远征计划成果。拜占庭人收复克里特的行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这同时也表明拜占庭海军实力得以恢复,海军正常运转。
 有学者研究认为,此期拜占庭海军建设渐入佳境,实力达到顶峰。东部地区阿拉伯人的入侵基本遭到遏制,只有塔尔苏斯的行政长官亚美尼亚人阿里多次入侵拜占庭领土。他从851年起连续三年发动夏季入侵,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破坏,塞奥多拉随后下令进行报复,855年,拜占庭军队在塔尔苏斯取得大胜,俘获了近2万名俘虏。
有学者研究认为,此期拜占庭海军建设渐入佳境,实力达到顶峰。东部地区阿拉伯人的入侵基本遭到遏制,只有塔尔苏斯的行政长官亚美尼亚人阿里多次入侵拜占庭领土。他从851年起连续三年发动夏季入侵,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破坏,塞奥多拉随后下令进行报复,855年,拜占庭军队在塔尔苏斯取得大胜,俘获了近2万名俘虏。

梅利蒂尼的埃米尔·阿穆尔统治下的阿拉伯人及其庇护下的保罗派
 ,是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时期最大的外患。塞奥多拉在结束毁坏圣像运动之后,对保罗派进行了打击,因为保罗派反对一切物质世界生活,包括圣像。皇太后命令保罗派皈依基督教正统信仰,否则将他们全部处死。大军前往疯狂镇压,杀死了上万保罗派信众,同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但其中一位领袖卡比亚斯(Karbeas)带领残存的5 000名保罗派信徒追随阿穆尔,逃到了梅利蒂尼。梅利蒂尼的埃米尔·阿穆尔此时处于半独立状态,愿意为保罗派提供庇护。从此,卡比亚斯带领保罗派,与阿拉伯人一起攻击拜占庭人的领土,取得了一些胜利,同时还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保罗派。最终他们得以建立两座城市阿加翁(Argaoun)和泰夫里卡(Tephrike)为活动基地,其势力逐渐发展。
,是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时期最大的外患。塞奥多拉在结束毁坏圣像运动之后,对保罗派进行了打击,因为保罗派反对一切物质世界生活,包括圣像。皇太后命令保罗派皈依基督教正统信仰,否则将他们全部处死。大军前往疯狂镇压,杀死了上万保罗派信众,同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但其中一位领袖卡比亚斯(Karbeas)带领残存的5 000名保罗派信徒追随阿穆尔,逃到了梅利蒂尼。梅利蒂尼的埃米尔·阿穆尔此时处于半独立状态,愿意为保罗派提供庇护。从此,卡比亚斯带领保罗派,与阿拉伯人一起攻击拜占庭人的领土,取得了一些胜利,同时还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保罗派。最终他们得以建立两座城市阿加翁(Argaoun)和泰夫里卡(Tephrike)为活动基地,其势力逐渐发展。

米哈伊尔三世亲政后,阿穆尔和卡比亚斯带领各自军队,两次入侵拜占庭领土。皇帝两次带兵迎敌,均遭遇失败,甚至被迫脱掉皇袍,扮成普通人,才得以侥幸逃脱。
 863年,阿穆尔率领4万人再度入侵,洗劫了亚美尼亚军区和海岸城市阿米索斯(Amisos)
863年,阿穆尔率领4万人再度入侵,洗劫了亚美尼亚军区和海岸城市阿米索斯(Amisos)
 。米哈伊尔三世命令色雷斯军区将军佩特洛纳斯,集结拜占庭帝国各大军区军队,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双方在拉拉卡翁河(Lalakaon)附近的泊松(Poson)相遇。拜占庭军队利用人数的优势,在敌人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形成合围。泊松一面靠山,于是佩特洛纳斯调配各大军区的军队,分别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将阿穆尔团团包围。
。米哈伊尔三世命令色雷斯军区将军佩特洛纳斯,集结拜占庭帝国各大军区军队,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双方在拉拉卡翁河(Lalakaon)附近的泊松(Poson)相遇。拜占庭军队利用人数的优势,在敌人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形成合围。泊松一面靠山,于是佩特洛纳斯调配各大军区的军队,分别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将阿穆尔团团包围。
 阿穆尔几次尝试突围,均以失败告终,绝望之下自杀身亡。他的儿子在逃跑时被俘虏,其余士兵全部被杀。
阿穆尔几次尝试突围,均以失败告终,绝望之下自杀身亡。他的儿子在逃跑时被俘虏,其余士兵全部被杀。
 这就是著名的拉拉卡翁战役。保罗派领袖卡比亚斯也在其中一个战场上死去。拜占庭人士气高涨,乘胜前进,立刻入侵阿拉伯人占领的亚美尼亚地区,杀死了迁徙至此的亚美尼亚人阿里。于是在同一年,拜占庭帝国东部的三大敌人全部战败,其领袖死去,部下作鸟兽散。
这就是著名的拉拉卡翁战役。保罗派领袖卡比亚斯也在其中一个战场上死去。拜占庭人士气高涨,乘胜前进,立刻入侵阿拉伯人占领的亚美尼亚地区,杀死了迁徙至此的亚美尼亚人阿里。于是在同一年,拜占庭帝国东部的三大敌人全部战败,其领袖死去,部下作鸟兽散。
 拜占庭帝国收复了领土,也收获了战场上的信心,改变了在这一区域的平衡趋势,反攻时代由此开启。
拜占庭帝国收复了领土,也收获了战场上的信心,改变了在这一区域的平衡趋势,反攻时代由此开启。

总体而言,在米哈伊尔三世的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仍然平稳运行,并在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当然,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帝国的重臣们,例如塞奥克提斯图斯、巴尔达斯、佩特洛纳斯等。现代学者普遍认为,米哈伊尔三世从未真正履行过统治职责
 ,他除了大肆花钱、纸醉金迷,只是默许了辅佐他的重臣将领的建议,而没有任何个人的建树,唯有对塞奥克提斯图斯和巴尔达斯的谋杀设计得特别精心。
,他除了大肆花钱、纸醉金迷,只是默许了辅佐他的重臣将领的建议,而没有任何个人的建树,唯有对塞奥克提斯图斯和巴尔达斯的谋杀设计得特别精心。
 现代学者得出这种结论,很大程度上源于拜占庭史料中对米哈伊尔三世负面形象的刻画。米哈伊尔三世的心腹瓦西里实际上是策划谋杀巴尔达斯和皇帝本人的真正幕后黑手,但他同时又是马其顿王朝的开创者,因此,马其顿许多皇帝,例如君士坦丁七世,通过御用文人,创作了许多作品,来为瓦西里的行为洗白,典型的例证便是《皇帝瓦西里传》,其中塑造了一个英勇无畏、正直公正的帝王形象,反复颂扬其丰功伟绩,以此反衬前朝末代皇帝的昏庸无道。
现代学者得出这种结论,很大程度上源于拜占庭史料中对米哈伊尔三世负面形象的刻画。米哈伊尔三世的心腹瓦西里实际上是策划谋杀巴尔达斯和皇帝本人的真正幕后黑手,但他同时又是马其顿王朝的开创者,因此,马其顿许多皇帝,例如君士坦丁七世,通过御用文人,创作了许多作品,来为瓦西里的行为洗白,典型的例证便是《皇帝瓦西里传》,其中塑造了一个英勇无畏、正直公正的帝王形象,反复颂扬其丰功伟绩,以此反衬前朝末代皇帝的昏庸无道。
 此外,君士坦丁七世还在大竞技场中央,仿照古埃及方尖碑,为瓦西里一世树立了一座用石块建筑的方尖碑,外表用青铜鎏金整体包裹装饰、镌刻瓦西里的功绩。这样,经过马其顿王朝作家近两百年的努力,米哈伊尔三世的丑恶嘴脸和瓦西里一世的高大形象便确立起来。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作为阿莫里王朝之后的马其顿皇帝,他理所当然要设法掩饰其先祖的道德污点,彻底搞臭前朝末代皇帝。耶尼修斯也认为米哈伊尔三世和瓦西里之间,是由于其他人心生嫉妒、有意挑拨而导致关系破裂,相互敌视。
此外,君士坦丁七世还在大竞技场中央,仿照古埃及方尖碑,为瓦西里一世树立了一座用石块建筑的方尖碑,外表用青铜鎏金整体包裹装饰、镌刻瓦西里的功绩。这样,经过马其顿王朝作家近两百年的努力,米哈伊尔三世的丑恶嘴脸和瓦西里一世的高大形象便确立起来。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作为阿莫里王朝之后的马其顿皇帝,他理所当然要设法掩饰其先祖的道德污点,彻底搞臭前朝末代皇帝。耶尼修斯也认为米哈伊尔三世和瓦西里之间,是由于其他人心生嫉妒、有意挑拨而导致关系破裂,相互敌视。
 而巴尔达斯的恶行,以及米哈伊尔三世的荒唐,很可能都被极度夸大了。
而巴尔达斯的恶行,以及米哈伊尔三世的荒唐,很可能都被极度夸大了。
历史研究不能完全依据推测,而要有充足的史料证据,但也要有合乎常理的合理想象。米哈伊尔三世是否沉迷走马放鹰、纸醉金迷的生活后人无法确知,但是他下令刺杀塞奥克提斯图斯和巴尔达斯,推翻皇太后并加害其母亲和亲姊妹都是不争的事实。他弃绝忠良,滥用皇权的细节虽然也不为后人所知,但他最后起用奸诈之徒瓦西里的史实也大致准确。据此,尽管马其顿王朝对他“妖魔化”的事实确凿无疑,人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即便不是恶徒也是昏君,至少是个心智不健全或者智能低下的人物。正是他的所作所为才为瓦西里乘虚而入、篡夺皇权提供了机会。阿莫里王朝的灭亡,米哈伊尔三世需要承担全部主要责任。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需要心智正常的皇帝、官僚系统、法律法规、武装力量和统一的思想来维护,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皇帝,阿莫里王朝的终结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1]
Chronographiae Quae Theophanis Continuati Nomine Fertur Libri I-IV,p.123;John Skylitzes,A Synopsis of Byzantine History,811-1057,p.50;Ph. Grierson,C. Mango and I. Šev
 enko,“The Tombs and Obits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s(337-1042);With an Additional Note”,p.19.
enko,“The Tombs and Obits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s(337-1042);With an Additional Note”,p.19.
[2]
John Skylitzes,A Synopsis of Byzantine History,811-1057,p.81;Ph. Grierson,C. Mango and I. Šev
 enko,“The Tombs and Obits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s(337-1042);With an Additional Note”,p.19.
enko,“The Tombs and Obits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s(337-1042);With an Additional Note”,p.19.
[3]
Genesios,On the Reigns of the Emperors,pp.80-81;John Skylitzes,A Synopsis of Byzantine History,811-1057,p.98;Chronographiae Quae Theophanis Continuati Nomine Fertur Libri I-IV,p.249;Ph. Grierson,C. Mango and I. Šev
 enko,“The Tombs and Obits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s(337-1042);With an Additional Note”,p.26.
enko,“The Tombs and Obits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s(337-1042);With an Additional Note”,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