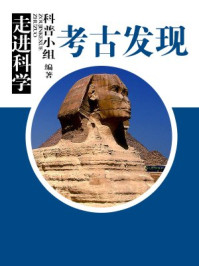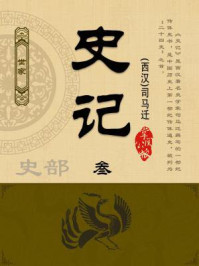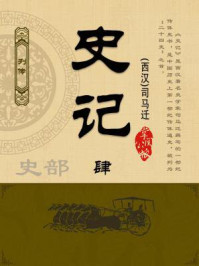米哈伊尔二世(Michael Ⅱ,Μιχα
 λ Β',生于770年前后,卒于829年10月2日,享年59岁)是阿莫里王朝第一位皇帝,也是王朝的创立者,820年12月25日至829年10月2日在位将近九年。
λ Β',生于770年前后,卒于829年10月2日,享年59岁)是阿莫里王朝第一位皇帝,也是王朝的创立者,820年12月25日至829年10月2日在位将近九年。
米哈伊尔二世,因生于阿莫里地区而被称为阿莫里人米哈伊尔,又因为说话口吃,所以也被称为“结巴”米哈伊尔。米哈伊尔二世是阿莫里王朝真正的奠基者。他比利奥五世年长些许,可能生于770年。父亲是东部军区的农兵,为帝国服兵役,获得相应的军役土地。米哈伊尔二世相貌普通,青年时期生活困顿,以饲养马匹和其他牲畜为生。
 据史料记载,米哈伊尔二世对马匹等牲畜独具慧眼,能够识别哪些牲畜善于负重,哪些奔跑迅速。他对这一技能颇为自豪。
据史料记载,米哈伊尔二世对马匹等牲畜独具慧眼,能够识别哪些牲畜善于负重,哪些奔跑迅速。他对这一技能颇为自豪。
 因为家境贫穷,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且常与牲畜为伍,故而米哈伊尔二世行为举止比较粗俗。根据史料记载,米哈伊尔二世说话随意,经常口无遮拦,且言语粗鄙恶毒。米哈伊尔命运的改变和利奥五世一样,都是因为得到巴登斯的赏识,成为后者的女婿,也因此和利奥五世成为连襟。在利奥五世登基成为皇帝并抛弃了结发妻子之后,米哈伊尔对此不满,认为利奥五世行为不端。说话恶毒的他在诸多场合公开批评连襟利奥五世,使用的都是污言秽语,传到皇帝那里后引得皇帝龙颜大怒,但利奥五世对他无可奈何,只是派人好言相劝。可是米哈伊尔照旧我行我素,即便利奥五世软硬兼施,也无法阻止他的攻击性言行。
因为家境贫穷,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且常与牲畜为伍,故而米哈伊尔二世行为举止比较粗俗。根据史料记载,米哈伊尔二世说话随意,经常口无遮拦,且言语粗鄙恶毒。米哈伊尔命运的改变和利奥五世一样,都是因为得到巴登斯的赏识,成为后者的女婿,也因此和利奥五世成为连襟。在利奥五世登基成为皇帝并抛弃了结发妻子之后,米哈伊尔对此不满,认为利奥五世行为不端。说话恶毒的他在诸多场合公开批评连襟利奥五世,使用的都是污言秽语,传到皇帝那里后引得皇帝龙颜大怒,但利奥五世对他无可奈何,只是派人好言相劝。可是米哈伊尔照旧我行我素,即便利奥五世软硬兼施,也无法阻止他的攻击性言行。

但行为粗鄙并非米哈伊尔二世最令人诟病之处,反而是他的成长经历所带来的宗教倾向成为后世史学家不断批判的焦点。米哈伊尔二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大量犹太人和阿斯加诺信徒聚居的地区。受生活环境的影响,米哈伊尔二世本人和家人都是阿斯加诺信徒。
 这一教派接纳基督教的洗礼,遵循除割礼外的摩西法典,每位阿斯加诺教徒都有一位犹太人精神导师和管家,打理精神和日常生活。
这一教派接纳基督教的洗礼,遵循除割礼外的摩西法典,每位阿斯加诺教徒都有一位犹太人精神导师和管家,打理精神和日常生活。
 米哈伊尔二世也不例外,他在一位犹太女导师的指引下,“没有保留任何纯洁之物……贬低基督教义”
米哈伊尔二世也不例外,他在一位犹太女导师的指引下,“没有保留任何纯洁之物……贬低基督教义”
 。后来,他甚至颁布法令,免除了犹太人每年一个诺米斯玛的人头税,这似乎更印证了他阿斯加诺教徒的身份。
。后来,他甚至颁布法令,免除了犹太人每年一个诺米斯玛的人头税,这似乎更印证了他阿斯加诺教徒的身份。
 但史料中对米哈伊尔阿斯加诺教徒身份的着墨,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说明他是一个异端,因为他继续坚持毁坏圣像的宗教政策,对犹太教徒的爱远远超过对基督徒的仁慈。后世史学家不断强化米哈伊尔深受犹太教影响的形象。12世纪史学家仲纳拉斯直接称米哈伊尔二世“属于犹太人”。12世纪末,另一位史学家叙利亚的米哈伊尔则编造了一则传言,声称米哈伊尔二世的祖父是犹太人。
但史料中对米哈伊尔阿斯加诺教徒身份的着墨,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说明他是一个异端,因为他继续坚持毁坏圣像的宗教政策,对犹太教徒的爱远远超过对基督徒的仁慈。后世史学家不断强化米哈伊尔深受犹太教影响的形象。12世纪史学家仲纳拉斯直接称米哈伊尔二世“属于犹太人”。12世纪末,另一位史学家叙利亚的米哈伊尔则编造了一则传言,声称米哈伊尔二世的祖父是犹太人。

米哈伊尔二世是否真的笃信阿斯加诺信仰、是否真的偏爱犹太教徒,我们无从确认。拜占庭史学家如此强调,主要是为了谴责米哈伊尔二世继续执行毁坏圣像政策。米哈伊尔二世是否为阿斯加诺信徒值得怀疑,那么,他对圣像的否定态度也值得再商榷。事实上,在统治初期,米哈伊尔二世对于是否继续毁坏圣像运动也是犹豫不决。他在登上皇位之后,感到政权不稳,因此希望能够拉拢更多的支持者,于是赦免了一些囚犯和流放者。许多崇拜圣像者也获准从流放地返回首都,包括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塞萨洛尼基的约瑟夫等。不过令他们失望的是,米哈伊尔二世并没有针对圣像崇拜活动采取任何官方的举措。特别是在821年1月,支持毁坏圣像的牧首塞奥多图斯死去后,米哈伊尔二世并没有安排尼基弗鲁斯官复原职,而是暂时空置牧首职位,不任命任何人担任这个重要职位。

由此可见,米哈伊尔二世最终选择的是折中方案。他希望从流放地被召回的崇拜圣像者与教会官员们进行辩论,因为后者支持毁坏圣像。但出乎意料的是,崇拜圣像者思想极端,坚决反对毁坏圣像,不与教会官员对话。教宗也公开反对毁坏圣像运动,使崇拜圣像者得到鼓舞。被罢免的牧首尼基弗鲁斯也给皇帝施加压力,他写信要求恢复圣像崇拜。一味妥协的米哈伊尔二世表明,愿意以恢复尼基弗鲁斯牧首职位为条件,换取他暂时搁置围绕圣像崇拜的争议,希望他采取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但再次遭到尼基弗鲁斯的拒绝。
 尼基弗鲁斯安排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等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去与皇帝面谈。米哈伊尔二世为了达到折中的目的,强行安排两派探讨圣像事宜,并安排了倾向于圣像的人做裁决者。塞奥多利等人对皇帝的偏爱并不领情,他们驳斥了毁坏圣像的观点,冒犯了皇帝。米哈伊尔二世宣称自己并不崇拜圣像,决定让教会搁置争议,保持他即位时的和解状态。因此,崇拜圣像的观点和行为仍然得到容忍,但其活动必须在君士坦丁堡之外进行。
尼基弗鲁斯安排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等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去与皇帝面谈。米哈伊尔二世为了达到折中的目的,强行安排两派探讨圣像事宜,并安排了倾向于圣像的人做裁决者。塞奥多利等人对皇帝的偏爱并不领情,他们驳斥了毁坏圣像的观点,冒犯了皇帝。米哈伊尔二世宣称自己并不崇拜圣像,决定让教会搁置争议,保持他即位时的和解状态。因此,崇拜圣像的观点和行为仍然得到容忍,但其活动必须在君士坦丁堡之外进行。
皇帝米哈伊尔二世试图调解崇拜圣像派和毁坏圣像派争议,但以失败告终,最终选择了继续执行毁坏圣像的政策。为此他开始重新考虑牧首的人选。虽然语法学家约翰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遭到崇拜圣像者的极度仇恨,米哈伊尔二世为了尽量减少反对的声音,于是任命了第二人选安东尼一世(Anthony Ⅰ,821—834年在任)。至于约翰,米哈伊尔二世安排他成为太子太傅,专心教导他的儿子塞奥菲鲁斯。

米哈伊尔终其一生,都未敢公开成为真正的毁坏圣像者。在其统治期间,他一直试图缓和与崇拜圣像者之间的关系。824年初,米哈伊尔二世派遣崇拜圣像派领袖撒塞拉里乌斯的利奥前去拜访斯图迪特派领袖塞奥多利,希望后者能够妥协。但塞奥多利强硬拒绝,他指出,信仰事宜应该由东、西方的宗教领袖们决议,特别是教宗,而不是皇帝。于是,皇帝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实现妥协的机会,他着手派遣使团前去罗马教区,试图得到教宗的支持。
为了达到目的,使团并没有直接前去拜会教宗,而是先出访法兰克皇帝“虔诚者”路易,因为路易不像教宗那样坚定地捍卫圣像崇拜的信仰。米哈伊尔让使团带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请求路易能够支持米哈伊尔使团前往罗马所追求的意愿。为了表明诚意,使团还带去了奢华的礼物——押解路易通缉追捕的格拉多(Grado)大主教福图纳图斯(Fortunatus)。此人从法兰克逃亡至君士坦丁堡,米哈伊尔这样做也算是送给路易一个特殊的礼物。使团在824年4月前往法兰克,准备随后去罗马。11月,“虔诚者”路易热诚接待了他们,在将他们送往罗马时也带着真诚的祝福,这表明他同意米哈伊尔关于圣像的态度。但此举对使团的罗马之行并没有任何帮助,最终他们在825年春季返回君士坦丁堡。由此可见,米哈伊尔二世在圣像争端中一直采取温和的安抚政策,甚至在后期开始针对宗教事务颁布敕令时,也只是禁止在圣徒画像上写上“圣徒”字样,而不是禁止绘制画像。

米哈伊尔二世对待圣像一直采取温和的方式,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在其统治期间,帝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他不希望宗教纷争进一步加剧帝国的思想混乱。当时,最大的动荡因素首先来自斯拉夫人托马斯对皇位的争夺。托马斯出生于亚美尼亚军区的斯拉夫家庭,在利奥五世登基成为皇帝后,被任命成为亚美尼亚军区内最重要的图尔玛克指挥官。在米哈伊尔二世成为皇帝时,托马斯虽然已经近60岁,且有一条跛腿,但依然精力充沛。根据史料记载,他由于作战勇敢、性格开朗、待人亲切而受到所有人爱戴。其天赋的所有贵族品质似乎可以与利奥五世媲美。
 在多数史料中,托马斯往往被视为反叛者。然而在当时的内乱中,他们的博弈更像是一场内战,一场在利奥五世死去之后围绕争夺皇权进行的内战。米哈伊尔二世通过阴谋,杀死了利奥五世,登上了皇位,而后不仅对君士坦丁堡严加控制,更安排首都牧首为自己加冕,这是他宣称自己皇位正统性的主要依据。但米哈伊尔二世谋杀利奥五世,也成为其继承皇位的污点。相对而言,托马斯坚决拥护利奥五世,其复仇的旗帜更容易获得利奥五世拥护者的同情。而且托马斯通过赋税减免等方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在多数史料中,托马斯往往被视为反叛者。然而在当时的内乱中,他们的博弈更像是一场内战,一场在利奥五世死去之后围绕争夺皇权进行的内战。米哈伊尔二世通过阴谋,杀死了利奥五世,登上了皇位,而后不仅对君士坦丁堡严加控制,更安排首都牧首为自己加冕,这是他宣称自己皇位正统性的主要依据。但米哈伊尔二世谋杀利奥五世,也成为其继承皇位的污点。相对而言,托马斯坚决拥护利奥五世,其复仇的旗帜更容易获得利奥五世拥护者的同情。而且托马斯通过赋税减免等方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在这次内战中,米哈伊尔二世最初的拥护者包括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军队、奥普斯金军区、亚美尼亚军区、查尔迪亚军区、马其顿军区等。托马斯的军队在内战伊始,穿过亚美尼亚,抵达查尔迪亚军区,由此获得查尔迪亚军区全境和亚美尼亚军区的部分领地。这年11月,托马斯派遣分队在马其顿军区沿岸登陆,进入色雷斯军区。色雷斯军区是在利奥五世统治时期重新恢复建制并日益繁荣,因此他们一直拥护利奥五世,反对谋杀者米哈伊尔二世。托马斯发现色雷斯军区“所有民众都在为他欢呼”
 ,因此很快就成为马其顿、色雷斯、塞萨洛尼基军区的新主人。米哈伊尔二世在欧洲的势力几乎全部倒戈,其掌控的军力仅剩下首都卫戍部队、奥普斯金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另一方面,在海军势力的比拼中,托马斯也占据优势。米哈伊尔二世控制的皇家舰队有大约100艘战船,而托马斯控制了西比莱奥特军区的全部船只,大约是70艘。同时,托马斯下令继续造船。在内战爆发后不久,托马斯伪造书信,声称自己在海、陆两线作战中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诱导驻守在希腊军区和所有海岛上的海军支持叛军,召集他们共同反对篡位皇帝。他们甚至用谷物运输船运送士兵,迫不及待地起航向首都进发,此时托马斯的船只总数大约有350艘,远远超过了对手。
,因此很快就成为马其顿、色雷斯、塞萨洛尼基军区的新主人。米哈伊尔二世在欧洲的势力几乎全部倒戈,其掌控的军力仅剩下首都卫戍部队、奥普斯金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另一方面,在海军势力的比拼中,托马斯也占据优势。米哈伊尔二世控制的皇家舰队有大约100艘战船,而托马斯控制了西比莱奥特军区的全部船只,大约是70艘。同时,托马斯下令继续造船。在内战爆发后不久,托马斯伪造书信,声称自己在海、陆两线作战中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诱导驻守在希腊军区和所有海岛上的海军支持叛军,召集他们共同反对篡位皇帝。他们甚至用谷物运输船运送士兵,迫不及待地起航向首都进发,此时托马斯的船只总数大约有350艘,远远超过了对手。

除此之外,托马斯还获得了其他方面的援助。在内战爆发后不久,阿拉伯人趁机大规模远征,他们“抓住机会肆无忌惮地洗劫所有岛屿和陆地,而且似乎将完全占领它们”。托马斯为了保卫自己和手下士兵的家园,在821年春与阿拉伯人进行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然后趁机向阿拉伯人提出结盟协议。他同意支付给哈里发一些贡赋,作为回报,哈里发认可托马斯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并同意提供援助。一方面,托马斯在哈里发的支持下,抵达阿拉伯势力范围的叙利亚安条克,接受正统派牧首乔布(Job)为其加冕,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为了增加托马斯的军力,哈里发同意他在阿拔斯王朝境内征募基督徒士兵。显然,托马斯在战争兵源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

米哈伊尔二世坐拥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坚守不出,他确信首都城防工事无比坚固。在多次攻击陆地城墙没有任何进展时,托马斯无计可施,只能诉诸海上进攻,但再次遭遇失败,因为他的战舰被守城部队施放的希腊火摧毁。于是托马斯集中大军,利用飞箭、投石器等,重点攻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相对薄弱的布拉海尔奈区域,但城中守军借助居高临下的位置,用飞箭和对攻器械击败了攻击者,迫使托马斯的士兵仓皇逃回营帐。与此同时,米哈伊尔二世在布拉海尔奈的圣玛利亚教堂上方树立起一面战旗,并指派自己的儿子塞奥菲鲁斯带领城中的修士,高举圣十字架和圣母的斗篷,在圣迹和其他民众的陪同下,绕着城墙而行,吟唱着连祷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神圣的援助,鼓舞士气。
 双方僵持不下。
双方僵持不下。
812年春季,托马斯建造了更多攻城器械,希望用它们从船上抛掷大石头,摧毁城墙薄弱部位。米哈伊尔二世站在城墙上向围城的士兵发话,声称只要他们弃暗投明,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可以被赦免,但是他的游说并没有成功。于是米哈伊尔二世出其不意,突然从城中出击,取得了一些胜利,尤其是在海上击退敌人。托马斯的海军为了发射石弩,减低水面颠簸的影响,将战船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定的平台,但忽视了防卫的问题。其攻城将士突然看到敌人袭来,一时仓皇失措,有的直接投降,有的未加抵抗、弃船而逃,纷纷涌上陆地。托马斯的海军遭受重创,以至于他们虽然继续封锁首都,但已经丧失了战场优势。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米哈伊尔二世向保加利亚人求助。他想起了与保加利亚人在816年签订的合约,于是遣使出访保加利亚可汗奥穆尔塔格,希望他能进攻托马斯。作为回报,米哈伊尔二世愿意提前更新四年后到期的合约,同时可能允许保加利亚人洗劫色雷斯和马其顿。奥穆尔塔格当然同意接受这样的便宜,于是在822年11月开始入侵拜占庭境内,打击托马斯的军队。托马斯被迫放弃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集结全军去对抗保加利亚人,结果两败俱伤。于是在君士坦丁堡的米哈伊尔二世大肆宣扬托马斯的战败,从而令托马斯的舰队丧失斗志而投降。托马斯只能放弃围攻,前往阿卡迪奥波利斯(Arkadiopolis)过冬。自此,托马斯已经承认自己无法在内战中获胜,虽然他仍拥有军队数量上的优势,但内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倒向米哈伊尔二世。
823年5月,双方各自集结兵力,在君士坦丁堡以西大约30英里的平原上进行决战。托马斯制定战略计划,令其军队佯装战败逃跑,然后在敌人追击时,再突然杀个回马枪。这种诱敌深入埋伏突袭的战术如果在以前尚可得胜,此时则容易导致失败。托马斯军队士气低落,佯装逃跑演变成了真的逃跑,结果全线溃败,许多人归降米哈伊尔二世。剩下的人一部分躲避在色雷斯的要塞之中,大部队则随从托马斯返回阿卡迪乌堡。米哈伊尔二世乘胜率军进行全面反击。阿卡迪乌堡遭受围攻五个月之后,因城中物资严重匮乏,只得投降,守军降将还交出了托马斯。米哈伊尔二世当然不能放过托马斯,残忍地处决了后者,既斩草除根,又杀一儆百。

此后,米哈伊尔二世开始清洗托马斯的势力,最终在824年3月班师回朝。他对托马斯的军队并没有大肆惩罚。除了来自哈里发帝国和斯拉夫人的援兵以及一些罪大恶极之人被处决,其他参与的拜占庭军队将士只是遭受了一些羞辱性惩罚。米哈伊尔二世下令将他们的双手绑在背后,在大竞技场游街。至此,长达三年多的内战最终结束。但拜占庭的兵力遭到巨大削弱,特别是海军的损失产生了真正深远的影响。
拜占庭海军遭受重创,导致帝国在海上丧失了基本的防御能力,也导致帝国的诸多岛屿无法获得帝国军队的援助。这集中体现在西西里和克里特的失守。826年春季,西西里军区的图尔玛克尤非米乌斯(Euphemius)统帅军区舰队,对非洲海岸发动了一次长途侵袭,俘虏了一些阿拉伯商人,抢夺了大量战利品。但在返回军区首府叙拉古之前,尤非米乌斯获悉他可能会被逮捕,因为他被指控从修道院诱拐修女成为自己的妻子。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割鼻之刑。为了逃避审讯,尤非米乌斯怂恿舰队占领了叙拉古,击败了军区将军,并将其杀害。至此,尤非米乌斯毫无退路,于是在826年年底宣布称帝。此后不久,尤非米乌斯被巴勒莫(Palermo)的军队击败,被迫逃往非洲,向当地的阿拉伯埃米尔求助。
埃米尔同意结盟,派去了70艘战船、700名骑兵和1 000名步兵,这足以对付西西里岛上大约1 000人的常规部队。作为回报,尤非米乌斯承认埃米尔是自己的宗主,承诺将西西里税赋的大部分缴纳给埃米尔。827年6月14日,联合军队在西西里西部海岸登陆,轻易击溃了岛上迎击的拜占庭守军,并重创拜占庭海军。他们很快占领了岛上大部分城镇和要塞。叙拉古在名义上投降,向阿拉伯人呈送人质和贡赋,但暗中加强城墙防御。827年年末,阿拉伯将领阿萨德(Asad)带着舰队,再度通过海陆进行围攻,但并未取得理想效果。
828年春,巴勒莫的军队试图营救叙拉古,但遭到阿拉伯人伏击,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围攻叙拉古的阿拉伯人也出现物资困难,他们缺少粮食,被迫以战马充饥。不久,疾病开始在阿拉伯营帐内爆发。夏初时分,阿萨德死去,可能源于疾病或者源于伤口感染。阿拉伯人自行选举了一位新的领袖穆罕默德,重整旗鼓。但在叙拉古即将沦陷时,米哈伊尔二世派遣的大规模舰队从海上杀出。面对饥荒和疾病,以及拜占庭大量舰队的支援,阿拉伯人仓皇撤去对叙拉古的包围,转向西西里岛的内陆地区逃窜。拜占庭人逐渐收复在西西里岛上的控制权。
829年年初,米哈伊尔二世派遣塞奥多图斯前去加强西西里的防御。在登陆之后,塞奥多图斯虽然遭遇了一些挫折,但很快击溃阿拉伯人的主力,杀死了许多阿拉伯人,并进而围攻阿拉伯人的防御营寨。由于要塞中物资不足,阿拉伯人试图发动夜袭,但拜占庭人将计就计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再次大败阿拉伯人。829年秋季,拜占庭人已经在西西里占据优势,很快就可以将岛上的阿拉伯入侵者全部清除。

相对而言,拜占庭帝国在克里特岛上的境况比较糟糕。一群来自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827年6月,前去侦查克里特,却发现岛上几乎没有海防,于是大肆掠夺,带回许多俘虏和战利品。828年春季,他们建造和准备了40艘船,1.2万名男女老少在阿布·哈夫斯(Abu Hafs)的带领下,再度登上克里特岛,但此次他们选择在此定居。于是他们在岛上修建新的城市,也是防御性的港口,取名哈达格(Al-Khandaq)。阿拉伯人以此为根据地,占领了克里特岛上许多城镇。米哈伊尔二世很快获悉克里特的情况,于是派遣安纳托利亚军区将军弗提努斯(Photinus)带领能够集结的舰队前去支援克里特。但双方实力差距较大,拜占庭海军溃败,弗提努斯只身坐着小船逃到蒂亚岛(Dia Island)。

米哈伊尔二世将夺回克里特的重任交给了西比莱奥特军区将军克拉特鲁斯(Craterus)。克拉特鲁斯指挥全部的70艘船和2 000名海军,于828年秋季在克里特岛上登陆。双方进行正面交战,战争从破晓持续到黄昏。拜占庭人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他们并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在夜间进行庆祝,结果饮酒过多,沉沉睡去。阿拉伯人在夜里发动突袭,大败拜占庭人,只有克拉特鲁斯本人得以乘坐小船,逃到科斯岛。但阿布哈夫斯派遣两艘阿拉伯船只,前去将其抓获,并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米哈伊尔二世收复克里特岛的行动以完败告终。

米哈伊尔二世意识到,想要清理克里特岛上的阿拉伯人,必须从长计议,重新进行帝国的海军建设。为此,他任命一位叫欧里法斯(Ooryphas)的人负责招募新的海军,并为每位海军准备了总计40个诺米斯玛的招募金,这超过了正常六年的军饷。在金钱的激励下,欧里法斯得以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军队。这支特殊的海军部队由于军饷数额特别高而被称为“四十诺”部队。在829年春,欧里法斯带着他的士兵登陆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并迅速清理岛上的阿拉伯人。此后他们开始在爱琴海海岛上加强驻守。

正是由于内战和西西里岛、克里特岛的困扰,米哈伊尔二世统治期间四面出击,努力取胜,希望帝国维持和平。为此,他在826年与保加利亚人延续和约,对哈里发在825年的海陆两线入侵暂时隐忍。而阿拉伯帝国内讧、哈里发被迫转向其内部秩序的建设,也给了米哈伊尔二世喘息的时间。
对于米哈伊尔二世而言,他最主要的任务并非开疆扩土,而是维系帝国的安宁,保持内外和平,使得帝国在一个稳定的王朝统治下,繁荣昌盛。为此,米哈伊尔二世试图建立新的家族继承。824年,米哈伊尔二世的第一任妻子塞克拉因病死去,他将其埋葬在圣使徒教堂,宣称自己悲痛不已,无心再娶。但实际上,米哈伊尔二世是想利用婚姻扩大势力,增加政治资本。他安排一些官员,让他们声称帝国如果没有皇后就不符合正常的统治秩序,然后让这些宫廷大臣催促自己再婚。米哈伊尔二世假意同意,但同意的前提是,他们要签署誓言,对自己的新婚妻子及其可能生下的孩子忠诚并顺从,哪怕是在自己死后也要信守诺言。米哈伊尔二世的要求得到官员们的同意,他因此得以建立王朝。与此同时,为了让自己的王朝统治更具合法性,他决定选择君士坦丁六世的女儿埃芙菲罗丝奈为新婚妻子,将其从修道院中召回,并举行盛大婚礼。

事实上,伊苏里亚王朝统治时间很长,也赢取了诸多胜利,足以获得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这一婚姻选择也符合他在圣像政策中采取的折中态度,因为一方面埃芙菲罗丝奈来自开启了毁坏圣像运动的伊苏里亚王朝,另一方面埃芙菲罗丝奈本人是崇拜圣像的虔诚信徒。总之,米哈伊尔二世通过第二次婚姻,既避免了激化宗教矛盾,还得以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和声望,最终建立起了新的王朝。这有利于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稳定发展。
829年,患有严重肾病的米哈伊尔二世于10月2日自然死亡,死后被埋在圣使徒教堂查士丁尼陵墓区中。
[1]
米哈伊尔二世因为延续毁坏圣像政策而遭到拜占庭史家的谴责,被称为“恶魔”“恶龙”。
 约翰·斯基利齐斯更是直言:“他对上帝不敬,因此为罗马帝国带来了万般邪恶。”
约翰·斯基利齐斯更是直言:“他对上帝不敬,因此为罗马帝国带来了万般邪恶。”
 客观而言,他在圣像问题上的政策是温和的,其根本目的是减少帝国内的教派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统治期间帝国遭遇的诸多灾难。对帝国而言,最大的灾难显然是他和斯拉夫人托马斯之间长达三年的内战,因为帝国的资源遭到了极大消耗。相对于利奥五世时期,米哈伊尔二世的统治使得帝国的实力衰退明显,但他尽力去维系帝国的安宁,在此过程中既取得过很大的成功,也有失败。最为重要的是,米哈伊尔二世成功建立的新王朝得以延续数代,保证了帝国政局的稳定,也是此时帝国迫切需要的,有助于帝国的复兴。
客观而言,他在圣像问题上的政策是温和的,其根本目的是减少帝国内的教派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统治期间帝国遭遇的诸多灾难。对帝国而言,最大的灾难显然是他和斯拉夫人托马斯之间长达三年的内战,因为帝国的资源遭到了极大消耗。相对于利奥五世时期,米哈伊尔二世的统治使得帝国的实力衰退明显,但他尽力去维系帝国的安宁,在此过程中既取得过很大的成功,也有失败。最为重要的是,米哈伊尔二世成功建立的新王朝得以延续数代,保证了帝国政局的稳定,也是此时帝国迫切需要的,有助于帝国的复兴。
 纵观拜占庭帝国史,有王朝和无王朝时期的政治秩序差别很大,前者极大降低了帝国最高权力交接的社会成本,而后者造成的动乱特别是引发的内战使社会各阶层都深受其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难以保证合适人选主宰帝国,因此米哈伊尔二世建立的新王朝具有积极的意义。
纵观拜占庭帝国史,有王朝和无王朝时期的政治秩序差别很大,前者极大降低了帝国最高权力交接的社会成本,而后者造成的动乱特别是引发的内战使社会各阶层都深受其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难以保证合适人选主宰帝国,因此米哈伊尔二世建立的新王朝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