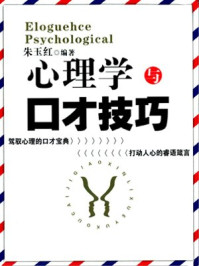自1912年以来,已有50多万学员参与过我开设的有关公众演讲培训课程。其中一些人还就为什么会报名参加这类课程,以及期待达到的效果做过书面说明。当然,他们的措辞不尽相同,但来信中所表达的核心期待及基本欠缺却是惊人的统一。接二连三的人在来信中写道:“一被要求起身发言,我就感到非常紧张、恐惧,以至思绪混乱、无法集中精神、记不清之前想要表达的话。我想获得自信、镇定,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生意场上、俱乐部里或是在公众面前,我希望逻辑严密,组织好自己的思绪,继而清晰且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成千上万的来信内容大致都是如此。
举个实际的例证吧。多年前,有一位D.W.根特先生参加了我在费城举办的公众演讲课程。开课不久后,他邀请我到“制造商俱乐部”共进午餐。根特先生人近中年,生活态度乐观,拥有自己的制造企业,还是教会工作及公民活动的领导者。在当天的饭桌上,他靠着餐桌说:“我曾多次应邀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讲话,但从没讲好过。面对公众,我就莫名地焦虑,脑子里一团糨糊,所以我一生都在极力回避演讲之类的事。但我现在已是大学董事会主席,必须主持会议并发言……您认为我在这个年龄还能学会演讲吗?”
“我认为吗,根特先生?”我回答道,“这可不是我认为的问题。我知道你能行,我知道你可以,只要你愿意练习,同时遵循那些方法。”
他乐于相信我说的话,可似乎觉得那些话过于乐观。“恐怕您只是出于善意,”他回答道,“才刻意鼓励我的吧。”
当他结束整个培训之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们再次相聚在“制造商俱乐部”,还共进了午餐。我俩还是坐在第一次见面的那个角落,用的还是那张餐桌。在提到我俩上次的谈话时,我问他是否还认为我当初太过乐观,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封底的笔记本,让我看了看他曾记录的那些演讲及日期。“有能力去做这些演讲,以及为社区做出自己的努力,”他坦陈,“我从中获得的快乐无疑是我一生中最满足的事情之一。”
我俩相遇之前不久,华盛顿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裁军会议。当得知英国首相计划出席此次会议时,费城的浸信会教徒给他拍去电报,邀请他前往他们所在的城市,并在即将举行的一场大型群众集会上做演讲。根特先生告诉我,他本人被该市的浸信会教徒推选,向听众介绍首相。
然而,就在两年多之前,这个人还跟我同坐一张餐桌,非常严肃地问过我他有无做公众演讲的能力。
此人演讲能力的神速进步是不是不可思议呢?没什么不可思议的。类似的例子成百上千。譬如,数年前,来自布鲁克林的一位内科医生,这里姑且称其为柯蒂斯医生,在佛罗里达州巨人队训练场附近过冬。作为一名热情的棒球迷,他经常去看巨人队的训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那些队员便熟悉了起来,甚至还应邀前去参加他们的庆功宴。
当咖啡和坚果送上餐桌,几位嘉宾被逐一邀请讲话,突然,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之后,柯蒂斯医生听到宴会主持人说:“今晚,在座嘉宾中有一位内科医生。我打算请他就棒球运动员的保健问题谈谈他的高见。”
柯蒂斯医生有这方面的准备吗?那是当然。他在该领域的发言权毋庸置疑:此人研究卫生学并行医30余年。他大可以在饭桌上与其邻座滔滔不绝地聊一整晚。不过,要起身,哪怕是跟寥寥数人说上几句同样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做演讲这事简直要命。一想到讲话这事儿,柯蒂斯医生就心跳急剧加速、惴惴不安起来。此前他从未做过任何公众演讲,而此时此刻,他脑子里的任何想法,都如鸟儿展翅,迅疾飞得不知去向。
他该怎么办呢?每位听众都在一个劲儿地鼓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柯蒂斯医生摇了摇头以示拒绝,可这反而让掌声愈加热烈,愈加让听众期待他的演讲。“柯蒂斯医生!讲几句!讲几句!”的呼声愈加响亮、紧迫。
柯蒂斯医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他深知自己如果站起身来,也讲不了几句,结果必然以失败告终。他起身,二话没说,转身背对那些朋友,继而默默地离开了现场。当时的他一定觉得尴尬无比,甚至颜面扫地。
难怪回到布鲁克林之后,柯蒂斯医生最先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报名参加我开设的公众演讲课程。他不想再有被弄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的时候。
柯蒂斯医生便是那种让老师非常高兴的学员:他学习起来认真到了极点;他非常想提高自己的演讲能力,就实现其愿望而言,他一心一意;他每次都悉心准备自己的演讲稿,每次都以顽强的毅力不断地练习,从来没有旷课或者缺席的现象。
他严格按照一名好学之人的习惯去做每一件该做的事。他进步的速度之快,大大超出了他本人的预期。上过几次课后,他演讲的那种紧张感已经降低,自信心逐渐增强。两个月下来,他俨然成为其所在小组的“明星发言人”。不久之后,他便收到前往各地演讲的邀请,并四处奔波起来。现在的他很享受演讲带来的那种感觉和愉悦,外加演讲带来的荣誉,也因此结识了众多的朋友。
纽约市共和党竞选委员会有一名成员,在听过柯蒂斯医生的一场公共演讲后,便诚邀他前去为其党派做一次巡回演讲。试想,那名政治家要是知道其邀请的演说家在一年之前的一场公共晚宴上还因为怯场而说不出话来,并在羞愧和慌乱中落荒而逃,他会是何等的惊讶!
在公众演讲时建立自信和勇气,以及面对公众时不乏沉着且清晰思考的能力,多数人认为如登天一样难,其实那难度顶多占完成一次成功演讲的难度的十分之一。它并不是极少数受上天眷顾的宠儿才能享有的天赋。对于公众演讲,只要有足够强烈的愿望,任何人都能将其潜在的能力开发出来。
坐着的时候思维敏捷,站起身来脑子却不听使唤,其中难道真有什么玄机吗?当然没有。事实上,在面对听众之前,你应该思考到位;听众的到来应该激发你的斗志,让你兴奋起来。多数演说家认为面前的听众是一种刺激,是一种灵感,能使演讲者的头脑更加清晰、敏捷。正如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彻所言,演讲者当时还没有想法、事实,观念会如“袅袅青烟飘然而至”。演讲者需要做的就是伸出双手抓住它们,趁热打铁。这应该成为你的一种体验。只要你不停地训练,且持之以恒,你就会拥有类似的经验。
说了这么多,你可能百分百地确信这一点:勤学苦练可以消磨你的“听众恐惧症”,同时给你带来自信心以及永不衰竭的勇气。
不要以为自己是个特例,你的演讲会难得非同一般。就连那些日后成为其同代人中最为雄辩的演说家,在其演讲生涯之初也曾被这种盲目的恐惧和自我意识所困扰。
美国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尽管曾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前几次进行公开演讲时,吓得两腿发抖。
在首次做讲座时,马克·吐温感觉自己嘴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心跳快得如同直冲领奖台领奖一般。
“南北战争”中的格兰特将军曾统率过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取得过维克斯堡战役的胜利。然而,当他尝试发表演讲时,他也承认心里有某种感觉,如同患上了骨髓痨
 。
。
作为其所处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法国政治演说家,尚·饶勒斯在鼓足勇气完成自己的首次演讲之前,也因不知怎样演讲而在下议院张口结舌地呆坐了一年之久。
“在我第一次尝试做公开演讲时,”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承认道,“我不妨直说,我当时简直难受到了极点。演说词里没有半点儿修辞,全是大白话,舌头不听使唤,刚开始连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英国杰出的演说家约翰·布莱特曾在国内竭力支持美国统一及其废奴事业。他曾在某校的教学楼前,面对一群听众发表了自己身为议员的首次演讲。在前往演讲的路上,由于他非常担心自己会搞砸,于是恳求随行的那名同伴,说只要看到他演说时出现任何紧张的迹象,就立即鼓掌给他打气。
面对人生的第一次演讲,爱尔兰的领袖查尔斯·斯图亚特·帕内尔也很紧张,据他的兄弟证实,他紧握双拳,到最后指甲掐进了掌心的肉里,并流出鲜血。
英国政治家迪斯雷利也承认,与其在下议院做那场首次演讲,他宁愿统率一支骑兵冲锋陷阵。他的开幕词简直失败得一塌糊涂。英国作家谢里丹的首次演讲也是如此。
事实上,正因为众多声名显赫的演说家都在自己的首场演讲中有过欠佳的表现,所以时下的议员们都有同感,那就是:年轻人首次演讲中出现的不祥之兆,会助他走上成功之道。所以,鼓起勇气吧。
回顾众多著名演说家的生涯之后,看到一名学员在演讲之初总略显忐忑不安且紧张激动时,我深感欣慰。
即使是在只有二十来人参加的小型商务会议场合,也应当有些许演讲的样子。发表演讲的人应该会有纯种马刚上嚼子的那种紧张感。两千年前,西塞罗就曾说过:“一切真正有价值的公众演讲都以紧张为特质。”
即使是在电台发表演讲,演说家们同样会有类似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风恐惧症”。查理·卓别林的名声虽然早已家喻户晓,但在发表电台演讲时,他总是将自己演说的内容全部写在纸上。早在1912年,卓别林就巡演全国,在美国演出了一部名为《音乐厅之夜》的幽默短剧。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英国出演正统戏剧。然而,当他走进直播间面对麦克风时,他感觉自己的胃里翻江倒海,就像在风起浪涌的二月横渡大西洋一样。
著名动作影星兼导演詹姆斯·科克伍德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是讲坛上耀眼的明星,然而,当他面对看不见的听众做完演讲走出播音室时,却在不停地抹去额前的汗珠。“相比之下,”他承认道,“参加百老汇的首映式可谓小事一桩。”
很多人,不管他们有多少演讲经历,每次登台前难免都会产生这种自我意识。但是,当他们起身适应几秒后,这种感觉就会随之消失。
就连林肯在做开场白时也有怯场之感。“林肯在演讲之前通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林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赫恩登如是说,“适应其周围环境,对他来说似乎是件力气活儿。在明显的自信心不足以及神经过敏的影响下,他会纠结好一阵子。每每见到这种情形,我都打心底里同情林肯先生。演讲伊始,他的声音听起来尖锐且令人很不舒服。整个人的行动方式、说话态度、面色黝黑枯黄、满脸皱纹、声音枯燥、站姿古怪、怯场举动等——这一切似乎都对他不利,但这种情形仅持续那么一小会儿。数分钟之后,他便镇定自若,热情洋溢、诚挚无限,这时,他的演讲才算正式开始。”
你的经历或许也跟他们一样吧?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才能,继而成为一名优秀的公众演讲者呢?要迅速且高效地达到这一目的,以下4个基本要素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