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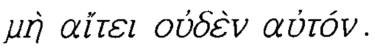
请什么也不要问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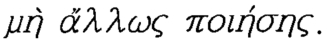
请不要用其他方法。
女人沉默地坐在朗朗跟读的学生中间,希腊语老师再也没有指责过她的沉默。他的背影倾斜着,握着松软布质黑板擦的手和胳膊大幅移动,将写满黑板的文字擦干净。
直到他停止动作,学生们都很安静。坐在柱子后面体形瘦弱的中年男人费力地伸展腰,用拳头敲打脊柱。满脸痘痘的哲学系学生的手指不停滑动在桌子上的手机液晶屏上。大块头研究生注视着黑板,张开与身形正相反的薄薄嘴唇,用听不见的声音跟读消失的单词。
“从六月开始,我们会读柏拉图,当然语法也会一起学习。”
希腊语老师将上身倚靠在擦干净的黑板上说,用没有握白粉笔的左手推了推眼镜。
“人类从沉默,到用‘啊啊、呜呜’等还未分离的音节进行沟通,在最初创造了几个单词后,语言渐渐有了体系。体系到达顶峰时,语言就会有极度精巧而复杂的规则。学习古语很难的原因就在于此。”
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道抛物线,左边上坡的角度很陡峭,右边的下坡平缓而长,他用拇指指着抛物线的顶端继续说。
“到达顶点的语言从那一瞬间开始画出平缓圆满的抛物线,变化成更容易使用的形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虽是一种衰退和淘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进步。今天的欧洲语言就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过程,而变成不再那么严格、精巧而复杂的产物。阅读柏拉图的著作,可以感受几千年前达到顶峰的古代希腊语的美好。”
在说下一句话之前男人停顿了一下,坐在柱子后面的中年男人用拳头捂住嘴短暂而清脆地咳嗽了几声,当他又长长地咳嗽了一下后,额头上长满痘痘的大学生回过头来不高兴地瞥了中年男人一眼。
“比如说,柏拉图使用的希腊语就像刚刚摘下的新鲜果实,他以后世代的古代希腊语急速衰退。随着语言消失,希腊国家也最终灭亡。从这一点来说,不仅是语言,柏拉图仿佛站在周围所有东西的夕阳前一样。”
她虽然认真地听他说话,但并不是每一句都能集中。一句话像长长的鱼被锯成段,像鱼鳞一样的助词与语尾在还没有分离之前堵在她的耳朵里。 从沉默。啊啊、呜呜。没有分离的音节。最初的几个单词。
失去语言之前——还在用它写文章的时候——她偶尔盼望自己使用的语言与那些更近一些。呻吟或低低的叫声,无声忍受疼痛的声音,狼叫声,在睡梦中哄孩子的声音,呵呵的笑声,嘴唇闭合又张开的声音。
她看着自己刚才使用的单词的形状,有时想张开嘴读它们。她这才后知后觉地明白,那如夹在架子上的肉体一样扁扁的形状,和自己想要读出它们的声音是多么不同。停止读之后她总是咽下唾液,像马上按住伤口止血,或者相反地,把血尽量多地挤出,阻挡细菌进入血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