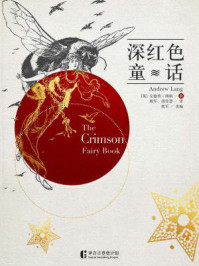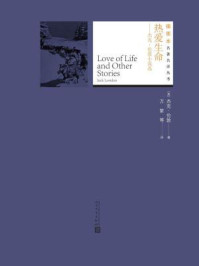此生之中总有空白,那些翻开“档案”时引人猜想的空白。“档案”是薄薄一页,装在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泛白的天蓝色文件夹里。曾经的天蓝色,已经发白。“档案”一词写在文件夹中央。墨色深黑。
这是于特的事务所留给我的唯一纪念,证明我曾经在那个窗口朝向院子的旧式三居室公寓里待过。那时我不过二十出头。于特的办公室在最里面那个房间,装档案卷宗的柜子也在那里。为什么是这份“档案”,而不是另一份?也许,就是因为那些空白。还有,它并不在放卷宗的柜子里,而就在那里,被随手丢在于特的办公桌上。如他所言,一个悬而未决的“案子”——它会永远是个悬案吗?——这也是他聘用我来“试工”(用他的话说)的那天晚上,他跟我谈的第一个案子。几个月后,另一个夜晚的相同时间,当我放弃这项工作,彻底离开事务所的时候,我瞒着于特,在和他道别后,悄悄地把随意放在他办公桌上的天蓝色文件夹里的这页档案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作为纪念。
是的,于特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关于这页档案的。我得去15区的一幢大楼的门房处询问门房太太,有没有一个叫诺埃尔·列斐伏尔的人的消息,一个给于特出了双重难题的人:她不只是忽然失踪,她的真实身份甚至都还不确定。去过门房之后,于特还让我带着他给的一张卡片去邮电局。卡片上标着诺埃尔·列斐伏尔的名字、地址和照片,用来取那些留局自取的邮件。这个名叫诺埃尔·列斐伏尔的人把它忘在了住所。接着我得去一个咖啡馆,打听人们最近有没有在那儿见过诺埃尔·列斐伏尔,还得坐在那里直到黄昏,以防诺埃尔·列斐伏尔出现。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同一个街区,同一天。
大楼的门房太太很久才来应门。我敲着门房的玻璃窗,越敲越响。门开了道缝,一张困倦的脸从后面探出来。我一上来就觉得她对“诺埃尔·列斐伏尔”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
“您最近见过她吗?”
结果她用干巴巴的声音回答我:
“……没有,先生……我有一个多月没见过她了。”
我没敢再问别的问题。也许是没时间问,因为她立刻关上了门。
在邮局,工作人员仔细看了我递给他的卡片。
“先生,但您不是诺埃尔·列斐伏尔。”
“她不在巴黎,”我对他说,“她让我来取她的信件。”
于是,他起身,走到一排格子架前,看了看上面为数不多的信件,回过身冲我摇头。
“没有诺埃尔·列斐伏尔的信。”
我只好去于特跟我说的那个咖啡馆了。
晌午刚过。小小的咖啡馆里没有什么人,除了一个男人,在柜台后看报。他没见我进来,继续看报。我不知道该如何起头提问。好像就直接把有诺埃尔·列斐伏尔名字的卡片递给了他?于特让我做的事情令我有些尴尬,我腼腆的个性适应不了。男人抬起头来看着我。
“您最近没见过诺埃尔·列斐伏尔吗?”
我好像讲得太快了,快到句子都没说全。
“诺埃尔?没有。”
他回答得那么简短,我差点要接着问他几个关于这个人的问题了。但我怕引起他的戒备心。于是,我在人行道上窄小的露天座位里挑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他过来点单。这是个打听更多消息的时机。一些无关痛痒的句子在我脑子里盘旋,可以从他那里问出些确切的消息。
“我还是等等她吧……诺埃尔可说不准……您觉得她还住在这个街区吗?要知道她约我在这里见面……您认识她很久了吗?”
可是当他端来我点的石榴汁时,我什么也没说。
我掏出于特给我的那张卡片。今天,一个世纪之后,我在克莱尔枫丹牌笔记本的第十四页停下笔来端详这张“档案”里的卡片。“准予无附加费用代为收取留局自取邮件凭证。许可事项1号。姓:列斐伏尔。名:诺埃尔,现居巴黎15区。地址:公会路88号。持证人照片。准予无附加费用收取留局自取邮件。”
照片比那种简陋的一次性成像照大很多。颜色过深。说不出她眼睛的颜色。也确定不了头发的颜色:褐色?浅栗色?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位的那个下午,我极尽专注之能事,盯着这张线条模糊的脸,我不确定能认出诺埃尔·列斐伏尔。
我记得那是早春时节。小小的露天座位沐浴在阳光里,不一会儿天阴了。露天座位的挡雨棚为我遮雨。当人行道上出现疑似诺埃尔·列斐伏尔的身影时,我就会盯住她,看她会不会走进咖啡馆。关于怎样搭讪,为什么于特没有给我更精确的指示?“您自己看着办吧。盯个梢,我得知道她是否还在这个街区转悠。”“盯梢”这个词让我笑出声来。于特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皱着眉,一副怪我轻浮的样子。
下午慢慢过去,我还坐在露天座位的一张小桌边。我想象着诺埃尔·列斐伏尔从住处出来走到邮局,又从邮局走到咖啡馆。她可能还会去街区里其他地方:电影院,几家小店……两三个她常在路上遇见的人本该能够证明她的存在。或者有一个和她一起生活的人。
我想着:每天都要去一趟邮局。总有一封信最终会落到我手上,永远到不了收件人手里的那些信中的一封。她没留地址就走了。或者,我在这个街区租个酒店房间住一段时间。遍寻这个区域,包括她的住处、邮局和咖啡馆,还可以以核心地带为圆心扩大搜寻范围。我会留意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熟悉他们的面孔,就像盯着钟摆看的人,随时准备抓住最为转瞬即逝的波纹。只要有点耐心就够了,而在我人生的这一时期,我感觉自己能不顾日晒雨淋,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等下去。
几个客人走进了咖啡馆,他们之中没有诺埃尔·列斐伏尔。透过我背后的橱窗玻璃,我观察着他们。他们坐在软包长凳上——只有一个例外,他站在柜台前和老板聊天。这个人一到,我就注意他了。他应该和我同龄,总之不会超过二十五岁。高大,褐色头发,身穿羊毛翻皮外套。老板用不易察觉的动作指了指我,他顺势盯着我看。但我们中间隔着橱窗玻璃,我轻微转过头,就能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先生,请问……先生……”
我有时在梦里听见这样的招呼声,假装温柔的语调,暗含威胁。是那个穿羊毛翻皮的年轻人。我装作没留意。
“请问……先生……”
他的语调更生硬了些,就像当场抓住你在做坏事的人叫你的声音。我抬头看他。
“先生……”
我吃惊于他使用“先生”这个字眼,尽管我们年龄相仿。他的行径紧张,我感到他对我有所戒备。我朝他粲然一笑,但这笑容好像令他恼火。
“听说您在找诺埃尔……”
他站在那儿,就在我的桌前,像是想要挑衅我。
“是啊。您也许能告诉我一些她的消息……”
“凭什么?”他傲慢地问我。
我真想站起来就走,留他呆立原地。
“凭什么?好吧,我是她朋友。她让我替她去取留局自取信件。”
我把那张卡片拿给他看,上面用订书机订着诺埃尔·列斐伏尔的照片。
“您认识她?”
他凝视着照片,然后伸出胳膊,像是要来抓那张卡片。但我一下子阻止了他。
他最终还是坐到了我的桌边,或者更像是他任由自己跌到了柳条椅里。我看出来他现在拿我当回事了。
“我不懂……您去邮局帮她取信?”
“是的。就在公会路上的那个邮局,稍远一点儿。”
“罗杰知道吗?”
“罗杰?哪个罗杰?”
“您不认识她丈夫?”
“不认识。”
我想,在于特的办公室里,我读那页档案读得太快了,短短一页,只有三段。然而,我印象中上面并没有说明诺埃尔·列斐伏尔已婚。
“您是说罗杰·列斐伏尔?”我问他。
他耸了耸肩。
“完全不是。她丈夫叫罗杰·比阿维沃尔……您呢,您到底是谁?”
他凑近我的脸,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我。
“诺埃尔·列斐伏尔的一个朋友……我只知道她婚前的名字……”
见我说得如此平静,他的情绪也缓和了一些。
“真奇怪,我从来没见过您和诺埃尔一起……”
“我叫埃邦,让·埃邦。我才认识诺埃尔·列斐伏尔几个月。她从没和我说过她结婚了。”
他沉默着,看起来相当失望。
“她叫我去邮局帮她取信。我觉得她不住这个街区了。”
“住这里的,”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她和罗杰曾住在这个街区,沃日拉街13号。后来,我就没有她的消息了。”
“您尊姓大名?”
我立即后悔以这种生硬的方式问了他这个问题。
“热拉尔·穆拉德。”
显然,于特的档案里有好多遗漏。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热拉尔·穆拉德。也没有罗杰·比阿维沃尔,这位诺埃尔·列斐伏尔所谓的丈夫。
“诺埃尔从没和您提过罗杰?也没提过我?这还挺奇怪的……我叫热、拉、尔、穆、拉、德……”
他一字一顿,响亮地重复了自己的姓名,就好像他要一劳永逸地使我相信他的身份,并唤起我的记忆,或者更像是想要说服我热拉尔·穆拉德有多重要。
“……我感觉我们在聊的不是同一个人……”
我挺想回答他,让他放心,告诉他他是对的,毕竟在法国肯定有许许多多诺埃尔·列斐伏尔。然后我们就能相安无事地告别了。
我试着大致写下那天下午和那个名叫热拉尔·穆拉德的人的对话,但那么多年过去了,记忆里只剩下一些片段。要是一切都录在磁带上就好了。这样,现在听来,我就不会觉得我们的对话发生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属于永恒的现在。我们大概会在持续的底噪上听到背景的杂音,公会路上春天午后的嘈杂声,甚至是旁边学校孩子们放学的声响——这些孩子现在应该已经是有一定年纪的大人了。这劈头盖脸的当下,完好无损地穿越近半个世纪的时光,本可以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那一时期的精神状态。于特在他的事务所里给我提供了一个职位——相当次要的职位,我原本完全不想向这个方向发展。我曾以为这份临时的工作会带给我各种素材,好在我将来进行文学创作时给我灵感。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生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