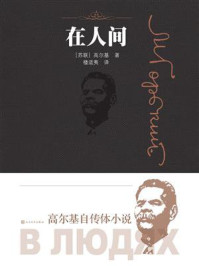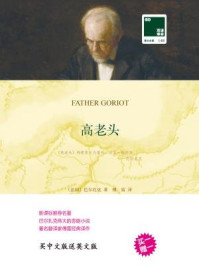这本求超越、求解脱的书,人却每把我锁在其中。我趁这次重版的机会,为新的读者们写下几点感想,并对这书写作的始末做一更率直的供认,借以稍释它以往的重负。
一、《地粮》不说是一本病人所写的书,至少是当他正在恢复康健,或是痊愈后所写的书——这人却曾是病者。即在本书的诗情中,已足显示出这种把生命当作行将失去的东西,而猛力地想把它抓住的企图。
二、我写这书,正当文学在极度的造作与窒息的气氛中;而我认为亟须使它重返大地,用赤裸的脚自然地印在土上。
这书怎样地与当时的趣味相左,只看它整个的失败就能想见。没有一个批评家曾提到它。十年中它正好销出五百本。
三、我写这书,正当自己结婚后,生活开始固定起来。我自愿地放弃某种自由,而这自由却正是我在书——一件艺术品——中所愿加倍地追偿的。不用说,我在极真挚的心情下写这本书,但同样真挚的是我心中的否认。
四、我再声明:我并不使自己止于此书。我所描绘的这种飘忽与随机的状态,我只画下其中的轮廓,正像小说家画下他主人公的轮廓,而这主人公虽然跟作者有相似之处,却只是作者自己想象的产物。即在今日我仍感到,当我画下这轮廓时我必先使它与我自己分离,或者也可说,先使我自己与它分离。
五、人每以这少年时代的著作来审判我,仿佛《地粮》中的伦理观即是我毕生的伦理观,仿佛我自己第一个就不遵守我所给予我年轻读者的忠告:“抛开我这书,离开我!”是的,我曾立刻离开那曾是写这《地粮》的我;所以当我回省我一生,我注意到其中最显著之点,不是我的无恒,而相反地,正是我的一致。这种内心与思想的一致我敢相信是绝无仅有的。在临死前能亲见自己始终贯彻一己所主张的那些人,我愿有人能把他们的名字列举出来,我将在他们的身旁占一席地。
六、更进一言:有些人在这书中只知看到,或只承认看到对欲望与本能的颂赞。我认为这多少带点近视。在我,当我重展这书时,我所看到的,更是对贫乏真谛的阐发。我抛开其余一切,至今矢志所保留的仍是这一点。因此之故,才有我日后援引福音中的主张,即是于“忘去自身”中完成自身最高的实现,完成幸福最大的要求与其无止境的期许。
“愿我这书,能教你对自己比对它感兴趣,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又比对你自己更感兴趣。”这话你在引言与卷末都能念到。又何须强我复述?
安·纪
一九二六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