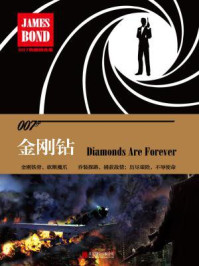牙梨哈的正常一直令纳谋鲁取费解。他了解那些专司刑讯的人,因为他不仅曾与其共事,早年的黑暗岁月中甚至还曾落入其手。这些人往往十分古怪,令人一看便心中发毛。牙梨哈却是例外。此人要么已学会对他人的磨难麻木不仁,要么便是装作如此。然而纳谋鲁取却无法断定是哪种情况,这也正是牙梨哈第二个令他费解之处。纳谋鲁取能活到今日,全凭一双能看透人心的眼睛,可他却看不透牙梨哈。
因此,当纳谋鲁取品味着新鲜槟榔带来的些微眩晕感步入刑讯处时,他一如往常地带着几分戒心。
看门的是个年轻后生,满身的实权衙门中差人的狂傲之气,显然还不曾吃过苦头。
“执事可在?”
“你是何人?”
“禁城察事厅纳谋鲁取,不知上下如何称呼?”
“赫兰族艾驰恩。”后生挺着胸自报家门。
“阁下家世显赫。”
“好说。”
“刑讯执事牙梨哈有阁下襄助,幸莫大焉。”
“有幸与牙梨哈家族次子共事,荣耀万分。”
“有幸与二位共事,实是荣幸之至。”
“好说。”
“牙梨哈执事可在?”
“执事方才接手一宗案件。”
“我正为此案而来。”
“腿子!”艾驰恩朝后院大喊一声。转瞬间一个南人老头迈着小碎步跑到艾驰恩面前,跪倒施礼。
“速去禀报执事书记,有回话速来禀报。”
老头领命,又迈着小碎步跑远。纳谋鲁取趁这片刻清闲嚼着槟榔,琢磨着这位对自己与察事厅一无所知的后生。任何一处部司中的不称职者总是最危险的,其能力低下程度也显示着其家族将其塞入官场的能力。然而这后生是否会在被碾得粉身碎骨前学会夹起尾巴做人?纳谋鲁取估计他有五成机会。显赫的家族或许能帮他逃过几次劫难,让他学乖,否则便无须再学了。
南人老头跑了回来,将一纸手令捧给艾驰恩。
“跟他走。”艾驰恩道。
南人老头引领纳谋鲁取朝刑讯处深处走去。从大门到后院办事区有两条通道。一条通道沿西墙而行,与刑房、牢房相隔甚远,专供文员和访客使用。除了个别“天赋异禀”的人,常人见了刑讯场面难免会感到不悦与不安,认为自己与受刑人的苦难多少有些干系。所谓“君子远庖厨”,与鱼肉隔离开来的刀俎多少能心安一些。
而另一条通道则恰好由刑房、牢房的中央穿过,这便是设计用意。帝国庞大,不乏以身试法者,刑讯处自然难得清闲,于是这条通道便成了一种工具,即刑讯的第一关。随后,失去自由的嫌犯便只能任由无形的爪牙慢慢掐入肌肤骨骼,撕碎五脏六腑。这一套刑讯方法纳谋鲁取深有体会。
纳谋鲁取被引入第二条通道。他不知道这是老头的无心之失,还是艾驰恩的有意羞辱,或者是牙梨哈的旁敲侧击。他不动声色地穿过悲鸣与啜泣,同时将这一猜测记在心里。
两人终于来到刑讯处执事牙梨哈的书房门前。老头上前叩门,一位面色苍白的年轻南人书记领两人入房。正在书桌前伏案工作的牙梨哈见到纳谋鲁取,立刻笑容满面地迎接过来,一副老友重逢的样子。
“牙梨哈执事。”
“老兄!”
“可否叨扰执事片刻?”
“你来啥都好说。来来来,咱后面聊。你俩,”牙梨哈转头对南人书记和带路老头道,“滚。”
牙梨哈和纳谋鲁取走进套间,盘腿坐在榻上,背后掖上靠枕。牙梨哈又拿出瓷杯,斟满两杯热腾腾的酸马奶。
“朝会如何?案子让谁办?”
“我。”
“定了?”
“尚未公布,但估计八九成。”
“恭喜恭喜。”
“我要那个侍卫。”
“抱歉,刑讯可是咱的差事。”
“话虽如此……”
“你听我一言,这差事咱熟,现下不比你当年,又多了许多新家伙什儿。”
“我须拿到此人。”
“为啥?”
“有话要问。”
“咱都不曾问出甚来,你能?”
“牙梨哈大人,现下我要此人自有原因。此案关乎禁宫安危,诸多内情你现下不知,将来可能亦不会知。圣裁一时三刻间便要颁布,届时我凭圣谕再来要人也是一般。你我素来交好,我才此刻前来。你将人与我,一则将来圣上知晓必定嘉许你晓事,二则免我凭圣谕领人时面皮尴尬。我来并非为难于你,是替你早做计较。”
牙梨哈倚在靠枕上,垂头沉思片刻。他虽年轻却并不糊涂,片刻便拿定了主意。
“本官不给你用刑。”纳谋鲁取对惊魂未定的南人侍卫道。侍卫的一只眼睛已肿成桃子,嘴里少了两枚牙齿,背上深达肌理的鞭痕纵横交错。二人此刻已回到纳谋鲁取的书房。纳谋鲁取又道:“本官问你,你须实话实说。本官知道你以为我等作好作歹耍弄于你,其实并非如此。本官非但不会搬出牙梨哈来唬你,还会想方设法将你留下。本官颇有些办法,问话一毕,便吩咐太医替你疗伤,若有问题再去问你。若非情势紧急,本官须不必现下问你。这些你可曾听清?”
“听……清了。”
“好。你从昨日讲起,一直到那宫女发现主子尸体。先说昨日晚上有何异常之事。”
“没……没有。”
“你将那位主子的一举一动细细讲述一番。”
“傍……傍晚,她……”
“她便是那位主子?”
“傍晚那位主子……”
“何日傍晚?”
“昨日傍晚。”
“几时?”
“申末,天色还早,主子出门时在俺们岗亭签的字。”
“你与主子可有言语?”
“就说请主子签字来。”
“主子有何言语?”
“没……没有。主子们都不和俺们讲话。”
“你看主子是否有不安之态?与平日有何不同?”
“没有。”
“好生想。神色是否慌张?眼神是否正常?衣着打扮与平素有何不同?”
侍卫想了想,似乎有话要说,却又咽了回去。
“你想起什么了?”
“只是……”
“随便说,不打紧。”
“若是非说主子有啥不同,若是俺非说不可,主子平日都是一般模样,可这位主子,好像有些……有些得意的模样。”
“得意?”
“像是有啥好事等着她了。她有点儿着急要走,可又不像平日那般对俺们很凶。”
纳谋鲁取停下来想了想。不对,现下还说不通。
“然后便又如何?”纳谋鲁取继续问。
“主子去了一个多时辰,又签字回宫。”
“具体几时?”
“记不准了,簿子上有。因为殿试的事,叫俺们来顶班的。”
“你这里出入签字规例如何?”
“进……进来便要签字。”
“进来何处?”
“前……前厅。”
“由外宫进来前厅?”
“对。”
“前厅通往内宫?”
“对。”
“主子们进门均须签字?”
“对。”
“签的是什么?”
“那个……卷轴。”
“本官问主子们签字都写些什么!”
“写……写名字。”
“卷轴放在何处?”
“现下?”
“不,平素放在何处?”
“俺们拿着。”
“拿在何处?”
“拿……俺们便是拿在手中,主子要签时便放在桌上。”
“你站在何处?”
“门口。”
“门里还是门外?”
“门外,俺们……站在外宫这边门口。”
“不在前厅中?”
“对,不在屋里……在屋外。”
“可曾进去前厅?”
“不曾……不敢!不许进去!”
“为何?”
“便是不许进去。”
“我问为何不许进去!”
“那……那便不知道了。”
“可曾见过旁的侍卫?”
“见过,换班时候便见了嘛。”
“不是,本官说内宫那边侍卫。”
“皇上那边的?”
“对。”
“没有。”
“为何?”
“不是……不是一个长官管。从来不曾见过。”
“平素你便站在门外,手中拿着卷轴,门上可有落锁?”
“对。”
“总是落锁?”
“自然!”
“开锁有何规例?”
“只有名册上的人方可进门。”
“有个名册?”
“对。”
“名册是写好的?你拿在手中?”
“对。”
“两边的侍卫都有这份名册?”
“对。”
“名册可会变化?”
“会。若是变了,他们便拿个新的过来给俺们。”
“近日可曾变化?”
“不曾。”
“那主子也在名册上?”
“主子们大多都在。”
“也有主子不在?”
“有。”
“为何?”
“俺说不来。”
“三夫人?”
“不在。”
“不在?”
“大主子走中厅。”
“不走你把守的这门?”
“从来不走。”
“好,便说现下有个主子来了,你如何措置?”
“主子签过字,俺便打开门锁。主子进了门,俺便将门落锁。”
“锁在你们这边?”
“对。”
“另一边什么样子?”
“门另一边?”
“对。”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是。”
“把手也无?”
“对,只是个光溜门板。”
“如此人如何能出来?”
“主子敲门,俺们这边开锁,将门打开。”
“对面内门也是如此?主子进门,敲对面内门,内门外侍卫听了便从外面开门?”
“俺说不来。”
“你不知道?”
“俺们不许进去。”
“你不曾有朋友在对面当值?可曾闲谈?”
“俺合计……俺合计,对面规例也是这般。”
“如此说来,前厅两侧房门都从外面落锁,屋内必定无法开门,对不对?”
“对。”
“若是要瞒过你与对面侍卫,悄悄从这房子中出去,有何办法?”
“绝无办法!”
纳谋鲁取从送来的卷宗中找出登记卷轴,很快便找到那项记录。记录显示死者于戌时签入,夜还不深。纳谋鲁取思索片刻,又找出她在申末签出的记录,仔细看了签名,随后又回到签入处两下比对。相比之下,签出时笔迹略显飘忽,带着些许年轻女子的幼稚,却又很有天赋。签入的笔迹虽然也大体如此,但审视之下笔法似乎沉稳了些。这其中有何缘故?纳谋鲁取无法确定,毕竟差异太小了。
“签入可是戌时?”
“对,俺觉得差不多。”
“那便不到两个时辰。”
“对。俺觉着对。”
“你将那位主子回宫时的模样讲述一番。”
“还是那模样。”
“还是得意的模样?”
“没。可是,主子出门时也不是特别得意。俺不是说她得意,就是俺觉着。”
“你看她情绪如何?伤心?有心事?高兴?”
“没啥……都和平日一般。”
“衣着如何?身上有何携带物事?”
“衣……衣着?”
“对,主子穿的是何衣裳?”
“俺……俺……主子换了身衣裳。”
“此话怎讲?”
“主子回来时衣裳不同。”
“这是否异于平日?”
“这……没有,她们平日便总换衣裳。”
“何人?”
“主子们。”
“主子有何举动?”
“她走过来,到俺们岗上,在卷轴上签了名字。”
“可有言语?”
“没有,平素也是这般。”
“可有人与她同行?”
“没。”
“无人护送?”
“没。”
“这是否异常?”
“有些。”
“你可曾记下?”
“记下啥?”
“记下之后上报。”
“上报不归俺们管。”
“倘若你上报此事,主子出入无人护送,算是何等异常?”
“照理是该有人护送,可俺们也见过……”
“见过主子无人护送?”
“对,有时候。”
“为何不曾上报?”
后生想了想,面露惊惧:“俺们只是个把门的。”
“那又如何?”
“就是把门。俺们便是这差事。后宫才管护送。”
“主子签过字,又怎样?”
“签过字便由俺们这边过去,进门,俺们将门落锁。”
纳谋鲁取仔细琢磨一番,却并无特别发现。
“现下且是这些,若有问题再来问你。你且坐好,本官吩咐人送你去疗伤。”
纳谋鲁取走出书房,踏上宫内长廊。长廊里燃着巨烛,回音激荡。右转两次之后,他便来到了直通内卫司的“明镜”长廊。工匠正为三日后的殿试张灯挂彩。纳谋鲁取绕过工匠,朝内卫司走去。一只老鼠慌里慌张地横穿长廊跑过。各部门的人都被抓差去准备殿试,连捕鼠人手都短了。
伴着脚步的层层回声,纳谋鲁取暗自揣摩着索罗。早在索罗刚刚在官场中立足时,纳谋鲁取便开始为其怒气而费解。他这怒气究竟来自何处?又为何经久不衰,源源不断地从那张怨毒的嘴巴里喷涌而出?
索罗如此怒气冲天,而纳谋鲁取也自知早晚会与他共事。因此索罗进宫后,三个月来纳谋鲁取一直在仔细观察他。
纳谋鲁取按一向习惯,从索罗模糊而零碎的言行中提炼其性格细节:此人目的何在?又遭遇了什么阻碍?
索罗的故乡远在西部大漠的对面。他虽算不上第一个由那里来到中原的人,但在此地同族寥寥。他的同乡多是生意人,鲜有久居皇城者。况且这些人大多并不显眼,体态、外貌并无太多的异域特征。
然而索罗却是例外。他自称是其部落血统使然。他最奇特之处是肤色,苍白堪比尸体,偏偏还生着黑硬的体毛。他眼窝深陷,双眉高耸有如屋檐;眼睛也怪异,总是圆睁着,眼皮翻折的方式也异于常人。最为骇人之处——那对眼珠子竟然是蓝色的。
各地语言纳谋鲁取颇听过一些,索罗的语言却闻所未闻。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拜访中,纳谋鲁取曾向索罗讨教其本族文字的写法。索罗便挥毫写下“Minichiatto de Solo”,说是念作“明尼察铎·狄·索罗”,这便是其名字的本乡本土的写法。
纳谋鲁取疑心索罗的怒气正是来源于其与众不同:他在这个世界没有朋友。
纳谋鲁取也曾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中——仅有忠诚,却无情谊。
不知不觉间纳谋鲁取已经来到内卫司门前,此处比平日热闹了许多——卫兵加了岗,还加设了巡逻队,均是响应早前的警讯。一番常例拜访手续之后,纳谋鲁取被引入内卫司的阴森走廊,未几已坐到索罗对面,正对着那双怒目。
索罗先开了口:“你是为我干的,还是为后生干的?”
“干的什么?”
“把我的人要回来。”
“为谁又有何分别?”
“有。”
“我为自己。”
“哈哈。估计是。”
“下官要见昨日申初至今日巳末在内宫当值的那个侍卫。”
“为什么?”
“这段时间,死者本应签出、签入内宫,却直至巳时方被人发现。下官须询问两次照面情形。”
“不给。”
“为何?”
“牙梨哈打了我的脸。他打了我的人。”
“但下官已将人要了回来。”
“没用。牙梨哈抓了我的人,你抓了我的人,大家会说,抓索罗的人没事。”
纳谋鲁取想了想,索罗言之有理,这正是人们会得出的结论。纳谋鲁取固然可以请来圣谕令他讯问两名侍卫,索罗也无话可说,但他却等不起。
“我问你,你问他们,如何?”纳谋鲁取继续道。
“你问什么?”
“死者模样、穿戴、异常之处、所携物事、心绪如何、往返间有何不同。”
“哈,不知道。”
“大人可以讯问当值侍卫。”
“他们也不知道。”
“何以见得?”
“那位主子没回来。”
“此话怎讲?”
“就走了,没回来。签出没签入。屋子里死了。”
“这段时间可有旁人从内宫签出?”
“没。”
“大人从何而知?”
“你以为我从何而知?”
“下官早晚还要问他们。”
“嗯,但是现下不行。现下什么人都来欺负我。”
纳谋鲁取靠着椅背,默默将事情在心中演绎了一番:那姑娘夜晚出宫,先在内宫一侧签出,穿过前厅,然后在外宫一侧签出,无人护送,或许有些兴奋,暂且不论。姑娘一个多时辰后回来,仍是孤身一人。一切安好,身上衣裳却换了。她由外宫签入,只向前走了几步,在内外两道门之间。她身后的门也落了锁。大约七个时辰后才有人看见她,但已经被捅死了。这中间她不曾出门,且内宫的侍卫离她仅数步之遥。此间内外两道门都落了锁,也无人听到任何异动,更无人签入、签出,且房间并无其他入口。
这种情形绝对说不通。纳谋鲁取将这些问题存在心中,让它们如藤蔓般慢慢发育、生长。
纳谋鲁取沿着黑暗的门廊慢慢朝柯德阁的书房走去。轻如耳语的备考读书声不断地从远方传来,打破了周遭的寂静。路上不时有老鼠窸窸窣窣地跑过。
纳谋鲁取一直痴迷于推敲旁人行为背后的动机。除了生性使然,而早年经历也强化了这一技艺。正是凭借这门技艺,他才能熬过凶险时局,熬过九死一生的净身与混迹南人间的日子。对于他的同行,寻找真相的过程仿佛是用事实填充地图,而他的图却由人们的动机与欲望织就。
这个过程从未改变。他的心中总是先浮现出一张人欲织就的大网,随后便有微茫的光线照在这纷乱的私欲上,将其主人的所作所为投射成缥缈的荫翳。他多年之前便已明白,虽然荫翳飘忽不定,但其上方的私欲总是有迹可循。沿着这张网上各色人等的真实欲望,他们的所作所为终究会被揭开。
意欲进宫的普通人只有两条可行之路:第一条便是像纳谋鲁取那样净身入宫;第二条则是通过两年一度的殿试。天下人皆可举业:先是乡试,再是府试,然后是会试,最后多年寒窗苦读的学子才终能面对登峰决战——殿试。
随后便是一场凶险无情的洗牌:有的家族黯然返乡,有的举族销声匿迹,最后只有寥寥数人能取得他们孜孜以求的权力。除了为权势不惜一切之人,其他人绝无可能在竞争中胜出而不失理智。因此现在确是杀人害命的季节,然而过去却无人会在殿试前动手。
这便是问题的关窍所在,这一次凶杀何以会发生于殿试之前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