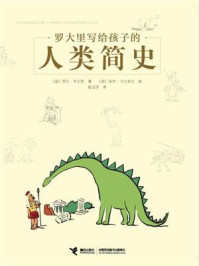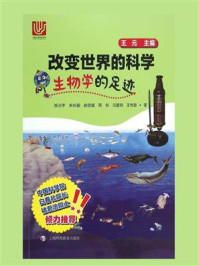有时候,最好的老师只对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无望的成人传授一回。
——佚名
用让人望而生畏的谜语来表达思想,不是今天的哲学家才开始的做法。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只是加深了人类无家可归的感觉。两千多年前,一个叫约伯的人,蜷伏在约旦的沙漠里,就他耳闻目睹到的不公义向上帝提出质疑。对此,旋风中的声音向哀求者反问了许多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正是现代科学试图解答的。耶和华反问约伯的问题包括: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雹仓吗?雨有父吗?鹰雀飞翔,是因着你的智慧吗?
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站在约伯身旁的以利户。他怯生生地向怒气冲冲的长者回应道,上帝并非没有显现自己。神可能会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言说,但人可能觉察不到。根据这些对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无论我们个人的信念如何,都不妨考虑一下,什么是隐藏的教师,以免我们对教师的理解仅仅局限为教育系统的一个环节。
一般而言,我们是在向教师学习,但教师并不总是在学校或在实验室。有时候,我们能学到什么也取决于自己的洞察力。此外,教师可能是隐藏的,即使是最好的教师也不例外。年轻人以利户观察到,老年人不总是富有智慧,教师传授的方式也未必都适合跟他学习的年轻人。
举例来说,有一次,我意外地从一只蜘蛛那里上了一课。
那是一个下雨的清晨,我在美国西部荒漠一个狭长的溪谷里寻找化石。突然,在眼睛水平线的高度,我看到了一只潜伏的圆蛛,体形巨大、黄黑相间,她的蛛网挂在高大的野牛草之间,就在沟壑旁。这是她的宇宙,她的感觉不会超过蛛网的纵横与轮辐。她纤长的腿可以精细地感受到蛛网上的任何风吹草动。她知道风在拉扯,雨滴在坠落,被困住的蛾子在挣扎。在蛛网的轮辐之下,有一缕结实的蛛丝,一旦有猎物进入,她会迅速赶来查看。
出于好奇,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铅笔,碰了蛛网的一角。很快,她就作出了反应。她开始拨动蛛网,颤动得越来越剧烈,直到肉眼难以看清。如果换作其他小虫,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早就被牢牢缠住了。颤动渐渐减弱,我看到蜘蛛开始轻车熟路地寻找猎物挣扎的迹象。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宇宙里,她从未遇到过铅笔尖这样的入侵者。蜘蛛习惯了蜘蛛的思维方式,她生活在她的宇宙里。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是非理性的、无关的,最好是她的食物。在幽深的溪谷里穿行的时候,我意识到,对于蜘蛛来说,我其实也是不存在的。

一边在溪谷里跋涉,我一边在想,此刻,在我的血管里,巨噬细胞在沿着毛细血管游荡,仿佛带着一点基本的智力:要是没有它们的悉心照料,我恐怕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对于这些如同阿米巴虫一样的巨噬细胞而言,这个有意识的“我”也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就像是一个化学网络,持续不断地给巨噬细胞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如果它们会思考,也许会认为这个自然环境是不朽的,因为一代又一代的细胞出生,死去,未来又有更多的细胞来重复这个循环。这个奇怪的化学网络里也包含了我的智力——它就像一道黯淡的光,飘忽不定、晦暗莫测,我自己也难窥究竟。
我开始看到,世界上的生物各自活在不同的宇宙里,有些较大,有些较小,但所有这些宇宙,包括人类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限的。我们都带着许多维度,穿过彼此的生活,就像幽灵穿墙而过。
从那以后,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与这只圆蛛邂逅的画面。但是,那个纤细的蛛网所传递的信息,直到现在才变得清晰起来。这次相遇,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如此不安?是蜘蛛对于人类胜利的漠不关心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胜利就是胜利,无法抵赖。我曾不止一次地察觉到——也在一层层的矿石里亲眼见过——漫长往昔岁月的痕迹。这些发现,都是现代科学的伟大功绩。我见过早期海洋中浮动的细胞——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人类,都是它们的后裔。远古海洋里的盐分,此刻正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远古海洋的岩石,此刻正凝结在我们的骨骼里。每次我们在海滩漫步,总有一种古老的冲动,驱使着我们甩开鞋子、脱掉衣服,到海带和朽木中间寻觅食物,仿佛我们是一群在连年战争中流离失所、思念家乡的逃亡者。
这的确是一场战争——生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漫长战争,而且已经持续了约30亿年。一开始,有一些奇怪的化学分子,在没有氧气的天空下游荡;亿万年之后,第一株绿色植物出现了,它学会了利用来自太阳——离地球最近的一颗恒星——的能量。人类的大脑,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有无穷无尽的梦想和渴望,消耗的也是植物的能量。
大脑的耗氧量比身体的其他部分都高,因此需要川流不息的血细胞为其供应氧气。一旦窒息,哪怕时间很短,我们称之为“意识”的现象就会消失于无机世界的茫茫暗夜。人体是一个神奇的容器,但是它的生命却密切依赖于一种它无法合成的分子——氧气。只有绿色植物知道这个秘密,能够利用来自遥远太空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
 。这个例子极好地说明,人的生存密切依赖于其他生物。
。这个例子极好地说明,人的生存密切依赖于其他生物。
所有对生物化石有过研究的人,都会承认,如果我们考虑到地球漫长的生命史,绝大多数——或许是90%以上——的物种,都已经灭绝了。那些比人类更古老的生命,或是已经灭绝,或是后代发生了剧变,以至于我们难以辨认出它们之间的关联。那些特化的生物,与塑造了它们的环境,一道灭绝了——老虎锋利的剑齿最终失去了用武之地,与此同时,人类用其制造出的长矛击倒了最后一只猛犸象。
在30亿年缓慢的摸索过程中,只有一种生物成功逃脱了特化的陷阱,活到了现在,这就是人类。要知道,特化曾经导致了无数的死亡和白费的努力。不过,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故事还没有结束。
随着人脑的出现,终于出现了这样一种生物,她们的直立身体解放了前肢,于是可以探索并操纵周围的环境。就这样,人类有了特化的大脑,由此摆脱了特化的命运。许多动物受环境塑造,只能适应于大自然的某些角落或罅隙,但这样的繁荣往往不会持续很久,它们很快就灭绝了。
我感到困惑不解,思绪一再回到草丛间蜘蛛的那个小小的宇宙——都是因为这个念头吗?
也许是的。
人类一度在洞穴的墙壁上想象动物,现在却要面对他们的心智在世界上留下的后果。人类,已经突破了藩篱,开始控制其他生命。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不断回忆起溪谷里邂逅蜘蛛的场景。
蜘蛛是人类的一个缩影,蛛网的轴辐体现了这种象征。人类,同样生活在一个网络里,这个网络延伸至星际空间,回溯至史前的黑暗疆域。在帕洛马山天文台上,有一只巨大的眼睛,注视着几百万光年外的空间,它的雷达可以听到最遥远的星系里的轻声细语,它可以通过电子显微镜凝视人体里极小的微粒。人类的这个网络,地球上还没有哪种生物编织出来过。就像那只圆蛛,人坐在网络的中心,聆听着。有了知识,人类就能回忆起地球的历史,包括人类出现之前的漫长历史。就像蜘蛛的触角,人类触摸到了一个自己永远无法亲身进入的世界。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借助机器,人类可以计算、分析、窥探未来,于是,模糊不清的未来也组成了这个网络的一部分。
不过,黄昏苍穹之下,这只蜘蛛仍然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记忆里。蜘蛛在它的宇宙里思考——准备应对雨滴和飞蛾的振翅,除此之外,它没有更多的期待,绝不会想到有一支铅笔横空闯入。
说到底,人与蜘蛛有什么区别呢?人的思考能力,跟蜘蛛的思考一样,都有局限。我们一边在思考最近的星系,一边要面对各种威胁:有毒的真菌、战争、暴力和人口压力,一边在追忆曾经的伊甸园,可惜后者已经消失在美洲的热带雨林里了。现在,这个梦想再次召唤它,就像是来自月球之外的蜃景。我进一步想,人类编织网络——这也许是天性。但是,我同时也想起那些巨噬细胞,它们在我体内熙熙攘攘;虽然身体早晚都会腐朽,但是细胞依然生生不息。如果说蜘蛛无法看到我的面孔,无法看到我是如何扰动了它的宇宙,那么,我们无法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沉醉于感觉的延展——事实上,我们的心智从冰河时代诞生伊始,在广袤的冰原上就开始了这种旅程——我们对此感到满足;不久之后,我们还要进军太空。仅仅凭借人的观察是不够的,哪怕是观察宇宙的边界;仅仅是掌握核能(就像掌握着一根长矛),或者看到闪电,或者看到远古和未来(人类早晚会实现这一点),也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人类的大脑只会重复老旧的圈套,而对于那些不知如何学习的野兽来说,自然界中充斥着这种圈套。
现在,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通过电波来聆听星系里的噪音,也不仅仅是解码DNA双螺旋里的生命语言。这些仍是我们拓展后的感觉。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无边的黑暗,这是一位梦想家的作品,他也想象出了光与星系。在行动出现之前,在物质存在之前,想象在黑暗中生长。人类也是这个终极惊奇与创意的一部分。当星尘渐渐变成人体内涌动的细胞,我们似乎在追寻着什么,也许是一种无法把握的实体;让我们记住,经历了冰河时期的人类,凝视着科学的魔力与镜像,最后建构起了自己。显然,他来不是为了看到自己,或者他狂野的脸庞。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是一个倾听者,且在追寻某个超越于自身之上的超验空间。他的追随者曾经给他起了许多名字,早在洞穴时代就开始了。人类,这个自我建构者,借助于天赋理性,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人类在不断地求索,如同亘古之初的那颗单细胞,不断求索那位神秘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