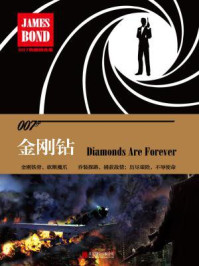还有几针,浴衣就缝好了。此时,阿峰突然停住了手。
夏日黄昏,房檐上方,乌云低垂,骤雨将至。指尖虽已裹上淡淡暮色,手却并非因此而停下。
十八岁时,她嫁到这个位于双叶町的当铺之家。丈夫佳助颇有出息,生活并无困顿之处。不过,只要邻里有求,她也会接些针线活补贴家用。可就在四年前,佳助醉酒后杀死一名赌徒,进了监狱。之后,阿峰便一人带着年幼的女儿,靠着手中这根针维系生计。佳助被判入狱五年,当时她想着无论如何得守住当铺,等待丈夫归来。可虽说已经嫁来十七年,没料到大难当头时,邻里如此薄情。最终在与狱中的佳助商量后,将当铺转让他人,阿峰则带女儿回深川的娘家等候丈夫出狱。父母已故,亲人仅剩在木场照料来往行人的叔父,但下町
 里人情深厚,阿峰像离婚后返回娘家的女儿,在儿时居住的大杂院中开始生活,周围邻里待她一如往昔。母亲在世时,就一直承蒙位于主干道的绸缎庄“市善”的关照,如今市善的人也盛赞阿峰“不愧是阿民的骨肉,缝边手艺举世无双”,交到手上的活计令阿峰母女衣食无忧。
里人情深厚,阿峰像离婚后返回娘家的女儿,在儿时居住的大杂院中开始生活,周围邻里待她一如往昔。母亲在世时,就一直承蒙位于主干道的绸缎庄“市善”的关照,如今市善的人也盛赞阿峰“不愧是阿民的骨肉,缝边手艺举世无双”,交到手上的活计令阿峰母女衣食无忧。
今日,阿峰将上午缝好的一件丝绸外褂送到市善时,在店头摆放着的男子浴衣布料中,蓦然看到一款淡茶底色、深紫色方框图案的料子,随即以格外便宜的价格买下,一回家便上紧缝制起来。
丈夫入狱后,每年一到风儿将河畔树木那刺鼻到恼人的气味吹来的时节,阿峰就会买回新的布料,为丈夫缝制衣衫。
衣服做好了,却没人穿。到去年为止做好的三件,如今都沉睡在柜子深处。一到夏天,阿峰就莫名地思念丈夫。肌肤的炽热不单因为酷暑。黄昏时分,坐在廊下,茫然望着不足两坪的后院,尽管周遭暮色笼罩,似乎融进了茂密的青草,身体却从内部燃烧起来。
为了平息这份燥热,阿峰便拿起针线,为狱中的佳助缝制浴衣。是前年的事吧。当质地凉飕飕、触感光滑的浴衣碰到肌肤时,阿峰倏地敞开衣衫,将缝至半途的衣袖带着针贴到了胸上。此时,隔壁的阿常刚好进来,那一幕好生尴尬!
不过,今年手中的针不同于前几年。在市善一看到那块料子,阿峰就决定要为阿安做件衣裳。
阿安名为仓田安藏,和阿峰是在一个大杂院一起玩大的发小。阿峰到了被唤作“姑娘”的婚配年龄时,邻居们都觉得她会嫁给安藏,阿峰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事实上,十八岁那年的春天,两人已私下约定秋天就结为夫妇。可就在之后不久,阿峰却因为某件事不得不嫁去现在的夫家,最终背叛了安藏。
在确定返回离开了十几年的老家时,阿峰最在意的便是安藏的反应。
阿峰出嫁后,安藏也成了家,但他的老婆由于产后身体恢复不佳去世,搏命生下的独子也在四岁那年掉入河中溺亡。如今安藏在木场的后边独自一人生活。他不时帮木场里的木材加工厂做些事,但主业是一名点灯夫,即傍晚时分点亮这附近到日本桥一路的瓦斯灯,清晨时分再赶紧去一一熄灭。
听说安藏也负责点亮大杂院一角的瓦斯灯,早晨和傍晚时分阿峰便不敢出门。夜里,走在大路上,瓦斯灯的亮光好似连成串的珍珠在闪耀,阿峰会突然生出眷念之情。这些灯都是阿安点的啊!无论发生什么,若当初与阿安如愿结为夫妇,两人现在会过得很幸福吧。然而,一想起每次去狱中探视时佳助那日渐消瘦的脸庞,阿峰便克制住这戳心的懊恼,反过来安慰自己:安藏肯定还在恨我吧,事到如今也没脸见他呀。
那是去年晚秋时分。正午,阿峰茫然地走在电车道上,突然从上方传来一个声音,“不会是阿峰吧”,阿峰抬头便看到了一张笑脸。原来是安藏正趴在梯子上给瓦斯灯点火。“等我一下,就好了。”安藏已年近四十,十多年未见,他的黑发中已然混杂着丝丝白发,但细长清秀的眼睛依然闪烁着往日的光彩。“阿安。”姑娘时对安藏的称呼竟脱口而出,“怎么回事嘛,傻不傻?这个时候点灯。”“不是,点火口有点毛病,我来修一下。”之后两人默契地一同朝过去经常光顾的荞麦面馆走去。饭还没吃完,阿峰就讲完了自己这十几年来的境遇。“你丈夫很快就能出来了,坚持一下,别泄气!若有什么要男人干的活计,我随时可以帮忙。”安藏说话还和从前一样亲切。大概每日早晚两次、跑三里路去点灯熄灯的缘故吧,他宽阔的肩膀和魁梧的身躯丝毫不见老去的痕迹。十六岁那年,因感冒发烧,阿峰曾被这个宽厚的后背背着去看医生……阿峰不由得想起姑娘时代的种种回忆。“对了,这阵子房子漏雨漏得厉害,有空时能帮我修一修吗?”临分别时,阿峰突然对安藏说道。第二天,安藏就带着工具爬上了房顶,之后便隔三岔五地顺道过来,帮阿峰修补这个破旧老屋的角角落落。
“让你丈夫同意离婚,和安藏重修旧好怎么样?”隔壁阿常看到两人后认真地说。
“婶儿呀,别这么说!再有一年多一点佳助就出来了。您这么说,安藏该不好意思来了。”阿峰虽然用爽朗的笑声打消了阿常的念头,可看到似乎没有听到两人对话、在土间
 默不作声磨着刨子的安藏那宽厚的臂膀,阿峰感觉有种笑不出来的积郁堵在胸口。
默不作声磨着刨子的安藏那宽厚的臂膀,阿峰感觉有种笑不出来的积郁堵在胸口。
为了感谢安藏平日里的关照,阿峰今天特意买回了浴衣布料。但在缝制过程中,她觉察到指尖充溢着一种去年为佳助做浴衣时没有的欢欣。她试图用每一针每一线填补上与安藏不曾共度的岁月。望向窗边的梳妆镜,镜中的眼眸熠熠生辉,仿佛融进了针的光芒。安藏常来走动之后,变新的不只是家里的门窗与院子的围墙,如同寡妇般枯萎的肌肤也有了光泽,虽不擦脂粉,但两鬓散发出过去几年不曾有过的油脂香气。
十七年前就已破碎的梦,事到如今,用这根针也难再缝合了吧……阿峰突然叹了口气,用针尖刺了刺镜中的脸庞,接着做活儿。缝着下摆,就在还剩几针就缝完时,阿峰冷不防害怕起自己的心思来。
最后一针缝完时,自己或许已把所有心思都缝进了给安藏做的浴衣里吧。
针尖积聚起残留在薄暮中的所有阳光,闪闪发亮。与那亮光一样,阿峰心里也有个东西在忽明忽暗地闪烁着。
阿峰闭上眼睛,在暮色中一口气缝完了最后几针,将做好的浴衣随便叠了叠,搁到了房间的一角。
胡同里响起千代的木屐声,“我把安叔叔带回来了。”她欢呼着拉开了玻璃拉门。
千代是阿峰与佳助婚后十二年才得来的孩子。随她出生而来的喜悦才过须臾,佳助就进了监狱。千代连父亲的面容都不记得,如今已过五岁。或许是父亲不在身边的缘故,她特别亲近安藏。一到傍晚,就去街角等待安藏从日本桥回来。不过,今天是阿峰说有事,嘱咐千代请安藏顺道来家里的。
“什么事?”
阿峰冲着被千代拉进来的安藏应道:“不是什么重要事情。”将手伸向浴衣,可这时被千代一句“安叔叔送了我一支簪子呢”打断了。定睛一看,在越发浓烈的暮色中,千代的桃瓣型发髻上插着一支淡红色的花状发簪。阿峰怔了一下。一边向安藏道谢,一边拉近煤油灯。真不巧,火柴用完了。
“噢,刚好我忘了熄掉这个,用这个点吧……”
安藏将用于点灯的竹子点火棒隔着拉扇门框伸了过来。四尺左右的细竹筒前端有一个黄铜短管,从那里喷出蓝色的火苗。安藏将火苗对准灯芯,点亮了煤油灯。
千代凑到了点亮的油灯旁。酷似她父亲的白皙皮肤上,发际处隐约投下一朵花的影子。发簪是桃花的形状。阿峰若有所思,转过头去,但安藏的表情与平时无异,他说了句“火柴用完了的话,我就把这个留在这里吧”,便把点火棒倚在了土间的水缸旁,“就这么放着,可以一直燃到明天早上呢。对了,你说有事……”
“噢,房子背面的檐廊地板松动了,我想着你有空时能不能帮我修一下……”
阿峰就这么笑着敷衍了过去。
那晚,正要躺下时,阿峰拿起了千代睡前郑重其事摆在枕边的簪子。一触到簪子的花瓣,那段难忘的往事就在指尖复苏了。
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在与千代差不多的年纪,安藏送给过阿峰一支一模一样的桃花簪子。小时候,大家都说安藏手脚不干净,阿峰年纪虽小,心里却也明白这是安藏偷来的,但她还是特别高兴,用香粉纸包起来,藏在了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她会不时跑去大杂院前边的弁天神像那里,偷偷在水池边照出自己插着簪子的模样。可是,之后不久,安藏被发现偷了房东家的钱,因此被父亲狠狠教训了一顿。阿峰害怕极了,就在那天,将簪子丢进了水池里。后来,安藏听阿峰讲了此事,不由得怒骂阿峰“蠢货”,还用气得发抖的手推倒了阿峰。
阿峰至今都无法忘记安藏当时那又生气又难过的眼神。三十年前的那支桃花簪分毫不差地叠在了这支簪子的上方,不知不觉间,阿峰已对着梳妆镜将簪子插进发间。三十多岁女人的凌乱圆形发髻与纤细稚嫩的花瓣毫不相称,即便如此,在煤油灯的亮光中,不仅能看清那朵簪花的颜色,甚至连气味都浮现出来。阿峰回想起倒映在弁天神水池里的儿时面孔。儿时阿峰的面容,虽然只能在池面那张水镜上映出瞬间,随即就消失在细碎的波光中,但花的颜色永久地浸染上了阿峰心底的涟漪。
循着花簪的颜色,阿峰在镜中的脸上寻找三十年前的自己,结果却看到了千代的脸。因为皮肤白皙,总觉得千代像父亲,但从作为女人来说过于浓密的眉毛和单眼皮的眼睛来看,其实千代原原本本地复制了自己。
或许是因为在千代的脸上突然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安藏在发现同样的簪子后才想要买下来的吧。安藏心中也深藏着经年不变的深情吧。
与闷热天气无关的别样燥热在阿峰的心底扩散,发觉镜中的自己已满面通红时,阿峰不禁摇了摇头,仿佛要拂去镜中的那张面孔。“叮”,簪子落在了榻榻米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宁静的夜晚,那余韵久久回荡在空气中,簪花与花影也鲜明地浮于夜色之上。花瓣上缠着一根阿峰的头发。细细的头发被花的艳丽夺去了色彩,显得格外干枯。
阿峰突然笑着叹了口气,随即钻进蚊帐,熄了油灯。土间里,萤火虫般的小火苗依然亮着。
那是傍晚时安藏留下的点火棒。果真能亮到早上吗?阿峰任由它立在那里。夏日深夜,土间一片漆黑,小小的火苗却始终燃着。
阿峰背叛安藏,嫁给佳助的起因是两百块钱。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作为木材经纪人的阿峰的父亲某日收完货款顺路回了趟家,钱袋子只在门口的窗台上放了一两分钟,竟被人偷走了。那时,两百块是笔巨款。若公开被盗一事,势必会丢掉工作,因此只有大杂院里的邻居知道此事。父亲一筹莫展,便拜访了那阵子不断托人来提亲的双叶町当铺的少东家,求他无论如何帮忙凑些钱,哪怕一半也好。少东家当场给了父亲两百块,但作为交换,提出想娶阿峰为妻。这位少东家就是佳助。父亲苦苦哀求,阿峰只能默默应允。阿峰怀着对安藏的深深歉疚,以卖身般的心态嫁给了佳助。佳助人不坏,只是从结婚那天起,他就喜欢喝完酒了耍酒疯,这也最终导致四年前那次事件的发生。不过佳助能干,待阿峰也好,在一起生活的十三年绝对不能说不幸福。然而,与安藏重逢,从那个自小就熟悉的人身上突然感受到了内心的安宁后,阿峰有时便会疑惑,佳助为何从未给过自己这样的感觉,与佳助在一起的十三年岁月怎会如此空洞。她甚至暗忖,是不是就是那两百块钱将自己与佳助捆绑在了一起。不过,这个念头一起,她就会责怪自己。不,佳助也很好,为了自己,为了这个家,他一直在努力。可无论怎样,阿峰都无法改变自己的想法,比起佳助出狱的日子,她更期待安藏的脚步声,哪怕安藏才几日没来。由于无法按捺住自己这种混账念头,今年她去监狱探视佳助去得更勤了。
给安藏做好浴衣的四天后,阿峰又去了监狱。又过了十天的下午,阿峰抱着某种决心出了门。她牵着千代的手,先去了木场的叔父那里,回来的路上去了安藏家。安藏住在六间狭长陋屋连在一起的大杂院内,他家是其中一间。说是家,其实只是个用木板搭建起的简陋空间。这是她第一次去安藏家。虽然下了决心,可真要去时又犹豫起来。阿峰手里折着一根柳条,蹲在河边眺望远处的白云。“快点去吧。”最后,还是被千代拉扯到了安藏家门前。
“虽然不是什么像样的房子,但也快进来吧!”
安藏正在土间刨刚砍下的木头。阿峰跨过门槛,随即在门口的横框
 上坐了下来。
上坐了下来。
“新木的气味真好闻……”阿峰喃喃自语。
“旧木也有旧木的香味。”安藏应道,“有事?”
“没啥事,刚从叔父那里回来……好像要下雨,就顺路过来了。”
“这种天气,雨下不来吧。”安藏不经意地看了看天空,笑着说。两人随便聊着,房间里眼瞅着就暗了下来。突然,雷声大作,房顶要被劈开一般,雨随即落下。豆大的雨滴落入水沟,仿佛有活物在里面跳跃。
“真的下起来了。夏天的天气最靠不住了。说起这个,我记得阿峰从前很会占卜天气呢。”
“……天气这东西,会占卜也没啥用啊!”
就像小时候占卜天气时那样,阿峰将脚上的一只木屐抛向土间的角落。木屐底朝上落在了地上,磨秃的鞋底暴露在外。轰隆隆的雨声中,阿峰翘起从裙摆下伸出的脚,茫然地望着底朝上的木屐。
“啊,对了。是叫阿信吧,你那去世的老婆。让我给她上炷香吧。”
阿峰上到连着土间的四叠半大的榻榻米上。最里面的三叠上摆着几件家具。说是家具,其实只有一个衣橱和一张矮脚餐桌,再就是有一个木箱。木箱上面放着一个小小的佛龛。佛龛上的油漆涂得有些粗糙,兴许是安藏自己做的。佛龛里摆着一大一小两个骨灰罐和两个牌位。阿峰坐下来,恭敬地双手合十。两个牌位并排立着,如同母子二人的身影。阿峰觉得那仿佛就是如今的自己和千代,曾因两百块钱使安藏陷于不幸,如今,不幸又回到了自己身上。
安藏从木箱里拿出玩具,跟千代一起玩耍起来。木箱里的玩具应该是安藏儿子的遗物。阿峰回到土间,坐到了窗边,心里有些别扭。“来你家避雨真避对了呢!……其实,下不下雨我都会来……因为有话对你说……”阿峰一口气咕哝了好多。对着只是转过头的安藏,她努力维持着一直强撑出的笑脸,毅然决然地说道:“我丈夫……佳助说想和我分开……他有别的女人了,以前我就隐约感觉到了。他说想跟那个女人一起生活……今天我去找叔父商量这事……叔父也说为了千代,最好还是……”
接着,阿峰就道出了事情的始末。那女人她也认识,艺伎出身,现在是一名教唱小曲儿
 的师傅,佳助会与赌徒打架也因那女人而起。那女人有门路,去监狱比她去得还勤,即便是入狱这四年,佳助也在背叛她。有些事,一旦开了头,就像大雨倾注,会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安藏与千代来回击打色玉
的师傅,佳助会与赌徒打架也因那女人而起。那女人有门路,去监狱比她去得还勤,即便是入狱这四年,佳助也在背叛她。有些事,一旦开了头,就像大雨倾注,会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安藏与千代来回击打色玉
 的声音透过雨声传了过来。
的声音透过雨声传了过来。
“佳助也说,如果我有合适的人,就同那人在一起吧……这样他也就放心了……可是……会有合适的人吗?”
阿峰沉默了下来,望着外面倾盆而下的暴雨。窗外,牵牛花的叶子被细细密密的雨脚打得七零八落。
千代投出的色玉偏了方向,滚到了阿峰脚下。阿峰用脚掷了回去,在千代接住之前,安藏伸手从榻榻米上方截住了。
“千代说,想要一个安叔叔这样的爸爸……”
安藏默不作声,倒是千代“嗯”地点了点头。插在发间的花簪摇动,发出几乎被雨声遮住的细微响动。
“那支花簪……阿安你还记得吧。很久之前的事了呢。我告诉你我把它丢进了池子里,你很生气……佳助虽然对我也很好,但我从没见他那样气恼过。”
阿峰说着说着,泪水便涌进了眼眶。这十几年,那支沉入池底的簪子,其实也沉潜在她与佳助的生活中。之所以经受住了丈夫坐牢的打击,就是因为心底永远珍藏着安藏送的那朵花吧……就像被雨声催促着似的,阿峰吐出了所有心里话,可安藏一直沉默地背对着她。或许是生气了吧,无论他发火还是笑话自己,都无所谓了,阿峰心想。
“就像这雨一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安藏将一只竹蜻蜓掷向空中,当作对阿峰的回应。竹蜻蜓搅动着淡淡的暮色,飞向房间深处,千代欢呼着追了过去。
“天黑了,点上灯吧。”刚刚站起身的安藏又坐了下来,将身体转向阿峰,冷不防说道,“小时候,有个‘昼行灯’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嗯。大白天提着灯笼到处走的那个人。”
那个衣着随意、脸涂得煞白、提着灯笼在大路上溜达的男人。可能脑子有问题吧,孩子们总凑到一起嘲笑他,说他那张涂成白色的脸也是灯笼,于是喊他“昼行灯”。
“……那个男人现在怎么样了?”
“死了。十年前被马车轧死了。当时也提着灯笼……我还是小孩时他就那样,二十年呀,每天都在大白天提着灯笼出来……不过,可能那就是他的生活吧。我最近常想,为什么小时候总笑他呢?”
安藏咧开嘴笑了笑,一声不响地从木箱里拿出一个竹筒望远镜,贴在眼部,扭过身体,将望远镜朝向阿峰的脸。隔着竹筒口的玻璃,阿峰看到安藏的眼睛像锥子一样刺向自己。与其说尴尬,其实阿峰更觉害怕。她垂下眼帘,瞅着榻榻米,问安藏:“看什么呢?”
“用望远镜看近处,什么也看不到啊……”
安藏放下竹筒的同时又转过身去,再次背对着阿峰。
“刚刚都是你的心里话吧。那我也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吧。十八岁那年,你背叛我,选择了现在的丈夫,不是因为两百块钱,而是看上了对方的家世。因为做了当铺家的太太,就可以从苦日子里逃出去。你走后,我发了疯似的喝酒。你听说了吧,听说后有过一点心疼吗?我倒是听说你和丈夫恩爱得很呢。”
安藏的双肩一直在抖动。听着他近乎悲愤的声音,阿峰猛然想起小时候安藏推倒自己时的那双眼睛。
“如今,因为丈夫入狱了,你就说要将过去全部抹去。你根本不懂男人。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跟别的男人过了十几年,身体比妓女还脏。混账!你把我当什么了?”安藏低声怒吼。然而,那声音随即又像紧绷的丝线突然断裂了似的,瞬间变成一句喃喃细语,“我可以。”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楚。
阿峰惊愕地转过头,看到安藏佝着背坐在那里,仿佛被自己的愤怒击垮了。
“……可以……是指……”
“……你刚刚说的……你丈夫说那样也可以的话,我可以。”声音从垂下的脖颈与肩膀的缝隙间传来,听上去好似从纸气球的裂缝中漏出的空气。安藏那突然佝下的背真的就像一只破裂的纸气球。
“阿安——”
阿峰终于叫了一声。雨声依旧。千代回到土间,一次又一次地放飞竹蜻蜓,兴致盎然。阿峰的手支在榻榻米上,突然,手边落下一颗雨滴。一颗、两颗……雨滴一颗接着一颗,像墨汁一般滴落,濡湿了阿峰的手,但阿峰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安藏的背。这个过去曾背着自己奔向医生的脊背,垂下来时,已能明显看得出年近四十,后颈的短发间也掺进了白发。这一年,在安藏身上看到的那一如往昔的活力与朝气,也是由深埋内心十七年的怨恨与辛酸而生的倔强吧。他坚持着那份倔强,拼命坚持着。“我可以”,但这句心里话终究还是从倔强的裂缝间漏了出来。阿峰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了。自己的自私令安藏生气,安藏生气,所以背对着自己,最后却还是点头说“我可以”——
竹蜻蜓碰到了安藏的肩膀。他把跑到身边的千代抱在膝上。“有件事我一直想问问你呢。”说着他回过头来。
“你爹的两百块钱被盗之后,阿峰,你也怀疑是我吗?”
“怎么啦?现在又提起这事……”
十七年前,那笔改变阿峰人生的钱被盗之后,其实大杂院的人都觉得安藏可疑。钱恰恰就在父亲离开的那一会儿被偷走了,肯定是大杂院的人干的,这对小时候就手脚不干净的安藏很是不利。当时安藏虽已成年,可就在五六年前,还被怀疑偷了木屐店的桐木木屐,差点惊动警察。大家都没明说,但私下都认为是他干的。老实说,听说钱被偷后,阿峰首先想到的也是安藏。但是,即便真是安藏偷的,若他知道阿峰将因此不得不嫁给别人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把钱还回来的。阿峰不认为是安藏偷的。那阵子,阿峰只是因为背叛了安藏,心里难受,故意躲着安藏而已。结果两人几乎没再说什么,阿峰就嫁去了双叶町。安藏大概因此误解了阿峰,以为阿峰的冷淡是怀疑自己偷了钱。出嫁的前一日,阿峰去邻居家告别,看到了在井边洗脚的安藏,他倔强地挺着脊背,一如今日。第二天,阿峰身着盛装,登上前来迎亲的车子时,没有再看到安藏的身影。
“怎么会怀疑你呢?我最了解你啊,你也知道,我是不会怀疑你的。怎么现在又提起这个?”
听了阿峰的话,安藏过了一会儿才应道:“也没啥。”接着对千代说:“明晚弁天神那儿有庙会,咱们一起去,好不好?”
千代的笑声与不知何时缓和下来的雨声交织在了一起。两三只麻雀飞来,在巷子里嬉闹,羽毛上闪着晶莹的露珠。
秋风起,大杂院角落的芒草结出白穗时,安藏每日点完灯就会顺路过来一起吃晚饭了。阿峰也是,一有空就去安藏家,像女主人一样洗洗擦擦,照料安藏的生活。虽然对大杂院的邻居什么也没说,但似乎有人察觉到了什么,讥讽阿峰最近变年轻了,看上去像是三十岁都不到……饭菜虽然粗陋,但三人围着矮脚餐桌吃饭的场景,有时会让阿峰陷入一种幸福的错觉,仿佛很久之前三人就是一家。阿峰请求安藏等来年春天佳助出狱后再开始一起生活,安藏也答应了。安藏想去见见佳助,但阿峰说:“我已经跟佳助说好了,佳助也很高兴,说这样他也就放心了,你就别再担心什么了。”
家里不断传出千代的笑声。
然而,九月过半的某一天,千代抽泣着回了家,后面还跟着一位年过五十,自称在日本桥经营女性日用小百货的男人。男人说千代头上的簪子是七月份店里丢的,自己今天来拜祭这附近的弁天神,碰巧看到了在神社院子里玩的千代。他说那簪子是专门拜托京都的手艺人做的,同样的簪子不会有第二支,那语气俨然就是怀疑千代偷了东西。阿峰一下子想到了什么,于是付了六十钱的簪子钱,把男人打发走了。阿峰哄了哄抽噎的千代,嘱咐道:“这事别对安叔叔讲哦。”此时,阿峰自然想到了安藏。
说是手脚不干净,但也只是孩子的恶作剧吧,直到现在阿峰还那么觉得。可都到了这个年纪,还没彻底改掉,难道是天生的毛病吗?不,不是那样的,那支桃花簪并不是给千代的,而是买给千代脸上映出的小时候的自己吧,阿峰自作多情地想。可如今的安藏没道理拿不出六十钱,为何还这么不舍得?一想到这里,阿峰感觉自己窥视到了安藏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心里不免有些难过。也可能只是店主搞错了吧。阿峰差点就想追问那晚也来家里的安藏了,可看到他高兴地拨弄千代发簪的样子,却怎么都开不了口。阿峰决定忘掉这件事,什么也不问了。绝不能因为这么件小事,让好不容易与安藏重新建立起来的关系再变得别扭起来。
九月底到了,就在阿峰快要忘掉这件事的时候,台风来了。白天,天气酷热,让人无法相信前些天刮的是秋风。到了晚上,居然狂风大作。夜越深,风越猛,后院的围墙在暴风雨中轰然倒塌。阿峰紧紧抱着吓坏了的千代,切身体会到只有女人的家多么脆弱无依。就在这时,全身湿透的安藏来了。他太担心母女二人,顶着暴风雨来了。只是看到那张脸,阿峰就感觉暴风雨声变柔和了。安藏立刻往雨窗上钉了钉子,忙活了好久。佳助从未给过自己这种体贴与踏实的感觉啊,阿峰再次感受到安藏待自己的好。
安藏一夜没合眼,风停雨霁后,一早就回去了。台风彻底吹走了夏日的余热,万里无云,碧空如洗,秋天来了。午后,阿峰去木场安藏家收拾。不出所料,安藏家门上的玻璃碎了一地,榻榻米也被雨水浸透了,一片狼藉。他竟然置自己家于不顾,去守护她们母女。可他人这是去哪儿了呀?也不管自己家里乱成这个样子。阿峰一边寻思,一边着手从倒下的佛龛开始收拾。想要将撒出的香灰放回香炉里时,手滑了,将大小两个骨灰陶罐中大的那个打落在地。罐子似乎本来就有裂痕,这下摔成了两半。里面装的应该是安藏去世的老婆吧,骨头散落在榻榻米上。阿峰感觉自己闯祸了,赶紧捡起骨头,包进纸里放了回去,突然又注意到从骨灰罐里落到榻榻米上的铜板和纸币。铜板上锈迹斑斑,纸币上也有挺多污渍,看上去特别旧。这是什么钱?阿峰呆呆地望了一会儿,随即用颤抖的手开始数,纸币与铜板加在一起刚好两百块。
那一刻,阿峰决定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把钱扒到一起。她甚至忘记骨灰罐被打破了。可就在此时,脚步声传入耳中。回头一看,安藏站在门口。
“你来啦。瓦斯灯被吹得东倒西歪,刚去看了看……”
安藏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他看到了从阿峰手中滑落的纸币。阿峰的脸比安藏还要惨白,她咕哝了一句:“这……”原本想说“这也没什么”,可后面的话却没能说出口。阿峰跑下土间,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穿上木屐、怎么跑回了家里。只记得走过安藏旁边时,她本想冲他笑一下。她一口气跑回家,甩掉木屐,一坐到榻榻米上就用双手捂住了脸。仿佛自己在偷东西时被抓了个正着似的,羞愧难当,面颊滚烫。何止羞愧,连一路狂奔引起的急切喘息此时也化成了愤怒与悔恨。
纸币和铜板都很旧,肯定是十七年前被偷走的那两百块钱。记得父亲说过,纸币和铜板各一半,这点也对得上啊。首先,安藏生活穷困,若不偷窃,不可能攒得出两百块钱。原以为是自己背叛了他,没想到十七年来一直被辜负的是自己。阿峰想起那个夏日傍晚安藏对自己的痛斥,两百块钱明明是他偷的,他明明知道自己因此将不得不嫁给佳助,竟然还能说出那种狠话来。嫁进把自己看成价值两百块钱抵押品的当铺之家,阿峰当初也恨过佳助,现在想想,还是佳助比较诚实。可佳助也不会回到自己身边了,自己的不幸实际上都因安藏而起……愤怒在阿峰胸中上下翻滚,难以平息。此时,千代刚好回来,看到千代发间摇动的花簪,阿峰忍不住伸手拔出,用力砸向了土间的一角。千代慌忙捡起,不知所措地望着母亲,仿佛要从母亲愤怒的眼神中保护那支簪子一般,将它紧紧抱在胸前。阿峰给了千代十文钱,交代道:“不许再戴这支簪子了,用这钱再买一支喜欢的吧。”
“可是,安叔叔……”
“安叔叔暂时不会来了。那支簪子也得还给安叔叔。”
说完,阿峰想起千代的小伙伴里有一个叫源太的孩子很会爬树。
“让小源把那支簪子系到瓦斯灯的高处吧,这样安叔叔看到就会自己处理了。”
阿峰从一件紫色的旧衬衣上撕下衬领,递给了千代。千代依旧紧紧抱着发簪,但似乎察觉到母亲的神情非同寻常,便默默地点了点头,向上瞟着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对母亲的不满。
如阿峰所料,安藏不再来了。阿峰本想将簪子同那日傍晚受到的斥责都还给安藏。安藏肯定发现了系在瓦斯灯上的花簪,由此明白了自己的心思吧,阿峰暗自思忖。半个月过后,阿峰感到自己的怒气已被凉爽的秋风吹散了。不,就像暴风雨一样,愤怒仅仅在胸中肆虐了一晚,第二天阿峰就不忍心责怪安藏了。自己才是被辜负的一方啊,尽管想到这个,阿峰胸中还会燃起一丝余怨,但十七年来,安藏内心的愧疚与悔恨肯定超过了自己。老毛病没忍住,偷了那两百块钱,竟然引起如此大的麻烦,想要承认的时候为时已晚。安藏没那么差劲,两百块钱之所以一分未动地放到了今天,是因为他一直都觉得愧对自己。就像两百块钱一分未动一样,十七年来,当年偷钱留下的愧疚与悔恨,在安藏心中也从未减轻过一分一毫。安藏就是这样的人哪——
然而,过去的事情不会因此都随风而去。是啊,或许安藏说声对不起,自己就不会在意了,但安藏可能无法如往常一样,再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已经知道真相的自己面前了吧。阿峰心里清楚,安藏就是这样的男人哪。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阿峰的记忆里,当时从骨灰罐里撒出的安藏老婆的骨头,比那时看到的两百块钱还要清晰。阿峰甚至在想,是安藏死去的老婆不愿丈夫与自己重修旧好,才让自己看到了那两百块钱吧,她或许希望借此断了两人的姻缘吧。到了傍晚,阿峰尽量不让千代出门,自己也开始避免在早晨和晚上外出了。
安藏突然不来了,大杂院里的邻居,尤其是阿常,都很纳闷。十月底时,阿常先说了句“我一直觉得发生了什么,果然是”,接着告诉阿峰,安藏最近要将一位点灯夫同事迟迟未嫁的妹妹娶进门。阿峰心里一阵难过,但随即就笑了。“阿安不喜欢别的男人碰过的女人呢。”
“我原以为刀会回到原来的鞘中呢……你俩那么情投意合……”
阿峰笑了。“婶儿,刀生了锈,就回不去原来的鞘了。”
阿常颇为善解人意地说:“听说瓦斯灯已经不时兴了,到处都在拆。安藏都那个岁数了,接下来还能有多大出息呢?除了做木工之外也没啥能干的了吧。想想将来,跟了安藏也不一定幸福……走着瞧吧,以你的相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人家做填房。”阿常安慰着阿峰,她以为是安藏厌烦了阿峰。千代年纪虽小,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最近也不怎么提起安藏了。可就在那天,千代一回到家就说:“安叔叔还没发现那支簪子哦。”那晚,夜深人静时,阿峰来到了大路的拐角处。仰望天空,不见月亮,夜色茫茫,唯有阵阵秋风吹过。瓦斯灯发出的光飘浮在深秋寂静的夜空中。系在灯下的花簪,只有花朵在亮光中闪烁,远远就能看到那淡红色的美丽光芒。阿峰用簪子向安藏宣告了两人的分别,然而,看着系在灯下、浮在夜中的那朵花,阿峰觉得即使现在缘分已尽,但幼时的两人依旧紧紧依偎在遥远的记忆中。千代不说,阿峰也能猜到簪子还系在那里,安藏也是看到后任由它系在那儿的吧。今天点火时,安藏也同自己一样,发现了那朵花的美丽吧。瓦斯灯的宁静沁入阿峰心底,听闻安藏即将再婚后就一直起伏不定的心绪终于因此平静了下来。就这样,她和安藏真的结束了。与十七年前一样,两人默默斩断了连接彼此的情缘。阿峰怀念着那快乐的两个月,将它收进了早已远去的童年回忆里,独自兀立在夜色中,久久凝视着闪亮的瓦斯灯。
腊月到了,接近年关时,阿峰嫁到神田和服批发店做填房的事匆忙说定了。对方年近五十,二十年前妻子还未生养就病故了,之后一直单身一人。在市善他不时见到阿峰,今年春天起特别关注起来,秋天快结束时托市善的老板正式提了亲。佳助的事情对方全知道,还说尽管千代身上流着杀人犯的血,但孩子终究无罪,很愿意阿峰带千代一起过去。阿峰也因此下定了决心。那人的确很好,如今已经把千代当成自己的孩子疼爱了,千代也格外喜欢这个新父亲。和服店铺面虽不太大,但规模不小,光工人就有八个。“看,我没说错吧。”阿常很为阿峰高兴,好似自己遇了好事。阿常说安藏也是一过年就会将填房娶到家。夏天约好结为夫妇的两个人,才过了一个秋天,就各奔东西了,阿峰深深感慨缘分的无常。缘分这东西,真是既有孽缘,也有善缘哪。不管安藏出于何种原因如此匆忙地决定再婚,跟那个女人生活应该会比跟自己在一起幸福吧。
婚事正式定下来的那天,阿峰亲手将系在瓦斯灯上、风吹雨淋了三个月的簪子取下来,丢进了弁天神前的水池里。对安藏的回忆,在五岁那年的夏天与这个夏天,相隔三十年,与两个花型相同的簪子一起沉进了池底。这个夏天发生的事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虽然怀念,但并无留恋。不可思议。
对方依从阿峰的意思,将婚期定在了来年春天。和服批发店的老板丧偶二十年未娶,这次结婚高兴得如同初婚一般,送的彩礼很有排场,安藏不来后一度冷清的家里再度热闹起来。与这寒酸之家毫不相称的结婚用品都系着红白相间的花纸绳,阔气地摆在房里。
阿峰本以为和安藏不会再见了,没想到还有三天就到除夕的时候,从外面一回来就听阿常说安藏来过,留下了这个,说着递来一个鲨鱼图案的方绸巾包裹。方绸巾里包着一个钱袋,里面塞着些纸币和铜板,正是九月末见过的那两百块钱。安藏肯定是在听说阿峰要成亲的事后,也想为这十七年做个了结,才来归还这个的。可这钱对阿峰早已没有用处了。傍晚,阿峰让千代去街角还给了安藏。千代回来后说,安藏接过包裹后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晌午,阿峰正在点炭火时,安藏又拿着钱来了。
三个月未见的安藏穿着短褂,“我来给前边的瓦斯灯点火,顺便……”与从前一模一样的声音。说完悄悄将昨日那个方绸巾包裹放在了门槛旁。
刚刚透过窗棂看到他在巷子一角支起梯子和点火棒的身影时,阿峰心里还怦怦直跳,再听到这一如往昔的声音,三个月来的别扭顿时化为了乌有。“不用了,已经……”阿峰平静地随口应道,将那个包裹推回给站在土间的安藏,对默不作声的安藏又说了句,“真的已经不用了。”逼仄的房间里摆放着结婚聘礼,和服批发店老板特意为母女俩准备的同一花色的新年礼服也醒目地挂在衣架上。安藏瞟了一眼这些东西,很快收回了目光。他看着阿峰,再次默默地将包裹推至阿峰膝前。“真的不用了……一切都过去了。那会儿我是很吃惊、很生气,不过现在已经不觉得这钱有什么重要的了。想来这次成婚也像是托这钱的福呢。听说你也要成亲了,得添置东西吧,能把这钱派上用场就好了。我要嫁到日子比较宽裕的地方去,用不着这钱了。”阿峰又把包裹推回给安藏,包裹一碰到安藏的手,立刻又被推了回来。阿峰发现安藏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不由得声音严厉地说了一句:“我不会收下的。”
“阿峰,这是给你的钱啊。”安藏终于开口了。
“过去可能是吧,就因为这个钱,我把身体卖给了佳助……不过,现在看来,和佳助的生活也绝不算不幸福啊……”阿峰还没说完,安藏就摇着头打断了她。
“不对,你收不收下都和我没关系,我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推你,可心里面,我就是想把这个钱甩到你面前。你一定认为这个钱是我从你家偷的,但我从来没有动过人家的钱。你可能觉得我这么没出息,一辈子也攒不出两百块钱,但这就是我在你嫁出去后的六年里攒下来的。我不仅点灯,还做木工,做苦力,拼命地干活。你因为两百块钱出卖了身体,不,不仅身体,你连心都卖给了别人,如果为了两百块钱,你连心都能卖掉的话,我想我也得存够这么多钱,然后把它砸在你面前……我老婆快死时,如果能让她吃些贵一点的药,或许能得救,可即便那时,我也没动这笔钱。在我眼里,这笔钱比我老婆的命还重要……现在终于可以了。我一定要把这笔钱甩到你面前。”安藏激动地说着,双手却平静地将包裹推向了阿峰。方绸巾包裹只是稍稍碰了一下膝盖,阿峰却感觉痛得像被利刃划过。
“阿安,这么重要的事,你为什么不早说呢……”阿峰声音颤抖着说。
“你看到这两百块钱时就怀疑我了,是不是?十七年前,你家的钱被盗时,你肯定也怀疑过我。对我来说,被你怀疑,和真的偷钱没有什么不同。我小时候确实偷过东西,可长大成人后一次都没有偷过。”
“可是……”
阿峰摇着头,把脸转向火盆。
“阿安,之前的那支簪子,不也是从日本桥的女性百货店里偷来的嘛。我知道的。那个店老板来过家里……”
“噢,你知道了……可你知道了为什么不高兴呢?从前……小时候,你那么喜欢我送的簪子。”
安藏的声音一直很平静,说完这句话,没等阿峰抬起头就离开了,只留下玻璃门传来的吱嘎声。阿峰不停地摇着头,脸被炭火烤得通红。即便听安藏讲了这十七年来的心里话,阿峰也还是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两百块钱的真正含义。什么都搞不懂了。现在唯一明白的就是,十七年前辜负他人的还是自己,那个曾经被自己辜负过一次的男人,这次又被自己辜负了,而且是以一种无可挽回的方式。迟了,即便知道了安藏的真心,也已经迟了——本以为自己了解安藏的一切,甚至超过了兄妹与夫妻。这十七年间,自己一直在用望远镜凝视着遥远回忆中的安藏,而再次回到自己身边的如今的安藏,自己恐怕什么都没看到。如果告诉他,自己把这次的簪子也丢进了池子里,他还会把自己推倒吗?阿峰一动不动地呆坐着,玻璃门再次传来吱嘎声,是安藏回来了吧,阿峰不由得站了起来,随即看到哭丧着脸的千代。“安叔叔突然变得好奇怪啊!”
阿峰急忙趿拉上木屐跑到了大路上,茫然四顾。后天就是除夕了,街上行人比平时多出许多。隔着人群,阿峰看到就在几处房子的前方,安藏将点火棒高高伸向瓦斯灯的背影。
行人都站住了,诧异地看着这一幕。
安藏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将前方的几个瓦斯灯都点亮了。看到这里,阿峰终于明白了安藏在做什么。安藏在大白天点亮了瓦斯灯,一个接一个地点亮了。他奔跑在瓦斯灯灯柱下,用点火棒点着火,仿佛用针线将瓦斯灯连成了一串。动作敏捷得令人惊叹,从背影却可以清晰地看出他老去的痕迹。
阿峰抬头仰望街角处那曾经系过簪子的瓦斯灯,却看不出它是否也被点亮了,只有冬日的和煦阳光在玻璃灯罩上闪动着。其他的瓦斯灯也一样,在被安藏挨个点亮后,能看到的只有映照着岁末灰白色天空的玻璃灯罩。
阿峰闭上了双眼。在眼前的黑暗中看到了梦幻中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