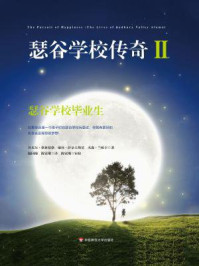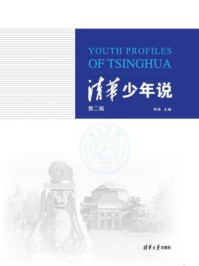我在着手写《追忆乌攸先生》这篇小说时,第一次意识到了生命、记忆以及写作所构成的那种神秘的关系。当时是在一辆拥挤而嘈杂的火车上,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汗渍和腐沤鱼虾的腥味,而窗外则是阳光明媚,青山如黛。树林、河流、田野交替掠过。在长达十四个小时的旅途中,我在日记本上写完了这个故事,自始至终,我沉浸在一种隐隐的激动之中,几乎忘掉了时间。
这篇小说的得失也许无关紧要,写作经历却显得不同寻常,因为我似乎已经隐约知道了应当如何通过写作为记忆中的某些事物命名,而写作则同时向我显露了它的奥秘和全部的意义。美好的心境来源于这样一种庆幸之感:在写作这篇作品之前,我的记忆一直在黑暗中沉睡;现在,它终于向我敞露了一线缝隙,记忆中的事物犹如一个个早已被遗忘的梦境突然呈现出来,使我感觉到了它的神秘、丰富、浩瀚无边。而语言正是在这样一种浩瀚的黑暗中开辟着道路,探测着它的边界,在它无限敞开的腹地设置路标。
记忆中的一条河流并非仅仅是一条河流。如果我们曾经为它感到激动,是因为我们的触目所见激活了我们的全部情感。我们之所以一遍遍地回忆起它的河床的颜色,两岸的树木和花草,它的形状、流速和气息,是因为我们试图复现出特定情境中的个人情感,并通过文字将它固定下来,仅仅通过地理学的方法去描绘记忆中的自然是难以想象的。我以为威廉·福克纳笔下的自然迷人而饶有韵致,因为他给记忆中的事物赋予了灵性和生命。
记忆中的一个午后也并非是统计学上的两个小时,假如我们恰好将这两个小时用来静卧遐思,那么是否意味着在这两个小时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呢?在我看来,一切都发生过了。我们常常对于那些记忆中的戏剧性事件给予过多的关注,并给予这些事件以合乎现存经验和概念的解释,而对更为广袤的记忆空间视而不见,对我来说,午后的两个小时也许意味着天空滚过的雷声,植物和树木的清香,意味着无边无际的寂寞,隐伏的不安或欲望,意味着万物的生长和寂灭,雪片或杏花无声无息地飘落……这是因为记忆中的事物因其隐喻的性质总是与其他记忆中的片段紧紧地牵扯在一起,它有着自身的逻辑与生命。
每一个人一生中所经历的事件难以数计,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经过记忆力的筛选被保存了下来,而大部分都被人遗忘了。这种遗忘有时出于自愿或习惯,有时则出于强迫——比如某件事情令人震惊或恐惧的程度超出了意志和想象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不管这种遗忘的形式如何,被遗忘的内容并非根本不存在,其实,它一直积存在我们的无意识之中,有时它通过梦的形式返回我们的意识,而在更多的情形之中,它往往受到我们正在经历的情境的触发,突然浮现出来,令人猝不及防。
因此,我以为遗忘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记忆。它不期而至,又转瞬即逝。
记忆中的事物一旦被意识唤醒,我们也许能够复述它的全部过程,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复述它的情境,情境之于事件的过程并非果核之于它的外壳——我们只要剥掉了它的外壳就能发现其核心。它更像一只葱头,我们剥到最后往往一无所有。普鲁斯特曾经告诉过我们,玛德兰点心所引发的对往事的妙不可言的感觉只保留了短短的一瞬,随着点心的味道渐渐迟钝,情境本身也一去不返。
许多年前的一天黄昏,我在听肖邦的《即兴幻想曲》时,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我隐约记起了幼年时代的一段往事。在过去,我的意识对它一无所知,仿佛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生过。当时,我和父母在外婆家做客。我的母亲在竹园的一张藤椅上熟睡,我在椅子边一直试图将她弄醒,但她始终安睡不动,后来我就哭了起来,惊动了我的父亲,他从房内跑出来,看了我半天,又转身离开了。在回忆这段往事的过程中,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午后的沉寂,竹子的芳香以及竹篱外的河道上敞亮的阳光,那是一种在忧郁中夹杂着惬意的感觉。事后,当我再次聆听肖邦的这首曲子,感觉却不再重现。后来,我在《背景》和《边缘》这两部作品中试图解释这种感觉,但仅仅只是一种解释而已。
我以为回忆是构成写作与记忆之间关系的中介,尽管它并不是写作的最终目的。回忆不是一种逻辑推理或归纳,它仅仅是一种直觉。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回忆往事之时,回忆自身带有强烈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是没有逻辑的,同时,我们并不总是立即就能发现记忆中事物的意义,它的意义在大部分场合中是暧昧不明的,回忆的内容和方式取决于自我的现时状态。因此,回忆往往是即兴的、跳跃的,而写作活动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即兴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记忆的内容互相交错混杂,回忆和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想象和拼合。
既然记忆的内容、回忆的方式和自我在写作中的现时状态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如何通过语言的组合去解释和发现这种联系就成了写作的关键。试图通过语言去再现记忆中的情境将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一方面,由于这种情境转瞬即逝,我们只能通过语言去模拟这种情境;另一方面,由于情境的产生取决于现时的状态与选择,写作活动必然意味着以下三种状态的互相通联:“现时的自我,保留其本质的对象物,鼓励我们再度寻求其本质的未来的对象物”(见普鲁斯特《重现的时光》)。
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小说不论其形式或效果,总是表现性的。小说艺术的最根本的魅力所在,乃是通过语言激活我们记忆和想象的巨大力量。
有一年,我整整一个夏天都被记忆中的两组画面所缠绕:一支漂泊在河道中的妓女船队(这个传说使我幼年时在长江中航行的许多夜晚历历在目);我和祖父去距离村庄很远的一个地方看望一个隐居的老人。
我在写作《青黄》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两组画面存在着怎样的联系,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去描述它们。后来,我这样设想:这两组画面至少在一点上有着相似的性质,那就是一种慵懒的寂寞。这种寂寞之感是我所熟悉的,当我想起轮船在幽蓝的月光下发出沉闷的叫声,当流水汩汩滑过船舷,或者在去探访老人的途中,我们在四月的田野中差一点迷了路时,这种感觉就会在心头涌现。尽管这种感情极其强烈,甚至贯穿写作的始终,但完成后的《青黄》似乎与上述两组画面并无太大的关联。这不禁使我感觉到,记忆中的某种情境有时仅仅诱发出写作的冲动,为写作的过程带来了一种心境,为作品规定了一种调性。这种最初的记忆在写作过程中很快会与其他的记忆片段融合在一处,最终为一种更淳厚、庞大的背景所吞没,而写作的最初契机反而模糊不清了。
试图清晰地说明记忆本身与我们的情感、欲望、生命状态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正是这种未明的、晦暗的联系为小说的写作开辟了可能的空间。换句话说,写作只不过是对个体生命与存在状态之间关系的象征性解释。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仿佛在一片幽暗的树林中摸索着道路,而伟大的作品总是将读者带向一个似曾相识的陌生境地。
我以为一个作家从事写作的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他有话要说。大凡有才能的作家都有着良好的记忆力,这种记忆力是以警觉和敏锐为前提的。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试图分辨在他身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对于他个人的生存究竟意味着什么。海明威终其一生只探讨了一种联系,他的所有作品也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和联系并非到了《老人与海》才最终完成,在他早期的作品《在密执安北部》中,它早已清晰地显露了出来,前者是对后者的进一步深化,但同时也是对后者的一种遮蔽。因此,尽管很多人将写作的目的规定为对自身生命的了解或解释,但这种解释往往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的魅力正在于它的相对性。情境不可复制,写作也不能从科学与知识的可操作性那里得到帮助。如果仅仅从修辞学的意义上来说,写作的确是一种略带冒险性的游戏活动。
在写作过程中,记忆的片段与其说是时间性的延续,不如说是空间性的拼合。二十世纪以来,很多作家尝试通过画面或空间性的场景的拼合所造成的流动性来取代传统的线性的叙事模式,那是因为他们存有这样一条重要理由:新的叙事方式更能模拟记忆的活动方式,从而更能造成感觉上的真实性。乔伊斯笔下的主人公布鲁姆因为看到一只多汁的水果从而联想到女人的乳房,进而产生妻子不忠的幻觉,从记忆活动的方式来看是可信的,因此,作者叙述中上述场景的切换亦在情理之中。普鲁斯特通过钟声意识到中午的康勃雷,通过供暖装置所发出的哼哼声意识到清早的堂西埃尔,是因为他确信,除了感觉与记忆的这种联想关系之外,不存在其他的关系。
许多人对于这种“感觉上的真实”似乎一直颇有微词,但我不知道除了这种真实之外还存在其他什么真实。
这里仅牵涉到了对于历史及其真实性的理解。我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确实一度对历史怀有很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并非来自社会学或考古学意义上的追根寻源,重要的是,我对历史的兴趣仅仅在于它的连续性或权威性突然呈现的断裂,这种断裂彻底粉碎了历史的神话,当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仿佛发现,所谓的历史并不是作为知识和理性的一成不变的背景而存在,说到底,它只不过是一堆任人宰割的记忆的残片而已。
如果说,一个作者敢于声称他所描述的历史就是“信史”,那么他不是出于虚妄就是出于无知。即便我们对历史的常识一无所知,我们对于历史本身亦存有记忆。或者说,历史的残片只有通过个人的意识活动——在写作上,它通常是一种直觉,才会显示出它全部的意义。因此,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同样在描述历史,其区别在于,历史学家依靠的是资料,而小说家则依靠个人的记忆力以及直觉式的洞察力。小说的作者更关注民间记忆,更关注个人在历史残片中的全部情感活动,更关注这种活动的可能性。
比如说,当一位法国当代作家描述到一位主人公的妻子被当地的权贵侮辱一节时,他冷静地表现了这个女人在这种境遇中的全部情感:一方面,她对事件本身感到羞辱和仇恨,同时她又在享受着身体方面的快感,如果我们将这种快感视为一种肉体的背叛的话,那么米兰·昆德拉笔下特丽莎的被诱奸则与其极为相似。
用歌德的话来说,人既是心灵的,又是肉体的。既是恶魔,又是天使。小说家介入历史,更重视个体生命以及记忆的复杂内容,他没有任何理由仅仅出于某种政治、时尚或道德的约束对这种内容进行简化。
最后,我想说明的一点是,我不认为我个人对自己的记忆有很深的了解,同时我也不认为弗洛伊德及现代心理学对包括记忆在内的人类意识的研究一定具有令人信服的基础。我写作,尝试解释个人的生命、感觉、记忆之间的种种关系,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也许,我们只不过是记忆的奴隶或影子罢了。
1994年5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