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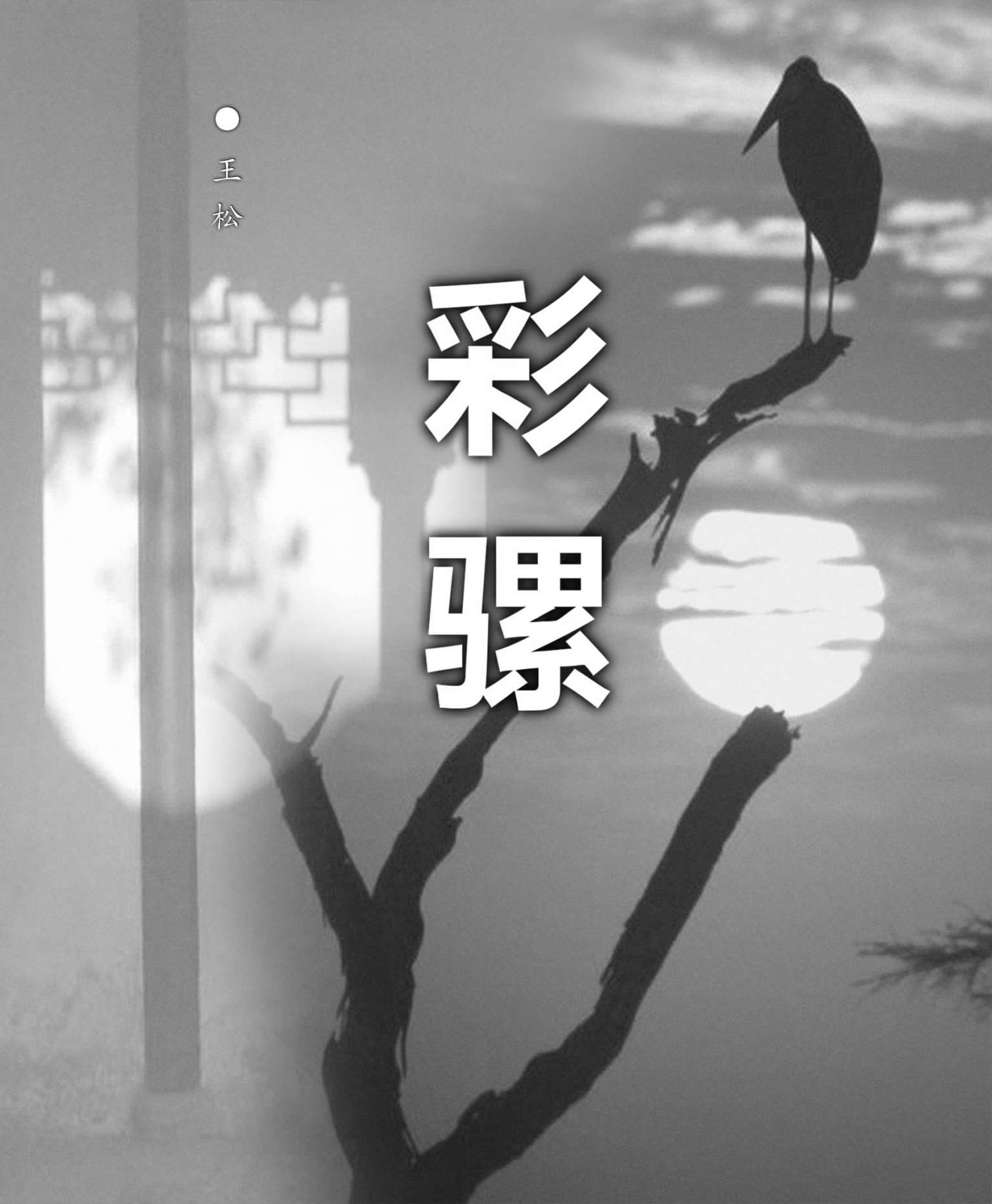

骡子第一次见兰大姑,是刚回南市的时候。
骡子对南市很熟悉。当年家住在北门外,常来这边闲逛。那时这一带还叫城南洼,刚开始热闹,往西不远有一片很大的湖面。湖是文人的说法,天津街上的人叫坑,水坑,但这一片比水坑大,比大水坑还大,中间还有一座小岛,有人取名叫“燕儿翅”,大概是说这小岛的形状像个小燕儿的翅膀。赶上阴雨,一眼望去烟波浩渺,湖心的燕儿翅漂浮着,若隐若现。常有文人相约,带了酒茶和纸笔墨砚,划着小船去岛上游玩。
骡子这次回来,这地方已变得快认不出了。西面的这片湖水还在,只是已经小得真成了水坑。东面却已是人头攒动,打把式卖艺的、卖大力丸的、唱玩意儿拉洋片的、顶坛子耍狗熊的。骡子这时才知道,这地方现在已叫“三不管”,天津人说话爱走小辙儿,一说就说成了“三不管儿”。但究竟是哪“三不管”,这里的人各有各的说法儿。曾有人在报屁股上写文章,专门说这“三不管”的来历,这一带是“中国地”,但跟前守着日租界,旁边又是法租界,本应属中国的官署管,而其实并不管,日本人和法国人更不管,是谓“三不管”。
摆茶摊儿的徐傻子乐着说,三不三的是瞎扯,干脆说吧,就是没人管。
骡子后来才知道,兰大姑的生药铺就在街拐角,把着白家胡同的西南口儿。
这次回来,毕竟已在外面闯荡这几年,也就明白,自己的玩意儿软硬先搁一边,到一个地方不能拉场子就练,总得先看一看。于是,带着徒弟端午和小满四处转了一下,也就大概知道现在这“三不管”的意思了。显然,跟唐山的“小山儿”和奉天的“北市场”大同小异。但说一样,也不一样,这里毕竟是天津。骡子自己就是天津人,所以深知天津人的脾气,倘好说,自然是怎么说怎么好,而如果不好说,那就怎么都不好了。
这时已经相中,在西坑的岸边有一块空地。一般撂明地儿,都想找宽绰地方,且最好挨着道边,这样人来人往才好四面招人儿。而这块地方身后是水,只剩三面,虽然宽敞也没人愿意来。但是,对骡子来说却是难得的地势,所以一眼就看中了。
骡子做的是彩门生意。
所谓彩门,也就是变戏法儿。手彩一类的小戏法儿,行话叫“抹子活”,大变器物或活物乃至变人一类的大戏法儿,叫“卸活”,也叫“落活”。骡子就是使落活,所以不能敞开四面,总得留一面。当然,也不能一上来就亮出家底。
在西坑边拉开场子,先使的是“签子活”。
签子活也不容易,是先变后练。开场先使几套好看的手彩,为的是引人,用行话说叫“圆粘子”。等看着跟前的粘子圆得差不多了,接着,再练吞宝剑或吞铁球一类的硬气功。这一练,就是硬碰硬的真能耐了。所以前面的手彩只是白送,到后面才要钱。骡子跟一般使签子活的还不一样。吞宝剑,行话叫“抿青子”,吞铁球也叫“滚子”,练这类功夫的一般都得五大三粗,腰圆背阔,这样气力才足。骡子却是条子身材,且生得眉清目秀,皮肤白得像女人,看上去还有几分文弱,不像是能把宝剑和铁球这类东西吞进肚里的。
虽是初到,在西坑边试了几天,生意竟然很好。
骡子圆粘子,跟别人也不一样。一般撂地儿圆粘子,讲的是“钢口儿”,也就是说话。场子跟前过来过去的都是人,得拿话把人叫住,还得能说过来,说过来了还不能让他听两句就走,这就是本事了,得有一套刮钢绕脖子的生意话,也就是所谓的“拴马桩”,能把“粘子”说的就是想走也迈不开步。但骡子不是,不说,只唱。这些年走的地方多,各地的小曲小调会的也多,所以肚囊儿宽绰,一天唱下来都不带重样的。而且有嗓儿,真高起来清脆嘹亮,且能打远儿,腔儿一落下来又低回婉转,还有些“云遮月”的意思。“三不管”这地方千奇百怪,五条腿的牛,三条腿的大姑娘,各种闻所未闻的邪性东西这里都有。但一个眉清目秀,看上去穿戴挺干净的年轻人站在明地儿这么字正腔圆地唱,行话叫“柳儿”,且忽而俏皮跳达,忽而又一咏三叹,还是一下就吸引了过往人的注意。有人不由自主地停住脚,就想多听几句。这时,骡子见跟前的人已经越聚越多,嗓子便也越发地放开。就在围观的人们一错眼神的工夫,手里就变出一只扑棱棱的家雀儿,一边唱着一松手,让这家雀儿飞了,接着两手一抖,又变出一只更大的鸽子。这鸽子的身上还带着风哨,两手捧着一扔让它飞起来,立刻带起一串呜呜的哨声。然后拉着云手胳膊一转,又变出一只海碗,跟着抬脚一跺,好好的一只空碗瞬间就盛满了酒,场子上立刻飘起一股浓郁的酒香。这前一手儿,空手变海碗,行话叫“揪子”,后一手儿空碗变酒,叫“拉拉山”。这时,围在跟前的人们已经看得啧啧称奇,登时爆起一片喝彩声。场子已经打起来,骡子也就不歇息,又抬手向徒弟端午示意。端午扬着双眉,一身青色的箭衣越发显得身材苗条,且一脸的英气,这时,就双手捧过一把宝剑。骡子抽剑出鞘,在空中挥舞着比试几下,剑刃立刻挂起锋利的呼哨声。
骡子的这把宝剑跟别人也不一样。一般抿青子,所谓的宝剑只比匕首长一点,再把剑柄去掉,剑锋也就没多少了。但骡子这却是一把真正的青锋剑,光剑锋就有一尺多长。当然,也不是拿过来就吞,还要再唱几曲,且有很好的身段,一边仗剑且歌且舞。骡子在这一行里行走,虽然长年风吹日晒,皮肤却很白皙,此时舞起这把青锋剑,猩红的剑袍,也就是剑穗随着上下翻飞,越发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这样歌舞一阵,才站定收势,先让全身的真气运行开,然后仰头,张口,收敛气息。此时,场子四周的人们也都屏住气。只见骡子手里的这把青锋剑闪着熠熠的寒光,就一寸一寸地送进口中,插入深喉。当然,这时没人喝彩,不是不想,是不敢。直到看着骡子再把这把青锋剑一点一点地从喉咙里拔出来,又在空中甩出一阵尖厉的呼哨,掌声和喝彩声才兜着四个角儿响起来。
接着,人们扔的钱也就像雨点似的纷纷落进场子。
骡子注意兰大姑,也就是在这时候。
撂明地儿,别管做的是哪路生意,说来说去,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人扔钱,有钱才能吃饭,正所谓没君子不养艺人。所以,也才把这撂地儿叫“画锅”。但一样的扔钱,其实也不一样。人都有一种随大流的心理,无论这个活练得有多精彩,场子上有多火,头一个扔钱的看着不起眼,其实也最关键,一是扔的时机,二是扔的多少。
起初骡子并没注意,后来徒弟小满一说,才发现,每到这时,头一个扔钱的,经常是一个年轻女人,而且总是在人们叫好叫得最热闹时,把钱扔进场子。她这一扔就有学问了,不光时机恰到好处,趁这热乎劲儿,也就把后面扔钱的带起来,而且一扔就是一个大子儿。这一来,后面有好面子的再扔,心里也就得掂量一下了。
这样有几次,骡子也就注意这个女人了。
这女人二十来岁,说不上多漂亮,但也不寒碜,从穿戴看不出是妇人还是还没出阁的大姑娘,眉心有一块指甲盖儿大小的浅红胎记,看上去像个有意点的红点,也就又多了几分姿色。这女人每次扔了钱,只朝骡子这边瞟一眼,就转身挤出人群走了。骡子的心里当然明白,她这样扔钱,别管有意还是无意,其实都是帮了自己。
这以后,他也就把这女人记住了。
骡子这些年,对女人的事不是很上心。不是不想,是一直没这心思。想和心思还不是一回事。夜深人静时,一个人躺在床上,也觉着该有个女人了。但早晨一起来,就又没这念想儿了。其实自己也知道,没这念想儿,只是因为还没遇上让自己心动的女人。
后来有一次,他在徐傻子的茶摊儿上喝茶,闲聊时想起这个女人,就随口说了一句。徐傻子整天在街上摆茶摊儿,这“三不管”犄角旮旯的事,没有不知道的。
这时一听就笑了,说,你说的是兰大姑啊。
骡子听了有些意外。看来,这女人在这一带挺有名。
徐傻子一边给骡子的碗里续着茶一边说,当然有名,在这“三不管”,你问现在的大总统是谁,也许十个人有九个半说不上来,可一提茂生堂生药铺的兰大姑,没有不知道的。
骡子一听更好奇了,放下手里的茶碗,“哦”了一声。
徐傻子又“噗”地一笑,这兰大姑,可是个人物。
徐傻子告诉骡子,这兰大姑是茂生堂生药铺的老板娘,且是个寡妇,不过她这寡妇正应了那句话,是酒糟鼻子不喝酒,枉担个虚名儿。当初她娘家姓兰,在锦衣卫大街上开着一个绒线铺。后来经媒人说合,跟茂生堂生药铺的郑老板定了亲。这郑老板叫郑三林,据说老家是甘肃的,长得粗脖子大脑袋,是个挺壮的男人。婚事放定,两边都挺满意,接着就换龙凤大帖,过彩礼,过嫁妆,又定下吉日良辰。本来所有的事都挺顺遂,可花轿把兰大姑抬过来的这天,却出事了。这郑三林是个急性子,干这点事等不到晚上,刚拜了堂,就扔下一院子来吃喜酒的客人拉着兰大姑钻进洞房。当时亲戚朋友一看都笑,说这郑三林猴儿急,吃鸡蛋都等不到剥皮儿。可正说笑,就听兰大姑在洞房里一嗓子一嗓子地叫起来。人们一听就更笑了,说这洞房里虽然都是这样的动静,可也得顾及一下外面的人,别折腾得太大了。但再一听,又觉着不对,兰大姑在里面不是叫,是哭,而且这哭好像也不是好哭。这才意识到,大概是出事了。于是也顾不上避讳,赶紧都拥进来。一看,这郑三林的裤子只脱了一半,还露着半个屁股,已经歪在喜榻上口吐鲜血死了。原来这郑三林看着挺壮,其实外强中干,这几年又经常去街上逛“花铺”,已经把自己掏成了空心儿萝卜。这回办喜事之前,知道自己的家伙顶不上劲儿,已经是个沾热就化的银样镴枪头,仗着是开药铺的,事先就给自己配了点壮阳药吃了。但他心气太盛,担心不够劲儿,一下就吃多了。这时来到洞房,撩开兰大姑的盖头,一见她这如花似玉的样子劲儿就上来了,二话不说按到喜榻上,一边扯自己的裤子,又来扒兰大姑的衣裳。可还没等扒开,只觉一股邪火涌上头顶,跟着喷出一口鲜血,就死在兰大姑的身上了。这时兰大姑一见人们进来,也顾不上羞涩,只是哭。人们一看,一下也都没了主意。好好一个人,突然就这么死在洞房的喜榻上,就算有一堂的喜客给做证,也总得有一个真凭实据的说法儿。这时有明白人,提醒赶紧报官。接着又叫来仵作,经勘验尸首,认定确实是死于毒火上头,此事才算有了一个了结。但警察录口供时,险些又闹出事来。这办案的警察也不会说话,问兰大姑,在洞房里是不是闹过劲儿了,才弄得这郑三林急火攻心死了。兰大姑在洞房时是突然出事,一下慌得没了主意,这时已经平稳下来,心里正没好气,一听警察这不着四六的话,登时就急了,指着这警察的鼻子说,当初你妈跟你爸入洞房时,脱裤子就干啊,你妈有这么大脸,我可没有。这警察一听也急了,问案这几年,还没遇上过这么泼的女人。幸好一块儿跟来的人赶紧给打圆场,说她大喜的日子出了这种事,正不是心思,话好话歹的别跟她一般见识。这才总算给圆过去了。
但这一来,这兰大姑也就成了喜堂上的寡妇,而且是让喜堂上的红花儿变了白花儿,总是不吉利,用天津话说,也就是“妨人”。洞房里闹出这么一出,在街上也就一时传成了笑话。后来还有人写成文章,在当时的小报上登出来。
徐傻子说到这儿,又摇头笑了,不过老话说,有一失,就有一得,她既然已跟郑三林拜过堂,也就是名正言顺的郑兰氏了,这以后,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这茂生堂生药铺的老板娘。
骡子听了也笑笑,心想,敢情这个叫兰大姑的女人,还有这样一段过往。
徐傻子又说,不过现在,这兰大姑在“三不管”,可是街上的一枝花儿。
骡子问,怎么讲?
徐傻子说,惦记她的男人就不说了,真打主意的也不少。
骡子“哦”了一声,心想,这样的女人,男人见了自然都得寻思寻思。
徐傻子又说,就说那于三儿,每回一见兰大姑,就像个绿头苍蝇似的跟过来。一边说着,就摇晃着脑袋嘿嘿笑了。
骡子问,这于三儿又是谁?
徐傻子哼唧了一声,这“三不管”看着没吗,其实这潭水,也挺深啊。
骡子又看了徐傻子一眼,见他不想往下说了,也就不好再问。
骡子发现,西坑边离白家胡同的西南口儿很近。
这白家胡同是个“裤衩儿胡同”,本来是南北向,但中间劈开了,又斜着往西分出一个岔儿,西南口儿正顶着石头胡同。这石头胡同很宽,其实就是一条小街。看来当初的这个郑三林很会找地方,这一带不仅人流量大,也很热闹。骡子傍晚收摊儿,特意朝这边溜达过来,发现这个茂生堂生药铺把着街角儿,旁边有几家饭庄,还有一个春昇茶馆。
骡子从不泡茶馆,没这习惯。来这里不光得有闲钱,还得有闲工夫,为的是听戏看玩意儿,或是提笼架鸟儿玩儿草虫的,一边喝着茶,互相显摆显摆。还一种则是做生意的,来这里是为了谈事。骡子做的是彩门生意,跟一般的生意是两回事。况且在这里泡一下午,只为喝碗茶,也耽误不起这工夫,用街上的话说,“没这闲钱补笊篱”。
所以喝茶,也就是徐傻子的茶摊儿。
骡子还有个毛病,肚里不能没食,一饿心就慌,跟着两眼发黑,浑身突突地出虚汗。所以平时出来,端午总给带着饽饽,路过徐傻子的茶摊儿时,就一边喝着茶垫上几口。
骡子发现,这徐傻子看着傻,其实是贼人傻相,心里比谁都精,整天在这南市口儿摆茶摊儿,跟前过来过去的各色人等和各种事也就都看在眼里。别人看了也就看了,他不是,就记在心里了。日子一长,眼也就越来越毒,别管什么人,只要搭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骡子不爱打听事,没这种兴趣。但这次毕竟刚回来,以后还要在这“三不管”“画锅”吃饭,地面儿上的事也就总要知道一些。来摊儿上喝茶,也就经常跟徐傻子聊几句。
徐傻子看出骡子是实在人,也愿意跟他说话。
徐傻子后来才说,这于三儿叫于三羊,说起来跟骡子也是同行,但不同道。
骡子听了觉着新鲜,就问,怎么叫同行不同道?
徐傻子说,这于三儿在柳叶儿胡同开着一个天外戏园,不过他这园子不唱戏,只演戏法儿,而且是专演洋人的戏法儿。但洋人把戏法儿不叫戏法儿,叫“魔术”,所以他这园子演的也叫“魔术戏”。这柳叶儿胡同就在前面不远,从名字就能知道,两头窄,中间宽,是个枣核儿形状,但比枣核儿大,所以叫“柳叶儿”。胡同的这头儿正对着南市口儿,另一头儿伸到日租界的里边,顶着旭街。于三儿的这个天外戏园就把着旭街的胡同口儿,所以专做租界里日本人的生意,长年请的也都是洋人,尤其是从日本来的魔术团。
骡子是天津生人,天津长大,也知道一些天津的老事。自从当年火烧望海楼,庚子年洋人又打进天津,天津人嘴上不说,其实心里都恨疯了,街上也就没人愿意做洋人的生意。
徐傻子看出骡子的心思,就又笑了,说,这于三儿,可不一样。
骡子问,怎么不一样?
徐傻子说,他自己总在街上说,就是这南市此地人。
说着,又“扑哧”一笑,其实谁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骡子知道徐傻子的脾气,在这个节骨眼儿,不能问,一问他反倒又不说了。
于是他点点头,只“嗯”了一声。
果然,徐傻子又朝四周睃一眼,才压低声音说,当初,他妈在南门外,是个“暗门子”。
骡子当然懂,“暗门子”是天津人的土话,也就是暗娼。
徐傻子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干脆凑过来,把一只手挡在嘴边儿说,据说,他妈那时还有个花名儿,叫“把儿兰香”,不光会唱曲儿,也会唱落子,所以虽是暗门子,可比落子馆里的那些姐儿们还火,要找她,都得事先打招呼。后来一闹洋人,她胆儿小,就不干了。但洋人进了城,就应了街上的那句老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有一回,几个日本人喝了酒,在街上闲逛,不知听谁说的,这南门外有一个叫“把儿兰香”的女人,长得如何俊,又如何的妙不可言,就一路找到她家。起初这“把儿兰香”不干,好说歹说,怎么说也不干,这几个日本人就急了,也是火都顶了膛……
徐傻子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这以后,就有了于三儿。
说完,他又眨眨眼,明白了?
骡子没说话,当然明白了。
徐傻子又说,后来这街上的人一说起于三儿,就有句话,他这人是个大明白,天底下没有不知道的事,可只有一样事说不上来,不知自己的亲爹是谁。
骡子一听,忍不住笑了,说,这话就太损了。
徐傻子说,损的还在后头呢。
骡子又点点头,看着他。
但徐傻子忽然摆手说,算了,这都是闲白儿,你先去撂地儿吧,吃饭要紧。
然后他又抬起头,看看天,哟,光顾说话,叉棚儿了!
徐傻子说的“叉棚儿”,是街上的话,意思是阴天了,要下雨。
骡子叹口气,是啊,撂地儿有句话,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今天算是泡了。
徐傻子说,干脆,我也收了吧。
然后他一边拾掇着东西,一边说,我接着给你说。
徐傻子说,街上的人都知道,这于三儿对兰大姑一直揣着心思。最早曾让人去保媒,当时兰大姑都没让媒人进门,直接就给回了,说不行。媒人问,为吗不行?兰大姑说不为吗,你回去说吧,不行就是不行。媒人回来对于三儿说了,于三儿还不死心。但后来也就不提这事了,只是总去买药。兰大姑是开药铺的,他买药,当然就不能不卖了。可是总这么买,兰大姑就又觉出不对了,谁家买药也没有这么买的,总不能拿着这些药材当饭吃。后来有一次,就问他,买这么多药材干吗用。其实于三儿来这儿买药材,是有两个目的,首先当然是为了让兰大姑高兴,越买她的药材,她药铺的生意也才越好。但另外还有一层,平时去他天外戏园的都是日本人,日本人最喜欢中国的生药材,又听说这兰大姑的茂生堂生药铺货真价实,于是这于三儿就大包大揽,说他跟这药铺的老板娘关系如何好,日本人也就都让他来这儿买药。那次兰大姑一再问,于三儿才把这另一层说了。当时兰大姑听了,没说话。不过从那以后,于三儿再来买药,别管买什么药,兰大姑就一概不卖了,也不说不卖,只说没货。再后来,街上的人给她出主意说,也别不卖,既然是日本人要,反正他们也不懂局,不给好东西就是了,掺了假他们也看不出来,就算看出来了也是冲于三儿说话,这个钱,不挣白不挣。但兰大姑说,她这茂生堂生药铺不卖假药,这是当年郑三林留下的话。
骡子听了心想,这个兰大姑,确实挺有意思。
徐傻子又笑了,说,后来还有个事,就更有意思了。
骡子看他一眼,你这是包饺子擀皮儿呢,还零揪儿。
徐傻子故意仰头看了一下天,要下雨了,还说?
骡子“哼”一声,看你心气。
徐傻子先把摆茶摊儿的家伙一样一样都装到小排子车上,一边用绳子捆着,一边说,就是今年夏天的事,这事要说起来就更乐了,后来有人不信,去问兰大姑,你猜兰大姑怎么说?
骡子说,怎么说?
徐傻子“噗”地一笑,兰大姑让问的人,自己去问于三儿。
徐傻子说,其实他也是听街上人说的。于三儿总想请兰大姑吃饭,但请了几回,一直请不动。其实谁都明白,于三儿这是憋着坏门儿。于三儿的酒量很大,据说大得没底儿,一斤烧酒喝下去跟没喝一样。但兰大姑也有酒量,只是没人见过。直到今年夏天,兰大姑才吐口儿了,对于三儿说,咱也不用吃饭了,你不是就想跟我喝酒吗?甭费事,咱就喝酒,只咱两个人喝。于三儿一听当然高兴,问兰大姑,在哪儿喝?兰大姑说,你定吧,听你的。于三儿一听更高兴了,说,那就在我园子跟前吧,有个日本人开的小酒馆,挺清静,酒也好。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
于三儿定这酒馆,确实没安好心。日本人把酒馆叫居酒屋。租界里的居酒屋也分几种,其中有一种是不光喝酒,喝完了还可以干别的事。于三儿说的,也就是这种居酒屋。那天于三儿特意定在晚上,兰大姑去了,就跟他喝起来。当时他俩到底喝的是中国的烧酒还是日本人的清酒,没人知道,但据说只喝了一会儿,这于三儿就不行了,还不是一般的不行,是躺在榻榻米上醉得不省人事了。直到第二天上午,他园子里的人还不见他来,听说头天晚上是去门口儿的居酒屋喝酒了,这才找过来。居酒屋的人说,是在这儿,头天晚上带着一个年轻女人来喝酒,后来就没动静了,也就没敢惊动。园子的人一听赶紧过来,拉开门一看,这于三儿还四仰八叉地躺在榻榻米上。弄回去又躺了三天,才醒过来。
骡子问,他不是酒量挺大吗,怎么醉成这样?
徐傻子咧嘴一笑,凑近了说,别忘了,这兰大姑是开生药铺的。
骡子愣一下,心想,这兰大姑,总不会也用了江湖上的门子?
骡子毕竟是做彩门生意的,知道有一个门子,叫“闹羊花”。
徐傻子捂着嘴哏哏儿一乐,别管叫吗花,据说,她就是用了这个门子。
骡子当年住北门外,家里在单街子开着一爿杂货店。
单街子紧贴着南运河的南岸,一边是水,另一边是住家和买卖铺面,所谓“单街子”,也就是这么来的。骡子的爹叫马青云,虽是生意人,却生性腼腆,脸皮儿比纸还薄,挺大个男人,一见女人没说话,脸先红了,直到三十大几还没成家。媒人也曾给提过几个,但都没成,人家不是看不上他这人,是受不了他的脾气,相看时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能把旁边的媒人也急出一身汗。后来媒人就明白了,他这辈子没有娶女人的命,再怎么给他跑也是白跑。
再后来,马青云娶了骡子的妈,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
马青云的杂货店把着街边,对面的河坡下面有个小码头,常有南边来的商船在这里停靠。一天上午,马青云正在铺子里算账,听见河边有人吵嚷。出来一看,是一条商船上的人跟河边锅伙的人起了争执,三说两说已经打起来。听旁边看热闹的人议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条商船是从苏南过来的,船上的船老大带着一个闺女,爷儿俩跑船。这次船过太湖时,见当地的螃蟹挺肥,也便宜。这船老大常跑天津,知道这边的人爱吃腥东西,尤其爱吃螃蟹,就顺手弄了一些,用个网子装好,拴在船尾,这样螃蟹一直在河里泡着也就死不了。本来盘算得挺好,到天津肯定不愁出手,真能卖个好价钱,爷儿俩这一路的挑费也就出来了。可没想到,来到天津,把船靠到这个小码头,刚一上岸就出事了。
这船老大并不懂天津的规矩。天津人确实爱吃腥东西,而且最爱吃海鲜,海鲜也叫“海货”。这些海货都是从塘沽的海边拉来的,天津人叫“海下”,每天专门有船在海下上了海货,然后沿海河逆流而上,拉到城里来卖。但这海货运上来不能随便卖,按规矩,必须先趸给河边锅伙上的人,再由锅伙统一开市发行。所谓锅伙上的人,也就是天津人所说的“混混儿”。这些人平时聚在南运河的河边,一块儿吃,一块儿住,就如同当年土匪的一个个“山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寨上”。但这些人虽然欺行霸市,也讲规矩,定的价格也还算合理。这个船老大当然不知道这里边的事,船一靠岸,就让几个船工把这些螃蟹弄到岸上来。天津人一见是南边来的螃蟹,这一路在河里泡着,青汪汪的还挺新鲜,自然都抢着来买。这一下锅伙上的人就不干了。于是过来几个人,要把这些螃蟹都买走。但他们出的价钱比船老大自己要的低,船老大当然不卖。这几个人一听就说,不卖也行,那就都别卖了。
说完,就把围着买螃蟹的人都轰走了。
这一下,这船老大的闺女就急了。这些螃蟹虽然一直泡在水里,但已经颠簸一路,现在一出水,如果不赶紧卖出去很快就死了,一死也就不值钱了。这船老大的闺女从小是在船上长大的,这些年跟着她爹走南闯北,不光见过各种世面,也养成了船家浑不懔的脾气,这时抄起一根杉篙就跳上岸来。这些锅伙上的人平时都是指着耍胳膊根儿吃饭的,一见是个黄毛丫头,根本没放在眼里。可没想到,几句话过来,这船老大的闺女把手里的杉篙横着一划拉,就把这几个人都划拉到河里了。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锅伙上的人立刻都跳出来。
马青云平时在这街上做生意,对锅伙上的人自然很了解。这些人看着挺凶,其实也讲礼讲面儿,凡事如果好说,也就好商量,但别惹急了,一急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于是他赶紧过来,把这事拦下了。
其实这时,这些锅伙上的人也正骑虎难下。这条商船毕竟是从南边来的,又是父女俩,锅伙上的人平时都自诩侠肝义胆,是英雄好汉,不想落个欺负外地人且还恃强凌弱的名声。但事情已架到这儿了,又没法儿收这个场。这时一见马青云出面,知道他是这街上杂货店的老板,也就顺坡下驴,给了他这面子。马青云虽然平时不爱说话,但街上的事还明白,于是又把锅伙上的几位“寨主”请到街上的羊肉馆喝了一顿酒,这事才算过去了。
这船老大拎着一篓“花雕”和几尺丝绸,带着女儿来登门道谢。马青云是生意人,场面上待人接物自然也能应付。但这时一见这船老大的女儿,脸登时又憋得通红,连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了。这船老大这些年已阅人无数,一看就明白了,这个年轻的马掌柜不光急公好义,也是个老实的正派人。再一说一聊,知道他眼下还没成家,心里就有了想法儿。他这个女儿叫红菱,已经十八岁,总不能跟着自己跑一辈子船,也就一直想为她寻一个妥靠的归宿。天津是水旱两路码头,又是繁华之地,倘真让女儿落在这里也是难得的好事。而这个叫红菱的女孩儿虽然整天在河上跑船,已养成火暴脾气,这时一见马青云腼腆得像个大姑娘,也一下就喜欢上了。爷儿俩回到船上,一合计,就央人来提亲。马青云平时已听惯街上女孩儿的大嗓门儿,这红菱虽然有脾气,说话却是吴侬软语,也觉着挺新鲜。
于是来人一说,也就成了。
这船老大还急着回去,既然事已说定,也不要繁文缛节,一顶花红小轿就把女儿送过来了。
马青云本来挺高兴,这些年相亲一直没成,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已没有娶老婆的命了,却正应了街上的那句话,“好饭不怕晚”,而且是“千里有缘一线牵”,这南运河上的一条商船,竟就把这样一个说话软声软气的可心女人送到自己眼前。这一想,也就越发觉得庆幸。
但让马青云没想到的是,这红菱一嫁过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马青云是开杂货店的,平时就指着门口儿的街坊照顾生意,跟邻里的关系也就处得很好。可这红菱一进门,本性的脾气就暴露出来,跟邻居一点亏不吃,没几天就在街上都打遍了。门口儿的街坊也都纳闷儿,这马掌柜平时为人和善,怎么娶了这么个张牙舞爪的女人。背地里就给她娶了个绰号,叫“母老虎”。起初红菱不知这“母老虎”是什么意思,但再一寻思也就明白了,从此索性跟左邻右舍越发打得乌烟瘴气。
马青云没想到娶回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女人,肠子都悔青了,但眼看木已成舟,也无可奈何。后来有了第一个儿子,就取名叫“友善”,马友善,意思是希望这女人生了这个孩子,从此身为人母,在街上再待人接物也就友善一些。再后来又有了第二个儿子,又取名“友闾”。马青云虽是做生意的,当年也读过几天私塾,为这第二个儿子取名“友闾”,意思是想让这女人跟邻里友好相处。但这女人的脾气是从胎里带出来的,已经长在身上,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从有了这两个儿子,倒顾不上跟邻里打架了,又整天冲这两个儿子大嚷大叫,从早到晚嚷得一条单街子都能听见。马青云一看,再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了。可自己又实在怵这女人,不敢跟她过话,想来想去,就找了街上上点年岁,又有头有脸的孟老先生,请他来跟这女人说说,要么把脾气改一改,要么就想个彻底的解决办法,反正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没想到,孟先生来了,话还没说完,这女人倒先流泪了,说,如果孟先生不来跟她说,有的话,她还真说不出口,当初自己也没想到,这样的日子真的是不习惯,自己从小到大一直在船上,四周除了水没别的,就是偶尔遇上一条船也是擦身而过,谁也碍不着谁,可现在不行了,这房前左右住的都是人,不是街坊就是邻居,整天出来进去的打头碰脸,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这些年,已在船上待惯了,一上岸时间长了,总觉着脚下发软,就像这陆地上的人刚上船时晕船,也觉着晕,再这样下去,只怕自己也活不长了。
孟先生是通达人,一听这女人说的话,就明白这事已经没什么可说了。于是对她说,既然如此,那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吧,不过有句老话,“一夜夫妻,百日的恩情”,况且眼下又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夫妻俩能一块儿过,自然是好合,实在不行了,也就好散,真打成乌眼儿鸡似的就没意思了。这女人到了这时,倒也通情达理,点头说,行,就听您的。
于是当天晚上,这女人就对马青云说,孟先生说得对,咱就好合好散吧。
马青云这时已巴不得,一听忙说,你说吧,怎么都行,都听你的。
这女人说,两个儿子,咱俩一人一个,友善跟我走,友闾给你留下,我这一走也就回苏南老家了,这边家里的东西我一概不要,要了也带不走,你给我点盘缠,能回去也就行了。
马青云一听这女人这样说,眼泪也忍不住流下来。
这以后,这女人就带着老大友善走了。马青云带着老二友闾,爷儿俩过日子。
友闾十七岁这年,马青云得了一场时令病,一入冬也走了。临终时,把儿子友闾叫到跟前,对他说,爹这辈子有件事,一直觉着对不住你。说着,叹口气,当初,没送你去读书。
友闾听了,只是看着爹流泪。
马青云又说,我知道,你这辈子不是做生意的,这杂货店真到你手里,几天就得黄了,以后的事,我都已托付给街上的孟先生了,他为人妥靠,我走以后,你听他安排就是了。
友闾点头说,知道了。
马青云走得很简单。在北马路买了一口寿材,杠房雇了个四人杠,就抬到城西义地埋了。
友闾送走父亲,身上还挂着孝,孟先生就做主,把单街子上的杂货店盘出去了。然后,把几块大洋和一堆大子儿连一张银票交给友闾,对他说,盘铺子的钱都给你存在银号了,这几块大洋连这点零钱也够你花一阵了,但也不能坐吃山空,趁现在,总得学一门日后能吃饭的手艺。友闾一听,跪下给孟先生磕了个头说,我爹说了,以后的事,都听您的。
孟先生说,我已跟太平街的刘掌柜说好,就去他的冥衣铺吧。
所谓冥衣铺,也就是专为白事做纸活的铺子,街上也叫“烧活”。这烧活看着简单,就是一些纸人纸马、车船轿屋,但也不容易,得先用竹篾扎了架子,再用粉连纸糊起来,还得栩栩如生,也是一门手艺。友闾的心眼儿灵,手也巧,跟着刘掌柜学了些日子,就已能独自上手了。但越干,心里却越觉着提不起劲儿,自己年纪轻轻,又活得好好的,整天摆弄这些死人用的东西,总觉着丧气。刘掌柜是爽快人,已看出他的心思,就说,人这一辈子,不是能干哪一行,而是喜欢哪一行,能干跟喜欢不是一回事,当然,倘真能把喜欢干的事当成一辈子的饭碗,这也是难得的福分。友闾一听,既然刘掌柜这样说了,也就索性把自己最近的想法说出来。他说,这些日子没事的时候常去南门外,看见有变戏法儿的,觉着挺好玩儿,也能赚钱,而且还专门有教戏法儿的,这要学会了,将来应该也是一门能吃饭的手艺。
刘掌柜听了沉吟一下,才说,按说有的话,我也许不该说,不过你是孟先生介绍来的,我跟孟先生已是这些年的朋友,就还是提醒你一句,街上的事没这么简单,你说的这教戏法儿的,我也听说过,有的只是江湖上的一种门子,跟正经生意不是一回事。
沉了一下,他又说,这一行里有句话,好人不多,坏人不少。
友闾点头说,我明白。
但友闾并没告诉刘掌柜,几天前,他已跟南市一个叫管云长的人说好了。
友闾这些日子没事的时候,常去南市,发现在一个角落的棚子跟前有个变戏法儿的。这人四十来岁,嘴里镶着一颗大金牙,身上穿着绸缎裤褂,还挂着一块金链子的怀表,看意思挺有钱。友闾在旁边看了几回,这人闲下来时,就过来跟他搭话,问他,是不是对这一行也有兴趣。友闾说是,又说,也想学几手,当然,该给钱给钱。这人一听就笑了,说,你这小兄弟,一听说话,就知道是个空码儿,这一行里的事可不是你想的这意思。
友闾不懂,问,空码儿是怎么回事?
这人说,空码儿,就是外行。
他又说,这不是给钱不给钱的事,这一行,不能轻易教人。
友闾说,可你现在这手艺,当初也得有人教,不教是怎么会的?
这人说,你这就说到点子上了,当然得有人教,可也分怎么教。
友闾说,你说吧,怎么教?
这人说,教分两种,一种是挑幅子,还一种就得正式拜师。
友闾说,拜师我懂,这挑幅子是怎么回事?
这人回手拿过一沓纸,抖了抖说,这就是幅子,一个大子儿一张,每张上写着一个戏法儿的门子,只要买去,像你这机灵的,醒攒儿也快,保证一看就明白,一学就会。
这人说的“醒攒儿”,友闾倒懂,意思是悟性好,凡事一点就透。
但他立刻说,我不是学着玩儿,要学,就正式拜师。
这人立刻不说话了,看看友闾。
友闾也看着这个人。
这人又沉了一下,才说,要真拜师,可就不是小钱了。
友闾问,得多少?
这人说,真把你教会了,就是一辈子的饭门,少说也得五十块大洋。
友闾听了立刻拨棱脑袋,说,五十块大洋,我可拿不出来。
这人问,你能拿多少?
友闾说,最多二十,我还得想办法去拆兑。
这人又想想,点头说,二十就二十,不过,我得要现洋。
友闾说,就算二十大洋也不是小数,你得容我几天,还要回去再想想。
这人说,你想可以,不过这事不能跟别人说。
友闾不明白,问为什么。
这人说,我刚才说了,这一行是不许随便收徒的,真让行里人知道了,这事就完了。
友闾“嗯”一声,说明白了。
这时,这人才告诉友闾,说自己姓管,叫管云长。又解释说,这是个艺名,既然是吃江湖饭的,讲的是义字当先,当年关二爷义气千秋,所以才斗胆借了他这“云长”两个字。
友闾一听,也告诉这管云长,自己姓马,叫马友闾。
这管云长说话有点口音,一听就乐了,说,马又驴,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又是马,又是驴,这是个骡子啊。想了想,就点头说,行,你如果真拜了我,以后的艺名儿就叫骡子吧。
他说着又笑了,骡子,这艺名儿也挺生色。
友闾嘴上对这个管云长说回去再想想,其实这时,心里已经打定主意。当年父亲在世时,常说一句话,一招鲜吃遍天,艺不压身,只要能学一门手艺,总比做生意强。
但友闾还是留了个心眼儿,并没把实话都说出来。当初街上的孟先生帮着把父亲留下的杂货铺盘出去,存在银号的钱是一百多块大洋。但孟先生说,倘日后要动这笔钱,必须先告诉他。孟先生说,按说这钱是你爹留给你的,跟我没一点关系,但他在世时,既然已托付我了,我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得替你把着点,不能让你胡乱花了。
不过这次,友闾还是没告诉孟先生。
于是几天后,他先去银号取出二十块大洋,就来南市找管云长。这管云长好像一直等在这里,这时接过这兜大洋,先哗啦哗啦抖了几下,点头说,行。
然后他又说,从今天起,你就叫骡子了。
友闾“嗯”了一声。
管云长又说,明天一早,咱爷儿俩就动身。
友闾问,去哪儿?
管云长说,关外,去奉天。
骡子起初并不喜欢这个艺名。骡子是畜生,好好的一个人,干吗要叫畜生名儿。但管云长告诉他,艺名儿是让街上人叫的,跟正经名字不一样,得生色,像蛤蟆李、大狗熊,也都是畜生,艺名儿越奇怪,才越容易让人记住。
骡子想想,觉得也对。
天津离奉天一千多里地,先坐车,又坐船,路上走了几天才到。奉天有玩意儿的地方是北市场。管云长对这一带很熟,先在附近找了一家干净的旅馆,出手也很阔绰,给自己和骡子一人开了一个单间。安顿下来,让骡子先歇歇,说自己出去见个朋友,商量一下后面的事,一会儿回来,就带他出去吃饭。骡子这一路也累了,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再睁眼时,天已黑下来,但仍不见管云长回来。就这样饿着肚子等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还不见管云长的人影。这时,旅馆伙计来了,对骡子说,按旅馆的规矩,住一天得交一天的店钱,不能赊。
骡子说,等一会儿师父回来,一块儿交。
伙计问,谁是你师父?
骡子说,昨天和我一块儿来的,他出去办事了。
伙计摇摇头,昨天这人只交了你的店钱,然后把他的房子退了,已经走了。
骡子一听不信,赶紧来到他的房间。果然,这边的屋里已经空了。骡子一下慌了,这次出来,所有的钱都在管云长这里,自己的身上只有几个零钱,现在倘再交了店钱,就连吃饭的钱也没了。于是店也不敢住了,赶紧拿上东西退了房,来到外面的街上。
骡子长这么大,还从没离开过天津,更别说出这么远的门。这时抬眼朝四周看看,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一屁股就坐在旅馆门口的石头上。此时,再回想自己在南市时,跟这个管云长认识的前前后后,才恍然明白了,看来,自己从一开始就钻了这个人的套儿。
接着,骡子就想起冥衣铺刘掌柜说的话,这一行里好人不多,坏人不少。
这样想着,骡子就在自己的脸上使劲儿扇了一下。
这时,从旅馆里走出一个人。
他来到骡子跟前,看看他说,这位小兄弟,这是遇上事了?
骡子抬起头,见这人五十来岁,穿得挺干净。但这时他没心思搭话,只“嗯”了一声。
这人笑笑说,你别误会,我也是在这儿住店的。
这人又说,你昨天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骡子问,看出什么了?
这人说,看出你这事,好像不对。
骡子一听,心里就来气了,想说,你既然已经看出来了,干吗不告诉我?但再想,又觉得这话没道理,人家跟自己非亲非故,干脆说根本不认识,凭什么告诉自己?
这一想,他就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了。
这人又说,你肯定饿了吧?我也还没吃早饭,咱先去吃点东西吧。
骡子听了,又朝这人看了一眼。
这人是个大脸盘子、肉鼻子、厚嘴唇,倒像是面带忠厚的样子。但骡子有了管云长这一次,这时,已不敢再轻信任何人了。这人又看看骡子,笑着说,我知道你怎么想。
骡子没说话。
这人说,这么说吧,你现在要么信我,要么别信,如果信呢,前面不远有个小面馆,就跟我去吃碗面,不过仨瓜俩枣的事,出门在外,谁都备不住有为难着窄的时候,这点接济也不叫事。当然,不信也无所谓,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本来就谁也不认识谁。
骡子听了没动,心里还在犹豫。
其实这时,饿是真饿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一口东西没吃,这时已经前心贴后背。可再看眼前这人,一时又拿不定主意。眼下自己在这奉天的街上,是人生地不熟,又刚让人骗了,心里还没缓过神来。这么想着,就又瞟了这人一眼。
这人又说,这么说吧,就算我也憋着骗你,你自己合计合计,我还能骗你什么,说句难听话,现在你身上抖落干净了估计也没几个大子儿,骗你这身衣裳,拿到估衣街上也卖不了几个钱。说着又“扑哧”笑了,真要拍花子,你这岁数,也嫌大了点。
骡子又想了想,这才慢慢站起来。
这人带着骡子来到前面的小面馆,给一人要了一碗热汤面,坐下来一边吃着,一边说,自己姓何,在行里官称老何。说着就笑了,又解释道,这老何不光是因为姓何,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江湖上把同行同道的人也叫“老合”,也就是伙计、爷儿们的意思,所以自己这老何在同行里叫来叫去,也就成了艺名儿。接着又说,昨天带骡子来的这人,他以前见过,也知道大概是干什么的,只是都是江湖上的人,不好给他点破。
说着,老何又看看骡子,听口音,你是天津人?
骡子说,是。
老何又问,当初跟这人是怎么认识的?
骡子觉得这老何挺实在,又吃了人家的面,这才把跟这管云长认识的前后都说了。
老何听了点头说,明白了,干这一行的,一般都是这个路数。
然后他才告诉骡子,这人干的这事,用行里的话说叫“挑厨供”,说白了,也就是借着卖戏法儿骗人。接着,就把这里边的事,用道儿上的话说也就是各种门子,都给骡子讲了。
骡子这才知道,这老何也是“彩立子”。所谓彩立子,也就是做彩门生意的。彩门生意分大戏法儿和小戏法儿两种,但一般变小戏法儿的不变大戏法儿,变大戏法儿的不变小戏法儿,这老何却是大小戏法儿都变。但大戏法儿跟小戏法儿不一样,小戏法儿只是手上的功夫,只要有个地方,一个人就能变,大戏法儿就不行了,不光对地方有严格的要求,而且一个人变不了,还得有帮手。这老何本来有个儿子,还有一个徒弟,一直是爷儿仨在这北市场变大戏法儿,也就是所谓的使落活。但他这儿子性子倔,脾气也不正,平时的想法儿总跟人拧着,别管遇上什么事,别人这么想,他偏不,非得那么想。老何也知道,这儿子大了,儿大不由爷,也就一直在心里忍着。但后来,这儿子越闹越不像话,老何实在忍不住,爷儿俩就闹翻了。这儿子一气之下,自己去了营口。临走撂下一句话,以后跟他这当爹的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从此井水不犯河水,自己另起炉灶了。当时这老何也是火顶了脑门子,见儿子已把话说得这么绝,一气之下也就让他走了。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过后消了气,才意识到不是这么回事。眼下自己跟前有个徒弟,使落活还行,可这儿子只身去营口,手艺还没学到家不说,真想找个帮手也没这么现成,倘只凭使抹子活,恐怕连饭也吃不上。这样想了几天,知道营口练玩意儿的都在洼甸市场,于是一咬牙,只好打发徒弟去营口的洼甸市场找儿子。临走又叮嘱,如果能把他叫回来最好,倘他不肯回来,就先留在那儿,给他做个帮手。但这徒弟一走,老何这里的落活也就只能放下了。
在这个早晨,老何对骡子说,小兄弟,我这儿有句话。
说着,看看他,我一说,你一听,行不行的都无所谓。
骡子已经到了这时候,点头说,您说。
老何说,我看你这孩子挺老实,人也机灵,如果后面还有别的道儿走,就该去哪儿去哪儿,要是暂时无路可走,就先跟着我干。接着又说,不过,咱话是这么说,真跟着我干,我管吃管住,零花钱也有一点,可不多,我能给你的,也就是教你本事。
骡子一听,立刻点头说,行,我干。
这以后,骡子也就跟了老何。
骡子觉得,这“三不管”就像一壶烧在炉子上的水,早晨是凉的,到上午,就开始咝咝啦啦地响起来,一过中午,也就烧开了,到了下午,尤其接近傍晚,就已经冒着热气滚沸起来。不过到这时,接近掌灯时分,虽然人已经多得挤不动,也就该收摊儿了。
骡子收摊儿,比做别的生意的还要早。这时不要说落活,就是抹子活也没法儿使了,人们看的就是你手上的功夫,天一擦黑也就看不清了。这个傍晚,骡子看看差不多了,就示意徒弟端午和小满。两人明白师父的意思,也就开始收拾东西。
往回走时,来到南市牌坊的跟前,老远就看见徐傻子在茶摊儿上朝这边招手。骡子在地儿上这一天,有些累了,想早点回去歇着。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朝这边走过来。
徐傻子倒上一碗茶,乐着说,我以后,可得上赶着巴结你了。
骡子在摊儿上坐下,看他一眼说,你这话,又是打哪儿说的?
徐傻子说,打哪儿说?当然是打街上说。
说着又一乐,你现在,在这“三不管”可出了名儿了。
骡子一愣,问,怎么出名儿了?
徐傻子说,尽人皆知啊。
骡子看看他,还是没懂。
徐傻子说,你可听明白了,你出名儿不是玩意儿出名儿,是人,你这个人出名儿了。
骡子又看看他,“哼”一声说,不懂你这路话。
徐傻子拎过歪嘴儿铜壶,一边给骡子续着茶,一边说,这几天,兰大姑在街上逢人就说,西坑边上新来了一个叫骡子的“彩立子”,玩意儿如何地道,钢口儿如何好,别人是说,他是“柳儿”,且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各地的小曲儿小调儿,能柳出花儿来。
徐傻子说着就又乐了,她这一夸你,把街上的人都惊着了。
骡子问,怎么?
徐傻子说,兰大姑的眼眶子高,还从没这么夸过人,她的药铺旁边的就是春昇茶馆,这一夸,茶馆里的人也就都知道了,茶馆的人一知道,街上还不都知道了。
说着他又问,你没觉出来,这几天,场子上的人渐多?
骡子想了想,还真是。
但他笑着说了一句,别挨骂了。说完,就起身走了。
这“别挨骂了”,是吃开口饭的常说的一句玩笑话,跟街上说的别打镲了,是一个意思。
一出南市口儿,端午在骡子身后说,对了,有个事,忘跟您说了。
骡子没回头,一边走着“嗯”了一声。
端午说,中午,那个兰大姑到地儿上来了,让给您传个话。
骡子又“哦”了一声。
端午说,她说,今天晚上,想请您吃个饭。
骡子咯噔站住了,回身看着端午,你怎么说?
端午“吭哧”了一下,我跟她说,师父一般不吃请。
小满在旁边埋怨说,你应该跟师父说一声,自己倒先给做主了。
端午扭过头,狠狠瞪了小满一眼。
骡子没再说话,就转身朝前走了。
骡子当初并没想过要收徒。在奉天时,虽然跟着老何学了几年,彼此也以师徒相称,但始终也没正式拜师。不是骡子不想拜,是老何不让。骡子一直追着提这事,后来老何干脆说,你非要正式拜师,是不是怕我不使劲儿教你?骡子赶紧说,这倒不是。骡子的心里当然有数,老何教自己,一直实心实意,就是真拜了师也不过如此。老何说,这不就结了,拜师说到底,也就是个样子,真拜了后来打成热窑的,也有的是,拜不拜的心里明白也就行了。
后来骡子才知道,老何跟前的这个徒弟,也没正式拜过。其实细想,干这一行拜师有拜师的好,不拜也有不拜的好。拜了自然关系更近,但一近了,也就容易出毛病,虽然像俗话说的,“师徒如父子”,可再怎么说毕竟也不是真父子,关系近得没缝儿了,很多事反而不好拿捏,一点没想到,或没做周到,也许师父就挑眼,反倒不如不拜,就像老何说的,只这样跟着学,彼此的心里都明白是这样一种关系也就行了,反倒好相处。
所以,骡子想,自己以后也只找帮手,不收徒。
再后来遇上端午和小满,是在唐山的小山儿。老何的儿子后来还是从营口回来了。爷儿俩一见面,毕竟是亲父子,这儿子当初跟着父亲时,诸事不用操心,这几年一个人在营口的洼甸市场“画锅”挣饭,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这时已没了过去的脾气,回来一见父亲,父子俩也就冰释前嫌。这时,骡子见老何的跟前有了儿子和徒弟做帮手,又凑成一套,自己这几年也已学得差不多了,就跟老何提出来,想回天津。
老何一听,也就答应了。
临走老何对他说,以后有事,随时来奉天找我。
骡子虽没正式拜师,跟老何也已是师徒之情。走时,给老何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骡子的心里当然明白,天津跟奉天不一样,码头更大。码头大当然有大的好处,人多,生意容易做,但能人也多,得有真本事。所以回来的路上,路过唐山时,就在小山儿停下来,想先试一试手,看独自一个人挑摊儿了,能耐行不行。
也就在这里,遇上了端午。
当时是一个上午,骡子这时已有一块固定的地方,正要做生意,就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儿走过来。这女孩儿倒不怯,过来先叫了一声大哥,然后就问,用不用帮手?骡子在这里只使抹子活,自然用不着帮手。但这女孩儿说,她急等着用钱,跟骡子帮一上午,给几个小子儿就行。骡子看看这女孩儿,身材挺苗条,长得也不难看,身上穿得也挺干净,就问了一句,急着用钱干什么?这女孩儿说,她兄弟突然得了时令病,一直拉稀,只几天人已拉得起不来了,现在还躺在店里,得赶紧给他买药,可身上的钱只够住店的,买了药,就得让人家赶到大街上来,那就更麻烦了。骡子当初也曾遇到过难处,于是说,既然是急着买药,就甭费这事了。说完,就从身上掏出几个大子儿,让她拿去赶紧买药。这女孩儿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钱接过来,在手里攥了攥说,行,这个钱,我得还您。骡子一听就笑了,说,你怎么还,你要是能还就不这么难了。又说,快去吧,都出门在外,这不叫事,钱不够再来找我,多了没有,一星点还行。这女孩儿听了,没再说话,冲骡子施了一礼就匆匆走了。
骡子在小山儿待了些天,觉得自己学的这点能耐还行。这一晚收了摊儿,打算再住一晚,第二天就奔天津了。正收拾,就见这女孩儿又来了,这回还带来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这女孩儿一过来就说,还真找着您了。说着,就拉过身边的这年轻人说,这就是我兄弟,要不是您那天帮我,他现在还不知怎么样呢。
说着,两人就给骡子行礼。
骡子赶紧拦着说,这不叫事,不叫事。
这女孩儿说,您说不叫事,可对我俩就叫事了,这可是救命的钱。
她又说,我那天说了,要把这钱还您,干脆,我俩就跟着您做个帮手吧。
骡子一听,看看她和这年轻人,心想,自己回天津以后,如果要使落活,还真得有个帮手。于是对这女孩儿说,我这行不比别的,一般不懂局的可干不了。这女孩儿立刻说,她和兄弟也学过,不过只是一点皮毛,但如果做个帮手,应该还行。
骡子又想想,说,我不打算在唐山,马上要回天津。
这女孩儿立刻说,那就更好了,我俩也是天津人,正好跟您回去。
骡子已经听出来,这女孩儿说话是天津口音,于是说,行,咱也别说定,先试试吧。
骡子这时才知道,这女孩儿叫端午,今年十九岁,兄弟叫小满,十七岁,两人是亲姐弟。本来家住在北门外的锅店行,但父母早亡。后来在天津实在待不下去,才出来了。
骡子一听,自己当年家住在单街子,离锅店街很近。
这姐弟俩一上手就看出来了,都挺机灵,门子的事一点就透,还真是干这个的。端午也曾提过几次,她姐弟俩想正式拜师。但骡子说的,也是当初老何说的那一套话,拜不拜师只是个样子,只要跟着学,心里明白也就行了。
这以后,端午也就不再提了。
骡子这次回来,一直忙撂地儿。现在稍稍安定了,才想起来,应该去单街子看看孟先生。
当年父亲去世,是孟先生给料理的后事。后来,也是孟先生帮着把父亲留下的那爿杂货店盘出去,又为自己安排了生计。这几年,骡子想起孟先生,总觉着有些愧疚。当初孟先生把盘铺子的一百多块大洋给存在银号里,曾反复叮嘱,日后要动这笔钱,一定跟他打招呼。当时孟先生说,按说这笔钱跟我没任何关系,但既然你父亲托付我了,我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得替你父亲把这笔钱看住了,钱再多,哪怕多得像一座山,如果随心所欲也不禁花,所谓坐吃山空,也就是这意思。但是,骡子后来决定拜那个管云长为师,从银号取出二十块大洋,却并没告诉孟先生。直到去了奉天,让这管云长骗了,流落到街上时,再想起孟先生才痛悔不已。可见自己不光少不更事,也实在没慭子,孟先生是读书人,且这些年阅人无数,如此不靠谱的事,当时如果跟他说了,他一定会拦住自己。
这次回来,他一直没去见孟先生,也是实在没有颜面。
但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应该去看一下老先生。
这天上午,骡子特意早出来一会儿,打发端午和小满先去地儿上,自己在街上买了几斤“小八件”,打了个蒲包,又买了一篓水果,就拎着奔北门外的单街子来。
已经几年了,这条街没怎么变样,只是行人少了,看着有些冷落。走过自己家当初的杂货店时,朝里看了一眼。现在已改成鞋帽店,生意也有些冷清。
孟先生的家在街拐角,跟前有两棵门槐。
孟先生早年是私塾先生,后来不干了,平时在家没事,只是给报馆写一些性情的闲散文章。家里有几间闲房租出去,用街上的话说,只是“吃瓦片儿”。这个上午,骡子见到孟先生有些意外。来时在心里算着,老先生应该已经八十多岁了,这时一见,竟然没怎么变样,仍然精神矍铄,脸上也很有光泽。孟先生见了骡子也很高兴,听他说了这几年在外面的情况,有些感慨,问骡子,当年你父亲临终时,曾对你说,他一直有件遗憾的事,还记得吗?
骡子当然记得,当时父亲说,遗憾的是,没让自己读书。
孟先生说,是啊,这话他也对我说过。
然后看看骡子,他又说,其实说来说去,你真应该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是骨子里的事,不在读书多少,有的人读了一辈子的书,可读了也就读了,到了也不是真正的读书人,也有人可能没怎么读过书,但还是读书人,这不是书的事,是人的事。
骡子听懂了,孟先生说的,其实不是书,是理。
孟先生又叹口气,不过话说回来,你现在沦落江湖,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年你父亲想的,也是想让你学一门手艺,眼下虽然吃的是撂地儿的饭,可凭的也是本事,用这一行的话说,是“平地抠饼,对面拿贼”,不光不丢人,我觉着,你父亲如果在天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不过,孟先生又说,常言说,江湖上最讲义气当先,这“义气”二字,你想过吗?
骡子听了看看孟先生,想了想,还真没认真想过这两个字。
孟先生说,其实,这不是一件事,是两件事。
骡子听了,又看看孟先生。
孟先生说,义是义,气是气,行走江湖,要记住,宜义,不宜气。
骡子立刻明白了,点头说,您放心,我这行也如同唱戏,只吃戏饭,不吃气饭。
孟先生听了,笑笑说,这我当然有数,所以我才说,你骨子里,还是个读书人。
骡子从孟先生的家里出来,在街上走着,心里忽然有些难受。刚才孟先生说,自己现在干这一行,也挺好,其实看得出来,他这样说,也是无可奈何。事已至此,他还能说什么呢。显然,当初父亲在世时,曾跟他说过一些话。只是现在,他不好说出来罢了。
这个上午,骡子来到西坑边的地儿上时,端午和小满已经圆起了粘子。端午正在场上使抹子活。小满一见骡子来了,赶紧过来说,这就踏实了,再晚一会儿,只怕他姐弟俩就撑不住场子了。说着,又拿眼朝场子的边上挑了一下。骡子刚坐下,正喝水,顺着小满的眼神看去,就见人群里站着一个年轻人。这人是个小个头儿,四方脸,两个鼻子眼儿朝上翻着,看穿戴,应该是哪个买卖家的伙计。骡子立刻想起来,这几天,这个年轻人经常来,但每次都是站在人群外面,也不扔钱,看一会儿就扭头走了。
于是他冲小满点了下头,意思是知道他说的是谁了。
傍晚收了摊儿,他才问小满,怎么回事?
小满说,这人是天外戏园的伙计。
小满虽然平时话不多,但心里有数。那天骡子在徐傻子的茶摊儿上聊天,徐傻子说的话,小满在旁边听了,就记在心里了。于是没告诉骡子,没事时,就到柳叶儿胡同的天外戏园去了几次。这天外戏园看门脸儿倒不是很气派,但有点东洋风格,门口挂着两个半人高的浅红色纸灯笼,上面写着又粗又大的黑字,旁边的墙上还贴着广告画,是一个绾着发髻的日本男人,袒胸露背坐在那里,好像正吞一匹马。小满曾听街上的人说过,于三儿最近请来一个日本人,最拿手的是“吞马术”,据说能把一匹活马吞进肚里。小满本想混进去,看看这吞马术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天外戏园的规矩跟南市的杂耍园子不一样,不是零打钱,得买票进去。小满就只好站在门口,假装看海报,两眼朝里边溜着。后来见这园子门口有个卖糖葫芦的,天津人叫“糖堆儿”,看年纪不大,就买了他一串糖堆儿,跟他闲聊。这孩子叫小尾巴,常年在这园子跟前卖糖堆儿。后来一来二去熟了,才听他说了一些这园子里的事。
这时,小满才告诉骡子,刚才这伙计叫黄七,其实是个安南人。
骡子听了,愣了一下。
安南人是天津人的说法儿,其实就是越南人。这些人当年是跟着法国人的军队来天津的,后来不打仗了,也就落下来,在法租界里混事。再后来,眼看法国人不行了,日本人在天津的势力越来越大,就又来投靠日本人,在日租界里为日本人干事。
小满又说,这黄七是于三儿跟前的人,还能说一口日本话。
骡子听了,没说话。
这时,骡子想起徐傻子说的话。
前一天傍晚,骡子收了摊儿,让端午和小满先回去,自己就奔南市牌坊这边来。骡子觉着徐傻子这人可交,平时又想听他说一些这“三不管”的事,所以一直说,想跟他喝一回酒,但忙忙叨叨的总没顾上。这个傍晚就过来,看他收摊儿没收摊儿。来了一看,徐傻子还没走,但已经把东西都装在排子车上了,就对他说,先别走,喝杯酒说说话。
徐傻子一听当然高兴,说,一直等着你这句话呢。
于是,他先把排子车拉到旁边一个不碍事的地方,让缝鞋的陈皮匠给照看一下,就跟着骡子来到街边的一个爆肚馆。骡子要了两碗水爆肚,又要了几个小凉菜,烫了两壶烧酒,两人就喝起来。看得出来,这徐傻子酒量不大,两盅酒喝下去,话匣子就打开了。骡子早就发现了,这徐傻子虽是摆茶摊儿的,按说对江湖上的事是个外行,但越是外行,说的话往往也越在裉节儿上。这个晚上,他一边喝着酒,一边摇头叹口气说,现在别说你撂地儿的生意难做,摆茶摊儿也一样不容易,这南市牌坊的跟前,从这头儿到那头儿一共有三个茶摊儿,从表面看,是你摆你的我摆我的,谁也碍不着谁,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心里都较着劲儿,你壶里沏的是哪种叶子,我壶里沏的是哪种叶子,互相都拿眼瞄着,你的茶叶稍差一点,下回人家喝茶的再打这儿过,就得绕着走了。说着就笑了,你们撂地儿的说起来,更如是,别管做哪路生意的,甭问,卖大力丸的绝不跟耍狗熊的争,耍弹变练的也不会跟相面算卦的争,真争的,都是做一路生意的,所以也才有那句老话,“冤家出在同行里”。
骡子不得不承认,徐傻子的这番话,真说到骨头里了。
接着,徐傻子就又说到那个于三儿。
骡子听了倒不以为然。这于三儿再怎么说,也是开园子的,又是洋人的戏法儿。洋人的戏法儿是单一路,行里叫“色唐立子”,跟自己是两回事,用天津话说,是“两河水儿”。
徐傻子却摇摇头,说,不是这么回事。
骡子听了,抬起头看看他。
徐傻子朝旁边看了看,伸过头说,有一件事,他跟你可是一河水儿。
骡子放下手里的酒盅,说,你说。
徐傻子说,兰大姑。
骡子立刻明白了。这一阵,这兰大姑总在街上夸自己,而且经常去西坑边的地儿上有意无意地照顾自己的生意。骡子也曾想过,如果真如徐傻子说的,这未必就是好事了。这一阵,小满也在街上听说,这于三儿看着是开园子的,其实也不是个善主儿。
徐傻子点头说,就是这意思。
接着,他又压低声音说,我一说,你就一听,最近,还是小心点。
骡子听了抬起眼,又看看徐傻子。
骡子回到天津,最想吃的就是天津的早点。
天津的早点就像烟卷儿,抽烟能上瘾。这早点,尤其是煎饼馃子和锅巴菜,吃着也能上瘾。所以天津人就是走到天边,也想家,其实想的不光是家,也是家里这煎饼馃子和锅巴菜。这两样东西不只是味道独特,还有个最大的特点,能解饱,用天津话说,也就是能搪时候。骡子最怕饿,一饿就心慌,只要早晨吃两套煎饼馃子,再喝一碗豆浆,天津人叫“浆子”,就能一直顶到下午。所以,每天早晨出来,端午就先去街边的摊儿上给骡子摊两套煎饼馃子。
但这个早晨,端午出来时一急,忘了带“挖单”。
挖单是变戏法儿时,蒙在身上的一块彩布,没有这块布,戏法儿也就没法儿变,于是赶紧回去拿。这一去一回,也就没顾上摊煎饼馃子,回来时,只给骡子带了两个枣儿饽饽。骡子看看时候不早了,也就没去徐傻子的茶摊儿,直接到西坑边的地儿上来。
骡子已经感觉到了,这些天,生意明显越来越好。以往来到地儿上,得先唱几段“开门柳儿”才能圆上粘子,现在不用了,每回带着端午和小满一到,就已经有人等在这里。听说话的意思,还有人是特意来的,不为看玩意儿,就想亲眼见一见这个骡子,听听他的柳儿。
当然,骡子的心里也明白,这应该是兰大姑一直在街上夸自己起的作用。
这个上午,骡子见场子人挺多,就使着劲儿地使了几个抹子活。
骡子有个习惯,在场上使活时,也看场子周围的人,但只看脸,不看眼。眼为心中之苗,别管什么人,一看眼,就容易看进去。平时看进去也就看进去了,但在场上不行,一看进去就容易分神。当初在奉天时,师父老何曾说过,彩立子撂地儿,跟在台上唱戏不一样,台上唱戏眼不能“馋”,一边唱着两眼往台下踅摸,非出毛病不可。但彩立子不行,眼还必须得“馋”,手里使着活,两眼得一直盯着场外,盯着,是为了看人的反应,你的活行不行,人家爱看不爱看,全都写在脸上,一发现不行,就得赶紧换,用他们吃开口饭的行话说,也就是“把点开活”。后来骡子才渐渐想明白了,场外的人爱看不爱看,是写在脸上,但不是写在眼上,所以只能看脸,不能看眼。看脸可以一目了然,而一看眼,也许就进去了。
这时,骡子发现,在场外站着几个人。这几个人抱着肩膀站在后面,但看得出来,都个头儿不高,挺壮,脸上没肉,皮像鼓面似的绷在腮帮子上。
于是心里明白,后面得加小心了。
这时,已经连着使了几个活,接着,又使了一个“碰花子”,也就是“杯中生莲”。这是个最好看的手彩,不光漂亮,也吉利,取“连连发财”“喜事连连”之意。场上顿时爆起一阵叫好。每回到这当口儿,端午就上去了,换下骡子,坐到旁边喝口水,也歇歇气。这时,骡子下来刚坐下,端午就过来,把一套煎饼馃子擩到他手里。
其实刚才,骡子在场上使着活已经一鼻子一鼻子地闻到了,觉着好像是煎饼馃子。这煎饼馃子要放生葱末儿,所以有一股很特殊的味道,哪怕在街上,老远就能闻见。当时骡子以为是场外的人,一边看玩意儿,一边在吃煎饼馃子,也就没在意。
这时低头看看手里,抬头问端午,这是谁摊的?
端午说,有人心疼你啊。
他又说,知道你爱吃,专门送来的呗。
说完,就扭头上场去了。
这套煎饼馃子还烫手,闻得出来,放了很多酱豆腐和辣酱,香味儿都窜鼻子。骡子先闷头三口两口地吃了,才抬起头问身边的小满,到底是谁送来的?
小满说,兰大姑。
骡子立刻扭过头,朝场子外面看了看。
小满说,她刚才放下就走了。
就在这时,骡子突然觉得有些累,还不是累,是困,好像也不是困,只是感觉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只想找个地方躺下,于是强撑着,晃了晃。
这时,小满也发现了,赶紧过来扶住他。
骡子使劲儿睁开眼,看着小满,只见他的嘴在动,声音却好像越来越远。
然后,就睡过去了……
骡子再睁开眼时,感觉自己是躺在一辆车上。这车一晃一晃的,好像是走在土道上。接着,就闻到一股马粪的味道。这才意识到,这应该是一辆牲口拉的大车。
坐在旁边的端午说,三天了,总算醒了。
骡子看看端午,发现她脸上有伤,一条胳膊也吊在胸前。
小满告诉骡子,那天上午,他吃了煎饼馃子刚睡倒,人群外面的几个人就跳进来砸场子。端午跟他们撕巴,也给打伤了。小满说,您要不是吃了这煎饼馃子,还不知会怎么样。
端午“哼”了一声,是啊,有人救了你啊。
骡子没说话,但已经意识到,自己是被使了门子。
接着,又闭上眼想,心想,离开这“三不管”,也好……
原刊责编 张雅丽
【作者简介】 王松,1956年生,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大量长、中、短篇小说,出版长篇小说单行本、个人作品集数十种。部分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并译介到海外。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