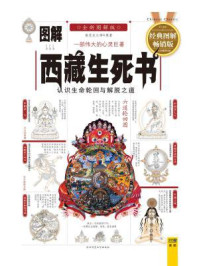虽然斯宾诺莎的哲学主要在于他反对上帝与世界之间以及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双重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是他的老师笛卡尔建立起来的,然而,在混淆和混用理由-结论关系和原因-结果关系上,他却依然忠实于他的老师;就他的形而上学来说,他甚至想从这种混淆中为他的形而上学获得比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更大的好处,因为他把这种混淆作为他整个泛神论的基础。
如果一个观念
潜在地
包含了它所有的本质属性,那么只通过分析判断就可以
明显地
从这个观念中把这些属性展示出来:它们的总和就是这个观念的定义。所以,这个定义与其观念本身只是形式上的差别,并无内容的不同;这是因为它正是由包含在这个观念中的那些判断所组成,并且就这些判断表现出它的本质来说,它们有在观念中存在的理由。从它们的理由来考察,我们同样也可以把这些判断看成是那个观念的结论。这样,一个观念与建立在它上面并通过分析从这个观念而推出的判断之间的关系,就恰恰是斯宾诺莎所谓的上帝与世界,或者一个唯一的实体与其无穷多的偶性之间的关系。“神,或包含无限属性的实体——神,或一切神的属性。”
 因此,它关系到了
认识理由
与其推论的关系;然而真正的有神论(斯宾诺莎的有神论只是名义上的有神论)则是这样来定义
原因
与结果的关系,在其中,原因始终是与结果不同并且与结果相分离的,这种关系不仅就我们考察它们的方式来说是如此,而且就它们本身来说也是真实地和本质地,因而永恒地是如此。平心而论,上帝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个带有人格特征的世界的原因,因此,非人格的上帝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然而,甚至正如斯宾诺莎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希求将上帝这个词加以保留,用来表示实体,并且明确地把它称为世界的
原因
。他在这样做的时候,除了完全将这两种关系加以混淆,并且混淆认识的理由的原则和因果性的原则以外,找不到别的方法。我想引证下面一段话来证明这一论断:“应当注意,凡任何存在的事物,必然有某种其所赖以存在的原因。并且应当注意,事物赖以存在的原因,不是包含在那个存在的事物的本性和定义内〔因为存在属于那个事物的本性〕,就必定在那个事物之外被给予。”
因此,它关系到了
认识理由
与其推论的关系;然而真正的有神论(斯宾诺莎的有神论只是名义上的有神论)则是这样来定义
原因
与结果的关系,在其中,原因始终是与结果不同并且与结果相分离的,这种关系不仅就我们考察它们的方式来说是如此,而且就它们本身来说也是真实地和本质地,因而永恒地是如此。平心而论,上帝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个带有人格特征的世界的原因,因此,非人格的上帝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然而,甚至正如斯宾诺莎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希求将上帝这个词加以保留,用来表示实体,并且明确地把它称为世界的
原因
。他在这样做的时候,除了完全将这两种关系加以混淆,并且混淆认识的理由的原则和因果性的原则以外,找不到别的方法。我想引证下面一段话来证明这一论断:“应当注意,凡任何存在的事物,必然有某种其所赖以存在的原因。并且应当注意,事物赖以存在的原因,不是包含在那个存在的事物的本性和定义内〔因为存在属于那个事物的本性〕,就必定在那个事物之外被给予。”
 在后一种场合他是指致动因,似乎是从后果而来;而在第一种场合,他指的则是一个纯粹的认识的理由。然而他将这二者等同起来,并以此为将上帝与世界等同起来开辟了道路,这正是他的本意。这就是他从笛卡尔那里学来的惯用手法。他用从外面而来的致动因替换了依赖于这个观念的认识的理由。“从神的本质的必然性,必然推出一切能处在无限理智概念之下的东西。”
在后一种场合他是指致动因,似乎是从后果而来;而在第一种场合,他指的则是一个纯粹的认识的理由。然而他将这二者等同起来,并以此为将上帝与世界等同起来开辟了道路,这正是他的本意。这就是他从笛卡尔那里学来的惯用手法。他用从外面而来的致动因替换了依赖于这个观念的认识的理由。“从神的本质的必然性,必然推出一切能处在无限理智概念之下的东西。”
 同时,他在任何地方都将上帝称为世界的原因。“一切存在的东西无不表现那种是一切事物原因的神的力量。”
同时,他在任何地方都将上帝称为世界的原因。“一切存在的东西无不表现那种是一切事物原因的神的力量。”
 “神是万物的固有因,而不是万物的超越因。”
“神是万物的固有因,而不是万物的超越因。”
 “神不仅是万物存在的致动因,而且是万物本质的致动因。”
“神不仅是万物存在的致动因,而且是万物本质的致动因。”
 “从任何一个给定的观念都必然有某种结果随之而出。”
“从任何一个给定的观念都必然有某种结果随之而出。”
 他还说:“一物如果没有外因是不能被消灭的。”
他还说:“一物如果没有外因是不能被消灭的。”
 证明:“作为不同于存在的本质、本性,因为物的界说是肯定该物的本质而不否定该物的本质,换句话说,它的定义是建立它的本质而不是取消它的本质,所以我们只要单独地注意一物本身,而不涉及它的外因,我们就绝不能在其中发现有可以消灭其自身的东西。”这意思是说,既然任何观念都不能包含与它自身的定义相矛盾的东西,也就是与它的全部属性相矛盾的东西,所以一个事物绝不能包含某种能成为使它毁灭的原因的东西。而这种观点,在稍嫌过长的第11命题的第二个证明中,被推向了极端,在其中,他将能够毁灭或消灭一个存在物的原因,与包含于一个定义中并导致这个定义毁灭的矛盾混同了起来。在这里,他是如此强烈地企图将原因和认识理由混同起来,以致他从不分开来说原因或认识理由,而是结合起来说“原因或理由”(ratio seu causa)。于是,为了掩盖他的诡计,这种情形在同一页中的出现达八次之多。笛卡尔在上面提到的公理中,也曾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证明:“作为不同于存在的本质、本性,因为物的界说是肯定该物的本质而不否定该物的本质,换句话说,它的定义是建立它的本质而不是取消它的本质,所以我们只要单独地注意一物本身,而不涉及它的外因,我们就绝不能在其中发现有可以消灭其自身的东西。”这意思是说,既然任何观念都不能包含与它自身的定义相矛盾的东西,也就是与它的全部属性相矛盾的东西,所以一个事物绝不能包含某种能成为使它毁灭的原因的东西。而这种观点,在稍嫌过长的第11命题的第二个证明中,被推向了极端,在其中,他将能够毁灭或消灭一个存在物的原因,与包含于一个定义中并导致这个定义毁灭的矛盾混同了起来。在这里,他是如此强烈地企图将原因和认识理由混同起来,以致他从不分开来说原因或认识理由,而是结合起来说“原因或理由”(ratio seu causa)。于是,为了掩盖他的诡计,这种情形在同一页中的出现达八次之多。笛卡尔在上面提到的公理中,也曾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这样,确切些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不过是笛卡尔本体论证明的实现。首先,他采用了上面我们引用的笛卡尔的本体论命题,“正是上帝本性的无限性,才是他不需要任何原因而存在的原因或理由”,并且,他经常说实体而不说神(在一开始时);他推论说:“实体的本质必然包含它的存在,因此实体一定是自因。”
 这样,被笛卡尔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同一个论证,被斯宾诺莎用来证明世界的绝对必然存在——它最终并不需要上帝。在命题8的附释2中,他讲得更加清楚:“正因为存在属于实体的本性,所以它的定义必然包含它的存在,因此只就实体的定义,就可推出它的存在。”但据我们所知,这个实体就是世界。命题24的证明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即在自身的定义中”,“因为一件事物如果就其本身来看其本身就包含存在,那么它就是自因。”
这样,被笛卡尔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同一个论证,被斯宾诺莎用来证明世界的绝对必然存在——它最终并不需要上帝。在命题8的附释2中,他讲得更加清楚:“正因为存在属于实体的本性,所以它的定义必然包含它的存在,因此只就实体的定义,就可推出它的存在。”但据我们所知,这个实体就是世界。命题24的证明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即在自身的定义中”,“因为一件事物如果就其本身来看其本身就包含存在,那么它就是自因。”
在笛卡尔那里是从纯粹 观念 和 主观 的意义上,也就是仅仅从 我们 、从 认识 的 目的 的角度来进行论述的东西,——在这个例子中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在斯宾诺莎那里则是从 真实 的和 客观 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他把这看作是上帝对世界的现实关系。在笛卡尔那里,上帝的存在包含在关于上帝的 观念 之中,因而这成为上帝真实存在的理由;在斯宾诺莎那里,上帝本身就包含在世界之中。这样,在笛卡尔那里只是认识的理由,到了斯宾诺莎那里就成了关于实在的理由。如果说笛卡尔在他的本体论证明的结论里,把上帝的存在说成是出自于上帝的本质,那么在斯宾诺莎那里则把它变成了自因本身,并且以此大胆地展开了他的《伦理学》:“所谓自因,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观念]即包含存在。”而对亚里士多德的告诫“存在不属于一物的本质”充耳不闻。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对于认识理由与原因的最明显的混淆。如果说那些惯于把词句错当成思想的新斯宾诺莎主义者(谢林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等等),经常沉湎于夸夸其谈,而对这个所谓的“自因”肃然起敬,那么在我看来,这个自因不过是要粗暴地割断永恒的因果链条的一个自相矛盾的词,一个前后的颠倒,一种对我们的无理要求,——简言之,在某种意义上恰如当看到自己够不着紧紧拴在钩子上的大军帽时就登上了椅子的奥地利人的所作所为。“自因”说的真正标志乃是明希豪森男爵,他骑着马落入水中时,就借助于“自因”的箴言,用腿夹住了他的马,并抓住了自己的辫子就把自己连同马一起提了出来。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伦理学》第Ⅰ部分的命题16。在这里我们看到,斯宾诺莎从该命题推断说:“从任何一物的定义里理智都可以推出这个定义事实上必然推出的许多性质,无限多的事物的无限多的样式是来自于神的本性的必然性”;因此毫无疑问,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与一个概念同它的定义的关系是同一的。然而,“神是万物的致动因”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是直接与此相联系的。在这里,认识理由和原因之间的混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后果了。但是,这也表现出我们这篇论文的题目的重要意义。
在力图把这个问题推向极端的第三个步骤中,谢林对这些谬误又贡献了一个小小的剧终余兴,——由于缺乏思想上的明晰性,前面两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曾坠入这种谬误之中。如果说笛卡尔碰到了不容改变的因果规律,这使他的上帝陷入了绝境,于是便采取将认识理由替换为所需要的原因的手法,以便平安地渡过难关;如果说斯宾诺莎从这种理由制造出一个实际的原因即自因,因而他的上帝就成了世界本身,那么,现在谢林则是使理由与结果在上帝自身之中就分裂了。
 他通过把问题提高到理由与结果的一个真正的、实在的本质,并且为我们引入了一个“在上帝之中并不是它自己本身,而是它的理由,这种理由作为一种原始的理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超越于理由的理由”的深不可测的东西,从而使事情更富于连贯性。这真是一种当之无愧的赞赏。大家知道,谢林是从雅可布·波墨的《人间和天上的神秘事物大全》中汲取了这一整套神话;但是在我看来大家所不太知道的,是雅可布·波墨自己又是从哪里找来这些东西,以及这所谓的深不可测的东西的诞生地又在何处,所以我想冒昧地提一提此事。这就是瓦伦汀派(公元2世纪的一个异端教派)的“无底深渊,超越于理由的理由”,它从自身的共同本质的沉寂中产生出理智和世界,正如伊伦诺斯(Irenäus)所叙述的
他通过把问题提高到理由与结果的一个真正的、实在的本质,并且为我们引入了一个“在上帝之中并不是它自己本身,而是它的理由,这种理由作为一种原始的理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超越于理由的理由”的深不可测的东西,从而使事情更富于连贯性。这真是一种当之无愧的赞赏。大家知道,谢林是从雅可布·波墨的《人间和天上的神秘事物大全》中汲取了这一整套神话;但是在我看来大家所不太知道的,是雅可布·波墨自己又是从哪里找来这些东西,以及这所谓的深不可测的东西的诞生地又在何处,所以我想冒昧地提一提此事。这就是瓦伦汀派(公元2世纪的一个异端教派)的“无底深渊,超越于理由的理由”,它从自身的共同本质的沉寂中产生出理智和世界,正如伊伦诺斯(Irenäus)所叙述的
 :“因为他们说,在那看不见的、不可名状的太空,有一个先天的存在,完满的永恒;他们把这叫作原始的混沌(Uranfang)、始祖(Urvater)或者原始根据(Urgrunnd)。他们说,它是处在极度的平静与安宁之中,万古长存,不可理解也不可感觉,不生不灭;而与它共存的就是思想,他们也把这称为
纯洁
和
沉寂
。这个原始根据有一次曾想到要从它自己那里显现出万物的开始,并且繁衍出后代,就像一个精子进入了子宫一样,进入了那一片沉寂的世界,——它决意这样来显示自己。现在这种受了精并且怀了孕的沉寂,产生出了理智,这是一个相似并等同于它的造物主的存在,并且只有它理解了其生父的伟大。他们也把这个理智称为万物之父或万物之始。”
:“因为他们说,在那看不见的、不可名状的太空,有一个先天的存在,完满的永恒;他们把这叫作原始的混沌(Uranfang)、始祖(Urvater)或者原始根据(Urgrunnd)。他们说,它是处在极度的平静与安宁之中,万古长存,不可理解也不可感觉,不生不灭;而与它共存的就是思想,他们也把这称为
纯洁
和
沉寂
。这个原始根据有一次曾想到要从它自己那里显现出万物的开始,并且繁衍出后代,就像一个精子进入了子宫一样,进入了那一片沉寂的世界,——它决意这样来显示自己。现在这种受了精并且怀了孕的沉寂,产生出了理智,这是一个相似并等同于它的造物主的存在,并且只有它理解了其生父的伟大。他们也把这个理智称为万物之父或万物之始。”
总之,这一定是通过异教史而传到了雅可布·波墨那里,而谢林的的确确又从波墨那里把它接收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