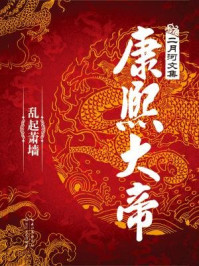如何解释中日两国对近代西方作出的不同回应,对治东亚史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个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迫使日本结束其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遂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全方位的工业化被延宕至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有关这两个国家并列发展的问题,詹森在他的著作中对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中日关系作了深入阐述
 。为了探讨中国的反应如此痛苦而迟滞的原因,历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伴随中国传统社会转变的“知识—伦理”问题上。现在我的研究正与这一主题有关。
。为了探讨中国的反应如此痛苦而迟滞的原因,历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伴随中国传统社会转变的“知识—伦理”问题上。现在我的研究正与这一主题有关。
列文森在20世纪50年代对此作了这样的阐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处在由‘天下’向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之中。”
 日本则不然,他们很早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民族认同感。中国人的那种“大一统”观念直至19世纪中叶受到近代西方冲击后才开始动摇
日本则不然,他们很早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民族认同感。中国人的那种“大一统”观念直至19世纪中叶受到近代西方冲击后才开始动摇
 。随后,思想领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新的世界意识直到19世纪末才确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调和现代观念与传统价值。
。随后,思想领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新的世界意识直到19世纪末才确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调和现代观念与传统价值。
在19世纪60—70年代,面对西方入侵和国内大规模的叛乱,为了恢复儒家秩序和王朝礼制,少数官僚和士大夫意识到中国需要“师夷长技”。由于他们试图捍卫的是传统儒家文化,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被视为“文化主义”,而非后来发展的民族主义。这种目的与手段(西方的技术)的内在矛盾,玛丽·C.莱特在她的书中已作了充分的阐述
 。刘广京的著作对“师夷论者”及早期以倡导改革而著称的儒家士大夫,如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冯桂芬(1809—1874)和郑观应(1842—1922)等作了充分的阐述
。刘广京的著作对“师夷论者”及早期以倡导改革而著称的儒家士大夫,如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冯桂芬(1809—1874)和郑观应(1842—1922)等作了充分的阐述
 。
。
在19世纪80—90年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民族主义的出现,它是建立在新的国家主权观念基础之上。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在对外政策领域已牢固地树立起国家主权观念。当时,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官员已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的概念,并能有策略地处理列强的要求,自觉维护国家的主权。石约翰在以德国要求租让山东为个案的研究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猛然醒悟过来,他们意识到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中国是极其脆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观念通过严复(1854—1921)的著作而家喻户晓。史华慈已对严复翻译斯宾塞、赫胥黎、斯密、孟德斯鸠、穆勒等人著作的思想意义作了透彻的剖析。他指出,严复所专注的是如何使国家富强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猛然醒悟过来,他们意识到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中国是极其脆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观念通过严复(1854—1921)的著作而家喻户晓。史华慈已对严复翻译斯宾塞、赫胥黎、斯密、孟德斯鸠、穆勒等人著作的思想意义作了透彻的剖析。他指出,严复所专注的是如何使国家富强
 ,这被视为改革的目标。张灏认为,1895年前后至20世纪初的10年是思想界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分水岭,期间至关重要的发展,不仅是人们放弃了“大一统”的观念,最终去接受国家观念,将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的政治目标,而且出现了现代的“国民观念”
,这被视为改革的目标。张灏认为,1895年前后至20世纪初的10年是思想界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分水岭,期间至关重要的发展,不仅是人们放弃了“大一统”的观念,最终去接受国家观念,将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的政治目标,而且出现了现代的“国民观念”
 。世纪之交,民族主义成为朝野知识精英政治理念的基调。“官僚民族主义”是实权派总督张之洞(1837—1909)决策的依据;“商业民族主义”激发“条约口岸”商人郑观应呼吁内在的制度变革
。世纪之交,民族主义成为朝野知识精英政治理念的基调。“官僚民族主义”是实权派总督张之洞(1837—1909)决策的依据;“商业民族主义”激发“条约口岸”商人郑观应呼吁内在的制度变革
 。事实上,19世纪末的变法维新运动,正是知识精英表达民族主义的最强音。
。事实上,19世纪末的变法维新运动,正是知识精英表达民族主义的最强音。
在19世纪末那些倡导改革的人群中,民族主义这一主流之下的支流是一种普遍的乌托邦主义。在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涛中,乌托邦主义是一条涓涓不绝的暗流。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书》是晚清阐述乌托邦主义的最具影响的著作。萧公权在他对康有为的研究中指出:康有为的民族主义观念和他对乌托邦的构想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发展的,后者与现实中国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即便如此,康有为的乌托邦主义对他的改革思想也产生过影响。彭泽周在比较研究了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日本明治初年的社会政治思想之后也揭示了这一点。他所做的关于康有为和福泽谕吉(1834—1901)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看法的比较研究让人深受启发。二人均崇拜斯密及其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福泽谕吉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哲学,并积极鼓励富人追逐利润。康有为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理想、优越的社会,他的理想社会是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即便如此,康有为的乌托邦主义对他的改革思想也产生过影响。彭泽周在比较研究了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日本明治初年的社会政治思想之后也揭示了这一点。他所做的关于康有为和福泽谕吉(1834—1901)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看法的比较研究让人深受启发。二人均崇拜斯密及其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福泽谕吉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哲学,并积极鼓励富人追逐利润。康有为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理想、优越的社会,他的理想社会是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在20世纪初的前10年中,接受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将这种理想主义转变为政治行动。普赖斯对这种乌托邦精神和民族主义如何激励了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作了分析。他们将这场革命视为通向“平等与自由的普遍道德秩序”进程中的“一幕不可阻挡的普世道德剧的一部分”
。在20世纪初的前10年中,接受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将这种理想主义转变为政治行动。普赖斯对这种乌托邦精神和民族主义如何激励了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作了分析。他们将这场革命视为通向“平等与自由的普遍道德秩序”进程中的“一幕不可阻挡的普世道德剧的一部分”
 。
。
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变法思想,不仅受到其知识取向的影响,且受到他们的社会政治身份的影响。如王韬,如果没有流亡沪、港的“条约口岸”而成为游离于正统秩序之外的知识分子,其变法思想将会有些不同。在对王韬的研究中,柯文将晚清的文化土壤分为沿海和内地,内地是传统秩序的中心,而沿海则处在直接面临西方文明冲击的文化边缘
 。
。
清朝个人的功名是决定其社会政治地位的最根本因素。然而,在19世纪末博得较高功名的人未必能享有崇高的地位,因为官僚机构早已饱和。不仅如此,此间由于人口增长及识字率的上升,围绕高功名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那些获得功名的士大夫要么不能入仕,要么被安排在微不足道的岗位上。当这种失落感与其民族主义的激情融为一体时,便助长了变法维新运动的火焰。
。那些获得功名的士大夫要么不能入仕,要么被安排在微不足道的岗位上。当这种失落感与其民族主义的激情融为一体时,便助长了变法维新运动的火焰。
我对黄遵宪(1848—1905)的研究将以前人对同类问题的研究为基础。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问题:甲午战争前中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现代化的。黄遵宪是第一位努力体认日本在受到西方冲击后发生巨变的中国人。他不仅对日本步武西方追求现代化感兴趣,而且关注日本的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以1877—1882年对日本的亲身考察为基础,撰著了一部充满魅力的《日本国志》。他在19世纪80年代呼吁国人应以严肃的眼光看待日本所取得的成就,并希望该书能对中国的变法起到借鉴作用。他关于明治时期的日本,特别是明治维新的论述,对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黄遵宪在这场运动中也扮演了一个领袖的角色。
在柯文的“社会—文化”图谱上,黄遵宪位于沿海与内地的中间地带,他被认为是“内地改革的先驱者”。作为举人,黄遵宪是一位合格的正统文化的精英,但他很快就踏上了中国驻外使馆官员的仕途,置身于王朝官僚体系的边缘。在通往中央官僚的仕途中,他不得不沿着一条近似于沿海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前行。换言之,他的仕途就是:受到那些需要外交人才的重臣举荐,最终作为高级候补官员受到皇帝的召见。就在他走向权力核心之际,其为官生涯被慈禧发动的政变打断。
黄遵宪的生涯代表了晚清帝国官僚流动的一种新模式。他是如何在仕途上谋求升迁的同时促进中国的变法?这也是我所要研究的一个子专题。
我用传记体的方法来展开此项研究,试图将黄遵宪刻画为一位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其独特的客家伦理背景,他的那些启迪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以及他在国内外的经历,共同塑造了他的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