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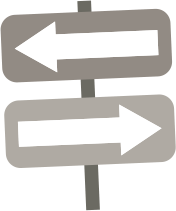 9 西安
9 西安
在 敦煌莫高窟,有着上千个人工开凿的洞窟,里面装饰着极为壮观的佛教壁画、文献、雕刻以及雕塑。它们被尘封了900年,直到1900年一个牧羊的小伙子误入一个小洞才意外发现了这些宝贝,因而与之前较早被发现的文物相比,它们保存得更为完好。
上次路过这里的时候,我曾在一位季先生开的旅馆吃饭。他待我极为周到热情,所以我想再次拜访他。我们俩志趣相投。季先生已经45岁了,但是他脸上毫无岁月留下的痕迹。他对自己的生意了如指掌,因为那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办起来的。他原来干农活儿,后来开始经营一个不起眼的早点铺,向其他农民售卖早餐。慢慢地他将早点铺扩张为一个能供住宿的设施齐全的旅馆。他热爱他的事业,他的员工也非常愿意为他效力,虽然工作时间长了点儿,但他们可以挣到比为政府部门工作更多的薪水。
季先生的饭店让我联想起300多年前美国荒凉的西部或英国的旅馆。它共有六间客房,每间有四张床,都是帆布床。卫生间在走廊尽头。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旅馆,随处可见。我们不愿意住在这样的老式旅馆,更喜欢那些专门招待外宾的新式的、更为舒适的友谊饭店。
我很想知道,近些年来,经济发展对他产生了何种影响。
季先生认出了我并热情招呼我,很高兴我又回来了。我和塔碧莎是唯一到过那里的外国人。我们很受欢迎,但对当地人而言我们是奇怪的外来访客,就像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亚拉巴马,我们以为中国人或巴基斯坦人是外星人一样。
我们坐在一张大桌旁,季先生坚持设宴款待我们。饭菜极为丰盛,有鸡肉和羊肉,拌着洋葱、大蒜和青葱的凉面,还有好多不在英语国家生长因而没有英文名字的蔬菜。我们身处沙漠中央,他居然能为我们弄到鱼。中国人不会长距离运输肉类,因此鱼肯定是在当地打捞的,这是中国人智慧的又一体现。
他说,大约一年前经济出现滑坡,但现在一切又恢复了。经济在复苏。
和全世界其他企业家一样,季先生工作总是超时——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时——忙于他的饭店业务,忙于挣钱。对他而言,工作不是负担,他乐此不疲,就像人们做着常做的事情一样。季先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他开心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一到嘉峪关——荒凉的西部沙漠与人潮拥挤的东部之间的历史分水岭——我们便出了事故。
连续几个星期,塔碧莎都是以每小时35~40英里的速度在双车道的柏油路上行驶。路两旁挤满了人。在中国,卡车、自行车以及行人从来不左右观望便径直涌入道路,这可真让人发狂。
我还能勉强适应,塔碧莎却不行。一位老人骑着自行车在她前面突然掉头,她被挡住了。路两边人太多而自行车就在她前面,她就要撞上人了。她紧捏刹车,猛摁喇叭,但前面那位老人可能耳朵有问题,也可能是故意不理她,因为在中国大型车辆得给小型车让路。她已经将速度降到每小时5~10英里,但是已停不下来,结果撞上了老人和他的自行车。
人群立刻涌了上来,警察赶到了。塔碧莎浑身颤抖,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于是上前处理。老人似乎伤得不重,但处于昏迷状态。虽然我看得很清楚事故不是塔碧莎的错,但依当地法律,她就是那个罪魁祸首。老人被人用手推车送往了医院。
围观的人群嘟嘟囔囔的,向我们投来厌恶的目光。警察担心我们再闹出事故,坚持要我们离开小镇。在美国,警察会领我们去警署,这样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但是在这里,他根本不担心找不着我们。我们太耀眼了,在该地区唯一的一条公路上,两个老外骑着两辆外国摩托车,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追捕到我们。
我们伤心地发动车子,沿着警察指示的方向行驶,等待他的处理。
不久,警察就在长城的最西端追上我们。
“你看,”他说,“你们得为那位老人以及他的家人作点补偿。”
得知他不是来逮捕我们的,我们松了口气。我问道:“好的,多少钱?”
“200美元。”
美元!在中国西部的黑市,200美元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收入甚至更多。
每次警察找我麻烦时,我都会索要收据,通常警察的气焰便会被压下去,因为他不知道我会将收据出示给谁看。
但是这位警察却毫不犹豫地给我收据。
我极不情愿地掏出钱,并请求他向那位受伤老人转达我们的关心。
我仍保留着那张在皱巴巴的纸上写着潦草汉字的收据。
汽油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国营加油站之间总是相距几百英里。在驾驶过程中,我们得一直盯着里程表,心里计算着什么时候又该加油了。
有一次,油箱快要空了,而我们还远离城镇。我们只好沿下坡路滑行,努力节省每一滴汽油。
我们来到一个四面环墙的军事哨所,走近其警卫室。我们使用手语,指着空了的油箱,试图说服他护送我们去军事基地的加油点。但是那个警卫并无权卖油,我们只好去找基地的司令官。
在陆司令简陋的办公室里,我们向他出示了护照、地图以及准许通行的文件。他皱起眉头。我们使出浑身解数,用尽各种会说的语言,包括当地语言、英语以及手语,向他解释说我们只是汽油用完了。
陆司令对我们两个骑着摩托车的西方人出现在他的国家中部感到一头雾水,而且令他更为震惊的是,我们居然进入了军事基地。
最后,我们告诉他,“要么以间谍罪逮捕我们,要么卖给我们点儿汽油”。
他笑了笑,指挥其手下给我们加油,而且任何人都不得收钱。
从嘉峪关出来几百英里后,油又快耗尽了。我们看见山边有人和小棚屋,路边摆着容量为10升、15升以及20升的汽油,用塑料罐和锡罐装着。路边的汽油黑市又一次救了我们。
在周游世界中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不必太担心耗油问题。在许多地方,黑市都会算好旅行者最有可能在哪儿耗尽汽油,然后在那儿守株待兔。譬如在中国,各城市之间相隔数百英里,黑市老板早就计划好把油运到最需要的地方,然后满心欢喜地卖给我们。
我们翻山越岭,最高曾到达海拔10500英尺,终于来到了兰州。这是个美丽的城市,风景优美如画。
我们参观了当地市场。和上次我到这里相比,市场规模扩大了,产品质量提高了,不过价格也涨了。由于不是丰收季节,加上没有人远距离运输农产品,一个小西瓜就卖2.7美元。
我四处寻找茶馆,这对于老外总是很困难的。如果问中国人哪儿可以找到茶馆,你总无法得到最直接的答案,因为开茶馆是不允许的。我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在1926年到芝加哥,要想找到地下酒吧也绝非易事。
在文化宫茶室,一群老人聚在这里,阳光透过茅草屋顶照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他们在这里玩扑克、骨牌还有麻将,消磨时光。茶室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准酗酒闹事、不准打架斗殴、不准乱说脏话”。一个表情痛苦、形容消瘦的中年歌手和一个三人小爵士乐队撕心裂肺地唱着,歌声里透着生活和爱情的残酷无情。可是人群里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脸上毫无生气,任由香烟的烟雾包围着,一副懒散、昏昏欲睡的样子,似乎他们已经看透茶馆外的生活。
他们看见我们甚是欢喜,递给我们小杯茅台,杯子很小巧,我们永远也不会喝醉。中国人谈起茅台的自豪语气就像南美人对波旁威士忌,或苏格兰人对苏格兰酒一样。茅台产自贵州,是用高粱和小麦酿造,再用五六年时间发酵的高度酒。酒的味道很怪,世上只有中国人才能习惯这种味道。喝完一杯,我就不敢再喝了。
我从女服务员那里买了一副中国扑克牌和两件夹克。夹克做得很时髦,上面绣着英文单词,但这里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单词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字母组合。虽然里面也有几个醉鬼,但茶馆的平静依然让我感到震惊。它让我想起了亚拉巴马围坐在商店、理发店或游泳池边的男人们,他们在那儿闲聊、喝酒、赌博,就想找个远离女人的地方。在这里,男人们可以叫上一壶茶、几瓶啤酒、几杯茅台,小赌一番,随意海侃,增进友情。没人规定女人不许入内,但在里面你永远也不会看见女人。酒馆是我祖父那个俄克拉何马州的酿酒师最爱待的地方。到了傍晚的时候,我祖母就会出来找他,风风火火地闯进各个牌室。她总是感到愤怒不已。每次当她费劲找到他时,她总是说:“可恶,我告诉过你不要再打牌了!”回想那时,俄克拉何马州很干燥,而酒是禁品,全靠私酒酿贩偷偷运来。有一个荷兰酿酒师居然在镇上享有盛名。他不仅拥有一家广播电台,还持有银行股份,而且是他那个阶层最受欢迎的年轻律师之一。我一直在想,他应该回国效力或者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更喜欢和好伙伴们聚在一起。
在兰州我发现空气污染很严重。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对烟囱进行控制。不过,在对待河流上,中国比其他大部分国家做得好一点,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捕鱼。而苏联地广人稀,人们在不经意间糟蹋了很多内河。
中国人只饮烧开过的水。我们住进宾馆时,宾馆就会给我们几个又大又漂亮的热水瓶,里面装满开水,可以24小时甚至48小时保温。我们可以用开水来泡茶或洗漱。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做法。既然热水瓶可以解决热水问题,又何必浪费燃料一直烧水呢?
从兰州到平凉,一路景色壮观。我们爬上一座高达7000英尺的山脊,沿顶端前进。在山脊上,中国人种植了茂密的树木来阻挡风沙。山坡两侧也种满了小树苗。
不知不觉,我们看见几个养蜂人和蜂箱,然后便是大片大片的蜂箱和众多的养蜂人。为了不被蜂蜇伤,我们压低头盔,戴上手套,全副武装起来。
我们了解到,这些养蜂人都是四处游走的,每人有5~50个蜂箱。不管养蜂人把蜂后带到哪里,工蜂都能紧随其后。从夏到秋,养蜂人根据花期,会在一个地方待上几天,等蜜蜂采完花蜜之后,再移到另一个地方。
无数只蜜蜂飞在空中,耳边全是嗡嗡声,这一壮观景色持续了15英里。养蜂人全家就在路边搭上帐篷,他们大多都不穿任何防护衣物,与蜜蜂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这是中国人生产力超强的又一例证。哪里有盛开的花朵,他们就把蜜蜂带到哪里,而不是让它们待在一个地方。由于蜜蜂的主人将采蜜期从几个星期延长到了半年,这些蜜蜂和中国人一样勤劳,它们的工作时间是其国外同类的6~7倍。
我们在中国还看到了许多其他的奇事,但没有一件比得上这绵延数英里的蜜蜂和养蜂人。就是这种生产率、智慧和勤奋,让我们相信,在21世纪,中国人会强于其他任何民族。
在两三百年前,西安被称为繁荣的“世界之都”。它的兴起早于罗马,也极可能比罗马更富裕。
自从衰败之后,西安便成为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个企业或民族的成功——尤其是巨大成功——往往孕育着衰落,甚至是毁灭。这正是这个真实的世界告诉我们的东西。随便列举几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埃及、玛雅、阿兹特克、罗马、希腊以及波斯,现在都已没落。
不过,西安仍是幸运的,辉煌的历史延续了它的生命。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长城的存在,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旅游中心,但是现在西安也成为游客关注的焦点。
2000年前,中国帝王去世后,他的陵墓会修建得十分豪华,还要有他在世的嫔妃、子嗣、大臣、护卫、厨师等人为他陪葬。后来有一位丞相不甘心自己将被陪葬的命运,便想出一个点子:为什么不按真人模样用陶建造雕像,然后让俑像而不是我们自己陪葬呢?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在位的皇帝,于是宫廷里所有人都有了自己的俑像。如今,被埋葬的8000兵马俑——士兵、战马、战车、将军、武器——都被挖掘出来,军队面向四面八方站立,保卫着死去的皇帝。
我曾见过这些兵马俑的照片,但当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时,感觉就如同看到了印度泰姬陵或美国大峡谷,我惊呆了。好几分钟我才缓过神来,明白这些面向八方站立的军队是真的,不是幻觉。兵马俑密密麻麻的,历经了几千年历史,每看一眼我都忍不住惊叹。
其他国家的博物馆曾展示过少量兵马俑,但要想真实地看见它们,真切地感受它们的威力,你必须到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是在1974年才被发现的,现在还在挖掘,谁知道在挖掘完之后还会有什么发现呢?现在,人们在西安才发现一个皇帝的陵墓,谁知道还有多少其他皇帝的陵墓呢?
和往常一样,我们住进全市最好的酒店——金花酒店。我们见到了酒店经理,名叫约翰·布朗,一个42岁的单身英国人。他的中部口音听起来并不地道。他管理着500名中国员工,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儿。她们打理着酒店,专门接待飞到西安参观兵马俑的外宾。酒店有自己的礼仪学校,手把手教这些女孩儿如何着装、化妆以及服务。对她们而言,这是一份极为荣耀的工作,就像35年前能当空姐一样。在这里我们听说,中国人被告知亲吻外国人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那会使他们生病。尽管如此,我还是对约翰的私人生活很好奇。
西安的旅游业极为兴旺,甚至许多教授都辞去工作到酒店担任职员。他们不认为这是身份的降低,而是获取金钱和名誉的途径。追求富裕生活的诱惑改变了人们的方向。
我们看见这里也有乞丐,但你一个星期看到的乞丐也没有在印度一个小时看到的多。他们在饭店外游荡,等待机会进来席卷桌上的残羹剩饭。他们不会干扰外宾。
我曾听说西安有一个巨大的鸟市。我们来回在市里穿梭,曾看见公园里坐着15~20位老人,每人手里提着一个鸟笼。鸟是中国宠物的精品:它不占空间,吃得又少。
不管怎样,我很想看看鸟市。可是我每次询问时,别人总告诉我根本没有,前两次旅行我都没有找到。这次,我在金花酒店和一群出租车司机混熟了,终于有位司机愿意带我们前往。
他开车带我们来到一个非常小的市场,和美国的起居室一样大小,里面卖些猫儿和狗儿。在当时的中国,猫儿和狗儿还不是流行宠物。塔碧莎和我打着手语,嘴里学着“啾啾”的鸟叫声,比画着告诉司机这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又去了几个错误的地方后,司机最后叫我们下车,用手指着前方,意思是接下来的路程我们得徒步走,车辆根本进不去。
他很英明。道路非常拥挤,人山人海。转过拐角,我们终于发现了大片的鸟市!道路两旁有数不清的鸟笼,有的放在地上,有的挂在自行车上,有的挂在树上,还有的挂在电线杆之间的绳子上。鸟品种齐全,有鸽子、长尾小鹦鹉、百灵鸟、金丝雀、燕子、画眉,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脑袋很漂亮的鸟儿。光是鸟儿就是几百种,还有其他养做宠物的奇怪的鸡、蛇以及金鱼。
鸟市上买方和卖方在砍价。当我们和一个卖主说话时,一只鸟飞出鸟笼,越过我们头顶,欲向山丘方向飞去。只见卖主伸出手来,一把便抓住了它,轻松得如同我从地上捡起一个苹果一样。我不知道是鸟儿更震惊些呢,还是我更震惊些。
还有两次我们看见卖鸟的人在空中抓住鸟儿翅膀的羽毛。我们唯恐错过什么,不知道该前进还是后退。我们猜想,鸟儿在这儿肯定是很廉价的商品,如同我家乡的猫儿一样。西安的鸟市充满着中国特色——高密度、商品堆积、人潮涌动。在这样拥挤的地方,出于好奇心,我们艰难地走完了鸟市。
自从回到美国,我便告诉朋友:“如果你去西安,一定要去看兵马俑,另外别忘了去看看鸟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