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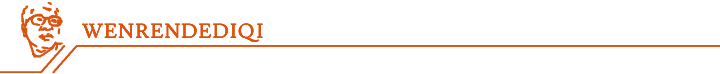
我为什么要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以往,我们总是讲思想史、学术史,我刻意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目的不是为了标新立异。
其实,早在民国时期,我们曾经把舆论界又称为言论界,也就是现在说的公共空间。我之所以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首先是要把它与思想史区别开来。在我看来,言论史关注的是当下,而思想史可以事后挖掘。比如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张中晓、顾准、林昭这些先驱者,他们当年的那些思想都是属于抽屉、档案柜,属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字,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没有一定的载体能够公开发表出来,所以他们只属于思想史,而无法进入言论史的视野。言论史当中的言论,必须通过某一载体,包括报纸、杂志或后来的广播、电视、互联网,乃至学校的讲台、公共集会上的演讲,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报刊这样的公共平台,通过这些载体表达出来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称作言论,而没有表达出来的,只是自己放在抽屉里,写给自己看的,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就不能成为言论史关注的话题。所以在中国言论史上,我们可能找不到顾准的身影,听不到张中晓的声音,更看不到林昭用鲜血写下的那些文字,这是言论史与思想史的不同。
其次,言论史和我们往常习惯所说的新闻史、报刊史、报业史也有很大的不同。言论史所涵盖的面要比新闻史、报刊史、报业史更大、更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新闻史是讲到鲁迅的,为什么会讲到鲁迅呢?不是因为鲁迅在新闻史或者报业史上有多么重要,或者他办过什么重要的报刊杂志,他是经手办过一些杂志,但那主要是一些文学期刊。在新闻史的格局中,鲁迅其实并不重要,我们之所以在新闻史上会讲到鲁迅,那是因为在鲁迅身后,他的地位被拔高了、被神化了,用三个“伟大”、七个“最”给鲁迅下的定语,就标志着鲁迅的地位已经不是与他身前实际身份相符的地位了。所以不论我们讲什么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乃至新闻史,都要把鲁迅写进去,甚至一章一节地写。实际上,讲新闻史是未必要讲鲁迅的。
那么言论史与新闻史的区分到底在哪儿呢?我想,比如说胡适办过《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你要把他写进新闻史、报刊史也是可以的,但他算不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而放在言论史上,胡适就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一生,始终恪守一句话,叫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八个字是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范仲淹还讲过一句比这更有名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实际上它的这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宋以来一千多年里,在中国读书人当中一直是十分重要的。胡适一生给他的朋友、学生留墨宝时,经常会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八字箴言,胡适的一生是与言论史分不开的。
还有一个人物,傅斯年,他是“五四”的学生领袖,但是在报刊史、新闻史上我们是找不到他的位置的——他虽然年轻时办过《新潮》,在新闻史上并不重要。但在言论史上,傅斯年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在1947年,他在中国言论界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无法比拟的。他在《世纪评论》《观察》《大公报》这些当时非常重要的报刊上发表了炮轰皇亲国戚、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大文章,当时影响之大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他的文章发表不久,宋子文就鞠躬下台了。当然历史研究表明,宋子文的下台,不仅仅是因为傅斯年写了几篇文章,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吁,还有其他一些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内耗、内斗的因素。但是,当中也确实包含了傅斯年、胡适等知识分子的努力在内。所以,放在言论史上,傅斯年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不仅是1947年,在1947年前,他在《新潮》上的言论,在《大公报》执笔的“星期评论”以及《独立评论》上的文章,都曾经影响了几代人。如果我们把视野局限在报刊史、新闻史,那么傅斯年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优秀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怀抱文章报国的理想,和推动中国文明进步所做出的努力,用言论史这个说法可能更能涵盖。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过很多的梦想。他们试图以实业报国,以教育报国,以科学报国,以乡村建设报国,这当中贯穿始终、影响巨大并形成了文人论政传统的,就是言论报国的理想。自1874年王韬先生在香港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具有评论性质的独立报纸《循环日报》,到1948年12月蒋介石下令关闭上海《观察》周刊,75年间,几代知识分子耿耿于怀的是他们的文章报国之志、言论报国之志。其中,涌现出了张季鸾、邵飘萍、林白水、胡适、鲁迅、傅斯年、王芸生、胡政之、储安平等一系列重要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来代替以往习惯的新闻史、报业史等说法,也为了与思想史这个说法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