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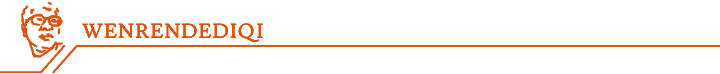
没有言论自由,就谈不上文明进步。在以往的史书中人们往往只重视那些怀抱宏大政治理想的献身者,他们毅然决然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民族重建的宏大叙事中,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我们不该忽略那些义无反顾、执着地争取言论自由的殉道者。而且从本质的意义上说,任何狭隘的政治信仰都是暂时的,政治的信仰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而人类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追求则是永远的,它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只要人类存在,就将继续为争取和捍卫这些神圣的原则而奋斗。
在百年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纪念碑上,不仅铭刻着无数先驱者的姓名,也铭刻着那些曾流星般划过夜空的报刊。
我总是忘不了1903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太炎先生在《苏报》发表的那些炽热的文字,少年邹容无所顾忌的青春呐喊,他的《革命军》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毫不含糊地向国人提出了创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尤其感动着我、震撼着我灵魂的是章太炎、邹容他们赴难时的表现,章太炎从容被捕之后,邹容本可幸免,但他毅然投案,在法庭上慷慨陈述,一丝畏怯也没有。邹容的作为让我想起了之前谭嗣同拒绝逃生的凛然选择,想起了之后秋瑾同样坦然地面对死神。我为本民族曾经拥有这样优秀的同胞一次次泪流满面,我为他(她)们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歌唱过、呐喊过而感到灵魂的温暖。少年邹容那一年只有18岁,他被租界当局判处2年徒刑(章太炎被判刑3年),最后惨死狱中,年仅20岁。他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称他为“大将军”。他的笑容永远停格在20岁如花的年华,但他的生命比一切即使活过了100岁的苟活者更长久。在神圣的死亡面前,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忘不了言论史上惨痛的一幕——1903年7月,“学识优良,性机警,广交游”的记者沈荩从外交界获得见不得阳光的《中俄密约》,在日本报纸全文披露,慈禧太后雷霆震怒。沈荩被捕,刑讯之下“慨然自承”。但根据清朝法律泄露公文并无重大罪罚,加上当时正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受到慈禧面责的权贵竟悍然将沈荩活活杖毙在公堂之上,打200多杖,“血肉飞裂,犹未致死”,最后用绳勒死。这是中国第一个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新闻记者,是20世纪为言论自由而死第一人,消息传出,报界一片大哗,纷纷发表评论责问当局。天津《大公报》全文刊出沈荩的绝命诗四首,详细报道了他被杖毙的残酷一幕,还登载了各国公使夫人觐见慈禧时对此表示不满的新闻。远在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写下了题为《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清廷不得不公布沈荩病死狱中的谎言,并在上海各报发表伪造的“绝命诗”。
我忘不了鉴湖女侠秋瑾在20世纪初甩下的沉重而悲愤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忘不了“人血馒头”和绍兴古轩亭。1907年,秋瑾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虽然仅出了两期,就因秋瑾的被捕就义而停刊,但这是中国最早的女报之一(在此之前,陈撷芬创办的《女苏报》可能是最早的女报),倡导女权平等,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在上个世纪初的暗夜里她倏地发出了妇女解放的先声。尽管这不是秋瑾被杀害的直接原因,但秋瑾为之牺牲的理想中无疑也包含了言论自由的理想。秋瑾就义之后,面对看客的冷漠和“人血馒头”的愚昧,上海各报纷纷发表的客观报道与评论也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我忘不了于右任百折不挠,在上海租界办报的那些日日夜夜,他手创的《神州日报》和《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特别是《民立报》直接呼唤了辛亥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转型。90多年后重读宋教仁他们发表在《民立报》上那些热情洋溢的政论,我们依然会受到震撼。
他们通过办报实现自己言论自由的理想,不为权势所屈服,不为金钱所诱迫,在100年前长夜如磐的清末,他们已深深懂得“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为报人之天职”,为此,《京话日报》的彭翼仲被发配新疆,《京话日报》及汪康年的《京报》、文实权的《公益报》等先后被封门。中国新闻史记载,仅据不完全统计,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间,至少有53家报纸被禁或被处分,17名报人被监禁,100多人被传讯、拘捕、警告或押解回籍,2名报人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