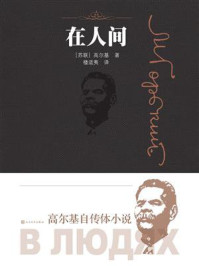在都灵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桥附近,一条狗站在码头上的渔夫身边。尚·菲列罗从上方的道路俯视着他们。他把摩托车停在人行道旁,把长手套和头盔搁在自己靠着的石护墙上。没有阳光,但是空气很闷,护墙石的颜色—罐子打开已久的榅桲果冻的颜色—在吸收热气。
小心,一个妇人的嗓音说,你不想它掉下去—她摸到那个头盔—还是你确实想?
她说的意大利语悠扬庄重,词语的含义不管多么平常,听着也像出自《圣经》。
“于是神就打发他离了伊甸园,去耕种他所从出的土地。”
按在头盔上的手和嗓音相称。如此细巧的手,主人往往有一头软缎般的头发、一种近乎伤口的表皮层的敏感,以及刚强的内心。
你没法从河里捞它出来,她说,河太脏,太臭了。
她进而用她的天使之手,摇晃护墙上的头盔。
是我们毁掉它的,她的嗓音继续说,我们什么都毁。
她的衣服又旧又有灰尘—像女人在集市上的一堆零碎衣裳中间翻拣、扔到一旁的那种衣服。她涂了口红—色调很大方,但涂得潦草,似乎她已不再能看见细巧的手指的动作了。
你可做的非常少,她说,你可做的好像永远也不会够。但是人必须继续。
有一天我要有个房子,但是不要在这凶险的山沟里。我要的房子每个窗子都能望见大海。妮农的家。一定有这样的地方。不是蓝色的海,是银色的海。我的房子里要有一间带餐桌的厨房,像克莱尔姑妈的那样,可以临窗切蔬菜。厨房里也要有一个梨木的餐具柜,像我们家楼下的那样。但是里面东西不同。那里不会塞满旧账单、照片、摩托车电池、由于太漂亮而从来不使用的碟子。我的餐具柜里要放又漂亮而我又会使用的碟子。在碟子上面那一格,我要放一列厚重的玻璃坛子,每个都有粗大的瓶塞—也许渔夫们肯给我几个他们让渔网漂在水中的软木浮子,每天早晨,我在卧室窗前都看见他们将大批的浮子拖到船上。我的玻璃坛子里面要存放糖、面包碎、咖啡、两种面粉、干蚕豆、脆玉米片、可可、蜂蜜、盐、帕玛森乳酪,还有给爸爸来访预备的蓝莓白兰地。
生命在于继续,护墙边的老妇人接着说,我们谁也停不下来。你从这儿拾起一样,你向那边带去一样,你醒来时有了个主意,你忽然想到你很久没有做某件事,你回家,把带回家的东西放进冰箱。每天你都在继续。你有留意那边那个带狗的男人吗?
有。
你有留意那带狗的男人?他是我丈夫。我的第二个丈夫。他先前在菲亚特上班。娶我没有带给他任何好处。我搞砸了他的人生。
尚·菲列罗背转身,解开皮夹克,把它放在护墙上。夏季的炎热来了。它会起起伏伏,一时凉爽些,一时热很多,袭来的狂风继以暴风雨,白蒙蒙的迷雾之中接连有昏昏欲睡的日子,但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如今的暑热会持续三个月方去。这缓解了未来的焦虑。也许会有绝望,尤其是百无聊赖的绝望,或是一阵突然而要命的疲倦。但是未来作为异样事物的威胁退得很远了。每天通向下一天,大致相同的日子。
你不穿夹克好。女人摸了摸放在护墙上的皮衣。品质很好!
尚·菲列罗的衬衣汗渍斑斑。
我努力把冰箱装满他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他从前喜欢的东西,她说。每天我都为他拿出一个什么。有时我试着给他惊喜,换他一个微笑。每天我都放回去一个什么。就像为旅行装备行囊。装备这冰箱是一门艺术,因为它很小,是从一辆拖挂式房车拿过来的。那房车报废了。把冰箱为他装满,这是我做的事。
三个穿牛仔裤的青年正在瞻仰人行道边的摩托车。
好美啊!
一小时三百公里!
表盘夸张了,不过她真可爱。
你觉得她有多重?
她很重。
又重又快。
看她成对的前灯。
好炫啊!
我丈夫打开冰箱的门,女人说,但只是为了给狗找点食物。我的丈夫,他失去了胃口。我去餐馆给狗找食物。不过,我永远不会拿餐馆后门交给我的食物去给我男人—这是个尊严问题。只有我亲手做的菜才配得上他。这是一生一世的任务。有一天他会再也不能吃下什么,包括他曾经那么喜欢的托尔泰利尼
 ,到那时,他们就会把他埋葬在那边的公墓里,那冰箱也会被扔到垃圾场上。
,到那时,他们就会把他埋葬在那边的公墓里,那冰箱也会被扔到垃圾场上。
阿斯克利皮欧街的理发师用左手一根手指按住我的头顶,让头静止不动,拿剃刀刮着我的脖子后面。老妇的嗓音从我耳边消失,另一个嗓音浮现了。
五百年前,嗓音说,有三位智者在公正的努希万
 面前,辩论在人生的深邃的愁海之中什么是最沉重的波浪。现在我认出这嗓音了。是来自亚历山大港的嘉里,他喜欢打断别人。一位智者说应该是疾病之苦,嘉里继续说道。另一位说应该是年老贫穷。第三位智者坚称,应该是死之将至而无所事事。最后,他们三个都同意,最后一种情形大概是最坏的。死之将至而无所事事。
面前,辩论在人生的深邃的愁海之中什么是最沉重的波浪。现在我认出这嗓音了。是来自亚历山大港的嘉里,他喜欢打断别人。一位智者说应该是疾病之苦,嘉里继续说道。另一位说应该是年老贫穷。第三位智者坚称,应该是死之将至而无所事事。最后,他们三个都同意,最后一种情形大概是最坏的。死之将至而无所事事。
他几乎没有捕捞过什么上来,老妇人在护墙边对尚说—几乎没有。我仅仅见过两回。你知道他平生的嗜好是什么吗?我来告诉你。柠檬曲奇!他酷爱曲奇。
尚·菲列罗注视着昼夜不停的暗沉沉的流水。
老妇人用她的天使之手打开钱包,宣告:我的钱不够。我有六千块,只是一包售价的一半!午休之后,他会就着他的黑咖啡吃曲奇。先生,也许咱俩,也许我们可以合着送给他一包柠檬曲奇?
信号工从他皮夹克的口袋里寻摸一点钱。
我学会写我的名字了:妮农。我坐在厨房的桌子前,书写。字母n像狗舌头的形状,字母i像种子在发芽,字母n的形状我说了,o是个吊环,n还是n。现在我会写我的名字了:Ninon。
尚·菲列罗坐在波河大道黄褐色的拱廊下的一张咖啡桌边。他面前搁着一杯卡布奇诺、一杯冰凉的水。这些水杯的闪光在整个城市无与伦比。他靠坐在椅背上;他已翻越重山。很可能,他祖父曾经到都灵来过一趟,跟公证人争吵一件事情。今天的拱廊呈现出旧档案的颜色,档案上的标签已经换过太多次了。一个笑声使他抬头。他花了点时间才找到那个在笑的人。是个女人的笑。不在拱廊内,不在酒吧里,不在报亭旁。那笑声听着像是来自乡间的一块田野。然后尚发现了她。她站在二楼窗边,在街对面,抖动着一块桌布还是床单。一辆电车驶过,但是他依然听见她的笑,电车过去后她也依然笑着,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粗胳膊短头发。没法知道她笑什么。她笑声停止的时候,非得坐下来喘气不可。
吉诺和我相爱了。我俯下身子。直起腰来的时候,我的膝盖会起褶子,褶子会微笑。我的中间是一个谜。这谜在肋骨开始,和我的裙子一样在比褶子略高的地方结束。我因为他而变得多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