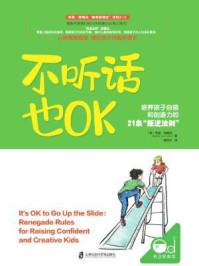认识戴维(David)是在2018年。他是个外形普通的白人男性,中等身材,棕色头发。医疗记录显示他的年龄是三十五岁,但他时常露出一种将信将疑的神情,这使他看起来似乎比实际年龄要小。当时我就想,他不会坚持来诊所的,咨询一两次后就不再来了。
但我知道我的预测未必准确。曾经有一些病人,我相信自己可以帮助他们,但事实证明他们的问题非常棘手,还有一些我认为没有康复希望的病人,结果他们的恢复力惊人。因此,现在看到新病人的时候,我会努力克制内心怀疑的声音,并牢记一点:每个人都有机会康复。
“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来这里。”我说。
戴维的问题始于大学,但更确切地说,是从他走进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那天开始。当时他二十岁,是纽约州北部一所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因为焦虑和糟糕的学业问题需要寻求帮助。
他的焦虑来源于与陌生人或不熟悉的人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脸会涨红,前胸和背部会出汗,思绪变得混乱。为了避免在众人面前发言,他选择了逃课。他曾两次放弃了必须参加的演讲和交流研讨会,最终在社区学院参加了同等课程才达到要求。
“你在害怕什么?”我问。
“我怕失败。我怕暴露自己的无知。我不敢寻求帮助。”
他花了四十五分钟进行预约,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完成了一份测试卷,然后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障碍(ADD)和广泛性焦虑障碍(GAD)。主持测试的心理医生建议他去看精神科医生,让医生开一种抗焦虑药物,以及(用戴维的话说)“治疗注意力缺陷障碍的兴奋剂”。他没有接受心理治疗或其他非药物性的行为矫正。
戴维去看了精神科医生,医生给他开了帕罗西汀(一种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选择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剂)和阿德拉(一种治疗注意力缺陷障碍的兴奋剂)。
“效果怎么样?我是说这些药的效果。”
“一开始,帕罗西汀确实能缓解焦虑。它让我不再流那么多汗,但并不能根治。我最终从计算机工程专业转到了计算机科学专业,我觉得这样会有所帮助,因为计算机科学专业不需要接触那么多人。”
“但因为我不敢发言,也不敢说我不会,所以我没有通过考试。后来补考也没有通过。然后我休学一个学期,以免我的平均学分绩点受到影响。最终我彻底放弃了工程学院,这真令我非常难过,因为我热爱计算机,并且想从事相关的工作。我成了一名历史专业的学生。这个专业的课堂规模较小,只有二十人,我可以不必与很多人打交道,还可以把答题卷带回家自己做。”
“阿德拉的效果怎么样?”我问。
“我每天早上上课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服用10毫克阿德拉,它能帮我集中注意力。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只是学习习惯不好。阿德拉能够弥补这一点,但它也导致我经常拖延。如果有考试,而我没有复习,我就会一整天连续服药,临时抱佛脚地准备考试。后来甚至到了没有它我就无法学习的地步,然后我开始想要更多的阿德拉。”
“这种药的获取困难吗?”
“不太难,”他说,“我总能知道什么时候该续药了。我会提前几天给精神科医生打电话。不会提前太久,也就提前一两天,所以他们不会怀疑。事实上,我的药可能……十天前就吃完了,但如果我只提前几天给医生打电话,他们会马上再给我开药。我还发现,最好是跟医生助理谈。他们一般不会问太多问题,而是直接续药。有时我会编造借口,比如说药店邮寄时出了问题。但大多数时候我用不着这么做。”
“听起来这些药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戴维停顿了一下,说道:“说到底,药物只起到了抚慰的作用。吃药可以缓解我的痛苦。”
2016年,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心理健康诊所向教职员工做了一场关于药物和酒精问题的演讲。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去过学生心理健康诊所了。那天我很早就来到现场,在前厅等待联络人时,我的注意力被墙上那些供人拿取的小册子所吸引。
一共有四种小册子,每种小册子的标题都包含“快乐”一词:快乐的习惯;良好的睡眠是通往快乐的道路;触手可及的快乐;七天让你变得更快乐。每本小册子里都介绍了获得快乐的方法:“写出五十件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观察镜子里的自己,并在日记中写出你喜欢自己的哪些地方”,“产生一系列积极的情绪”。
还有一段话最能说明问题:“优化时间管理与各种快乐策略。有意识地确定时间和频率。以做好事为例:通过自身实验,确定对你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每天做很多件好事,还是每天做一件好事。”
这些小册子表明,追求快乐已成为现代人的座右铭,它将“美好生活”的其他定义排除在外。甚至对他人的善举也被视为获得个人快乐的策略。利他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善行,它已经成为我们获取个人“幸福”的手段。
20世纪中叶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在其著作《治疗观的胜利》(
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 Uses of Faith After Freud
)中预见了这一趋势:“信仰宗教的人生来
 就渴望得到救赎;学习心理学的人生来就是为了获得快乐。”
就渴望得到救赎;学习心理学的人生来就是为了获得快乐。”
不止心理学在鼓励我们追求快乐。现代宗教也提倡将自我意识、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宗教体系作为最高善(the highest good)。
作家和宗教学者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在其著作《坏宗教》(
Bad Religion
)中,将新世纪“内心的神”(God Within)的宗教体系
 描述为“一种既具有普适性又能抚慰人心的信仰,使人获得不一样的快乐……没有任何痛苦……它是一种神秘的泛神论,在这种信仰中,神是一种体验,而不是一个人……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类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道德劝诫。人们不断呼吁‘同情’和‘仁慈’,但面临实际困境的人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指导。唯一的指导基本都是‘如果这么做让你感到快乐,那就这么做’。”
描述为“一种既具有普适性又能抚慰人心的信仰,使人获得不一样的快乐……没有任何痛苦……它是一种神秘的泛神论,在这种信仰中,神是一种体验,而不是一个人……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类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道德劝诫。人们不断呼吁‘同情’和‘仁慈’,但面临实际困境的人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指导。唯一的指导基本都是‘如果这么做让你感到快乐,那就这么做’。”
2018年,凯文(Kevin)的父母带他来找我,当时他十九岁。父母担心他不上学,保不住工作,也不会遵守任何家规。
和其他人一样,凯文的父母也有缺点,但他们一直在努力帮助凯文。他们既没有虐待他,也没有对他不闻不问。但问题是,他们似乎无法约束凯文。他们担心提出要求会“让他感到压力”或“使他受到创伤”。
孩子的心理是脆弱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观念。在古代,孩子被视为缩小版的成年人,他们出生后就完全成形了。大多数西方文明认为,人之初,性本恶。父母和监护人的任务是用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从而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为此可以使用体罚和恐吓等策略来规范孩子的行为举止。但这种做法在现代社会已不被认可。
今天,我看到很多父母会担心自己做的事或者说的话会给孩子留下心理创伤,导致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忍受情感痛苦甚至精神疾病。
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他开创了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幼儿时期的经历,即使是那些早已被遗忘或长期存在于意识之外的经历,也会造成持久的心理伤害。不幸的是,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早期创伤会影响成人精神病理学,这一观念已经演变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即任何困难的经历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在日后需要接受心理治疗。
我们不仅在家里努力让孩子远离不良的心理体验,在学校也是如此。在小学阶段,每个孩子都会获得相当于“本周之星”的奖励——并非因为孩子取得了什么成就,这种奖励一般都按字母顺序轮流发放。每个孩子都被教育要警惕霸凌者,遇到霸凌事件时不要做旁观者,要挺身而出。在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讨论引发不良反应的诱因和安全空间。
父母的养育和教育都受到了发展心理学和同理心的影响,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化。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个人的价值并非取决于他取得的成绩,我们应当停止校园和其他任何地方的身体和情感暴力,创造安全的思考、学习和讨论的空间。
但我担心,他们的童年被过度净化,甚至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在一个相当于软壁病房的环境中抚养孩子,孩子不会受伤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法为步入这个世界做好准备。
保护孩子免受逆境之苦,是否让他们对逆境产生了极度的恐惧?使用虚假的赞扬,规避现实世界的影响,以此来提升孩子的自尊,是否会让他们变得狭隘、自负,对自己的性格缺陷一无所知?满足孩子的所有欲望,这个时代是否在鼓励一个新的享乐主义?
在第一次会面时,凯文就向我分享了他的人生哲学。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被吓坏了。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我想待在床上,我就待在床上。如果我想玩电子游戏,我就玩电子游戏。如果我想吸一管可卡因,我就给毒品贩子发短信,他会顺路把可卡因捎给我,然后我就吸上一管。如果我想做爱,我就上网找人,跟她们见面,然后做爱。”
“结果怎么样,凯文?”我问。
“不太好。”有一瞬间,他看上去很羞愧。
在过去三十年里,我看到越来越多像戴维和凯文这样的患者,他们占尽了生活里的一切优势——能够提供支持的家庭、优质的教育、稳定的经济、良好的医疗条件,但他们却出现了退缩性焦虑、抑郁和身体疼痛等问题。他们不仅没有发挥自己的潜力,甚至连早上起床都做不到。
我们为了打造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而不懈努力,这也为医学实践带来了变革。
在20世纪之前,医生认为一定程度的痛感有益健康
 。19世纪大多数外科医生都不愿意在手术中采用全身麻醉,因为他们认为疼痛能够增强免疫和心血管反应,加速身体的恢复。虽然据我所知,没有证据表明疼痛会切实地加速组织修复,但有新的证据显示,在手术中使用阿片类药物
[1]
会降低组织的修复速度。
。19世纪大多数外科医生都不愿意在手术中采用全身麻醉,因为他们认为疼痛能够增强免疫和心血管反应,加速身体的恢复。虽然据我所知,没有证据表明疼痛会切实地加速组织修复,但有新的证据显示,在手术中使用阿片类药物
[1]
会降低组织的修复速度。
17世纪的名医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对于痛感的观点是:“我认为……尽一切努力完全抑制疼痛和炎症反应是非常危险的……毫无疑问,让四肢产生适度的疼痛和炎症,这是大自然为了实现最明智的目的而使用的工具
 。”
。”
相比之下,我们希望今天的医生能够消除所有疼痛,这才是富有同情心的治疗师应当发挥的作用。任何形式的疼痛都被视为危险的,不仅因为疼痛本身,还因为人们认为疼痛会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神经创伤,激发大脑对未来可能产生的痛感做出反应。
大量让人感觉良好的处方药
 也能让我们看到疼痛范式的转变。如今在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和超过二十分之一的儿童
也能让我们看到疼痛范式的转变。如今在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和超过二十分之一的儿童
 每天都在服用精神治疗药物。
每天都在服用精神治疗药物。
在世界各国,帕罗西汀、百忧解和西酞普兰等抗抑郁药的使用量都在增加
 ,其中美国位居各国之首。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每1000人中有110人)服用抗抑郁药,其次是冰岛(106/1000)、澳大利亚(89/1000)、加拿大(86/1000)、丹麦(85/1000)、瑞典(79/1000)和葡萄牙(78/1000)。在25个国家中,韩国排名最末(13/1000)。
,其中美国位居各国之首。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每1000人中有110人)服用抗抑郁药,其次是冰岛(106/1000)、澳大利亚(89/1000)、加拿大(86/1000)、丹麦(85/1000)、瑞典(79/1000)和葡萄牙(78/1000)。在25个国家中,韩国排名最末(13/1000)。
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德国的抗抑郁药使用量增加了46%,同一时间段内,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抗抑郁药使用量增加了20%。虽然我们尚未统计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的数据,但通过观察销量趋势可以推断,这些国家的抗抑郁药的使用量也在增加。在中国,2011年抗抑郁药的销售额达到26.1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19.5%。
2006年至2016年,美国兴奋剂处方(阿德拉、利他林) [2] 的数量翻了一番,其中还包括为五岁以下儿童所开的处方。2011年,在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障碍的美国儿童中,三分之二的患儿都服用了兴奋剂。
苯二氮卓类镇静药物(阿普唑仑、氯硝西泮、安定)也具有成瘾性
 ,或许是为了抵消服用兴奋剂所带来的影响,这类药物的处方量也在增加。1996年至2013年,美国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成年人数量增加了67%,从810万人增加到1350万人。
,或许是为了抵消服用兴奋剂所带来的影响,这类药物的处方量也在增加。1996年至2013年,美国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成年人数量增加了67%,从810万人增加到1350万人。
2012年,全美阿片类药物的处方量足以让每个美国人拥有一瓶药片。不仅如此,美国阿片类药物服用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也已超过枪支或车祸造成的死亡人数。
如此一来,戴维认为他应该用药片来麻痹自己,似乎也不足为奇。
抛开这些逃避痛苦的极端案例不谈,事实上,哪怕只是轻微的不适感,我们也无法忍受。我们不断分散对当下的注意力,去寻求快乐。
正如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重返美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Review
)中所说:“一个体量庞大的大众传媒行业,基本上它并不关心对错,而是关心些虚构的、几乎完全不着边际的东西……未能周全考虑到人对消遣的爱好乃是无穷无尽的
 。”
。”
同样的,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著作《娱乐至死》(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的作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也写道:“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
 。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而是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
。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而是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
我有一位名叫苏菲(Sophie)的病人,来自韩国,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她因为抑郁症和焦虑症前来咨询。我们谈了很多事情,她告诉我,除了睡觉以外,其余时间她基本都要连着一个电子设备:刷Instagram、看YouTube上的视频、听播客和音乐播放清单。
我建议她尝试走路去上课,路上什么也不要听,让自己的想法浮现在脑海中。
她用既怀疑又害怕的眼神看着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道。
“好吧,”我谨慎地斟酌语言,“这是一种熟悉自我的方式。你可以尽情地体会身体的感受,不要试图控制或逃避。用电子设备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可能只会加重你的抑郁和焦虑,一直回避自己会让你精疲力竭。我想,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去体会自我,也许你会产生新的想法和感受,并帮助你体会到与自己、与他人以及与世界的更深入的连接。”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但这么做太无聊了。”
“是的,的确如此,”我说,“无聊不仅仅是乏味,它可能还会令人恐惧。它迫使我们直面有关意义和目的的大问题。但无聊也是一个发现和创造的机会。它为新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没有它,我们就要无休止地对周围的刺激做出反应,从而无法产生真切的体会。”
接下来的一周,苏菲尝试走路去上课,并在这个过程中不使用任何电子设备。
“一开始很难,”她说,“但后来我习惯了,甚至有点儿喜欢这种方式。我开始注意到那些树。”
回到戴维的故事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整天吃药”。2005年他从大学毕业后就搬回家与父母同住。他曾想过去上法学院,于是参加了LSAT考试(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还不错,但想到要去申请,他又放弃了。
“我几乎一直坐在沙发上,内心积聚了对自己和世界的愤怒和怨恨。”
“你为什么生气?”
“我觉得自己浪费了本科的学习时间,没有学习我真正想学的东西。我的女朋友还在读书……她成绩很好,拿到了硕士学位,而我却在家里无所事事。”
戴维的女朋友毕业后在帕洛奥图(Palo Alto)找到一份工作。戴维跟随她去了那里,2008年二人结婚。戴维在一家科技初创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那里有年轻聪明的工程师,他们很乐意拿出时间与戴维相互交流。
于是戴维重新开始编程,学习了他原本想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所有内容,但他还是不敢去都是学生的房间。他被提升为软件开发者,每天工作十五小时,在工作之余每周跑步三十英里。
“为了做到这一切,”他说,“我服用了更多的阿德拉,不只是早上,而是一整天连续服药。早上醒来吃阿德拉。晚上回家,吃晚饭,然后吃更多阿德拉。吃药变成了我的生活常态。我还会喝大量咖啡。到了晚上,我需要睡觉,然后我就想:现在该怎么办?于是我又去找精神科医生,说服她给我开了安必恩。我假装不知道安必恩是什么,但其实我的母亲和几个叔叔都在长期服用这种药。在软件发布会之前,我还说服医生给我开了一点儿用于治疗焦虑症的劳拉西泮。从2008年到2018年,我每天服用30毫克的阿德拉、50毫克的安必恩,以及3到6毫克的劳拉西泮。我想:我有焦虑症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我需要用这些药物进行治疗。”
戴维将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归咎于精神疾病,而不是睡眠不足和过度刺激,他用这种逻辑来证明自己继续服药的合理性。多年来,我在许多患者身上都看到过类似的恶性循环:他们服用处方药或其他药物,企图弥补自我关爱的不足,然后将药物带来的问题归咎于精神疾病,因此又需要更多的药物。就这样,毒药变成了维生素。
我开玩笑地说:“你好像在吃A族维生素:阿德拉、安必恩和劳拉西泮。”
他笑着说:“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你妻子或其他人知道这些情况吗?”
“不知道,没人知道,我妻子也不知道。有时候安必恩吃完了,我就会喝酒,或者吃了太多阿德拉的时候,我会发怒并对她大喊大叫。但除此之外,我把它藏得很好。”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厌倦了。厌倦了日日夜夜服用兴奋剂和安定剂的日子。我开始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样就解脱了,其他人也会生活得更好。但我的妻子怀孕了,所以我知道,我必须改变。我告诉她我需要帮助,让她带我去医院。”
“她有什么反应?”
“她带我去了急诊室,当结果出来时,她感到很震惊。”
“为什么震惊?”
“因为那些药片,我正在吃的所有药。我所藏匿的药,以及究竟我藏了多少药。”
戴维被诊断为兴奋剂和镇静剂成瘾,被送进精神科住院病房。他一直待在医院,直到他戒掉了阿德拉、安必恩和劳拉西泮,并且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整个过程花了两周的时间。他出院回家,和怀孕的妻子住在一起。
我们都在逃避痛苦。有些人选择吃药,有些人选择窝在沙发里,一边上网冲浪一边在网飞(Netflix)上刷剧,还有一些人选择阅读爱情小说。我们总会做点儿什么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然而,所有这些试图让自己远离痛苦的努力似乎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痛苦。
《世界幸福报告》
 (
World Happiness Report
)对156个国家的公民幸福感进行了排名。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居民的幸福感低于2008年。其他在财富、社会支持和预期寿命方面程度相近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日本、新西兰和意大利,居民自评的幸福指数也出现了下滑。
(
World Happiness Report
)对156个国家的公民幸福感进行了排名。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居民的幸福感低于2008年。其他在财富、社会支持和预期寿命方面程度相近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日本、新西兰和意大利,居民自评的幸福指数也出现了下滑。
研究人员采访了二十六个国家的近十五万人,以确定广泛性焦虑障碍的患病率。广泛性焦虑障碍表现为过度且无法控制的担忧,从而对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研究人员发现,与落后贫穷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焦虑症发病率更高
 。作者写道:“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这种疾病在高收入国家更加普遍,危害更大。”
。作者写道:“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这种疾病在高收入国家更加普遍,危害更大。”
1990年至2017年,全球抑郁症病例增加了50%
 。增速最快的是社会人口指数(收入)最高的地区,尤其是北美地区。
。增速最快的是社会人口指数(收入)最高的地区,尤其是北美地区。
此外,有越来越多的人的身体出现了疼痛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包括一些健康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疾病或组织损伤,但依然会感觉全身疼痛。这种无法解释的身体疼痛综合征的患病人数逐渐增加,类型也日益多样化:复杂的局部疼痛综合征、纤维肌痛、间质性膀胱炎、肌筋膜疼痛综合征、骨盆疼痛综合征等。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包括一些健康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疾病或组织损伤,但依然会感觉全身疼痛。这种无法解释的身体疼痛综合征的患病人数逐渐增加,类型也日益多样化:复杂的局部疼痛综合征、纤维肌痛、间质性膀胱炎、肌筋膜疼痛综合征、骨盆疼痛综合征等。
研究人员向全世界30个国家的居民提出以下问题和选项:“在过去四个星期里,你的身体是否感到过隐痛或疼痛?从来没有;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感到身体疼痛的频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
34%的美国人表示他们“经常”或“非常频繁”地感到疼痛,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为19%,日本有18%,瑞士有13%,南非仅有11%。
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空前富裕、自由、技术先进和医疗发达的时代
 ,我们却比以往更加不快乐,更加痛苦?
,我们却比以往更加不快乐,更加痛苦?
我们之所以如此痛苦,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规避痛苦。
[1] 在手术中使用阿片类药物:维多利亚·K.尚穆加姆、卡拉·S.科奇、肖恩·麦克尼什、理查德·L.阿姆杜,《针对慢性创伤的阿片类药物治疗与愈合率之间的关系》,《创伤修复与再生》( Wound Repair and Regeneration )25,第1期(2017):120-30,https://doi.org/10.1111/wrr.12496。
[2] 兴奋剂处方(阿德拉、利他林):布莱恩·J.派珀、克里斯蒂·L.奥格登、奥拉佩朱·M.西莫扬、丹尼尔·Y.钟、詹姆斯·F.卡吉亚诺、斯蒂芬妮·D.尼科尔斯、肯尼斯·L.麦考尔,《2006年至2016年美国与各地区处方兴奋剂的使用趋势》,《公共科学图书馆期刊》( PLOS ONE )13,第11期(2018),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