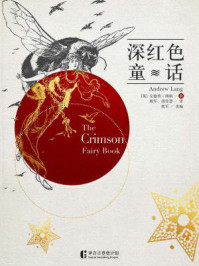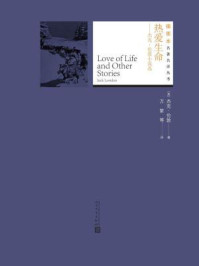杰夫把手上的牌一张一张地甩到假日酒店那深绿色的床罩上,正面朝上。他以最快的速度将牌从不断变少的扑克牌中发出去,同时,弗兰克以熟悉的催眠语调在一旁念念叨叨:“加四、加四、加五、加四、加三、加三、加三、加四、加三、加四、加五——停!底牌是张A。”
杰夫慢慢地将方块A翻过来,然后两个人都笑了。
“哈,太妙了!”弗兰克得意地大笑几声,用力一拍床罩,把牌全都弹到了空中,“我们真是最佳拍档,兄弟,我们将所向披靡!”
“来瓶啤酒吗?”
“妈的这还用说!”
于是杰夫放下交叉的双腿,起身穿过房间,朝桌上的冷饮走去。一楼房间的窗帘开着,他一边撬开两瓶库尔斯啤酒的瓶盖,一边用爱慕的眼神,深情地盯着他那辆停在路边,在图库姆卡利旅馆停车场的灯光照耀下正闪闪发亮的灰色全新斯蒂贝克亚凡提。
从亚特兰大开回来,这辆车一路上已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和评价,而在接下来前往拉斯维加斯的途中,估计受到的关注同样不会少。坐在这辆车里,杰夫感觉无比轻松自在,其“未来主义”风格的设计和仪器设备甚至让他获得了某种安慰。这种有着长长车头、较短后车厢的机器,即使在一九八八年看上去也是最先进的,非常吸引眼球;说真的,他似乎记得八十年代还有一家独立制车厂依然在生产限量版的亚凡提。对身处一九六三年的他来说,这辆车,就像是时光旅行中的同伴,是在属于他的那个年代印象中疾驰的豪华防护壳。如果说老雪佛兰唤起了他对旧日时光的怀念,那亚凡提引发的则是他对未来更加强烈的想念。
“喂,说好的啤酒呢?”
“来啦。”
他递给弗兰克一瓶冰啤,然后拿起自己的那瓶,喝了一大口。五月底马多克一毕业,他俩就出发了。杰夫很久没去上课,己经被退了学,不过他一点也不在意。马多克想去南方,在新奥尔良停留几天庆祝一下,但杰夫坚持走更近的路线,即沿着伯明翰、孟菲斯和小岩城走。在这些城市周边,每几百英里就有段新建成的州际公路,限速七十或七十五,这些平坦宽阔的偏僻路段,让杰夫得以将亚凡提最高一百六十迈的时速发挥到极致。
那晚和朱迪·戈登的失败约会带给杰夫的沮丧和怅然,多半都被德比赛马会胜利的喜悦给驱散了。自那以后,除非擦身而过,他再也没有在校园里见过她。他也无须再为应该如何解释自己的处境而苦恼,除了清晨醒来的那些时候,大脑会寻找着无法找到的答案。不管真相可能是什么,至少他现在有证据可以证明,他对未来的认知并不只是幻想。
到目前为止,杰夫总有办法引开弗兰克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让他能够赢得如此惊人的胜利?现在,马多克以为杰夫是个有先天缺陷的天才,懂得某种神秘之术。这种形象,在杰夫拒绝在德比赛马会后两个礼拜举行的普里克尼斯赛马会上继续下注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他确定夏多克会赢得该年度三冠王系列赛事的其中两场,却记不得是哪匹马输了德比赛马会后面的哪项比赛,因此,他不顾弗兰克的反对,坚持只当旁观者。结果,糖果斑点以三个半马身的差距拿下了比赛。至此,杰夫不仅确定了即将到来的贝尔蒙特赛马会的赢家,更确信糖果斑点的再度崛起,必定会推动夏多克的赔率飙升。
赌赋予了杰夫新的使命感,让他从玄学和哲学的绝望泥潭中抽身,不再挖掘深藏其中对自身处境的解答。否则,即便他现在还没精神错乱,可再这么为那些难以解释的事费神上一两个月,最后也会被逼疯。赌博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直接得令人欣慰:非赢即输、要么是借方要么是贷方、不是对就是错。就这么简单,没有模糊地带,没有其他猜疑;特别是在你已经提前知晓了结果的时候。
弗兰克已将四散的牌收拾好,正在切牌、洗牌。“嘿,”他说,“咱们玩两副牌吧!”
“好啊,有何不可?”杰夫张腿跨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他拿过牌重新洗了一遍,然后开始发牌。
“加一、加一、零、加一、零、减一、减二、减二、减三、减二……”
杰夫满足地听着一连串熟悉的数数,计算发下来的一点和十点张数。弗兰克正废寝忘食地背诵着一本新书中的图表,该书名为《击败庄家》,是关于计算机研究出来的二十一点下注策略。杰夫亲自看过后才知道,这种算牌术有多么管用。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各大赌场已经开始禁止使用这些手法的玩家进场。然而,在这个时代,庄家和赌区经理们欢迎所有会算牌术的玩家,当他们是好骗的傻瓜。弗兰克应该玩得很好,至少能保本。而且,如果二十一点牌桌上赢钱的快感能让他专注于赌局上,或许能稍微转移下他的注意力,不再过分关注杰夫有望在贝尔蒙特赛马会上赢得的惊人胜利。
“减一、零、加一——停!底牌是十点。”
杰夫将梅花J展示给弗兰克看,然后两人击掌庆祝。弗兰克喝光啤酒,把瓶子放到床头的半打空瓶旁。“嘿,”他说道,“进城那会,我们经过的一家汽车影院在放《诺博士》,想不想去看看?”
“拜托,弗兰克,那部电影你都看过几遍了?”
“三四次吧,每次看都觉得比前一次好。”
“你够了啊,我已经看了够多的詹姆斯·邦德了。”
弗兰克疑惑地看着他,“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就是不太想去而已。你把车开去,钥匙在电视机上。”
“你怎么了,在帮教皇服丧吗?我可不知道你还是天主教徒呢。”
杰夫大笑,伸手拿起鞋子。“胡说八道什么呢,好吧我去,至少不是罗杰·摩尔演的。”
“罗杰·摩尔又是什么鬼?”
“此人有一天会成为圣徒的。”
弗兰克摇摇头,皱起了眉头。“我们现在说的是罗马教皇的死,还是詹姆斯·邦德,还是别的什么啊?知道吗,兄弟,有时候我真心不懂你丫到底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弗兰克,我也不知道啊。走吧,看电影去,我们正需要暂时逃离一下现实。”
第二天他们轮流开着亚凡提,一路前往赌城拉斯维加斯。杰夫从没去过内华达州,比起他记忆中电影和电视里呈现的八十年代歌舞秀,霓虹灯饰装点下的脱衣舞场显得比较冷清,少了点张牙舞爪的奢华与俗丽。这是霍华德·休斯
 之前的赌城,他会意过来,这是希尔顿和米高梅大手笔创建大型赌场饭店前的赌城。现如今,那些占据了内华达州六〇四号公路上这一小片超现实世界的,是战后黑帮盛行年代留下来的那些低矮却充满独特风味的建筑,像是“沙丘”、“热带街”与“沙滩”等酒店。拉斯维加斯“鼠帮乐队”,仿佛直接走出了伴着摇摆舞曲和响指声的老式黑帮电影。燥热的空气中仍依稀嗅得出一丝刺激的罪恶气息。
之前的赌城,他会意过来,这是希尔顿和米高梅大手笔创建大型赌场饭店前的赌城。现如今,那些占据了内华达州六〇四号公路上这一小片超现实世界的,是战后黑帮盛行年代留下来的那些低矮却充满独特风味的建筑,像是“沙丘”、“热带街”与“沙滩”等酒店。拉斯维加斯“鼠帮乐队”,仿佛直接走出了伴着摇摆舞曲和响指声的老式黑帮电影。燥热的空气中仍依稀嗅得出一丝刺激的罪恶气息。
他们住进了弗拉明戈酒店,并在酒店赌场里寄存了一万六千美元的现金。满脸殷勤笑容的酒店副经理免费为他们安排了三室的套房,还包了他们入住期间的所有饮食。
弗兰克一晚上都在观察二十一点的牌桌——通过分牌和加倍下注的规矩、不同庄家的速度和性格。杰夫陪他看了一会儿就觉得无聊了,便在赌场里头四处闲逛,沉浸在此处的奇异氛围中。这里的一切都显得虚幻:象征着巨额资金的斑斓筹码、打扮得光鲜靓丽的男男女女……虚张声势的性感外表和豪掷千金的假象背后,隐隐透着一股绝望。
杰夫转完后早早地回了房间,看着《杰克·帕尔脱口秀》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发现弗兰克正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嘴里嘀嘀咕咕的,还不时看看一叠临时记忆卡。
“和我一起吃早餐去?”
弗兰克摇了摇头,“不去了,我想把这些东西再最后温习一遍,中午前去玩两把。我要在早班结束、庄家开始警觉撤退前赢他们几局。”
“有道理,那祝你好运。我估计会待在游泳池附近。记得告诉我事情的进展。”
杰夫独自坐在酒店餐厅可供六人进餐的餐桌前,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赛马消息报》。他开心地注意到,夏多克在贝尔蒙特赛马会上的赔率还在持续攀升;至于报上提到的其他众多大大小小的比赛,他就没什么兴趣关注了。他狼吞虎咽地吞下了双份炒蛋加厚厚的乡村火腿,接着又干掉了一大块松饼和第三杯牛奶。在过去那几年,他已经习惯了早上什么都不吃,或是在上班路上匆匆忙忙地吃块丹麦酥、喝下第一杯咖啡,他一天要喝很多杯。但现在这具新的年轻身体有着他自己的食欲。
等杰夫回到房间换好泳衣时,弗兰克已经下到赌场去了。他拿了块超大的毛巾和一本《视觉生活》杂志,在经过酒店礼品店时停下来买了瓶科普特防晒乳(他注意到上面没有标明PABA指数),然后在游泳池边找了张椅子躺下。
他立刻就看到了她:湿漉漉的黑发、棱角分明的颧骨,酥胸饱满而坚挺、腰肢纤细,一双长腿优雅而匀称。她从泳池中起身,嘴角含笑,在沙漠的艳阳下光彩夺目,朝杰夫走来。
“嗨,”她打了声招呼,“这把椅子有人坐吗?”
杰夫摇摇头,做了个手势请她坐下。于是她四肢舒展地躺下,将还在滴水的湿发撩到帆布躺椅的背后晾干。
“要喝点什么吗?”杰夫开口问道,暗自希望自己的眼神不会在她遍布水珠的胴体上停留太久、太明显。
“不用了,谢谢。”她轻启檀口,依然微笑地直视着杰夫,缓和了拒绝时的尴尬,“我刚喝了杯血腥玛丽,天气太热,感觉头有点晕晕的。”
“没习惯之前会这样的,”他附和道,“你从哪儿来?”
“伊利诺伊州,就在芝加哥附近。不过我来这里已经几个月了,我想我可能会待上一阵子。你呢?”
“我目前住在亚特兰大,”他告诉她,“不过我是在佛罗里达长大的。”
“哦?那我猜你肯定很适应这里的太阳喽?”
“差不多。”他耸耸肩。
“我去过迈阿密几次。那儿蛮不错的,希望也有赌场可以让你们玩。”
“我是在奥兰多长大的。”
“那是哪里?”她问。
“就是靠近——”杰夫差点就要说“迪斯尼乐园”,幸好及时刹车,改成“肯尼迪角”,虽然他知道那地方真正的名字并不是这个,即使是一九八八年。“……靠近卡纳维拉尔角的地方。”最后他如是说道。他的犹豫似乎让她有些不解,幸好这尴尬的一刻很快就过去了。
“那你看过那些火箭发射吗?”她提了个问题。
“当然。”说着,他想起了一九六九年,他和琳达开车去那里看阿波罗十一号升空的那次。
“那你觉得,他们真的像宣称的那样,登上了月球吗?”
“很有可能。”他笑着答道,“对了,我叫杰夫,杰夫·温斯顿。”
闻言,她伸出一只纤柔小手,手指上没有戴戒指,他立刻握住它们,抓着一小会儿。
“我是夏拉·贝克。”她将手抽回,抚过未干的直发顺着脖颈下滑,“你在亚特兰大做什么工作呢?”
“呃……其实我还在上大学。但我在考虑去当个记者。”
她亲切地露齿而笑,“还是个大学生呀?那你的父母肯定很有钱喽,既能送你上大学,还能让你来拉斯维加斯玩。”
“不是的。”他回道,感觉挺好笑。她的年纪也就是二十二三岁,他却总是下意识地用相反的角度来考虑年龄差距。“我在这儿花的都是自己的钱,是从肯塔基赛马会上赢来的。”
她抬了抬精致的眉毛,有些动容:“是吗?这么说你在这里有辆车?”
“是呀,怎么了?”
她将古铜色的修长手臂慵懒地伸过头顶,顿时双峰被样式保守、过时的泳装勒得曲线毕露。对杰夫来说,这和她穿着一件八十年代暴露的法式泳装,或是什么也不穿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充满了诱惑。
“我只是在想,也许我们可以走开一小会儿,避避太阳,”她说道,“比如说开着车去米德湖兜个风,你有兴趣吗?”
夏拉住在天堂和热带赌场度假村附近一间整洁的小复式公寓里,跟一个叫贝基的女孩合租。贝基在机场服务台上大夜班,从下午四点到凌晨十二点。而夏拉除了晚上到赌场或是下午在酒店泳池边闲晃外,似乎没其他事可做。
她并不是妓女,只是众多拉斯维加斯女孩中的一个,喜欢玩乐,不介意时不时收个小礼物或一把筹码。杰夫将接下来的四天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了她的身上,还为她买了几件小礼物——一条银质脚链、一个颜色正好和她最喜欢的洋装相配的真皮钱包——但她从不提钱。他们泛舟湖上,驱车前往顽石坝
 ,相约沙漠酒店看西纳特拉的歌舞表演。
,相约沙漠酒店看西纳特拉的歌舞表演。
然而,绝大多数的时候他们都在做爱。做得最多且印象较深的是在她的公寓和杰夫住的酒店套房里。夏拉是整个事件发生以来他睡的第一个女人,也是他婚后除了琳达以外的第一个。夏拉对性的饥渴远甚于他自己。她的放荡不羁就如朱迪之羞涩天真一般,让杰夫沉迷,陷在她不加节制的情欲中无法自拔。
弗兰克·马多克则偶尔从拿钱办事的女孩们身上找找乐子,她们是各个娱乐厅或赌场的一大特色。他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二十一点牌桌上,忙着赢钱。到了贝尔蒙特赛马会那天,他的赌金已经上涨了九千美元。他慷慨地拿了三分之一给杰夫,答谢他一开始为自己提供了赌资。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现在一共在酒店里寄存了将近两万五千美元。尽管还有些保留,弗兰克还是愿意支持杰夫坚持的计划,把这笔钱全押在一次赛马上。
规定的赛马时间到来的那个周六,杰夫正和夏拉一起,坐在弗拉明戈酒店的泳池边。
“你不打算去看看电视直播吗?”看杰夫丝毫没有从藤编坐垫上起身的迹象,夏拉问道。
“没必要,我已经知道结果了。”
“你喔!”她大笑着给了他的屁股一下,“有钱的大学生,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呢。”
“如果我错了,就不会有钱了。”
“会有那么一天的。”她边说边伸手去拿防晒油。
“什么意思?是说我会有错的一天,还是说我会有变穷的时候?”
“哎呦,傻瓜,人家不知道啦。给,帮我抹抹腿背。”
杰夫沐浴在阳光下,昏昏欲睡。而当弗兰克一脸不可置信地从酒店里走出来时,他的手正放在夏拉光洁的大腿上。看见朋友的这副表情,杰夫连忙爬起了身。天哪,也许他们不该把全部身家都押上的。
“怎么了,弗兰克?”杰夫问道,身体绷得紧紧的。
“所有的钱,”弗兰克粗声粗气地回答说,“妈的所有的钱啊。”
杰夫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发生什么事了?快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弗兰克的嘴唇向后扯了扯,露出一抹奇异的笑容,“我们赢了。”他低声说。
“赢了多少?”
“十三万七千美金。”
杰夫舒了一口气,松开了弗兰克的胳膊。
“你是怎么做到的?”马多克紧紧盯着杰夫的眼睛问,“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到现在你己经连续三次说对了。”
“运气,纯粹是运气。”
“运气?才怪。德比赛马会那次,你把所有家当全押在了夏多克身上,就差没把传家宝拿去当了。你肯定知道些什么,只是不说而已,是吧?”
夏拉咬着下唇,抬头若有所思地看着杰夫,“你确实说过你知道结果会是如何。”
杰夫不想转到这个话题上。“喂,”他笑着说道,“说不定下次我们就把钱全输光了好吗?”
弗兰克闻言咧开了嘴,心中的好奇似乎消失了。“有了这样的成绩,我愿意追随你到任何地方,孩子。那咱们什么时候再大干一场?你又有什么好的预感了吗?”
“没错,”杰夫说,“我有预感,今晚夏拉的室友会打电话请病假,然后我们四个会搞个超棒的庆祝会。我现在就敢赌这个。”
弗兰克听完大笑,走到泳池边的吧台,点了一瓶香槟,夏拉则跑去打电话给室友了。杰夫瘫坐回垫子上,气恼自己说太多了,同时想着要怎么跟弗兰克说,他们的赌伴关系已经结束了,至少今年夏天是没有了。
他肯定不会直说,他们今年不再对任何比赛下注了,因为他已经记不得谁赢谁输了。
杰夫在热羊角面包上涂了薄薄的一层橘子酱,咬掉了酥脆的一角。从福煦大道的阳台上,他可以看到凯旋门以及布洛涅森林的大片绿地,从公寓走过去很轻松就可以到达。
夏拉坐在铺着亚麻桌布的早餐桌对面,朝他露出微笑。她从盘子里拿起一颗红艳艳的大草莓,先在一碗鲜奶油中浸了浸,再裹一层糖粉,然后慢慢地舔起这熟透的莓果,在嘴唇含住果子的那一刻,双目直勾勾地看着杰夫。
杰夫把正在看的《国际先锋论坛报》放在一边,饶有兴致地欣赏她和草莓的即兴表演。反正报纸上依然还是那些令人沮丧的新闻。譬如肯尼迪在巴黎东部的分裂城市发表了《我是一个柏林人》的演说;越南,佛教僧侣们开始在街头自焚,以此向吴庭艳政府
 抗议。
抗议。
夏拉再次将草莓浸入浓稠的鲜奶油中,接着素手轻抬,放在张着的嘴唇上方,然后伸出舌尖,舔去滴下的白色液体。晨光中,她的丝质睡袍变得微微透明,杰夫可以看见她的乳头在薄薄的布料下挺立着。
他已经为巴黎纽利区的这间两室公寓付了一整个夏天的租金,除了偶尔到凡尔赛宫或枫丹白露玩几天外,他们都待在巴黎。这是夏拉第一次到欧洲旅行,而杰夫则曾经和琳达参加过一次赶场般的跟团旅游,这次他希望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感受这座城市。自然,他达成所愿了:夏拉旺盛的情欲与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漫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意走进一家感兴趣的小饭馆或咖啡厅享用午餐;若是雨天(那个夏天经常有雨),他们就窝在舒适的公寓里,沉溺于彼此的肉体中,慵懒地度过漫长的一天。窗外,那弥漫在巴黎的不合季节的朦胧寒意则沦为了他们激情的完美陪衬。杰夫将内心的恐惧裹进夏拉乌黑柔滑的发间,将未曾消减的不安埋藏在那对散发着香气的柔软双峰之中。
她看着桌对面的杰夫,眼中闪过调皮的光芒,突然挑逗般地一口含住那饱满的草莓。顿时,一股细细的鲜红汁液溢出,染红了她的下唇,而她伸出一根蓄着修长指甲的纤纤细指,缓缓地将它拭去。
“今晚我想去跳舞,”她说,“我要穿那件新买的黑裙子和你跳舞,下面什么也不穿。”
杰夫任由自己的目光在那白色丝袍包裹下曲线毕露的娇躯上徘徊。“下面什么都不穿?”
“或许会穿双丝袜,”她轻声说道,“然后按你之前教我的那样共舞。”
杰夫笑了笑,指尖轻轻地划过她露在睡袍外的光滑大腿。三星期前的某个晚上,他们曾到一家近来开始在巴黎流行的“迪斯科舞厅”跳舞,杰夫很自然地带着夏拉跳起了一种舞步迂回、无固定舞步的舞,那种舞十年后才会出现。她当时就喜欢上了那种舞蹈风格,并增加了几个自创的挑逗动作。其他跳着摇摆舞或瓦图西舞的一对对舞伴们,则一个接一个地退到后面,欣赏起杰夫和夏拉的舞步来了。起初众人还在试探、犹豫,然而随着热情的不断上涨,所有人都开始不约而同地跳起了那自由奔放的性感舞蹈。
现在,他和夏拉几乎每隔一夜就会去新潮吉米或是慢步舞俱乐部,而她早已开始按照穿在身上能让她在舞池中展露出多少迷人风采的准则,来挑选当晚的礼服。杰夫喜欢看着她,看到其他跳舞的来模仿她的动作,甚至越来越多地模仿她的穿着,从中获得不少乐趣。想到自己不过是某天晚上和夏拉出去跳舞,却可能在无意中改变了流行舞蹈的历史,还加速了作为六十年代中后期标志的女性时尚的情欲革命,他不禁笑了起来。
她抓起他的手,带着它在睡袍下的大腿间游移。他的羊角面包和法式咖啡在餐桌上渐渐冷却,连同困扰了他整个春天的时光之谜一起,被抛到了脑后。
“等到家的时候,”她低语,“我会把丝袜给你留着的。”
***
“快跟我说说,”弗兰克问,“巴黎之行怎么样?”
“真的非常不错。”杰夫一边告诉他,一边在广场酒店橡树厅里的宽扶手椅上坐下,“我正需要这样的旅行。对了,你感觉哥伦比亚大学怎样?”
他的老搭档耸耸肩,示意服务生上前。“看起来就跟我预计的一样,并不轻松。还是喝杰克丹尼吗?”
“我是能找到就喝这个。那些法国人听都没听过用麦芽发酵的威士忌。”
于是,弗兰克点了杯波旁威士忌,又为自己点了杯格兰利威。一阵忽隐忽现的小提琴声从棕榈餐厅飘来,穿过敞开的酒吧大门,消散在优雅古老的纽约酒店大堂中。在那宁静祥和的乐声之中,偶尔还能听见酒杯轻碰的几声脆响,以及周围人交谈时那枯燥而模糊的嗡嗡声,谈话内容在餐厅厚重帘幔及豪华皮革的阻隔下,变得模糊不清。
“我在法学院的第一年,去的并不全是我期待中的那种酒吧。”弗兰克笑容满面地说道。
“这是你从‘莫伊与乔伊’提升了啊。”杰夫表示认可。
“夏拉也一起过来了吗?”
“她今晚看《边缘之外》去了,我跟她说我是来谈生意的。”
“你们俩挺合得来的,我猜。”
“她挺好相处的,人也有趣。”
弗兰克点点头,晃了晃服务生放在他面前的冰凉酒饮。“那,我想你没怎么再跟那个和我提起过的埃默里女孩见面了吧。”
“朱迪吗?没有,去拉斯维加斯之前我们就分手了。她是个好姑娘,挺讨人喜欢的,可惜……过于天真。还是太年轻了啊。”
“她不是和你一样大吗?”
杰夫警惕地看着他,“弗兰克,你又在扮演大哥了?想说我没办法搞定夏拉或其他事是吗?”
“不,不是,只是——你总是让我惊奇不已,没别的意思。第一次见到你时,我以为你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别的不说,赛马方面你还有得学呢,但是你亲自证明了你确实有两把刷子。我的天哪,你不仅赢了那么多钱,开着亚凡提四处兜风,还能带着夏拉这样的女人飞去欧洲……有时候,你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成很多。”
“我想现在是时候换个话题了。”杰夫生硬地说道。
“听着,我并无意冒犯谁。夏拉是个难得的好女孩,我很嫉妒你。我只是觉得……觉得你好像比我认识的人都成熟得快,我不知道。我没打算对你进行价值评判。妈的,我就把它当成对你的赞美吧。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没其他意思。”
杰夫端着酒往后靠在椅背上,想要放松因紧张而绷紧了的肩膀。“我想那是因为我对生活怀有很大激情吧,”他说,“我想做很多事,而且要迅速把它们做好。”
“嗯,我想你己经领先世界上那些容易受骗的蠢蛋很大一步了。再接再厉,希望你一直这么顺利。”
“谢谢,我敬你一杯。”他们各自举起酒杯,默默地忽略刚才两人之间的剑拔弩张。
“对了,你刚才说,你跟夏拉说你要和我谈生意是吗?”弗兰克说。
“是的。”
弗兰克呷了口威士忌,“那,要谈什么?”
“得看情形。”杰夫耸了耸肩。
“什么情形?”
“要看你对我的提议是不是感兴趣喽。”
“在今年夏天你办成那些事情后?你觉得我还会不听你其他疯狂的主意吗?”
“这事远比你能想象的还要疯狂。”
“说来听听。”
“世界职业棒球大赛,还有两个礼拜。”
弗兰克挑了挑眉,“我了解你,估计你想押道奇队赢吧。”
杰夫顿了一下,“没错。”
“喂,咱们说正经的。我承认,你在德比和贝尔蒙特赛马会上确实干得漂亮,可是拜托!洋基队的曼特尔、马里斯都回来了,而且头两场比赛还是在纽约?不行,老兄,你他妈想都别想。”
杰夫身子往前凑了凑,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地说:“比赛结果就是那样的。那是一场完胜,道奇将连赢四场。”
弗兰克皱着眉头,奇怪地看着他,“你真的疯了。”
“我没疯。那是真的。一、二、三、四场。我们这辈子都不用愁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能这辈子只能回‘莫伊与乔伊’喝酒了吧。”
杰夫喝完最后一口酒,坐了回去,然后摇了摇头。弗兰克继续盯着他,似乎要找出杰夫发疯的原因。
“不然我们下的少一点,”弗兰克松口了,“比如说赌个几千刀,就五千好了,如果你坚持你的预感的话。”
“全都押上。”杰夫坚决说道。
弗兰克点了根泰瑞登,一直没把眼睛从杰夫脸上挪开。
“你究竟怎么回事啊?你是下定决心输一把还是怎的?你要知道,好运终归是会用完的。”
“这事我绝不会弄错的,弗兰克。我会押上我剩下的所有钱,我给你的条件跟上次一样:我出钱,你下注,七三分账。如果你不想的话,你不用冒一点风险。”
“你知道你押的那队赔率是多少吗?”
“不太确定。你呢?”
“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不过——肯定是糊弄人的赔率,因为只有容易上当的笨蛋才会去下注。”
“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我们现在的情况?”
“出于好奇,我会的。”
“去吧,我在这儿等你,再叫点酒。记住,我们不只要赢一场。道奇队会获得所有胜利。”
不到十分钟,弗兰克就回来了。
“我的赌注经纪人嘲笑我,”他边坐下拿冰凉的威士忌边说,“他居然在电话里嘲笑我。”
“赔率是多少?”杰夫平静地问道。
弗兰克一口气喝下半杯酒,“一百比一。”
“你会帮我下注吗?”
“你真打算这样做了,是吗?不只是开开玩笑。”
“我不是开玩笑的。”杰夫声明。
“是什么让你对这些事如此肯定呢?你还知道什么世界上其他人都不知道的事呢?”
杰夫眼神闪了闪,竭力保持声音的平静。“这我没办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你,这并不只是我的预感,而是确定无疑的事。”
“这在我听来似乎很可疑啊——”
“我发誓,里边绝对没有违法的勾当。你也知道,如今他们没法操纵职业棒球赛了,即便可以,我又怎么会知道什么内幕呢?”
“可你说那话就像知道很多事啊。”
“我就知道这么一点:我们不会输掉这次赌注的,绝对不会。”
弗兰克目不转睛地看着杰夫,一口气喝光了剩下的酒,然后又叫了一杯。“妈的,”他嘀咕着,“去年四月遇到你之前,我以为我今年都得靠奖学金过活了。”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想我会加入你这个愚蠢的计划。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等第一场比赛结束,估计我会想把自己脑袋炸开找找答案。不过还有个事。”
“你说。”
“以后别再说七三分账、把全部的钱都押下去这种屁话了。咱们都碰碰运气吧,把从拉斯维加斯赢来剩下的钱全投进去——我从牌桌上赢的也加上去——赢的我们平分。同意吗?”
“成交,老搭档。”
那个十月,是科法克斯和德拉斯戴尔二人的十月。
头两场比赛,杰夫带夏拉到洋基球场去看了,而弗兰克甚至没法坐到电视机前观看。
道奇队以五比二拿下了开幕战,那场比赛由科法克斯主投。第二天站上投球区土墩的是强尼·波德瑞斯,在王牌后援投手罗恩·佩安诺斯基的协助下,他让洋基队得了一分,可惜道奇队仍以十支安打得四分的成绩获得了胜利。
第三场比赛在洛杉矶举行,那是“大人物”德拉斯戴尔的经典一战:一比零完胜洋基队,把洋基击球手们一个接一个放倒。九局中的六局,德拉斯戴尔都让至少三个击球手出局。
第四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就连在纽约皮埃尔酒店用彩色电视看比赛的杰夫,也开始紧张得冒汗了。惠特尼·福特,洋基队的主投手,再次对上科法克斯,两人均使尽全力,拼了个头破血流。洋基队的米奇·曼特尔和洛杉矶道奇队的弗兰克·霍华德各自都击出了本垒打,将比分在七局结束时打成了一比一平。接着乔·佩皮通在给三垒手克力特·波伊尔传球时出现失误,使道奇队的吉姆·吉列姆得以攻进三垒。下一个站上击打区的是威利·戴维斯,在他一记深远的安打下,吉列姆跑回本垒得分。
于是道奇队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以四连胜击败了洋基队,这是该纽约球队自一九二二年被巨人队打败后,第一次输得这么惨。这是棒球史上爆的一次大冷门,是杰夫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就像他不可能记不住自己的名字一样。
在杰夫的坚持下,弗兰克将十二点二万美元的赌金分别交给六个城市的二十三个不同庄家,并在拉斯维加斯、雷诺和圣胡安的十一个赌场分开下注。
这次,他们总共赢得了一千两百多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