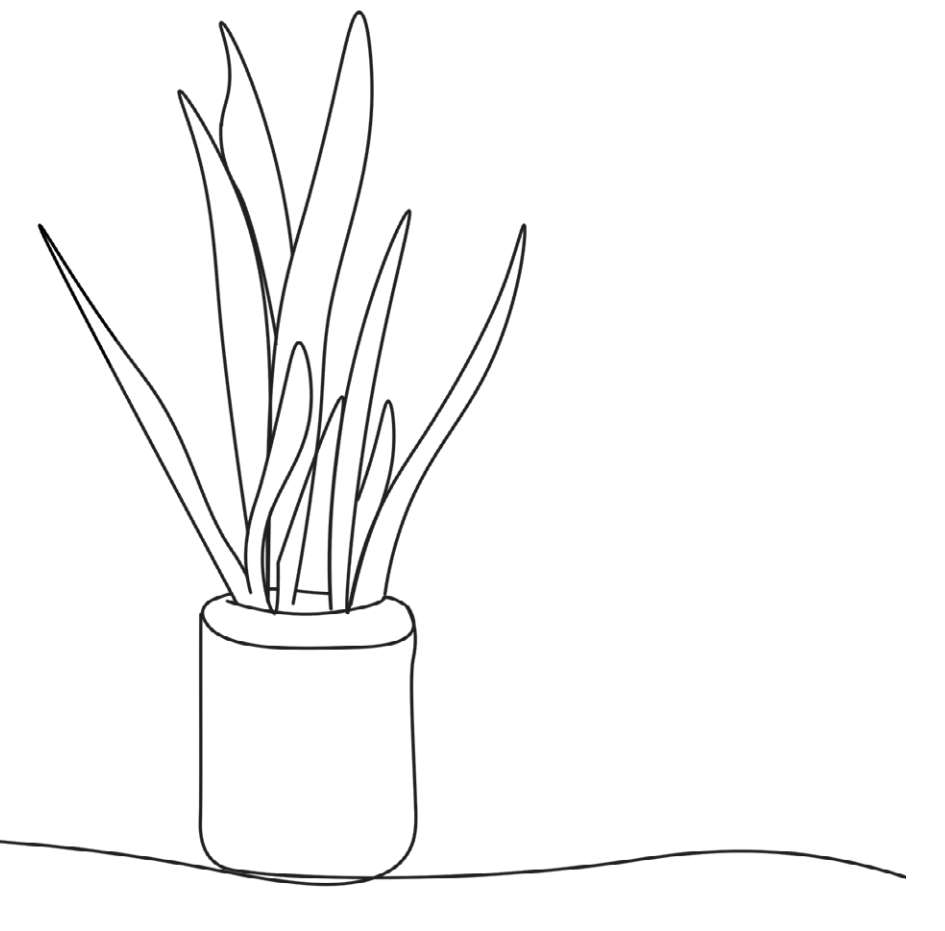算来我“北漂”已是第七个年头了,回首向来处,撞过南墙受过伤,也收过鲜花、喝彩和掌声,但我总以为, 人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我们在其间闯荡,不问前程,只为体验,只为成长,只为尽兴一场——这就是我想要的松弛感。
和其他“北漂”不同,我来北京是因为离家出走,不是为了追求梦想。
我在广东读本科,学校里九成学生都是本地人。最优秀的一批学长学姐们本科毕业就匆忙“杀”入职场,有人创业当老板,有人三年做到业务主管,有人常年全球飞、住五星级酒店,令我等后辈好生羡慕。我们深受其影响,坚信“学而优则贾”。
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选择继续深造,似乎不是最优解。
4 年大学读完,我无论如何不想在象牙塔里继续“蹉跎岁月”了,各行各业的实习做了 5 份,只想尽快进阶,当上“都市白领丽人”。
但我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非常看重学历,不远千里把我从广州薅回家,按头让我复习。
复习了没几天,实在啃不动那几本厚书,年少轻狂,我跟他们俩“道不同,不相为谋”,毅然离家出走,来了北京。
我对生活的态度一向如此,随心随性,不屑于活在他人的舌尖上,只为自己做决定。
离家那天起,得失输赢,苦与乐,才真正有了分野。
人生这盘棋,从今往后,没人能替我下了。
我在凛冽的北风里,一夜长大。
刚来北京,我借宿在表哥家,表嫂临盆在即,不大方便,一周后,我搬出来,住天通苑。
三居室,我住朝北的一间。
房屋很新,但入住后不知为何经常头疼,后来才知是甲醛超标。
半个多月后,我谋到一份出版工作,公司不大,在望京,需坐 1 小时地铁,不算远。
但天通苑居住人口巨大,据说工作日每天有 50 万人出行,单是早高峰进地铁站,就要排队 40 分钟。
公司要求早上 9 点到岗,但如果 7 点出门,撞上早高峰,必然迟到。为了错峰,我 5 点 45 起床,匆匆洗漱,6 点出门,7 点半就来到工位。
我们在一幢别墅里办公,环境宜人,午休时,在别墅区里溜达溜达,看花、喂猫、晒太阳。
只是周围小饭馆很少,午饭只能常年吃外卖。为了减少开支,我每晚做好次日的午饭,装在书包里,第二天带到公司,加热来吃。
但我其实不太会做饭,打开饭盒,经常发现茄子还生着、鸡翅做咸了、金针菇没味儿……只能勉强充饥。
每逢月底,人事部的同事会在楼顶天台给当月生日的小伙伴们举办生日会。
年底开年会,老板和总监们大方,红包都奔五位数去。
可能因为每天到岗太早,我很快就升职、涨薪。顶头上司说:“你是全司升职最快的员工。”
我负责的第一本外版书,是托朋友介绍他北大的学妹来当翻译的。她是第一次当译者,我是第一次当编辑,最后那本书竟销售了 10 万册。不断加印、再版,许多年后还能在书店找到那本书的踪影,令人欣慰。
那时,我的同学们纷纷闯入互联网行业,月薪是我的 2倍,偶尔相聚,总会劝我入局。
虽然我认同工作是谋生,但总觉得人应该在可选范围内,做自己喜欢的事,奔走在热爱里,才能不那么紧绷和焦虑。
我总觉得,钱不是省出来的,是挣出来的。
主业驾轻就熟后,我也想着拓宽副业,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想让自己过得更舒服。如果为了热爱的事业,家徒四壁,食不果腹,那也算不上爱自己。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顺利进入一家全球英语培训机构,做线上口语老师。
彼时我还住在天通苑,因为之前的房子甲醛超标换到了顶层,只有 3 个邻居,但室内面积更小了。每晚 8 点到家,还要做饭,忙完倒头就睡,只能趁双休日,从早到晚地上课。
我算了笔账——因为有了课时费,时间比从前更加宝贵,是真正的“一寸光阴一寸金”。时值盛夏,某个夜晚突然屋顶漏雨,把半张床都打湿,我顺势搬到望京去了。
租金涨了不少,于是我更加勤勉地上课。
下午 6 点下班,20 分钟到家,不吃晚饭,只当减肥。
我掐着时间 6 点半准时上线,5 节课,11 点半下线,嗓子里像有锅炉在烧。
那段时间我不再加班,每天都步履匆匆地奔跑在地铁 14号线,我从没觉得辛苦,只是庆幸不必在天通苑挤早高峰。
半年后,我终于攒够钱,买了一辆小小的雪佛兰。
爱自己,从来不是纵容自己的懒惰,而是适当自律,为了更广阔和自在的人生放弃短暂的行乐。
望京的房子老旧,楼层低,有数不清的蟑螂。
睡眼惺忪的早晨,拉开冰箱门、打开微波炉、拎起垃圾袋……它们无处不在,让人瞬间睡意全无。
某天傍晚回到家,发现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课也没法上,邻居也都没回家,我坐在床上,想象满屋的蟑螂向我围拢而来,把自己吓得够呛。
收拾好小包袱,火速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订了房间,奢侈地打了车,半小时后,我已泡在酒店温暖的浴缸里了。
后来跟朋友说起,我曾因为害怕蟑螂,花了半个月工资,在家附近的五星级酒店住了一晚,朋友对我肃然起敬。
我不心疼钱,我心疼自己,何况钱好挣,快乐很难。
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经常遭遇坏事,倒霉的时候总归短暂,那就应该在最痛的时候好好拥抱、疼惜自己,否则平日里哪有那么多机会,对自己大献殷勤呢?
你要成为那个给自己雪中送炭的人。
没过多久,我收到来自行业头部公司的邀请。我选择跳槽。
第二家公司规模大、制度成熟、组织架构完善,我迅速成长,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职场心态,终于完成从“学生”到“社会人”的强力转型。依托更大的平台,为今后的写作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结识了众多作家和媒体人,他们一直给予我榜样的力量和无私的帮助。
我从没后悔过当初的决定。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有远见的一次跳槽。
只是那时我身心俱疲,于是再次出走,提出裸辞。
知止常止,急流勇退,纵是在 25 岁——最适合拼搏奋斗的年纪,我依然允许自己停下来,坐一会儿,歇一歇。
裸辞之后,我在欧洲漫无目的地游历,写就《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这本书很不顺利,花了将近 5 年才定稿,却没公司愿意出版。市场看重“热度”,我却像一个老工匠,一字一句打磨手艺,追不上风云变幻的图书行情。
曾经的约稿编辑纷纷婉拒了我的新书,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悄悄说:主编说你过气了。
从没当过明星,居然也会“过气”。
我倒是不生气,写作是放长线,急不得,做了几十页毛遂自荐的策划案,一边慢慢物色出版公司,一边又逐字修订。
对于写作,我也允许自己停下来,歇一歇。
《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上市后,我妈怕我压力太大,时常来电探问我的精神状态。
我其实很满意,这本书能顺利出版已是胜利,加上身边的亲朋好友解囊支持,不遗余力地帮我宣传推荐——我先后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文艺广播宣讲新书——书的销量一路高歌,攀上新书榜单前十名。
有此成绩,我很知足。
更重要的是,我笃信这本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一生欠安》写于 18 岁,凛冽、桀骜、愤世嫉俗,正是常常在深夜痛哭的年纪。写爱而不得的女人和轻诺寡信的男人,对待感情,满纸质问。文字表面克制,内里尽是激烈、尖锐的对峙。
《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上市时,我快 30 岁了,饿过肚子,赔过笑脸,见惯别离,饮过苦酒,习得包容和慈悲,懂了世人皆苦。戒了情绪,只把书中人的不得已都剖开来,给你看。
我依然深爱着笔下的人物,但除了鸣不平,更试图回到“案发现场”,探寻另一种改写结局的可能——是怎样的局限使她们无法圆满?作为看客的我们又能否幸免?这本书凝结了我此时全部的智慧。
欣喜自己的成长,也能坦然面对所有读者的喜欢——我尽力了。
停下来,是为了更好地出发,休整了几个月,我重返职场。
从欧洲回来,进入一家出版社,在这里才明白,父母当年按头让我考研之明智。
我开始暗无天日地复习,准备考研。
我想人总是这样,被迫去做事总是心不甘情不愿,若是自己认定的事,吃多少苦、流多少汗都甘之如饴。
本科毕业时啃不完的厚书被我重新拾起。白天工作繁重,夜晚焚膏继晷,终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在职研究生,在读期间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在职研究生如期毕业。
我搬了好多次家,最终搬到三环里的一居室,没有了合租的邻居。
不久,我终于买到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自此之后,我的租房生涯彻底结束。
生活本应进入平稳的轨道,我却再次裸辞。
因出版社业务调整,我转岗去做行政,日常工作包括订盒饭、领盒饭、送盒饭,负重极限是 10 盒菜、10 盒主食、10 个火龙果加 10 个 100ml酸奶,持之以恒 4 个月,胳膊上都练出了肌肉。
公司楼下有台不大好用的扫描仪,我其中一项工作是一张一张地扫描文件,每扫描 5 张卡一次纸。
500 页的文件,我站在旁边,5 张一接,5 张一接,接到第 100 次就大功告成。
“嗡”“嗡”——纸张从机器“嘴”里吃进去,又从“脑袋”上吐出来。
我总觉得它吃进去的是我的青春。
工作 4 年,我热爱这个单位,喜欢我的领导和同事,它也给予我所有的体面和自由——办公室和家在同一小区,每天中午能在家午休;工资与毕业时相比翻了 5 倍,下午 4:45就下班,有时间创作、充电;单位为青年员工提供了很多学习、进修、见世面的机会,我作为青年业务骨干,讲座、培训、汇演从不缺席。
但这些“羡煞旁人”的外在条件,都抵不过日复一日的庸常。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不再成长,不再创造,在舒适圈里画地为牢。
于是,28 岁,衣食无忧的我,辞去光鲜的工作,在就业的凛冬放弃了“背靠大树”的温暖。
我走在北京长长短短的街巷里,看这 7 年不曾驻足观赏的“北平之秋”;走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听穿越千年的琉璃光盏中盛满的历史之音;在高高低低的寺庙、道观,磕长头祈求身心清洁,不惹尘埃。
我来到彩云之南的西双版纳,一个人漫步在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感受深秋的炽热与神秘;在吊脚楼里和傣族少女锻打一柄雕花的银梳,听她讲傣族的风俗习惯;进苍蝇小馆点一碗地道的撒撇米线,跟厨师小哥聊聊他心中的“西双版纳美食地图”。
我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给耄耋之年的奶奶洗头、更衣、洗脚。奶奶把我养大,但我以前从来没有为她做过这些,我更没有想到,她已然衰老至此……和爸妈一起逛街、吃日料,想带他们去所有我去过的地方,听他们讲大半生所有的不开心与不甘心,单是陪伴,已是奢侈。与多年未见的老友相见,在时过境迁里,感受彼此从未改变的真诚和祝愿。
我想过一种只悦己、不悦人的生活,不求理解,但求无愧于心。
在我心里亦有一杆衡量意义与标准的秤,世俗之见与我无关,孰重孰轻,我自有判断。
有人说,高级的人生充满松弛感。以我有限的阅历而言,松弛感无非是:为自己做决断,生活在热爱里,爱自己并允许自己停下脚步,最终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当你内心足够笃定时,便不会过度纠结,自我消耗。姑娘们,大方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