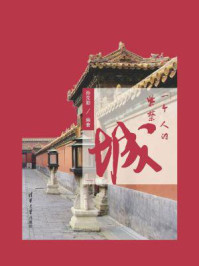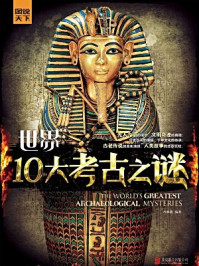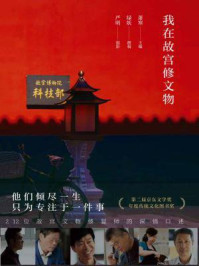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遣策共有722支。一号墓竹简312支,长均27.6厘米,出土于东边厢北端,堆放在68号漆盒的上面,部分压在48号漆鼎和49号陶鼎的下面。三号墓竹简和木牍410支,纪年木牍出自东边厢,其余5件木牍与全部遣策竹简出自西边厢北端。这批专门记载丧葬事务的竹简,为研究文字词语、典章名物、丧葬礼俗乃至西汉初年的社会生活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多年来,学者对马王堆汉墓遣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遣策文字考释及其内容研究上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一号墓遣策出土于东边厢北端,出土时由于编缀的绳索朽断而自然散落为五个小堆。从残存的绳痕判断,竹简是在写好后再用细麻绳分上下两道交错编联成册。由于出土时竹简已有相当程度的散乱,原来的次序无法完全弄清。对于竹简的排序,各家意见不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根据竹简散落的方向和简文的内容,大致确定所记器物的类别和次序。大体的顺序为:开头是副食品、调味品、酒类和粮食,其次是漆器、陶器、梳妆用具和衣物,最后是乐器、竹器以及木制和土制的明器。
 已故古文字学家唐兰认为,遣策中明器的次序,可以与《仪礼·既夕礼》相对照。根据随葬明器的实际内容,参照《既夕礼》的明器陈列次序,分为下列十类:葬具(包括椁中
已故古文字学家唐兰认为,遣策中明器的次序,可以与《仪礼·既夕礼》相对照。根据随葬明器的实际内容,参照《既夕礼》的明器陈列次序,分为下列十类:葬具(包括椁中
 度、缕帷和非衣)、食物(包括肉食、粢食、枣梅等)、谷物(包括米、种等)、菹醢(包括魫、
度、缕帷和非衣)、食物(包括肉食、粢食、枣梅等)、谷物(包括米、种等)、菹醢(包括魫、
 、萦鱼、醢、酱、菹、梅、笋等)、酒、用器(包括漆器、瓦器)、燕乐器(包括笙、竽、竽律)、内具(包括奁、镜、疎比、巾枕戴、
、萦鱼、醢、酱、菹、梅、笋等)、酒、用器(包括漆器、瓦器)、燕乐器(包括笙、竽、竽律)、内具(包括奁、镜、疎比、巾枕戴、
 、履等)、燕器(包括竹器、席等)、其他(包括聂币、犀、象、金、钱等宝货以及马、牛、羊、鸟等明器)。
、履等)、燕器(包括竹器、席等)、其他(包括聂币、犀、象、金、钱等宝货以及马、牛、羊、鸟等明器)。

三号墓遣策包括6支木牍和404支竹简(内含3支残简)。出土时已散乱,无编连痕迹。5件木牍均是一组竹简所记同类随葬品的小结。为明晰起见,发掘报告将木牍和竹简统一编号。遣策虽已散乱,但随葬物品前后次序大体清楚:起首为纪年木牍,然后依次为男女明童、车马、各种食物、漆器、土器、其他杂器和丝织物。
 伊强《谈〈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遣策释文和注释中存在的问题》一文,对三号墓遣策的编排进行了重新整理,将三号墓竹简和木牍统一编排,做出大致的分类。有小结木牍可资依凭的类别竹简,其前后顺序依据小结木牍来确定。没有小结木牍可资依凭的类别竹简,其前后顺序大致仍沿用三号墓之旧。重新编排后的竹简和木牍,分纪年木牍、男子明童、女子明童、车骑、羹、食物和谷物、衣服、兵器、乐器、漆器、土器、博具、丝织物、杂器及其他,
伊强《谈〈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遣策释文和注释中存在的问题》一文,对三号墓遣策的编排进行了重新整理,将三号墓竹简和木牍统一编排,做出大致的分类。有小结木牍可资依凭的类别竹简,其前后顺序依据小结木牍来确定。没有小结木牍可资依凭的类别竹简,其前后顺序大致仍沿用三号墓之旧。重新编排后的竹简和木牍,分纪年木牍、男子明童、女子明童、车骑、羹、食物和谷物、衣服、兵器、乐器、漆器、土器、博具、丝织物、杂器及其他,
 将原有编排顺序按类进行整理,重新编排,解决了一些不合理的归类。但在其他类中,将几支小结简如“右方廿一牒丙笥”“右方十三牒稍筍”孤立地归入其他类,与原分类简内容分离,显然是欠妥当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基本上遵从伊强的排序,称释文简序编排与伊强的不同之处在于简20、简407和简320,在释出“象”后为“疎比”的基础上,将此简改置。
将原有编排顺序按类进行整理,重新编排,解决了一些不合理的归类。但在其他类中,将几支小结简如“右方廿一牒丙笥”“右方十三牒稍筍”孤立地归入其他类,与原分类简内容分离,显然是欠妥当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基本上遵从伊强的排序,称释文简序编排与伊强的不同之处在于简20、简407和简320,在释出“象”后为“疎比”的基础上,将此简改置。

马王堆汉墓遣策出土以后,学者们就开始了对简文字词的考释与研究。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能够了解词义,通读简文,为深入研究简文内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3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对遣策进行了初步考释,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通过对遣策的考释,弄清了简文所反映的汉初物产。这些物产有粮食、瓜菜、草药、肉食品、调味品、饮料酒、果品、饼食品等。烹调或加工方法计有羹(
 羹、白羹、巾[堇]羹、逢[葑]羹和苦羹等)、炙、脍、濯、
羹、白羹、巾[堇]羹、逢[葑]羹和苦羹等)、炙、脍、濯、
 (熬)、昔(腊)、烝(蒸)、煎、濡、脯、苴(菹)等。这些有关饮食生活方面的文字资料,丰富了我们对汉初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习惯的认识和了解。对于汉初丧礼制度的研究,简文也有重要价值,简文和有关文献记载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对照起来。文献记载致奠的主要物品是牲体、濡物、醴酒,主要奠器是鼎、匕、笾、豆、甒。简文把致奠的五种肉羹和鼎放在“遣策”的首位,另有一组简专记鼎匕,这绝不是偶然的。所谓笾、豆、甒,演变到汉代就成了盘、盒、壶、锺、钫、罐等类的器物,亦即简文所记的“卑
(熬)、昔(腊)、烝(蒸)、煎、濡、脯、苴(菹)等。这些有关饮食生活方面的文字资料,丰富了我们对汉初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习惯的认识和了解。对于汉初丧礼制度的研究,简文也有重要价值,简文和有关文献记载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对照起来。文献记载致奠的主要物品是牲体、濡物、醴酒,主要奠器是鼎、匕、笾、豆、甒。简文把致奠的五种肉羹和鼎放在“遣策”的首位,另有一组简专记鼎匕,这绝不是偶然的。所谓笾、豆、甒,演变到汉代就成了盘、盒、壶、锺、钫、罐等类的器物,亦即简文所记的“卑
 ”、“合”(“笥”亦称“合”)、壶、锺、钫和“资”。至于牲体的烹调加工以及其他奠器、物品,大体也可以互为参照。这些都可说明汉初的丧葬制度是战国丧葬制度的延续。
”、“合”(“笥”亦称“合”)、壶、锺、钫和“资”。至于牲体的烹调加工以及其他奠器、物品,大体也可以互为参照。这些都可说明汉初的丧葬制度是战国丧葬制度的延续。
 唐兰先生《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一文,利用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各种学科知识系统地对一号墓312枚遣策简进行考释,不仅是一号墓遣策考释的力作,而且在文字考释方面也是不可多得的文章。
唐兰先生《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一文,利用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各种学科知识系统地对一号墓312枚遣策简进行考释,不仅是一号墓遣策考释的力作,而且在文字考释方面也是不可多得的文章。
 朱德熙、裘锡圭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考释补正》一文中,针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的遣策考释中的某些文字提出了新的考释。
朱德熙、裘锡圭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考释补正》一文中,针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的遣策考释中的某些文字提出了新的考释。

三号墓遣策与一号墓遣策在文字和简文内容上大同小异,发掘报告对三号墓简文作了初步的考释。周世荣《长沙马王堆汉墓简牍文字研究》一书对于文字考释中未加释读的字进行了考释,对某些已经考释的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出土的大量帛书文字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许多研究者经过简与帛的文字对照研究,对遣策简文有了新的认识,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自九十年代至今,对于马王堆汉墓遣策文字的考释呈现出多元化和对以往马王堆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性研究的趋势。许多研究者也着重考释一号墓遣策文字研究中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刘钊先生《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考释》对照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的相同简文,认为简239的第三个字应按李家浩先生和周世荣先生所释为“庸”,并举出了新的论证依据。
刘钊先生《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考释》对照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的相同简文,认为简239的第三个字应按李家浩先生和周世荣先生所释为“庸”,并举出了新的论证依据。
 王贵元先生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中将简208中的最后一字释为“定”,并与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上的字对照,指出“定”应指案上用于丧祭之食物,观点较为新颖。
王贵元先生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中将简208中的最后一字释为“定”,并与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上的字对照,指出“定”应指案上用于丧祭之食物,观点较为新颖。
 陈松长先生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遣策释文订补》一文中,对一、三号汉墓简文中共有的“黄卷一石,缣囊合笥”进行考证,认为是“黄卷一石,原本是用缣囊盛放的,但在下葬读遣时没有缣囊,故临时改为竹笥盛放”,可做参考。
陈松长先生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遣策释文订补》一文中,对一、三号汉墓简文中共有的“黄卷一石,缣囊合笥”进行考证,认为是“黄卷一石,原本是用缣囊盛放的,但在下葬读遣时没有缣囊,故临时改为竹笥盛放”,可做参考。
 范常喜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级绪巾”补说》中认为简文中的“纹绪巾”应释为“级绪巾”,可能是一种用纻做成的覆盖在裾上的蔽膝。
范常喜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级绪巾”补说》中认为简文中的“纹绪巾”应释为“级绪巾”,可能是一种用纻做成的覆盖在裾上的蔽膝。
 这些文章都是对遣策文字考释的力作,对很多以前文字考释中遗留下来的问题给出了新的解答,有理有据,开阔了我们的研究思路。
这些文章都是对遣策文字考释的力作,对很多以前文字考释中遗留下来的问题给出了新的解答,有理有据,开阔了我们的研究思路。
李均明、何双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木楬》一文,对一号墓312枚简逐个进行了考释,虽然没有逐个注释,但他的考释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也被很多研究者采纳。
 李均明先生还在2009年出版的《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对一号墓简文进行了新的考释,也修订了他以前的一些研究。
李均明先生还在2009年出版的《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对一号墓简文进行了新的考释,也修订了他以前的一些研究。
 王贵元《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一文,是作者阅读《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所作笔记的初步整理稿。作者认真比对了书中遣策的图版,提出了一些文字隶定方面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解释和论证。
王贵元《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一文,是作者阅读《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所作笔记的初步整理稿。作者认真比对了书中遣策的图版,提出了一些文字隶定方面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解释和论证。

近年来,一些高校的学位论文也出现了专门针对马王堆汉墓遣策文字进行考释的研究。如北京大学伊强的硕士论文《谈〈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遣策释文和注释中存在的问题》
 、西南大学贺强的硕士论文《马王堆汉墓遣策整理研究》
、西南大学贺强的硕士论文《马王堆汉墓遣策整理研究》
 、安徽大学魏灵水的硕士论文《汉墓出土遣策选释》
、安徽大学魏灵水的硕士论文《汉墓出土遣策选释》
 、华东师范大学孙欣的博士论文《汉墓遣策词语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孙欣的博士论文《汉墓遣策词语研究》
 、郑州大学张如栩的硕士论文《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研究》
、郑州大学张如栩的硕士论文《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金菲菲的硕士论文《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集释》
、首都师范大学金菲菲的硕士论文《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集释》
 等,对遣策文字进行了考释,在认可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伊强在《谈〈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遣策释文和注释中存在的问题》一文中分三个部分论述遣策释文和注释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部分讨论的是释文,主要是遣策文字释读和释文标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中关于文字的隶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在一些句读方面做了一些适当的调整;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的是注释中的字义、词义解释等方面;第三部分是遣策竹简的编排,重点讨论的是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遣策竹简的重收、断简的拼合和竹简内容归类等方面,该文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孙欣博士论文《汉墓遣策词语研究》,以近几十年来出土的汉墓遣策所载词语为研究对象,将零散的汉墓遣策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了马王堆汉墓遣策部分词语分析研究,并尽量将词语所代表的事物与墓葬出土实物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为汉代语言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贺强的硕士论文对马王堆一、三号汉墓遣策进行了研究。论文主要是对两墓简文的文字内容进行整理考释,并就文字和词汇分专题进行个案研究。金菲菲的硕士论文《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集释》,主要搜集近年来学者们对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的研究成果,结合新材料对遣策进行综合性汇释,并尽可能和随葬器物对应,使我们对汉代的丧葬习俗、随葬器物及其命名等有进一步的认识。
等,对遣策文字进行了考释,在认可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伊强在《谈〈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遣策释文和注释中存在的问题》一文中分三个部分论述遣策释文和注释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部分讨论的是释文,主要是遣策文字释读和释文标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中关于文字的隶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在一些句读方面做了一些适当的调整;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的是注释中的字义、词义解释等方面;第三部分是遣策竹简的编排,重点讨论的是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遣策竹简的重收、断简的拼合和竹简内容归类等方面,该文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孙欣博士论文《汉墓遣策词语研究》,以近几十年来出土的汉墓遣策所载词语为研究对象,将零散的汉墓遣策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了马王堆汉墓遣策部分词语分析研究,并尽量将词语所代表的事物与墓葬出土实物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为汉代语言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贺强的硕士论文对马王堆一、三号汉墓遣策进行了研究。论文主要是对两墓简文的文字内容进行整理考释,并就文字和词汇分专题进行个案研究。金菲菲的硕士论文《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集释》,主要搜集近年来学者们对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的研究成果,结合新材料对遣策进行综合性汇释,并尽可能和随葬器物对应,使我们对汉代的丧葬习俗、随葬器物及其命名等有进一步的认识。
研究马王堆汉墓遣策时,一些研究者对遣策的语言和语法进行了研究,特别是针对遣策语言中的量词、语序等。如孙欣博士论文《汉墓遣策词语研究》对量词“具”进行了一些语法上的研究,认为量词“具”确为汉代通用量词,它既可以异物相配,也可以同物相配,而且多适用成套、配对的事物。如马王堆汉墓遣策“五子检(奁)一具”是一个由五部分组成的梳妆奁盒;再如“疎比一具”,是一套梳篦,包括梳和篦两种。简文丰富的量词,是反映汉语量词史的宝贵材料。研究遣策中的量词,对先秦两汉量词的研究是很有裨益的。在遣策文字语序方面,孙欣在其文章中也有探讨,认为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中烤炙体积较大的动物肉,构成为“动物+炙”;烤炙动物个别部位的肉,构成为“动物部位+炙”;体积较小的动物,可整个烤炙,构成为“炙+动物”,其规律性强,未见例外。遣策的这种语言规律,在史籍中也大都符合。

王贵元先生和张显成先生在简帛量词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已写有多篇文章,对马王堆汉墓遣策中的量词也多有关注。王贵元《汉代简牍遣策的物量表示法和量词》一文认为,遣策文献对语言研究有很大的优势,如遣策书写时间与墓葬时间相同,时代明确;遣策都是墓葬时代的原始记录,没有传抄有意或无意篡改的疑虑;古墓葬随葬品丰富,涵盖了所有的生活用品,能较全面地反映当时语言的物量表示法和量词用法。他把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量词进行归类,一类是固定量词,如两、合、双、具、枚、石、斗、斤、丈、尺、寸;还有一些是临时量词,如牒、鼎、笥、器、器盛、粢。
 张显成《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中的量词》一文详细介绍了马王堆汉墓遣策中量词的一些用法。通过研究,纠正了一些量词产生的时代,如囊为盛物单位量词,原来以为产生于唐代;器为盛物单位量词,原来以为产生于六朝等。简文中的这些量词,刷新了我们原来对它们产生时代的认识。他认为简帛量词的研究意义重大,尤其是对先秦两汉魏晋汉语量词断代史的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
张显成《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中的量词》一文详细介绍了马王堆汉墓遣策中量词的一些用法。通过研究,纠正了一些量词产生的时代,如囊为盛物单位量词,原来以为产生于唐代;器为盛物单位量词,原来以为产生于六朝等。简文中的这些量词,刷新了我们原来对它们产生时代的认识。他认为简帛量词的研究意义重大,尤其是对先秦两汉魏晋汉语量词断代史的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

作为随葬物品清单,遣策为我们提供了解汉初丧葬制度不可多得的资料。学者除考释文字、研究语法之外,还从遣策记录的具体内容、汉初丧葬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遣策记录的用鼎制度,有学者进行了详细讨论。俞伟超先生《马王堆一号汉墓用鼎制度考》一文认为,遣策所记随葬物品同实际的出土物有些出入,但要研究当时规定的葬制,当以遣策为主要依据。就以用鼎制度来说,遣策所记的鼎数,应当比实际随葬的漆(陶)鼎更符合当时的列侯之制。他认为一号墓遣策记载的羹鼎九鼎牛、羊、豕俱全,当是大牢九鼎;白羹七鼎以牛羹为首,当是大牢七鼎,七件漆鼎所盛何物不详,数既为七,亦当是大牢七鼎。这样,如加上漆鼎,当九、七三牢,如不计漆鼎为九、七二牢。《仪礼·聘礼》是诸侯相问之礼,往往礼加一等,所以东周时用九、七二牢是诸侯之礼。
 《试论马王堆汉墓丧葬用鼎》一文对俞伟超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遣策记载的成套羹鼎,作为遣送死者的最后一次祭奠之礼器被详细记录于遣策中,它与周制遣奠时上大夫(卿)用正鼎九鼎之制基本一致。遣策所反映的是汉初的葬制,与周制有着渊源关系。从羹鼎所用牲体、和羹之菜和用鼎制度的规定性来看,汉初葬制既循周制又有汉制不拘周制的变更。随葬漆、陶鼎则是作为遣送死者的入圹明器而记录于遣策中,它反映的应是汉初丧葬的明器制度。”
《试论马王堆汉墓丧葬用鼎》一文对俞伟超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遣策记载的成套羹鼎,作为遣送死者的最后一次祭奠之礼器被详细记录于遣策中,它与周制遣奠时上大夫(卿)用正鼎九鼎之制基本一致。遣策所反映的是汉初的葬制,与周制有着渊源关系。从羹鼎所用牲体、和羹之菜和用鼎制度的规定性来看,汉初葬制既循周制又有汉制不拘周制的变更。随葬漆、陶鼎则是作为遣送死者的入圹明器而记录于遣策中,它反映的应是汉初丧葬的明器制度。”

《试论马王堆一号汉墓用鼎制度》一文认为是“正鼎三套并各有陪鼎三件”,分别用于宗庙祭祀之正祭馈食、次日绎祭和朝践之时。该墓中理应下葬鼎九、七、三、三、二共24件,漆木鼎7件,锡涂陶鼎6件,可能因空间狭小而未能全部放入随葬。因此,研究其用鼎制度,当以遣策记载为准。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需了解周代宗庙祭祀活动的全过程。通过分析《周礼》《礼记》等记载及注疏所见祭祀前备牲、灌祭、杀牲、朝践、馈食、绎祭等过程中用鼎与用牲情况,认为周代诸侯等级宗庙祭祀时朝践、馈食、绎祭分别用正鼎七、九、七三套,而卿(上大夫)则用五、七、五三套。一号汉墓共使用正鼎三套,分别为漆画鼎七件一套,酑羹九鼎、白羹七鼎,并各有陪鼎三件。这三套正鼎的出现与《周礼》记载的宗庙祭祀仪式中的朝践、馈食、绎祭三个环节密切相关。当然在汉代其具体使用之法可能并不如礼经所载,但制度的来源当本自周礼。

遣策记录的食物,《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所载食物考述》一文结合历史文献,对涉及食物的部分加以整理与研究。从食物种类、烹饪加工方式、盛装器皿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考证,认为“民以食为天”,可见食物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在古代更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由于史籍上并未留下有关中国古代饮食生活及习惯的详细记载,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研究缺少了资料基础,而马王堆三号汉墓饮食实物与遣策的出土,正好化解了这个难题,为我们研究汉代饮食文化提供了丰富可信的珍贵资料,勾画出汉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与人们日常生活情景。其丰富的饮食实物,精美的饮食器具,多样的烹制方法,无不展现出汉代饮食文化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遣策记录的家僮,《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研究》一文认为,轪侯家中拥有较为完备的家吏管理体系及仆从系统,主要有处于管理阶层的家吏、属官及保卫仪仗人员、娱乐服务人员、生产及服务的奴婢。家吏包括家丞、家吏、谒者,负责维持轪侯家中日常的各种事务及生活秩序,确保轪侯能享有各项周到的服务;属官及保卫仪仗人员包括宦者、偶人、乐队、从者、卒等,负责日常的保卫工作及出行仪仗;娱乐人员包括美人、才人,确保轪侯的娱乐享受需要;生产及服务的奴婢包括奴、婢、竖,主要负责府中日常的具体劳动,如府内的清洁、食物的获得和供给、服侍主人等。这一体制很好地维系了轪侯府中的日常管理,反映出汉代列侯家中的管理方式,同时也反映出汉代列侯地位极其优越,生活极度奢华。

综上所述,对马王堆汉墓遣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字词研究上,在简序、字词、语法研究上也已产生了较多的成果。有学者涉及一些具体内容的分析,但多是粗浅的尝试,至少在典章名物、丧葬礼俗、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马王堆汉墓遣策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需要我们做出多方面、多角度、多学科研究的努力,才能把研究推向深入。我们利用与实物直接接触的有利条件,尝试将文字词义与随葬器物联系起来,突破传统训诂学的指向性解释,将词语代表的事物与墓葬出土实物的考察结合起来研究,力求获得更多诠释的启示。
鉴于作者的学识、视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以此求教于学界诸家,希望能够为遣策的深度研究提供考释与研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