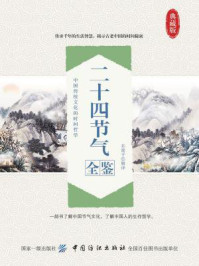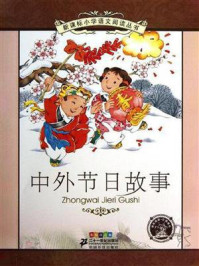文化学家、音乐学家牛龙菲先生在其著《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中,以“文化人类学性质之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思路,以不同历史阶段中音乐社会功能的不同性质和乐师社会身份的不同性质来进行中国音乐文明历史的分期”,将中国古乐分为四大时期:巫乐期(周秦之前)、礼乐期(魏晋之前)、宴乐期(宋代之前)、俗乐期(近代之前)。他指出:巫乐期,音乐乃是原始巫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乐师主要以巫师的面目出现;礼乐期,音乐乃是礼的附庸、政的奴婢、刑的补充,乐师主要以工伎的面目出现;宴乐期,音乐乃是“娱密座,接欢欣”、佐酒进食之背景,乐师主要以家奴的身份出现;俗乐期,音乐真正进入俗众的生活,乐师主要以戏子的身份出现。

潮州音乐是古代中原汉族音乐与本地土著音乐交融互渗的产物,始于唐代。对其历史源脉,陈天国、苏妙筝曾在文中有述:潮州音乐“保留有汉唐遗响的弦诗乐,有宋代的宫廷古乐,有宋明代的软硬套古乐,宋元的戏剧音乐,有明清的外江乐,有明以前一直流传下来的‘香花板’‘禅和板’佛乐唱腔等”
 。对其形成过程,王耀华、杜亚雄在《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指出,潮州音乐“除从本地区民间音乐和兄弟乐种吸收营养外,还承唐、宋燕乐(潮人称古调、古乐)、法曲、道调的遗绪,受宋元南戏(包括正字、弋阳、昆山诸腔、潮调,以及其他古老戏曲)音乐的影响”
。对其形成过程,王耀华、杜亚雄在《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指出,潮州音乐“除从本地区民间音乐和兄弟乐种吸收营养外,还承唐、宋燕乐(潮人称古调、古乐)、法曲、道调的遗绪,受宋元南戏(包括正字、弋阳、昆山诸腔、潮调,以及其他古老戏曲)音乐的影响”
 。以上是对潮州音乐历史源脉的大致钩沉。周秦(巫乐)、魏晋之前(礼乐)的潮州音乐状况由于资料受限我们不得而知,但唐宋(宴乐)及明清(俗乐)之前的音乐状况我们可从乐史资料中获得基本的认知。
。以上是对潮州音乐历史源脉的大致钩沉。周秦(巫乐)、魏晋之前(礼乐)的潮州音乐状况由于资料受限我们不得而知,但唐宋(宴乐)及明清(俗乐)之前的音乐状况我们可从乐史资料中获得基本的认知。
关于乐史资料,牛龙菲先生将其划分为“乐响、乐谱、乐器、乐典、乐像和乐俗”六个等级。乐响(第一等级),即以音响为载体的乐史资料;乐谱(第二等级),即音响的符号化记录(可通过乐谱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将其“还原”为实在音响);乐器(第三等级),是音乐的活化石(可通过乐器以及材料工艺感知其音声状貌、审美趣味和文化取向);乐典(第四等级),即音乐典籍资料;乐像(第五等级),即音乐图像或塑像;乐俗(第六等级),即音乐所依存的民间民俗(牛龙菲先生强调,乐俗由于其“渊源的难以追溯,又使其不能作为历史的确证”,所以被视作“第六等乐史资料”)。
 以下从乐响、乐谱、乐器、乐典、乐像和乐俗六个方面(等级)对潮州音乐的历史遗存情况加以分述。
以下从乐响、乐谱、乐器、乐典、乐像和乐俗六个方面(等级)对潮州音乐的历史遗存情况加以分述。
古代潮州音乐的“乐响”,因时代久远不得而知。但从遗续的音响中依然可以感知其历史渊脉。如潮州外江乐,宋代杂剧兴起并繁荣,北宋建都汴梁(今开封),曲调多为北曲;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曲调多为南曲。北曲刚劲,定弦较高;南曲柔婉,定弦较低。当今遗存的潮州外江乐就分北路和南路两种风格,北路定弦“士工”(la、mi,亦称“西皮线”),南路定弦“合尺”(sol、re,亦称“二黄线”),此体现了潮州外江乐与宋代杂剧音乐的相承关系。
潮州音乐的记谱形式,有二四谱、工尺谱、锣鼓经等。二四谱属于数字谱,是潮州音乐所独有的记谱形式(潮州方言唱念),所以又称“潮州二四谱”。用“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个数字为谱字,对应简谱
 、
、
 、1、2、3、5、6。通过“三、六”两音的“轻、重”变化和“五”音的“活奏”等,使一首“二四”曲谱奏出四种不同调体的音乐来。著名音乐学家、律学家、武汉音乐学院教授郑荣达先生在《潮乐“二四谱”溯源——兼与〈仁智要录〉筝谱比较研究》一文中曾述,“潮州音乐先前用汉文数字作为乐谱谱字符号,是目前所见遗存的传统音乐谱种中罕见的一种乐谱形态……”
、1、2、3、5、6。通过“三、六”两音的“轻、重”变化和“五”音的“活奏”等,使一首“二四”曲谱奏出四种不同调体的音乐来。著名音乐学家、律学家、武汉音乐学院教授郑荣达先生在《潮乐“二四谱”溯源——兼与〈仁智要录〉筝谱比较研究》一文中曾述,“潮州音乐先前用汉文数字作为乐谱谱字符号,是目前所见遗存的传统音乐谱种中罕见的一种乐谱形态……”
 工尺谱属于文字谱,用于“七声”记谱,始于唐代,普及于宋代。二四谱先于工尺谱,依此推断二四谱在唐代已在潮州音乐中使用,且在后来的应用中,工尺谱受潮州二四谱的影响,产生了“轻四、重四”
工尺谱属于文字谱,用于“七声”记谱,始于唐代,普及于宋代。二四谱先于工尺谱,依此推断二四谱在唐代已在潮州音乐中使用,且在后来的应用中,工尺谱受潮州二四谱的影响,产生了“轻四、重四”
 现象。锣鼓经应该在宋代已传入潮州。
现象。锣鼓经应该在宋代已传入潮州。
潮州音乐的“乐器”,体现了充分的历史性、地方性和独特性。“徽”最早指系琴弦的绳,后指七弦琴琴面上的音位标识(古琴镶嵌十三个螺钿,称“十三徽”)。迄今潮汕人将弦乐器的千金称“徽”,上把位称“上徽”,下把位称“下徽”。潮州二弦是潮州音乐中最具地方性的拉弦乐器,因其形制、奏法、音质、音色的独特而成为识别潮州音乐的重要符号。二弦源于唐代北方奚部族人(游牧民族,又称“奚人”)乐器——奚琴(后称“嵇琴”),其与唐初中原汉族乐器轧筝(有说从秦筝演变而来;有说从中国西南或南方丝绸之路传入,见《南诏奉圣乐》)发音方式相近,都用竹片“轧弦发音”,发音原理上属板箱型、竹擦弦鸣乐器,也是我国最早的弓弦乐器。奚琴以竹片置于两弦间而轧之,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旧唐书·音乐志》)。“轧”(动词)者“锯”也,潮汕人将拉弦乐器称“弦”,将拉弦乐器演奏称“锯弦”,在日常生活中将聊天也称“锯弦”,如“食饱无事就过来滴茶甲锯弦哩”(当意义加强时称“锯帕弦”)。

图 1-16 唐代紫檀五弦琵琶琴身螺钿图案
奚琴是胡琴类乐器的前身。唐宋时期,奚琴“在福建南音、秦腔、潮州音乐等(地方音乐)中称为‘二弦’……潮州则由奚琴而改成‘竹弦’,再由竹弦而改成南洋进口的乌木代替竹筒,以蟒皮代替桐板面而成现今的潮州‘二弦’”
 。还有,潮州乐器制作惯于在器身表面镶嵌精美的螺贝装饰图案。相传这一装饰工艺源于商代的漆器,谓称“螺钿”,用螺壳与海贝,磨制成人物、花鸟、文字或几何图形等薄片镶嵌在器物表面。至唐代,螺钿工艺已达到成熟之境,广泛应用于漆器、家具、乐器、屏风、盒匣、盆碟、木雕及相关的工艺品上。图1-16 是流入日本的唐代紫檀五弦琵琶(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内的正仓院),其将唐代螺钿镶嵌工艺发挥到了极致,表现了大唐盛世的华贵气象。螺钿这一中国传统乐器制作工艺在潮州传续至今。
。还有,潮州乐器制作惯于在器身表面镶嵌精美的螺贝装饰图案。相传这一装饰工艺源于商代的漆器,谓称“螺钿”,用螺壳与海贝,磨制成人物、花鸟、文字或几何图形等薄片镶嵌在器物表面。至唐代,螺钿工艺已达到成熟之境,广泛应用于漆器、家具、乐器、屏风、盒匣、盆碟、木雕及相关的工艺品上。图1-16 是流入日本的唐代紫檀五弦琵琶(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内的正仓院),其将唐代螺钿镶嵌工艺发挥到了极致,表现了大唐盛世的华贵气象。螺钿这一中国传统乐器制作工艺在潮州传续至今。

图 1-17 潮州二弦琴身螺钿图案
潮州音乐的“乐典”,主要见于遗存的音乐文本和仕潮文人官员的著述中。宋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既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文学与音乐的结合达到了完美之境。宋词是在相对固定的曲调中填入唱词,曲调称为“词牌”,发展至元代又称“曲牌”。潮州音乐中尚保留了大量的词牌、曲牌名称,如《六么令》《刮地风》《西门子》《醉花阴》《喜迁鹰》《水仙子》《点绛唇》《耍孩儿》《满江红》《西江月》《尾声》等。现存潮州大锣鼓的牌子套,如《岳飞会战牛头山》《薛丁山三休樊梨花》《关公过三关》《薛刚祭坟》《刘秀复中兴》《十八寡妇征西番》《黄飞虎反朝歌》《六国封相》《秦琼倒铜旗》《瓦岗起义》等,都脱胎于宋元及明代以来的戏剧音乐。
现存的《荔镜记》《荔枝记》《金花女大金》等明代戏文,不仅讲述了发生在潮州民间的风物习俗和真实故事,还描述了当时潮州音乐的活动状貌。如:“今冥灯光月团圆,琴弦笙箫,闹满街市”(《荔镜记》);“笙箫和起入人耳,真个称人心意,恨织女牛郎都不相见”(《荔镜记》);“香车宝马闹满处,琵琶龙笛,琴弦声和”(《荔镜记》);“元宵好景家家乐,箫鼓喧天处处闻”(《荔镜记》);“听见城楼鼓角惨,三四更声。纱窗外,月光都成镜”(《荔枝记》);“且喜到得潮州城,城内车马得人惊,弹琴吹箫实好听”(《荔枝记》)等。戏文中还讲到闹元宵、花灯、影戏、打秋千、舞狮、鳌山景、吃槟榔、穿木屐乃至“搬戏”(指请戏班到地方或家中演戏)、“做功德”(指请僧众诵经念佛以超度亡灵)等诸多潮州地方习俗。
1975 年12月23日,潮州市潮安县西山溪排涝工程施工中在凤塘镇书图村挖掘出土明代宣德年间戏文抄本《刘希必金钗记》(简称《金钗记》),这是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南戏写本(比成化南戏刻本《白兔记》早30 余年)。该戏文的发掘对于研究我国南曲戏文的流变、传播和明代闽南方言、风俗状貌有着重要的价值。对《金钗记》的学术价值,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第三次理事会上讲:“潮汕地区的历史文物,可供独立研究的东西很多,明本《金钗记》戏文的出土,我认为是足以举行一次国际性的会议来加以详细研究。”
 中国戏曲史家、中山大学吴国钦教授认为:“使用了大量的潮州方言土语俗语,大量采用潮韵,还用了潮人熟悉的人文景观、名物胜迹。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刘希必金钗记》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出现的潮州戏剧本,属最古老的潮剧本子。”
中国戏曲史家、中山大学吴国钦教授认为:“使用了大量的潮州方言土语俗语,大量采用潮韵,还用了潮人熟悉的人文景观、名物胜迹。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刘希必金钗记》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出现的潮州戏剧本,属最古老的潮剧本子。”
 据潮籍戏曲研究学者詹双晖博士统计,《刘希必金钗记》全剧共用约200 支曲子,约100个曲牌。这些曲牌来源广泛,“有宋人词牌、民间歌谣曲牌、北曲、唐代大曲及庙堂音乐曲牌”等。
据潮籍戏曲研究学者詹双晖博士统计,《刘希必金钗记》全剧共用约200 支曲子,约100个曲牌。这些曲牌来源广泛,“有宋人词牌、民间歌谣曲牌、北曲、唐代大曲及庙堂音乐曲牌”等。
 该抄本还附录了《三棒鼓》和《得胜鼓》两个锣鼓谱,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潮州锣鼓经记载。陈天国先生讲,依此“可将潮州锣鼓经的历史推至宋代”
该抄本还附录了《三棒鼓》和《得胜鼓》两个锣鼓谱,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潮州锣鼓经记载。陈天国先生讲,依此“可将潮州锣鼓经的历史推至宋代”
 。该锣鼓谱迄今尚在海陆丰正字戏戏班中使用。
。该锣鼓谱迄今尚在海陆丰正字戏戏班中使用。
潮州音乐的“乐像”,保留了足量的唐宋遗风。唐代大曲的多曲连缀,“从‘入破第一’至‘出破’还整套保存在清代刊印的潮剧戏文中……其中的‘催’‘煞’等术语还保留至今”
 。如《锦上添花》《春晴鸟语》《金龙吐珠》《倒插花》《蜻蜓点水》《平沙落雁》《双娇娥》《双蝴蝶》《十八菩萨》《混江龙》十曲连成一套(还有很多套曲形式)。潮州音乐中的琵琶、秦琴等弹弦乐器至今保留了唐代“斜抱”的演奏方式。唐代燕乐坐部伎演奏以“赤足盘坐,右足托琴”为主,这一演奏姿势保留于潮州二弦中并成为潮州二弦演奏的标准姿势:“赤足席地半跏趺坐,右足架在左腿上,足底朝天来承放二弦筒。”
。如《锦上添花》《春晴鸟语》《金龙吐珠》《倒插花》《蜻蜓点水》《平沙落雁》《双娇娥》《双蝴蝶》《十八菩萨》《混江龙》十曲连成一套(还有很多套曲形式)。潮州音乐中的琵琶、秦琴等弹弦乐器至今保留了唐代“斜抱”的演奏方式。唐代燕乐坐部伎演奏以“赤足盘坐,右足托琴”为主,这一演奏姿势保留于潮州二弦中并成为潮州二弦演奏的标准姿势:“赤足席地半跏趺坐,右足架在左腿上,足底朝天来承放二弦筒。”

以下是唐代奚琴与潮州二弦演奏姿势对照图:

图 1-18 唐代奚琴(左)与潮州二弦(右)演奏姿势对照图

潮州音乐的“乐俗”,主要依附于民间民俗活动。最为突出的是潮州锣鼓乐、潮州庙堂乐和潮阳笛套乐三个乐种,分别是从游神赛会、功德道场和祭祀典礼中伴生、发展而来。
如潮州锣鼓乐,源自明代潮州城楼差役鸣告官员出行和发号节事指令的敲击锣鼓。古代潮州城分设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城楼上有差役驻守,这些差役负责开闭城门和管理城门内外的治安。发号示令的主要方式是敲击锣鼓,不同等次、内容的示令,敲击不同的鼓点。这种从城楼上传来的锣鼓声长期传入人们的耳帘,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构成。在长期的情感认同中,锣鼓成为潮州地方民间民俗活动(节日庆典、游神赛会、功德道场等)中不可或缺的乐器,从而衍生出了潮州锣鼓乐这一独特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饶宗颐先生在《安济王考》中说:“潮安所祀神,以安济圣王为最尊。”
 潮人称神为“老爷”,安济圣王被称为“大老爷”,安济圣王庙则被称为“大老爷宫”(今“青龙古庙”)。青龙古庙建于明代,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每年正月安济圣王巡游是潮州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号召力最强的民俗活动。潮州大锣鼓正是伴随这一民间民俗活动应运而生。2012年2月,潮州“青龙庙会”被列入广东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8年1月,青龙古庙被中共潮州市委宣传部、潮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评为“潮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地理坐标”。
潮人称神为“老爷”,安济圣王被称为“大老爷”,安济圣王庙则被称为“大老爷宫”(今“青龙古庙”)。青龙古庙建于明代,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每年正月安济圣王巡游是潮州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号召力最强的民俗活动。潮州大锣鼓正是伴随这一民间民俗活动应运而生。2012年2月,潮州“青龙庙会”被列入广东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8年1月,青龙古庙被中共潮州市委宣传部、潮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评为“潮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地理坐标”。

图 1-19“游神赛会”中的潮州大锣鼓
(司鼓及供图:丁泽楷)
宋代有一种被称为“缠达”的说唱艺术,也叫“转踏”“啭踏”。音乐程式是前有引子,后接两个轮流反复的曲调,用于表达一个故事情节。至今潮州人用“踏踏缠”来形容讲话啰唆、翻来覆去的人。潮州大锣鼓传统牌子套《抛鱼》主要是《梆子腔》《贼句》两个曲调的反复,加上锣鼓段和插段构成,其结构程式与“缠达”一脉相承。宋代百戏如“顶砻”“掉斗”“掉锣”“飞钹”“倒吊吹双嘀嗒(唢呐)”等在潮州流传。木偶戏、皮影戏在潮州更是源远流长,且形式多样(清末时潮人将皮影戏与木偶戏合称“纸影”,并分化出“白竹纸影”“圆身纸影”“柴头戏”“布袋戏”等)。这些百戏、木偶戏、皮影戏都对潮州音乐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潮州音乐源远流长,素有“唐宋遗音”“中原遗响”“华夏正声”之称。1986年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1907—2000)在汕头聆听了岭海丝竹社演奏的潮州细乐《小桃红》后,赋诗:“潮州音乐有宗风,流畅中和听不同。曲调宋元应有自,《浪淘沙》又《小桃红》。”
 这是对潮州细乐《小桃红》及潮州音乐的高度赞誉。1988 年,古筝大师、中国音乐学院曹正教授为“澄海潮乐研究会”成立题写贺词,称“潮州音乐乃华夏正声,中国民间音乐之精粹”。2001年10月,民族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教授观看了广东潮剧院一团的进京演出,称“潮乐才是真正的唐乐”。音乐理论家、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称“潮州音乐是中国民乐的根”。琵琶大师、中国音乐学院刘德海教授对潮州音乐抱有浓烈的兴趣,2002年他将潮州音乐作为“‘1’行动计划”(刘德海先生于2002 年起正式启动的传统音乐保护活动)的首选,专程抵潮考察潮州音乐,其间曾感慨地说:“这就是我苦苦寻觅的华夏正声!”
这是对潮州细乐《小桃红》及潮州音乐的高度赞誉。1988 年,古筝大师、中国音乐学院曹正教授为“澄海潮乐研究会”成立题写贺词,称“潮州音乐乃华夏正声,中国民间音乐之精粹”。2001年10月,民族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教授观看了广东潮剧院一团的进京演出,称“潮乐才是真正的唐乐”。音乐理论家、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称“潮州音乐是中国民乐的根”。琵琶大师、中国音乐学院刘德海教授对潮州音乐抱有浓烈的兴趣,2002年他将潮州音乐作为“‘1’行动计划”(刘德海先生于2002 年起正式启动的传统音乐保护活动)的首选,专程抵潮考察潮州音乐,其间曾感慨地说:“这就是我苦苦寻觅的华夏正声!”

2016年10月,杜亚雄教授专程抵潮考察潮州音乐,观看了潮州西湖儒乐社、汕头岭海丝竹社老艺人的表演,走访了普宁钧天乐社,考察了潮州大锣鼓的民间传承状况。
2017年10月16—17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齐琨教授、杨红教授、刘嵘副教授、张英杰秘书一行4人专程抵潮考察潮州音乐,聆听了潮州西湖儒乐社老艺人的表演,古朴典雅、风韵独特的潮州音乐给几位音乐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使考察更深入,他们在潮州市文化馆就潮州弦诗乐、潮州细乐、潮州大锣鼓、潮州筝及潮州音乐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等问题与文化馆领导和老艺人进行了座谈。

图 1-20 杜亚雄教授(第二排左五)同潮州湘桥区意溪镇中津村少儿大锣鼓队合影(施绍春供图,2016年10月20日)

图 1-21 齐琨教授(前排左三)、杨红教授(前排左五)、刘嵘副教授(后排右二)、张英杰秘书(后排右一)与潮州西湖儒乐社老艺人合影(张英杰供图,2017年10月16日)
当代著名潮籍剧作家郭启宏先生曾就潮州音乐的神韵品格这样讲:“自然和谐的天趣最终染就潮州音乐的颜色——绿!……潮州音乐之所以出绿,盖因它不曾有过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怪诞不经,狂躁冲动。演奏者淡泊名利,优雅平和,常处太极态,讲究‘神’‘气’‘韵’‘味’,操弦促柱,一音三韵,雅而不矜,丽而不俗,味足神完。”
 2002 年10 月31 日,第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北京保利剧院隆重推出潮州音乐专场,音乐会由刘德海先生担任主持和乐团指挥,参加演出的有民乐演奏家张维良、杨靖及中国音乐学院师生组成的大型民族乐队。演出曲目:①潮州弦丝:《迎仙客》《千家灯》《百家春》;②潮阳笛套锣鼓:《登楼》;③潮州弦丝:《大八板》;④潮州弦丝:《出水莲》《昭君怨》;⑤潮州弦丝:《柳青娘》;⑥潮州弦丝:《柳摇金》;⑦潮州弦丝:《平沙落雁》《粉红莲》;⑧潮州大锣鼓:《抛网捕鱼》。演出结束后,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刘德海先生真挚而深情地高呼:“潮州音乐万岁!绿色音乐万岁!万岁!”
2002 年10 月31 日,第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北京保利剧院隆重推出潮州音乐专场,音乐会由刘德海先生担任主持和乐团指挥,参加演出的有民乐演奏家张维良、杨靖及中国音乐学院师生组成的大型民族乐队。演出曲目:①潮州弦丝:《迎仙客》《千家灯》《百家春》;②潮阳笛套锣鼓:《登楼》;③潮州弦丝:《大八板》;④潮州弦丝:《出水莲》《昭君怨》;⑤潮州弦丝:《柳青娘》;⑥潮州弦丝:《柳摇金》;⑦潮州弦丝:《平沙落雁》《粉红莲》;⑧潮州大锣鼓:《抛网捕鱼》。演出结束后,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刘德海先生真挚而深情地高呼:“潮州音乐万岁!绿色音乐万岁!万岁!”
据潮汕墓葬出土的兵器和礼器考证,先秦以前中原、吴越文化已传入潮地。由于潮汕地区多锡矿,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在这一地区广泛铸造。潮阳、惠来出土的青铜甬钟、汕头举丁村出土的青铜鼎和铜觚、揭阳中夏村出土的铜剑及米字纹陶罐、惠来华湖乡出土的青铜甬钟,特别是兴宁县新圩镇大村古树窝出土的青铜编钟(共六件,五件为一套,另有一枚单钟),其“音列结构为大二度关系,不同于中原古钟多为大三度或小三度的情况,明显有百越地区特点”
 。
。
潮州音乐的渊源可追溯至隋唐,而其真正形成是在唐宋。隋唐之际潮州土著与中原移民对立,陈政父子入闽,屡平“蛮僚啸乱”,促进了土汉融合。明廖用贤撰《尚友录》(卷四)载:“隋朝协律郎陈政晚年,于唐初入闽垦殖,其子陈元光精通音乐,素以乐、武治化潮、泉二州著称。”
 中唐时期中原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全面进入潮州,对潮州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佛教空前盛行,全国十大州府(厦门、普陀山、南昌、大同、临海、郑州、泉州、福州、潮州和邢台)兴建开元寺。随着潮州开元寺(738年建)及潮阳灵山寺(791年建)的兴建,加上中原南来仕宦的频繁出往,一些佛教法曲和宫廷燕乐涌入潮地,潮州和潮阳成为丝竹吹管、钟鼓和鸣最大的集散地。
中唐时期中原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全面进入潮州,对潮州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佛教空前盛行,全国十大州府(厦门、普陀山、南昌、大同、临海、郑州、泉州、福州、潮州和邢台)兴建开元寺。随着潮州开元寺(738年建)及潮阳灵山寺(791年建)的兴建,加上中原南来仕宦的频繁出往,一些佛教法曲和宫廷燕乐涌入潮地,潮州和潮阳成为丝竹吹管、钟鼓和鸣最大的集散地。
历史上,中原儒家文化全面输入潮州是以韩愈入潮为标志。韩愈治潮八月,虽身处逆境,但仍一心为民,造福一方,推行各项改制措施,驱鳄除害、关心农桑、释放奴婢、延师兴学,促进了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的发展,使潮州从一个“蛮夷之地”逐步迈向“岭海名邦”。韩愈移潮后,其功绩为潮人所称颂。为感念其恩德,潮人将东山改称“韩山”、恶溪改名“韩江”,还为其建祠立庙。时至今日,仍保留着韩文公祠、祭鳄台、景韩亭、昌黎旧治坊、太山北斗坊等众多与韩愈有关的文物古迹和传说故事。千百年来,“崇韩”“敬韩”情结在潮人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

图 1-22 韩愈像

“驱鳄除害”是韩愈在潮为官期间,为民造福的一大壮举。韩愈《潮州祭神文五首》中有这样的记述:
选牲为酒,以报灵德也;吹击管鼓,侑香洁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当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飨!(自第二首)
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谨卜良日,躬率将吏,荐兹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声,以谢神贶。神其飨之!(自第三首)
谨具食饮,躬斋洗,奏音声,以献以乐,以谢厥赐,不敢有所祈。尚飨!(自第五首)

其中,“吹击管鼓,侑香洁也”“侑以音声,以谢神贶”“躬斋洗,奏音声”是对当时潮州民间祭神仪式中音乐活动的描述。
唐时,在韩愈之前后还有一些宰相文人被贬潮州,如常衮[729—783,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李宗闵[约783—846,字损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杨嗣复[783—848,字继之,又字庆门,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市)人]、李德裕[787—850,字文饶,小字台郎,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县)人]等,这些人虽对潮州音乐未有直接建树,但其深厚的人文素养和高尚的个人品格,对潮州音乐的熏染与风格的形成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中原佛教音乐与潮州本土民谣小曲融合,最终形成了潮州庙堂音乐;中原儒家音乐与本土地方音乐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浓郁文人气质的潮州弦诗乐、潮州细乐(又称“儒乐”)。此外,道教音乐在唐代传入潮州。“唐,交趾道士年百岁渡海舟覆,流至潮州,结庵于金山。”
 唐咸亨年间(670—674),龙虎山道士陈假庵在潮阳东山玄帝庙西建超真观,并创建东岳庙。
唐咸亨年间(670—674),龙虎山道士陈假庵在潮阳东山玄帝庙西建超真观,并创建东岳庙。
 宋政和元年(1111),海阳县城内建“玄妙观即天庆观”
宋政和元年(1111),海阳县城内建“玄妙观即天庆观”
 。宋绍兴年间(1131—1162),揭阳县治西约一里建元妙观
。宋绍兴年间(1131—1162),揭阳县治西约一里建元妙观
 。宋咸淳四年(1268),道士高道惟在潮阳贵屿创崇贞观。佛教与道教、佛寺与道观近乎同步入潮,并行发展,且互为影响。正如潮州白塔寺正殿牌匾述:“万善崇归儒道共参僧,寿康并臻添筹同证禅”(开元西堂宏钦撰,吕新民时年九十有一敬书)。只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逐渐成为潮人信仰的主流,佛教音乐日渐兴旺,道教音乐则渐次衰落。
。宋咸淳四年(1268),道士高道惟在潮阳贵屿创崇贞观。佛教与道教、佛寺与道观近乎同步入潮,并行发展,且互为影响。正如潮州白塔寺正殿牌匾述:“万善崇归儒道共参僧,寿康并臻添筹同证禅”(开元西堂宏钦撰,吕新民时年九十有一敬书)。只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逐渐成为潮人信仰的主流,佛教音乐日渐兴旺,道教音乐则渐次衰落。
南宋末年(1278)宋帝南逃,政治中心南移,加剧了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随之,大量中原文化(包括衣冠、文物、音乐、习俗等)传入潮州,使潮州的乐风乐俗嵌入了宫廷文化的特质。左藏朝散大夫吴丙(字汝光,原籍江西永福)随南宋名臣文天祥南渡,携大批乐工、歌伎,宫廷礼乐落户潮阳。自此,潮州酬神祭祀、礼佛斋蘸中的民风民俗以及民间笙弦歌舞开始全面承袭中原古风,并呈现出了蓬勃兴盛的发展状貌。宫廷音乐按演奏场域分为“外朝音乐”和“内廷音乐”,按功能性质分为“典制音乐”和“娱乐音乐”。受宋代教坊(两宋时期最重要的俗乐机构)大乐的影响,具有浓郁典制风格的成套祭祀音乐——“大晟乐”出现于潮州孔庙(俗称“红学宫”)的祭孔仪式活动中。史载,宋代潮州地区登进士者有一百多人,且“仕皆倡琴瑟,重乐以治民”
 。饶宗颐先生在海外搜集到的《永乐大典》十三萧“潮”字号“潮州府”(残卷)总目十五“学校”中,记述了嘉定十四年(1221)重修供奉孔子的宣圣庙大成殿及恢复祭孔旧制的情况,并对宋代潮州祭孔“大晟乐”的活动情况有以下描述:潮城孔庙每年仲春(农历二月)、仲秋(八月上旬)举行祭孔典礼,演奏整套的“大晟乐”。迎神、送神奏《凝安》《安宁》;奠币奏《明安》;酌献奏《成安》;升殿、降殿奏《同安》;终结时皆奏《文安》。所用乐器有编钟、编磬十六枚,琴自一弦到九弦共十张,笙、瑟、凤箫等。“大晟乐”的演奏初由士子“执器登歌”,后因“岁月侵久,士失其传”,淳熙年间改由民间乐工演奏。
。饶宗颐先生在海外搜集到的《永乐大典》十三萧“潮”字号“潮州府”(残卷)总目十五“学校”中,记述了嘉定十四年(1221)重修供奉孔子的宣圣庙大成殿及恢复祭孔旧制的情况,并对宋代潮州祭孔“大晟乐”的活动情况有以下描述:潮城孔庙每年仲春(农历二月)、仲秋(八月上旬)举行祭孔典礼,演奏整套的“大晟乐”。迎神、送神奏《凝安》《安宁》;奠币奏《明安》;酌献奏《成安》;升殿、降殿奏《同安》;终结时皆奏《文安》。所用乐器有编钟、编磬十六枚,琴自一弦到九弦共十张,笙、瑟、凤箫等。“大晟乐”的演奏初由士子“执器登歌”,后因“岁月侵久,士失其传”,淳熙年间改由民间乐工演奏。
 以上演奏阵容之庞大、形式之正规可见一斑。南宋是潮州音乐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今天,潮州音乐中依然保留了浓郁的宫廷古韵。
以上演奏阵容之庞大、形式之正规可见一斑。南宋是潮州音乐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今天,潮州音乐中依然保留了浓郁的宫廷古韵。
明清时期是潮州音乐发展的成熟期。明代前170 余年间,潮州社会安定,区域人口除自然增长外还有大量移民迁入。人口的增长使农业得到发展,加上水路的繁荣,促进了粮食的商品化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由此带来的城市文化生活的繁荣,为潮州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景象。成化四年(1468),江西提学李龄
 告老回乡,带来百余套宫廷乐谱,逝后供放于孔庙,被奉为“圣乐”,唯举人以上才能习之,逢祭孔之日才可奏之。为防遗失,李龄之女将部分藏谱移于其夫林大春
告老回乡,带来百余套宫廷乐谱,逝后供放于孔庙,被奉为“圣乐”,唯举人以上才能习之,逢祭孔之日才可奏之。为防遗失,李龄之女将部分藏谱移于其夫林大春
 处。林大春性敏慧、好乐,常居棉城,关注并介入地方和乡族事务,他将其教于乐工,由此得以相传。其后,曾任广西兵备副使的陈淳临
处。林大春性敏慧、好乐,常居棉城,关注并介入地方和乡族事务,他将其教于乐工,由此得以相传。其后,曾任广西兵备副使的陈淳临
 因平交趾有功,荣归故里,朝廷赐予一班乐师、歌伎随其还乡,使宫廷音乐在潮落户生根,形成以笙、箫、管、笛为主器,富含宫廷风韵的地方乐种。除了宫廷音乐外,还有诸如纸影戏、皮影戏、布袋戏及杂耍、顶砻、戴碓等民间百戏为潮州音乐注入了新的元素。明、清之际,戏曲艺术在中国步入全盛期。在潮州,随着宋元南戏、弋阳腔、昆腔、西秦戏、外江戏、正字戏的流入和盛行,催生了潮音戏(潮剧)的兴起与繁荣。同时大量外来曲牌、牌子曲、锣鼓乐以及各种乐器、演奏方法、组合程式的出现,为潮州弦诗乐、吹管乐和锣鼓乐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因平交趾有功,荣归故里,朝廷赐予一班乐师、歌伎随其还乡,使宫廷音乐在潮落户生根,形成以笙、箫、管、笛为主器,富含宫廷风韵的地方乐种。除了宫廷音乐外,还有诸如纸影戏、皮影戏、布袋戏及杂耍、顶砻、戴碓等民间百戏为潮州音乐注入了新的元素。明、清之际,戏曲艺术在中国步入全盛期。在潮州,随着宋元南戏、弋阳腔、昆腔、西秦戏、外江戏、正字戏的流入和盛行,催生了潮音戏(潮剧)的兴起与繁荣。同时大量外来曲牌、牌子曲、锣鼓乐以及各种乐器、演奏方法、组合程式的出现,为潮州弦诗乐、吹管乐和锣鼓乐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晚清时期,民间善堂、佛社、茶馆林立,乐社、乐馆、锣鼓馆遍布潮汕城乡各地。庙堂佛乐、宫廷雅乐、民间俗乐、文人儒乐深入社会各群体,并活跃于民间礼俗和休闲娱乐,造就了大批专业与半专业的潮乐工作者,促进了潮州音乐的繁荣与发展。至民国时期,潮州音乐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汇集南北、融合雅俗于一体的地方音乐格局,分化出多个独立的子乐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潮人大量移居南洋,使潮州音乐传播到了海外。
潮州会馆是潮人在外谋求生存、开拓事业而自行成立的,具有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的民间组织。这一组织为沟通同乡感情、互助团结、共谋福利、兴办教育、赈灾义举和传扬潮州文化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在沪经商的潮州人(当时的上海人称潮州人为“潮帮”)在上海成立了“潮州会馆”(地点:洋行街105号)。上海的潮州会馆“在义捐、办学、救灾等方面对家乡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至20世纪30年代,潮州人在沪人数达数十万。随着大量潮人入沪,上海各潮人聚居区成立了潮乐社团。潮州音乐在上海得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主持录音部工作)的关注、喜爱和推赏。在聂耳的力荐下,潮州会馆乐师演奏的《寒鸦戏水》《柳青娘》等一批潮州音乐代表作品被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发行于海内外。
。至20世纪30年代,潮州人在沪人数达数十万。随着大量潮人入沪,上海各潮人聚居区成立了潮乐社团。潮州音乐在上海得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主持录音部工作)的关注、喜爱和推赏。在聂耳的力荐下,潮州会馆乐师演奏的《寒鸦戏水》《柳青娘》等一批潮州音乐代表作品被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发行于海内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农村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民间乐社、锣鼓馆被文化室、俱乐部、生产队代替。地方音乐文化得到政府和文化部门的重视,相继成立了专业、半专业的音乐工作团体,致力于潮州音乐的发掘、搜集、整理、创作、研究、表演和人才培养。活动场域从乐社、闲间、庭院、书室的自娱自乐拓展到大众舞台,潮州音乐进入了真正创新发展的繁荣期。1953年潮州民间音乐研究组及1956年潮州民间音乐团的成立,为潮州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图 1-23“潮州市潮州民间音乐团”牌匾

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先走出潮州大地的是潮州大锣鼓,重大活动事项有:
(1)1952年12月,由陈名贤领队,著名艺人邱猴尚、陈松、周才等廿二人组成的潮州大锣鼓,赴广州参加欢迎苏联红旗歌舞团访问演出(演奏曲目《抛网捕鱼》)。这是潮州大锣鼓首次抵穗演出,司鼓邱猴尚,唢呐领奏周才。

(2)1953年4月,由邱猴尚、王嗳仔、王通权、王良元、林捷鹏、陈松、周才、傅振尧、陈梅松、赖细弟、李贞奎、谢执等12 位民间艺人组成的潮州大锣鼓,
 作为广东代表队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作为广东代表队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表演《抛网捕鱼》(司鼓:邱猴尚,唢呐领奏:周才),荣获优秀节目奖。
,表演《抛网捕鱼》(司鼓:邱猴尚,唢呐领奏:周才),荣获优秀节目奖。

(3)1956年8月,潮州民间音乐研究组林云波、周才、苏文贤、傅振尧与汕头潮乐改进会杨广泉、林运喜、杨海林、吴锡有等组成潮州大锣鼓演奏队,进京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演奏大锣鼓《庆丰收》(编曲:陈松、周才、林云波,司鼓:林运喜,唢呐领奏:张天平)等获优秀节目奖。

(4)1957年8月,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
 受文化部的委托,华南歌舞团作曲家蔡余文(1921—2012,广东陆丰大安人)负责潮州音乐节目的挑选和队伍的组建工作,并担任艺术指导。“他参与整理加工的潮州大锣鼓《抛网捕鱼》、潮州小锣鼓《粉蝶采花》,以及由广东汕头鼓乐演奏家林运喜先生改编的潮州大锣鼓《画眉跳架》均获得了‘金质奖章’,为我国的民间音乐艺术在国际上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受文化部的委托,华南歌舞团作曲家蔡余文(1921—2012,广东陆丰大安人)负责潮州音乐节目的挑选和队伍的组建工作,并担任艺术指导。“他参与整理加工的潮州大锣鼓《抛网捕鱼》、潮州小锣鼓《粉蝶采花》,以及由广东汕头鼓乐演奏家林运喜先生改编的潮州大锣鼓《画眉跳架》均获得了‘金质奖章’,为我国的民间音乐艺术在国际上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图 1-24 潮州音乐代表队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影

“文革”开始(1966),潮州音乐陷入消沉期,特别是庙堂音乐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几乎销声匿迹。推动潮州音乐发展的两个重要机构潮州民间音乐研究组和潮州民间音乐团被迫关停。“文革”结束,潮州音乐获得新生,1979年潮州民间音乐团恢复运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潮州音乐迎来了全面创新发展的新局面,在题材内容、和声配器、演奏技法和舞台表演上,兼收并蓄,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19年4—10月,中共潮州市委宣传部、潮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讴歌新时代,畅想中国梦,展示潮州文艺创作的新成就,举办“潮人故里·精美潮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潮州市文学艺术系列展演活动”。为配合该项活动,潮州市音乐家协会举办“潮人故里·精美潮州原创音乐作品征集活动”。此次活动要求以“潮人故里·精美潮州”为主题,体现地域性、本土性和传统性,同时兼顾时代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共征集作品23 首,其中器乐作品10 首(合奏9 首,独奏1 首),声乐作品13首(独唱12首,合唱1 首)。为体现公平、公正原则,特邀请广东省著名词曲家进行匿名评审,最终选出8 首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其中:器乐作品5首,分别是潮州筝乐《红楼潮韵12首》(作曲:辜玉斌)、二胡与小乐队《潮韵流芳》(作曲:沈松敏,配器:陈继志)、潮州大锣鼓《抗战颂歌》(作曲:杨清波、陈继志,配器:陈继志,配鼓:丁泽楷)、潮州大锣鼓《强渡乌江》(作曲:杨汉荣,配器、配鼓:杨汉荣,司鼓:杨瀚)、潮州大锣鼓《马发守潮州》(作曲:杨业成,配器:杨汉荣,配鼓:黄义孝);声乐作品3首,分别是歌曲《工夫茶》(作曲:连向先,作词:叶方义)、方言混声合唱《韩江情歌》(作曲:刘锡樑;作词:陈耿之)、歌曲《韩江边,是我家》(作曲:郑皓丹,作词:余培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