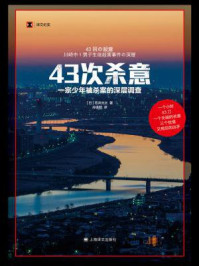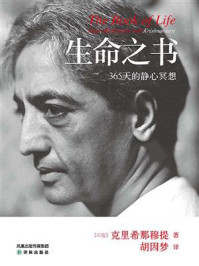|
11 |

进步的浪潮到底有多坚实深厚?如今取得的进步会不会哪天戛然而止,甚至出现反转?暴力史为我们看待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我曾在之前出版的作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里指出,不论用哪个客观指标衡量,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都出现了下降。可是当我还在伏案写稿的时候,就有不少审稿的同仁提醒我说,恐怕在第一本书到达书店之前我的牛皮就要吹破了。那段时间,人们一直被伊朗要与以色列或是美国开战,甚至可能打核战争的愁云所笼罩。
在新书实际出版的2011年发生了一连串的坏消息,几乎让这本书沦为废纸:叙利亚内战打响,西欧恐怖袭击猖獗,美国警察枪击伤人事件频发,愤怒的民粹主义情绪在西方社会蔓延,导致仇恨犯罪和种族主义、厌女症(misogyny)
 大行其道。
大行其道。
人们不愿意相信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在下降,不仅不愿意相信,随处可见的消极新闻带来了认知上的偏差,让人们仓促地得出结论,认为暴力事件正在愈演愈烈。所以在接下去的5个章节中,我将用回顾事实数据的方式梳理近年来发生的各种消极事件。我将画出数种暴力现象发展至今的历史轨迹,图上用箭头标记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数据的截止点。
 7年左右的光景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转瞬即逝,但是对一本书和其中观点而言,这眨眼的工夫足以区分它到底是对热门观点的跟风,还是对历史潮流的洞见。更重要的是,我将挖掘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历史驱动力,以便解释这些潮流和趋势的成因,并把它们放在本书的主题——进步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为此,我需要介绍一些新的概念和想法,以便解释这些“驱动力”的本质。首先,我选择以最极端的暴力事件作为开始:战争。
7年左右的光景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转瞬即逝,但是对一本书和其中观点而言,这眨眼的工夫足以区分它到底是对热门观点的跟风,还是对历史潮流的洞见。更重要的是,我将挖掘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历史驱动力,以便解释这些潮流和趋势的成因,并把它们放在本书的主题——进步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为此,我需要介绍一些新的概念和想法,以便解释这些“驱动力”的本质。首先,我选择以最极端的暴力事件作为开始:战争。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战争一直都是各国政府最青睐的消遣活动,而和平不过是从一场战争结束到下一场战争开始之间的喘息。
 这可以在图11-1里看到,图中标注了在过去500年中,每个时代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们处于战争状态时间所占的比例。所谓的大国就是有实力将自身的影响力延伸到国境线外的国家或帝国,它们通常旗鼓相当,这些国家一起掌握了每个时代里全世界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这可以在图11-1里看到,图中标注了在过去500年中,每个时代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们处于战争状态时间所占的比例。所谓的大国就是有实力将自身的影响力延伸到国境线外的国家或帝国,它们通常旗鼓相当,这些国家一起掌握了每个时代里全世界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大国之间的战争,比如世界大战,是我们这个富有同情心的物种所能想象的、最具破坏性的毁灭事件,它们造就的受害者比其他所有形式地区冲突的总和更甚。图11-1显示,在世界进入现代前夕,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几乎总是处于战争的状态。而近几年,它们几乎没有发动过战争:曲线最后一个拐点代表的是朝鲜半岛的战争,而那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
大国之间的战争,比如世界大战,是我们这个富有同情心的物种所能想象的、最具破坏性的毁灭事件,它们造就的受害者比其他所有形式地区冲突的总和更甚。图11-1显示,在世界进入现代前夕,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几乎总是处于战争的状态。而近几年,它们几乎没有发动过战争:曲线最后一个拐点代表的是朝鲜半岛的战争,而那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

图11-1 大国间战争(1500—2015年)
资料来源:Levy & Thompson 2011,更新了21世纪的数据。2000—2015年除外,其余年份以25年为统计单位,数据代表大国间开战的年数占25年时间区间的百分比。箭头指示的区段为1975—1999年,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图5-12中最后25年的数据。
大国战争时间的锯齿图没有体现出两条有关战争的相反趋势。
 在450年的时间里,由大国发动的战争持续时间变得越来越短,发动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军队智囊越来越优秀,部队训练越来越有素,武装配备越来越先进,实际发生的战争伤亡反而变得更惨重,换句话说,世界级的战争变得更短但是破坏力更惊人。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之后,战争的三项指标——频率、时长和破坏力才依序出现了下降,世界由此进入了被称为“长期和平”的历史阶段。
在450年的时间里,由大国发动的战争持续时间变得越来越短,发动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军队智囊越来越优秀,部队训练越来越有素,武装配备越来越先进,实际发生的战争伤亡反而变得更惨重,换句话说,世界级的战争变得更短但是破坏力更惊人。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之后,战争的三项指标——频率、时长和破坏力才依序出现了下降,世界由此进入了被称为“长期和平”的历史阶段。
这不只是因为大国之间停止了纷争。在传统观念里,战争意味着交战两国派出制式统一的部队并发生武装冲突,但战争的这种经典定义似乎已经不再适用。
 1945年之后,没有哪一年爆发的战争数超出三起,在1989年后绝大多数的年份里都没有发生战争,而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2003年后,战争已经销声匿迹,这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最长的、没有爆发国家间战争的间隔记录。
1945年之后,没有哪一年爆发的战争数超出三起,在1989年后绝大多数的年份里都没有发生战争,而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2003年后,战争已经销声匿迹,这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最长的、没有爆发国家间战争的间隔记录。
 如今,国家军队间的遭遇战只会造成数百人的伤亡,历史上那些曾经全民动员、动辄死伤数百万人的全面战争已然作古。不过,“长期和平”的说法在2011年的确受到了挑战,比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朝鲜与韩国之间的冲突,所幸每一场冲突的双方最终都能退一步海阔天空,而不是趁势将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由地区冲突上升为全面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战争被当成一种极端手段,每个国家(几乎)都在不惜代价地避免亮出这张底牌。
如今,国家军队间的遭遇战只会造成数百人的伤亡,历史上那些曾经全民动员、动辄死伤数百万人的全面战争已然作古。不过,“长期和平”的说法在2011年的确受到了挑战,比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朝鲜与韩国之间的冲突,所幸每一场冲突的双方最终都能退一步海阔天空,而不是趁势将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由地区冲突上升为全面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战争被当成一种极端手段,每个国家(几乎)都在不惜代价地避免亮出这张底牌。
战争的版图也在持续缩水。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达成和平协议,冷战时期最后的遗留问题以及西半球最后一场活跃的政治性武装冲突由此宣告结束。在数十年前,这样的和平协议是难以想象的。
 与哥伦比亚的情况类似,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共和国以及秘鲁,左派的游击队也曾同以美国为后台的国家政府进行着抗争,而尼加拉瓜则正好相反(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在美国的支持下抗击着左翼政府),这些内战总计导致超过650 000人丧生。
与哥伦比亚的情况类似,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共和国以及秘鲁,左派的游击队也曾同以美国为后台的国家政府进行着抗争,而尼加拉瓜则正好相反(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在美国的支持下抗击着左翼政府),这些内战总计导致超过650 000人丧生。

其他广阔地域也为世界和平的实现添砖加瓦。西欧从来都是血腥的修罗场,战争冲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鼎盛之后,西欧诸国迎来了超过70年的和平时光。尽管仍有严重的政治分歧,但是今天的东亚和东南亚几乎不会再发生频繁的地区间冲突。
目前世界上的战争几乎全部局限在尼日利亚等地区内,生活在该地区的人口不到全世界的1/6。发生在那里的战争无一例外是国家的内战,按照乌普萨拉大学战争冲突数据研究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UCDP)的定义,内战指发生在国家政府与有组织团体间的武装冲突,并且需要有可信的途径证实冲突的年均伤亡规模在1 000人以上。在此,我们的确能找到一些有关战争势头波动的最新原因。冷战结束后全世界内战的数量出现了陡峭的下降态势,从1990年的14起减少到2007年的4起,随后又在2014年和2015年增加到11起,2016年上升到12起。

引起内战数量反弹的主要原因是由激进的组织引发的武装冲突,2015年的11起内战中有8起,2016年的12起中则有10起。要不是这些极端组织的存在,世界上每年的内战数量可能根本不会有变化。也许下面这个数字不是巧合:2014年和2015年各有两起内战是由另一个反启蒙思想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挑起的。
当前最惨烈的内战发生在叙利亚,仅2016年,叙利亚内战造成的战争死亡人数就达到了250 000人(保守估计),它也是图11-2中,世界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在近年攀升的主要原因。


图11-2 战争死亡人数(1946—2016年)
资料来源:数据改编自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7。1946—1988年: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Oslo Battle Deaths Dataset 1946—2008, Lacina &Gleditsch 2005。1989—2015年:UCDP Battle-Related Deaths Dataset version 5.0, Uppsala Conflict Date Program 2017, Melander,Pettersson, & Them ńer 2016。世界人口数据:1950—2016, U.S. Census Bureau; 1946—1949, McEvedy & Jones 1978,有修改。箭头所指的时间为2008年,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图6-2中最新数据的年份。
在走过一段让人惊讶的、近60年的下降时期后,战争死亡人数在曲线的尾巴上出现了一段小的上扬。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人类最惨烈的时光,每年每10万人中有近300人死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数据没有在图表中标出,如若不然,整条曲线后半段的变化趋势和它相比就只能像是一条扁平的、稍微褶皱的地毯而已。如图中所示,战后时期的战争死亡率呈过山车式的下降趋势,各个尖峰依次代表(每年每10万人中)朝鲜战争的22人、60年代末70年代初越南战争的9人,以及80年代两伊战争的5人,随后在2001—2011年间,这条曲线一直徘徊于0.5人附近。反弹出现在2014年,曲线回到了1.5人,并于2016年略微下降至1.2人。2016年的数据也是我们目前能够掌握到的最新数据了。
2012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关注新闻的人可能会因此而认为和平的历史进程开起了倒车,这场屠杀将之前人类数十年的努力付之一炬。他们会这么想大概是因为忘记了,2009年后许多内战的结束都没有伴随锣鼓喧天的仪式并昭告天下(这些从内战中脱身的国家包括安哥拉、乍得、印度、伊朗、秘鲁和斯里兰卡),他们还忘记了从前内战的血腥程度,例如发生在中南半岛(1946—1954年,50万人死亡)、印度(1946—1948年,100万人死亡)、苏丹(1956—1972年,50万人死亡;1983—2002年,100万人死亡)、安哥拉(1975—2002年,100万人死亡),以及莫桑比克(1981—1992年,50万人死亡)的内战。

叙利亚内战迫使绝望的难民背井离乡,许多人历尽千难万险到欧洲寻求庇护,对于这番悲惨景象的想象让一种说法甚嚣尘上,它认为现代社会的难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都多。但是这只是历史健忘症和可得性偏差的又一个体现。政治学家约书亚·戈尔茨坦(Joshua Goldstein)指出,与1971年孟加拉国战争期间的1 000万、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的1 400万难民相比,叙利亚的400万难民只能算小巫见大巫,更何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欧洲难民的数量就有6 000万,而且这些历史时期的世界人口还远远不及如今。

拿冷冰冰的数字来比较并不是为了淡化今天难民们所受的痛苦。我们不应当忘记从前的战争受害者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策制定者们以准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为人类谋求福祉,尤其是要防止他们得出这样的危险结论:当今世界依旧纷争动乱不断。这个结论会诱使他们抛弃全球合作,或者选择向冷战时期那种虚无的“稳定”国际关系中退守。“不是世界出了问题,”戈尔茨坦指出,“而是叙利亚出了问题……曾经(在别的地方)结束过战争的政策和措施,只要稍加努力和变通,也同样可以结束如今发生在南苏丹、也门甚至是叙利亚的内战。”
大量屠戮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的类似行为被称为种族灭绝、大屠杀或者单方面暴力,这种行为与战场上造成的伤亡不相伯仲,两者也常常难以区分。根据历史学家弗兰克·乔克(Frank Chalk)和库尔特·乔纳森(Kurt Jonassohn)的说法:“世界上所有地区、所有历史时期都发生过种族灭绝事件。”
 在战争的白热阶段,种族灭绝死亡率的巅峰值高达年均每10万人中350人。
在战争的白热阶段,种族灭绝死亡率的巅峰值高达年均每10万人中350人。
 与“世界永远不会从战火中吸取教训”的断言相悖,战后的人类社会一点也不像腥风血雨的20世纪40年代。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种族灭绝造成的死亡率一直呈锯齿状的下降趋势,这可以通过图11-3中的两组数据看出。
与“世界永远不会从战火中吸取教训”的断言相悖,战后的人类社会一点也不像腥风血雨的20世纪40年代。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种族灭绝造成的死亡率一直呈锯齿状的下降趋势,这可以通过图11-3中的两组数据看出。

图11-3 种族灭绝造成的死亡率(1956—2016年)
资料来源:PITF,1955—2008年: 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 State Failure Problem Set , 1955—2008, Marshall, Gurr & Harff 2009;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2015。计算过程参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第338页。UCDP, 1989—2016年: UCDP One-Sided Violence Dataset v. 2.5-2016 , Melander, Pettersson, & Themnér 2016;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2017, "High fatality" estimates,由UCDP的Sam Taub修订,世界人口数据来自US Census Bureau。箭头所指的时间为2008年,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图6-8中最新数据的年份。
图中的尖峰代表了布隆迪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仇杀事件(1965—1973年,14万人死亡)、孟加拉国战争(1971年,170万人死亡)、苏丹内战(1956—1972年,50万人死亡),还有距离较近的、发生在波斯尼亚(1992—1995年,22.5万人死亡)、卢旺达(1994年,70万人死亡)和达尔富尔(2003—2008年,37.3万人死亡)的大屠杀等历史事件。

从2014年到2016年,不断涌现的惨剧让又一个暴力时代已然来临的印象深入人心。
 谁都不能用“可喜可贺”来形容无辜平民遇害这样的事,但是和从前的岁月相比,21世纪的数字真可谓九牛之一毛。
谁都不能用“可喜可贺”来形容无辜平民遇害这样的事,但是和从前的岁月相比,21世纪的数字真可谓九牛之一毛。
诚然,光是数据库里的数字并不能很直观地用于评估潜在的战争风险:现代战争不常发生但是破坏力惊人,历史资料在预测战争发生率方面仍显得异常紧缺。
 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只会发生一次的单向世界,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本已不多的历史数据,我们需要用这些数字结合一些额外的知识,以便分析战争发生的原因,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座右铭所言:“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对于战争的减少,我们发现它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战争数量以及战争伤亡人数的减少,它还体现在许多国家战争储备资源的缩减。征兵的力度、军队的规模和全球军费支出占GDP的百分比都在最近的数十年内呈下降趋势。
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只会发生一次的单向世界,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本已不多的历史数据,我们需要用这些数字结合一些额外的知识,以便分析战争发生的原因,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座右铭所言:“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对于战争的减少,我们发现它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战争数量以及战争伤亡人数的减少,它还体现在许多国家战争储备资源的缩减。征兵的力度、军队的规模和全球军费支出占GDP的百分比都在最近的数十年内呈下降趋势。
 最重要的是,男人们(还有女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最重要的是,男人们(还有女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理性与启蒙时代的来临,让进步人士或教派将指责的矛头对准了战争,其中的代表包括帕斯卡、乔纳森·斯威夫特、伏尔泰、塞缪尔·约翰逊以及贵格会等。他们也为减少甚至消除战争献计献策,尤其是康德和他著名的论文《永久和平论》(
Perpetual Peace
)。
 启蒙思潮被认为是18世纪和19世纪世界战争减少甚至期间出现短暂和平的主要原因。
启蒙思潮被认为是18世纪和19世纪世界战争减少甚至期间出现短暂和平的主要原因。
 不过,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康德和其他先贤们认为的和平促进力量才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成效逐现。
不过,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康德和其他先贤们认为的和平促进力量才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成效逐现。
我们在第1章里看到,许多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都推崇“温和的商业”,他们认为国际贸易的甜头会让苦涩的战争黯然失色。这当然合情合理,战后国际贸易在各国GDP中占有的比重扶摇直上,定量分析也证实,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贸易往来频繁的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更小。

启蒙思想的另一个影响,是让民主政府成为醉心功勋的领导人的制动器,防止激进的个人将整个国家拖进毫无意义的战争里。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定给民主制度一个机会(第14章会有进一步探讨)。尽管有一种一刀切的说法认为两个民主制国家之间永远不可能发动战争,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有待商榷,但是我们手头的数据无疑能够佐证一种分层的民主和平理论,也就是两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它们之间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就越小。

现实政治(Realpolitik)
 也是助力长期和平的因素之一。迫于两国在冷战时期毁灭性的军备竞赛(哪怕不考虑核武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不得不对开战的想法深思熟虑,令世界感到惊讶和欣慰的是,它们最终没有打响这场战争。
也是助力长期和平的因素之一。迫于两国在冷战时期毁灭性的军备竞赛(哪怕不考虑核武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不得不对开战的想法深思熟虑,令世界感到惊讶和欣慰的是,它们最终没有打响这场战争。

不过,在造就当今国际政治秩序的众多单一因素中,有一条很少被我们提起,即战争是非法的。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这一点都无从谈起。战争是其他政治手段的延续,战胜国可以获得战利品作为回报,而战争的对错往往无关紧要。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受到了他国的怠慢,它就可以向对方宣战,用侵占领土的方式作为补偿,同时希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能够承认这场领土的吞并活动。
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内华达、新墨西哥和犹他州之所以会成为美国的州,是因为在1846年,美国由于墨西哥长期拖欠债务而发动了战争并侵占了这些土地。同样的故事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承诺,仅在出于自我防卫或者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首肯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战争。国家是不朽的,领土也会代代相传,如今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没法指望从世界其他国家那里获得认同,因为它们能得到的只有谴责。
法律学者奥娜·哈撒韦(Oona Hathaway)和斯科特·夏皮洛(Scott Shapiro)主张战争的非法化才是长期和平得以实现的最大功臣。国际社会应当在战争非法化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个想法最早是由康德在1795年提出的。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它第一次以国家间共识的形式出现是在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
Pact of Paris
)里,或者称为《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
Kellogg-Briand pact
),而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才让它真正生效。从那以后,触犯侵略战争禁忌的国家往往会受到军事上的反击,例如在1990—1991年,国际社会曾组成同盟抗击并挫败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在更多的时候,这条禁忌只是作为一个规范,仿佛在说“发动战争不是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该有的行为”,它的权威由经济制裁等象征性的惩罚措施作为保证。这些惩罚措施的有效性取决于当事国家对自己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地位重视程度,这里应当再次提醒,在面对民粹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的今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重视并且加固国际社会价值观的原因。

规范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被打破。某些愤世嫉俗的观点似乎确实在理,它们认为除非人类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不然所谓的国际规范和公约不过是毫无效力的一纸空文,总有国家可以目空一切地触犯它、凌驾之上。哈撒韦和夏皮洛对此的回应称,哪怕是一个国家国内的法律也时常会被人触犯,小到违章停车,大到杀人放火,但是效力有限的法律总比无章可循要强。根据他们的计算,在签订《巴黎非战公约》前的100年,世界上每年遭到吞并的领土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但是在1928年之后,遭到强占的几乎每一块土地都最终物归原主。弗兰克·凯洛格(Frank Kellogg)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他们分别是时任美国国务卿和法国外交部长)才是笑到最后的人。
不过哈撒韦和夏皮洛指出,国家间战争的非法化同样有它不利的一面。历史上,由于欧洲殖民国家往往会极尽所能榨取和搜刮自己的殖民地,留下一个个空虚疲乏的国家——国境线模糊,没有继任的中央权力机构。这些国家通常会陷入内战和帮派纷争中。在新的国际秩序下,这些战乱不断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不能成为其他国家发动军事行动的目标,而只能数年甚至数十年地维持无政府的动乱状态。
国家间战争的减少始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内战造成的人员伤亡远远比不上侵略战争,而即便是内战的数量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下降。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大国们挑起内战的兴趣逐渐被尽早结束战争的心情所取代,这让它们纷纷倒向支持联合国颁布的、与和平进程有关的提议和努力,此外,它们奔走于好战的国家之间并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多数情况下,这些行动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的确成果斐然。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大国们挑起内战的兴趣逐渐被尽早结束战争的心情所取代,这让它们纷纷倒向支持联合国颁布的、与和平进程有关的提议和努力,此外,它们奔走于好战的国家之间并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多数情况下,这些行动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的确成果斐然。

不仅如此,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富有时,发生内战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富裕国家的政府有能力为国民提供医疗、教育和治安等公共服务,因此可以在民众拥护程度上胜过国内的反叛势力。此外,它们也有实力重新夺得边疆领土的控制权,那些地区一般有军阀、黑手党和游击队(这些角色通常由同一帮人扮演)盘踞。
 有鉴于许多战争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交战双方同时陷入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恐惧(这种博弈的情况被称为安全困境或霍布斯困境),所以邻国间关系的和平稳定,无论最初是谁对谁表现出友好和睦的姿态,都能起到自我强化和平的效果。与之相反,战争则具有感染他国的传染性。
有鉴于许多战争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交战双方同时陷入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恐惧(这种博弈的情况被称为安全困境或霍布斯困境),所以邻国间关系的和平稳定,无论最初是谁对谁表现出友好和睦的姿态,都能起到自我强化和平的效果。与之相反,战争则具有感染他国的传染性。
 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如今战争区域持续减小、世界大部分地区迎来和平的现象。
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如今战争区域持续减小、世界大部分地区迎来和平的现象。
启蒙思潮和后来的政策携手降低了战争的发生率,世界的价值观也随之改变。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那些致力于实现和平的力量,某种程度上都是民心所向的结果:政府的天平之所以向和平倾斜只是因为人民希望获得和平。至少从“民谣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和平是个“好东西”的想法就已经渐渐深入人心,对和平的向往成了西方人的第二天性。如果有国家要发动军事干预,它们必须师出有名,战争只能是在遭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以暴制暴的无奈手段。但是就在和平成为人们心头好之前没多久,战争才是人们共同的追求。战争曾被认为是光荣、振奋人心、鼓舞精神、有男子气概、崇高、英勇、无私的象征,人们认为它可以净化娇气、自私自利、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横行的、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社会。
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和平是个“好东西”的想法就已经渐渐深入人心,对和平的向往成了西方人的第二天性。如果有国家要发动军事干预,它们必须师出有名,战争只能是在遭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以暴制暴的无奈手段。但是就在和平成为人们心头好之前没多久,战争才是人们共同的追求。战争曾被认为是光荣、振奋人心、鼓舞精神、有男子气概、崇高、英勇、无私的象征,人们认为它可以净化娇气、自私自利、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横行的、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社会。

今天,这种可以通过屠戮他国国民,摧毁他们的道路、桥梁、农场、住宅、学校和医院来彰显荣耀的想法简直犹如疯子的呓语。但是在19世纪的反启蒙运动中,这种观念的信徒甚众。美化军国主义的风潮一度非常流行,而且不只是头戴尖盔的军队高层这么做,就连许多艺术家和有识之士也颇为热忱。战争“拓宽了人们的思路,锤炼了他们的个性”,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如是写道。战争是“生活的本质”,法国作家左拉曾这么说。(战争)“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基础……(并且)是人至高品德和才华的体现”,作家、艺术批评家约翰·拉斯金写道。

对军国主义的美化里有时候也会掺杂着对种族主义的美化,种族主义是指对本族群语言、文化、国土和种族的过度拔高和粉饰,它强调种族的热血和赤魂,认为一个国家的昌盛必须借由建立种族血统纯正的主权国家。
 种族主义的力量来源于煽动盲目的国民观念,让人们相信暴力抗争是生命力的天性(“茹毛饮血,尖牙利爪”)与人类进步的动力。这与启蒙运动的思想大相径庭,启蒙运动认为人类进步的动力是解决问题。以暴制暴的价值观演化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相契合。黑格尔认为历史前进的力量势必造就一个超级帝国,战争是必要的。黑格尔写道:“是战争从社会固化和停滞的泥潭中拯救了国家。”
种族主义的力量来源于煽动盲目的国民观念,让人们相信暴力抗争是生命力的天性(“茹毛饮血,尖牙利爪”)与人类进步的动力。这与启蒙运动的思想大相径庭,启蒙运动认为人类进步的动力是解决问题。以暴制暴的价值观演化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相契合。黑格尔认为历史前进的力量势必造就一个超级帝国,战争是必要的。黑格尔写道:“是战争从社会固化和停滞的泥潭中拯救了国家。”

不过,美化军国主义的最大推动力或许是衰退主义,后者是一种在有识之士中盛行的、厌恶普通人安于平和富足生活的意识形态。
 在叔本华、尼采、艺术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和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影响下,文化批判主义在德国变得尤为根深蒂固。(我们会在第23章再对这些观点进行探讨。)
在叔本华、尼采、艺术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和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影响下,文化批判主义在德国变得尤为根深蒂固。(我们会在第23章再对这些观点进行探讨。)
直到今天,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们还是对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共同点颇多的国家(它们都是老牌的西方国家、信奉基督教、高度工业化并且社会富裕)会选择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浴血拼杀而感到迷惑不解。背后的原因繁多而复杂,但是某种程度上是与双方意识形态的不和有关,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指出,“一战”前的德国人自视甚高,认为“他们不屑于和欧洲或是传统西方国家的国民为伍”。
 尤其是,德国人认为启蒙运动带来的自由、民主和商业文化正在蚕食西方社会的活力,不列颠和美利坚则在一旁煽风点火、落井下石,而他们英勇地抵挡住了诱惑。
尤其是,德国人认为启蒙运动带来的自由、民主和商业文化正在蚕食西方社会的活力,不列颠和美利坚则在一旁煽风点火、落井下石,而他们英勇地抵挡住了诱惑。
许多德国人相信,只有救赎的灰烬才能让新的英雄主义和社会秩序获得涅槃,关于战争的浪漫幻想最后统统在战火中被燃烧殆尽,实现和平成了每一个西方社会和国际机构的终极目标。人类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至于荣誉、名声、卓越、男子气概、英雄主义以及其他种种由于雄性激素过剩而催生的幻想,若为生命故,一切皆可抛。
虽然人类实现和平的进程正在断断续续、跌跌撞撞地稳步推进,有很多人依旧不相信有实现世界和平的可能性。他们坚持认为,人类的天性里对征服占领有近乎无厌的欲求。其实他们不光这样看待我们自己的天性,许多评论家会把雄性智人的自大投射到几乎所有智慧生物身上,他们警告我们一定不要试图寻找外星人,以免更高等的地外文明发现我们的存在并赶来奴役我们。尽管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在不少好听的歌里都唱到了世界和平,这样的歌声在现实面前依旧太过美好,美好得像一种绝望的天真。
事实上,战争可能就像横在我们面前的瘟疫、饥荒和贫穷一样,只是我们这个受过启蒙思想熏陶的物种必须学会克服的另一个障碍。虽然侵略战争带来的短期利益非常诱人,但是更好的策略莫过于尽量避免发起具有破坏性的冲突或是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毕竟如果你成了别人眼中的威胁,那就相当于给了别人先发制人的好理由。从长远来看,一个各方都避免发动战争的世界才是对所有人而言都更好的世界。新兴的事物如国际贸易、民主制度、经济发展、维和力量以及国际法律和规范,都是助力建造这样一个世界的有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