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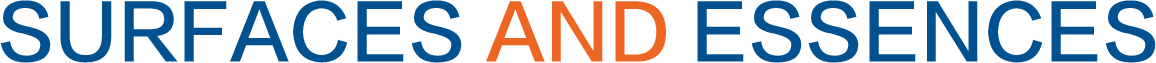

当回顾往事,沉浸在成书之初的美好回忆中时,我们可以清楚地记得最初的关键时刻。那是1998年7月中旬,在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那是首个以“类比”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由心理学家Boicho Kokinov、Keith Holyoak和Dedre Gentner共同组织。那次令人难忘的会议聚集了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大家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交流思想,分享类比研究的热情。那次会议也为我们二人在索菲亚第一次见面提供了机会,我们一见如故。相识的火花令人愉悦,并逐渐演变成长久而坚固的友谊。
2001年至2002年,侯世达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学术休假期间,受Jean-Pierre Dupuy之邀,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做了一系列关于认知的报告。当时,桑德尔刚刚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作类比和范畴化的专著。在一次报告期间,他自豪地送给新朋友侯世达一本。侯世达读后,欣喜地发现二人关于认知的观点非常相似。之后,一段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两人又在巴黎和图卢兹进行了两次短暂会面,辅以电邮和电话,学术探讨与友情交流并进。
2005年2月,侯世达邀请桑德尔来布鲁明顿,和朋友一起庆祝他60岁的生日。生日聚会期间的某一天,侯世达向桑德尔提出,他希望去巴黎几周,两人一起把桑德尔的书译成英文,桑德尔欣然同意。在侯世达7月到巴黎后不久,最初的计划很快得到扩展,最终两人决定合写一部关于类比的专著,研究其在思维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两人决定用非专业的方式处理这个题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并运用大量具体实例为理论观点提供佐证。我们希望这本书对思维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来说浅显易懂,同时雄心勃勃地希望它也能被学术界接受,并且可以提出一个关于认知的全新创见。这也成了这本著作发端的时刻。
在巴黎的三周,两人反复讨论了许多想法,最终完成了一份40页的文稿,主要内容是谈话的片段和笔记,以及该书的简要大纲。2006年到2009年的四年之间,每年我们都会花一个月的时间到彼此的居住地工作。另外,侯世达还在2010年学术休假期间在巴黎待了整整8个月。在写作期间,两人通过电邮和电话不断交换意见,书也从几个细胞演化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复杂有机体。
这一切都表明,眼前的这本书是长期合作的成果,它终于走向成熟,和读者见面了。我们希望书里传递的信息具有永久的价值,尽管这一信息根植于当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事实上,正如我们的一位朋友曾经欣喜描述的那样,它根植于“充满活力的思想之中”。尽管书的起源带有时空的特殊性,但是它的关键思想具有足够的普遍性,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
这本合著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创作过程,对此我们十分骄傲。它不但是由两人合写的,而且是用两种语言同时写作的。具体来讲,这部著作有两个原版,一本是法文版的,一本是英文版的,两者互为译本,或者可以说两者都不是译本。无论你怎样看待,它们都具有平等的地位,是同一个抽象思想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具象化身。也就是说,本书存在于思想的而不是言辞的以太界。
当然,写作的过程涉及繁杂的翻译工作,但是这些翻译工作就发生在原文形成的时刻。有时,我们把思想从英文传递到法文,有时又反过来,关键在于思路的交流伴随着两种语言的往复交流。这种做法十分罕见,并致使我们多次修改原文,以一种聚合的方式使原文与译文更加接近。尔后,如此生成的文本再次经历新一轮的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个大脑的交流。经过这样的多次往复,终于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均衡。
这两个版本,也就是英文版和与之对应的法文版,都经历了两种语言的反复过滤。我们发现这种特殊的动态过程经常使文本变得高度清晰,因为翻译会令文中不严谨、表达模糊,以及逻辑关系不通顺的地方暴露无遗。翻译凸显这类缺陷,正像打开手电筒,把光束投向布满尘埃的阁楼一样。这个过程也像是磨刀,因为这一反复交流的过程也是把我们要表达的思想不断锐化的过程。所以,本书有两个原版。这不仅仅是一种有趣的猎奇,更重要的是,这一直是我们的指导原则,让我们不断聚焦于目标:一致而清晰。至少我们是这样看这本书的,希望本书的读者也可以这样看。
我们鼓励有能力的读者把两个版本找来,对照阅读部分章节,因为每个版本里的思想、形象和遣词造句都深深根植于它所基于的文化。这是一个极佳的锻炼机会,意味无穷又引人入胜,因为我们要不断面对挑战,为一个习语、场景或者语误在两种语言中找到一个恰如其分又相互对应的表达方式而绞尽脑汁。我们要时刻保持警觉才能找到绝配。对于任何一位热爱语言的人来说,将两个版本对照阅读,除了可以获得新的思想(这当然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之外,这还是一次特殊的阅读体验,它可以让你体会同样的思想是如何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呈现的,简言之,是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