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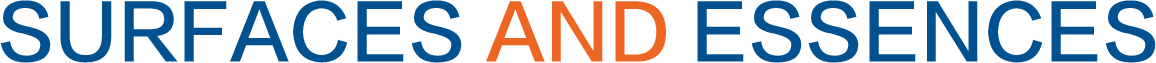

正如上面几个例子所展示的,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一点儿”有几个比较固定的句法位置,如果它不在这几个位置上就会显得有“一点儿”奇怪。事实上,这些句法位置构成了“一点儿”的另一个特性。在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成百上千个“一点儿”。在第一次听到“一点儿”出现在某个有点奇怪但又合理的句法位置时,我们会觉得有些诧异,但是久而久之,就越来越习惯在这个位置出现的“一点儿”,并且把这种用法内化成自己的习惯。于是这个“一点儿”就慢慢变成了潜意识中的某种条件反射,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它很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说“他一点儿也不注意形象”,而不是“他也不一点儿注意形象”?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我一点儿也不想吃饭”,有时候又说“我不想吃一点儿饭”,但绝不会说“我不想吃饭一点儿”?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她有一点儿缺德”,而几乎不能说“她有一点儿缺席”?为什么“差一点儿摔坑里”和“差一点儿没摔坑里”都可以说,却不能说“没差一点儿摔坑里”?这时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较为抽象的范畴:“一点儿”可以出现的句法位置,而且这些句法位置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以前人们也许不能接受用“有一点儿淑女”来表示一个人“有一点儿淑女的样子”,而现在用“有一点儿”直接加上名词来表示“有一点儿……的样子”似乎正逐渐被接受。比如在网上搜索一下就能找到这样的例子:“我是一个有一点儿淑女也有一点儿野蛮的灰姑娘”“……很干练,有一点儿女强人”“东北小伙有一点儿虎”,等等。“淑女”“女强人”“虎”这样的名词渐渐有了形容词的属性,“一点儿”能出现的句法位置也就更多了。
这就意味着,“一点儿”这个范畴,也就是所有能激发出“一点儿”这个词的情境,所有给人以“一点儿”感觉的情境,都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认知情感方面的,也就是在对比之后我们希望强调“少量”这个情况;另一个则是句法方面的,也就是我们能在快速的语流中毫不费力地把“一点儿”放在正确的句法位置上。
读者可能会觉得,你们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一点儿”这个词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其背后的概念,另一个则是它的语法功能。所以说白了,你们就是想说“一点儿”有语义和句法两个方面(哪个词不是呢?),而且这两个方面是相互独立的心理官能。这种观点似乎认为语义和句法两个领域互不相干、独立自主。然而是否需要将二者如此区分开来还有待讨论。有没有可能,人类在学习语言中的语法结构和身边的物质世界时所采用的认知方式其实同根同源呢?
其实我们从小就要学会在抽象的语法世界中找到方向,就像我们需要学会在身边的物质世界中生存下来一样。小孩子总是从“一点儿”的最简单的语境开始学起,比如说“有一点儿冷”“多一点儿”,等。这些最简单的用法就构成了这个范畴的核心,就好比提姆的妈咪是他心中 妈咪 这个范畴的核心,月亮是伽利略心中 卫星 这个范畴的核心一样。在学习的过程中,小孩子可能会说出各种错误的用法,比如“今天不一点儿冷”“我喜欢一点儿幼儿园”,等等。但是这些错误的用法很快就会由于身边大人的冷淡反应或者纠正错误而被抛弃不用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孩子逐渐就能听懂、看懂,并且正确使用一些复杂的用法了。比如,“这件事儿让我有一点儿伤心”“韩梅梅一点儿都不懂事”,等等。这些用法就好比是提姆脑中 妈妈 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其他人的妈妈,或者说就是伽利略脑中木星的卫星。每次孩子听到一个关于“一点儿”的新用法,比如“冬天的雪一点儿一点儿地化了”,他脑中一点儿的类别就变得更加模糊,然后向外扩展到那些与这个新用法有类比关系的用法,比如,“天一点儿一点儿地热起来了”,或者“我存的零花钱一点儿一点儿地变多了”。因此,孩子就会逐渐尝试更多的新句型,来拓展一点儿的用法范畴;并且根据他人对这些新句型的不同反应,在脑中强化或者放弃这些新句型。
孩子们逐渐修正 一点儿 这个范畴(既包括语义的,也包括句法的)时所用到的认知机制,与他们修正、调整其他任何类别所采用的认知机制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他们自己知道怎么做,不需要在学校接受任何训练。可以这么说,孩子们毫不费力、不知不觉地就成为“一点儿”这个范畴的专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不断遇到各种各样包含“一点儿”的语句,无论是书面语、口语、正式文体,抑或是随手写的便签。他们都能够轻轻松松地分辨出各种用法是否合适,然后以此调整或者不调整自己脑中 一点儿 这一类别。正是如此,他们就一点儿一点儿地建立起自己对一点儿的理解,也就是这个词在句法或者语义上能够出现的语境。虽然每个人的一点儿各不相同,但都会包含一个范畴核心,核心的周围都有一圈光晕。一点儿这个范畴和物质世界的范畴一样,都有非常典型、毫无争议的成员,比如典型的“椅子”、典型的“一点儿”的用法;也有在类别边缘、模棱两可的情况,比如又像又不像“椅子”的椅子、似乎可以用“一点儿”但好像又不太顺口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