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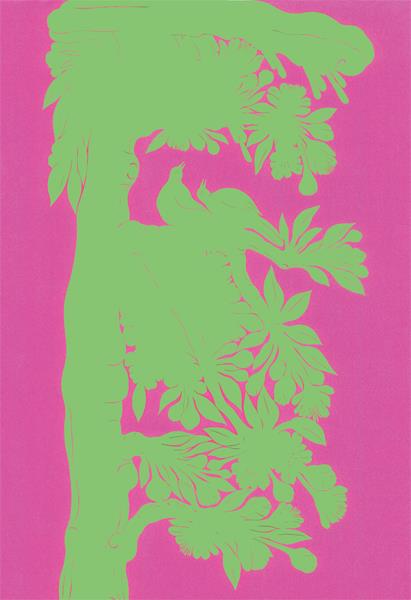
那年我十三岁,淘气得不得了。我上树掏鸟,不小心摔了下来,腿折了。起初,我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以为在家里躺几天,就又可以蹦蹦跳跳了。然而,右腿越来越疼,脚腕肿得连秋裤都穿不进去了。父母这才用架子车把我拉到了县医院。
这是我第一次住院。病房干净整洁,有现成的开水,在我看来就是奢侈的宾馆。我天真地以为,身体上的任何毛病,只要到了医院,总会有办法医治。然而在经过两次手术后,我的腿仍然没劲儿,有时还会突然失去知觉。父母越来越忧愁,我也模糊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开始害怕了,一个残酷的词——残废,迅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开始胡思乱想。我想我再也不能跑跳了,也不能去上学了,我会永远坐在轮椅上,成为父母的累赘。我的脾气开始变得暴躁,我动不动就和父母吵架。我说我不想再受罪了,我要回去。我下一句想说的是“我不想活了”,可我不敢说出口。这句话太可怕了,就像一口吊在绳子上的随时都会倾翻的黑锅。我不想就这样放弃。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被摧毁,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躺着,望着天花板发呆。
父母想尽各种办法来安慰我,甚至护士和医生也来劝我,要我配合治疗,说第三次手术一定会成功的。我将信将疑。
一天,病房里住进来一位老奶奶,她是被人用板车推进来的,听说是得了骨髓炎。她躺在我对面的病床上,不时有儿女来看她。看得出,她家境很好,是城里人。当天晚上,老奶奶和我父母便熟识了,自然而然地聊到了我的腿。老奶奶看我把头蒙在被子里,就故意和我说话,说她以前在乡下教过书,问我是哪所学校的。我知道她想开导我,可我不想接她的话茬儿。
父母埋怨我没礼貌,被老奶奶制止了,她说她也是病人,知道病人的难受;虽说难受但也得受,不能老沉溺在难受里,那样会越想越难受。说着,她从兜里掏出几粒糖,递给我的父母,让他们转交给我。
随后的日子里,老奶奶为了鼓励我,让我振作起来,给我讲了许多小故事。一方面我承认老奶奶的故事讲得很好,我对她不再反感;另一方面我又在心里嘀咕,这里不是课堂,是医院,一阵阵袭来的疼痛是不讲道理的。
一天清晨,我从被窝里探出头,望向窗外。突然,在窗户的右上角,看见了一枝桃花。准确地说,只有六朵,嫣红的,新鲜极了,我似乎能闻到香味。我向窗外探去,渴望能看到更多的桃花。可一阵疼痛又把我的身体拉了回来。这时,一阵微风吹来,桃花乱颤,仿佛在跳舞,似乎整个春天都跃到窗口,向我招手。我已经好久没到室外去了,几乎已把春天遗忘。我虽看不清这枝桃花的全貌,心里的激动却是强烈的。老奶奶看出了我的兴奋,她徐徐地说:“花信风,第十三番花信风吹来了!”
花信风?十三番?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老奶奶兴致勃勃地说:“花与风之间是有约定的。每年从小寒到谷雨的这四个月时间里,一共要吹二十四番风。一番风吹来,一种花开。一番风吹开梅花,二番风吹开山茶,三番风吹开水仙,四番风吹开瑞香……直到立夏,所有的花都开放。风有信,花不误,岁岁如此,永不相负,这样的风便叫花信风。”
我满怀惊奇地听着,多美的风啊!多美的约定!
我问老奶奶:“海棠花是哪一番风吹开的?”老奶奶掐指算算,笑着说:“是第十六番风。再过三十天左右,那风一吹,海棠花就开了,一定的。”然后她问我:“为什么喜欢海棠?”我说:“我家院子里有,我不清楚它开了没有。”老奶奶微笑着说:“花信风,人信己,你安安心心地做第三次手术……说不定,一个月后,还真能回家看上海棠花哩。”接着,老奶奶给我朗诵并讲解了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我对“海棠依旧”“绿肥红瘦”有了莫名的亲切感。
在我顺利做完第三次手术,临出院的前几天,我才从父母那里得知,其实老奶奶得的并不是骨髓炎,而是骨癌。我躺在病床上,看着老奶奶正和儿女们笑语盈盈地说着话,鼻子一酸。我在被子里攥紧拳头,暗暗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一定能站起来。因为,我想回家看海棠花开,我相信海棠依旧。

(王传生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一书,赵希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