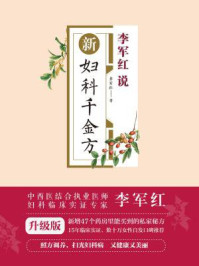摘了令我透不过气、捂得我下巴上青春痘前仆后继的一次性口罩,扯下把我心爱的板寸压得立体造型全无的一次性帽子,我走出人流室,去配膳室拿水杯泡了一大杯茶,顺便到办公室看看午饭前还有几个人流要做。
琳琳对面是一对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女孩子一脸紧张凝重,男孩子一脸满不在乎,一边不停地抖腿,一边拿一双机灵的大眼睛左顾右盼。人流室外的这些男孩子故意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他们比女孩子还紧张,心中还没数。
琳琳应该已经问好病史,写好病历,正用签字笔指着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密密麻麻的人流手术并发症逐条讲解,只等他俩签字,然后把女的送进人流室,交给我开工。
琳琳一条一条地讲完各种最终都可能导致死亡的意外后,男孩子不抖腿了,女孩子神情更加凝重,两人低声嘀咕了几句,女孩子怯生生地问:“大夫,出血是什么意思?术后需要大补吗?”
“刮宫是把已经深深扎根子宫的胎儿机械性清理出来,相当于起重机强拆房子,大树连根拔起,当然要出血。但是只要手术顺利,一般出血不多,还不如你来一次大姨妈的量呢,健康人一次流血400毫升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根本不用大补,补完了都变肥膘贴你脸上。”
“那感染呢?会得盆腔炎吗?”
“人流是医疗器械通过宫颈进入子宫,把里面怀孕的东西弄出来,如果器械消毒不严格,或者生殖道本身有潜在感染,或者手术后流血时间长又不注意个人卫生,就有发生感染的可能。你做过阴道分泌物检查,协和医院的消毒你尽管放心,人流器械和进行心脏手术的高端器械都一样严格按程序消毒,医生操作的时候也会小心,不会轻易将外面的脏东西带进去,手术后还会预防性地给你吃几天消炎药,不用太担心。”
“我听人家说,吃消炎药不好。”
“啥好不好的,做人流还不好呢,那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没病谁会让你吃药?我们开药又没回扣。”
琳琳的解释通俗易懂,从医生的角度也算仁至义尽,但是,我感觉她正在慢慢失去耐心。
虽然整天面对差不多的病人,说差不多的话,是人都会烦,没人能整天带着微笑耐心解释,但琳琳还是训练有素的,她清楚自己的职责。
“大夫,那子宫穿孔是怎么回事儿?穿孔了会怎么样?”
琳琳说:“上了人流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子宫穿孔相对少见,发生率大概千分之二。”
“子宫穿孔了,是不是以后再也不能生小孩了?”
“谁跟你说的?”
“我……”女孩子支支吾吾地低下头,但她很快又扬起一双明眸认真地盯着琳琳,希望眼前这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医生给她说清楚。
“当然不是了!最容易造成穿孔的是医生最开始时用来探子宫腔长度和方向的探针,那东西很细,和圆珠笔芯差不多,只要穿的不是要害部位,医生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病人经过休息观察,大多数都能自愈,不影响以后的生育。”
“那……您说的少数情况会怎么样?”女孩子穷追不舍。
“少数情况要多惨有多惨!要是穿孔在大血管经过的地方,就会发生内出血,医生要把你拉到大手术室,打开肚子进行止血和修补子宫,要是能顺利止血和修补,结果还不算太坏,要是修不好,或者出血不止,为了救你的命,就有可能切掉子宫。
“最可怕的不是探针穿孔,而是带着负压吸引力的吸管发生穿孔,更可怕的是穿孔已经发生,但是医生浑然不觉。这时,吸管会穿过子宫进入腹腔,甚至把大网膜和肠子通过子宫和阴道拽出来,要是肠子拉破了,就得开刀补肠子。伤的是小肠还好办,当场缝上就行,大不了切除一段再接上,要是伤了直肠,有时候就得先做造瘘。造瘘懂吗?就是把肠子截下来,接到肚皮上,大便改道从肚皮排出,没有肛门括约肌,粪汤子随时产生随时往外流,等一个月以后,再开一次刀把肠子送回去,悲剧吧?谁摊上谁倒霉,病人、大夫都倒霉。”
琳琳一通发飙,男孩和女孩都被吓住了,不作声,也不签字,大眼瞪小眼,一齐没了主意。
“快签字吧,做手术就跟过马路似的,每个人都有被车撞飞的可能性,但那都是小概率事件。没事儿咱在家好好待着,谁来来回回过马路玩啊?当然不用冒这些个风险,明不明白?”
俩年轻人还是不吱声,也不签字。
琳琳抬头看见我,说:“我去趟卫生间,你帮我向领导汇报一下,这病人我搞不定,不签字没法做人流,赶紧办退院。”
钱老姐今早交完班就不见了,护士长说她去人事处办理开会的事去了,我上哪儿找她汇报去?
我四下环顾,不见钱老姐回来,本想上前和解一下,说几句平时常劝那些犹豫不决、患得患失、难下决心的女孩子的话。例如,别怕,快签字吧,那些吓人的意外确实有可能发生,但还是相对少见的,医生手术的时候都会尽力做好。或者是,快签字吧,上午要是做不上,就没法赶在下午办出院手续,晚上你就得住在医院没法回家了,怎么和家长交代?
还没等我开口,只听咣当一声,办公室最里头洗澡间的门开了,顶着一头湿淋淋的头发扭着胖屁股的钱老姐从里头出来了,她虎着那张喜马拉雅猫一样的胖脸,极其不爽的样子。
计划生育办公室是三人间病房改造的,房间最里头是卫生间,卫生间里有一个淋浴喷头,永远有医生、护士或者护理员在各个时辰湿淋淋地从里面走出来。她们或丰腴或骨感,或手里拎着洗澡篮子,或怀里抱着洗脸盆子,或者还滴着水的长头发拧成一个古式的发髻顶在头顶,或者短头发湿漉漉贴在前额和脑瓜皮上,光脚趿拉着各式批发市场最常见的塑料拖鞋,啪啪啪一路小跑,快速穿过庄严肃穆的办公室,看得前来谈话签字的男家属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一愣一愣地不知道是看好,还是不看好。
钱老姐一有烦心事就洗澡,这是她独有的强迫症,估计是在人事处办事不利,受了什么闲气。她刚刚在洗澡间穿衣服的时候,肯定把办公室里头小医生和大学生的一来二去都听了个明白。
她把装着洗发水、沐浴露、梳子、毛巾的塑料篮子往办公桌上一摔,说:“你们没完没了地问这些干什么?当初干什么去了?连避孕都不懂就敢上床瞎整,这得有多大胆子撑着,怎么现在又怕这怕那知道谨小慎微一步三回头了?这就是无保护性生活的代价,必须承受,怕也没用。就算医生一五一十都给你们讲清楚了又能怎样?你们有选择吗?这人流能不做吗?难道大学不上了,回家生孩子去?有那勇气和胆量吗?”
钱老姐干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耐心就像她一去不返的青春,早已被彻底熬干。
“没有。”女孩一边嘟囔着,一边低下头,用涂成粉红色的手指甲抠我们的木头办公桌。
“那还考虑什么?你们拿什么本钱考虑?从什么角度考虑?你们俩的考虑有什么用?从上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你现在都怀孕9周加5天了,肚子里的孩子一天不停地在长大,你们要是再回去考虑两个礼拜,普通的电吸人流都没法做了,就得钳刮加碎胎,碎胎懂不懂?就是先把已经成形的孩子在子宫里头绞碎夹烂,再一块一块钳出来,这是逼我们医生作孽呀!”
“钳刮加碎胎”听得一对年轻人同时咧嘴。
“赶紧签字做手术,今儿周五,趁周末好好休息两天,周一还有课要上吧。”
“嗯,阿姨我听您的,我怕疼,做的时候能手轻点儿吗?”女孩子说。
“就你怕疼,谁不怕疼?我们这儿没有手重的大夫,就算有不怕疼的,我们也不下狠手。”
“阿姨,我不是那个意思,您别生气。”
“放心吧,我让小张医生给你做,她手最轻了,再说还打麻药呢。”钱老姐又没管住自己的嘴。她应该感觉到了自己的尖酸刻薄,赶紧往回补。
一听要打麻药,女孩子的问题又来了:“打麻药会不会影响智力?我还在上大学,将来还要考研究生呢。”
“我的妈呀!年轻人,你们都是听刘伯承元帅不打麻药剜眼珠子的故事中毒了吧?还是关公光着半个膀子边下棋边刮骨疗毒的故事听多了?就打点麻醉药睡一小觉,影响不到智力,况且咱就做个人流,离脑袋远着呢。再说了,你上大学需要脑子,人家大街上拉车卖菜的就不需要脑子?瞧你们这些大学生,怎么都被教育成这样,就知道以自己为中心,真把自己当祖国的花朵人民的财富了?”
这倒霉孩子,一句“将来还要考研究生”又把钱老姐惹毛了。
俩小孩总算痛快地签字画押,转眼被移交到了我的手里。
那时协和还没有常规开展静脉全麻人流,无痛人流对专业人士来说也算个新鲜词,只有个别VIP可以享受。现在倒好,地铁、站牌和公交车身上不是无偿献血、科学避孕、防治性病、杜绝吸毒等公益宣传,而是充斥着无痛人流、男科医院、性病不孕等医疗广告,这就是生机盎然、春风十里的国际化大都市——我深爱的北京。
我没有精力去研究有关人流的医学史,但从1978年拍摄的著名医学惊险片《昏迷》中得知,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人流就已经使用全身麻醉了。不让病人在疼痛和恐惧中接受创伤性检查和治疗,是现代医学对人体最基本的尊重。我们学得西方医学的皮和毛,很多重要理念却未得骨肉精髓。
和片中同一时代的中国女性,做人流都是“生刮”。手脚麻利的医生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搞掂,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伴随各式嗷嗷乱叫和哼哼唧唧之后,久经考验、吃苦耐劳的妇女同志一骨碌跳下人流床,穿上裤子,回家继续劳动。
人流的特点是做的时候疼,做完立马不疼,即使有些不舒服,也只是些微的酸酸坠坠。子宫内里的伤口修复差不多需要两个礼拜的时间,还没等好了伤疤,早就没了疼。所以,男有“一夜九次郎”,女子也当仁不让,太多的“一流一沓子(一辈子做过12次人流)”,甚至还听说有“一流24次”,不过我没见过。
协和还算人道,在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常规开展无痛人流的年代,就已经常规使用杜冷丁进行止痛,药物推入静脉后相当于半麻,大部分病人效果还不错,晕晕乎乎地手术就做完了。有些人效果差些,床上病人大呼小叫外加张牙舞爪,床下医生或者柔声细语或者大声呵斥,总之,连安慰带哄骗,医生和床上的病人一样,嘴上手上两不闲,最终几分钟搞定手术。
大学生上了人流床后,护士给她推了杜冷丁和非那根。我准备给她做内诊摸清子宫的大小和位置,手刚碰到,她就触电似的往回缩屁股,我一直说放松放松,才好歹摸了个清楚。护士也是好说歹说,才勉强完成了外阴阴道的冲洗消毒。
我铺好有洞的手术巾,用窥具轻轻撑开阴道,看到宫颈。局部消毒后,钳夹宫颈前唇,借此抓持子宫,我将细细的探针顺着宫颈口轻轻探向宫腔,了解宫腔的深度和方向。这时,不适和紧张导致她的身体不停扭动,任我怎么劝,她还是哇哇乱叫。
我坐在手术椅上,扭头看钱老姐,一双眼睛从帽子和口罩之间发出道道无助和求救的光。
钱老姐一扭一扭地走到我身后,一双胖手重重搭在我肩膀上,意在让我稳住,然后冲着床上粗声粗气地喊道:“别动!铁家伙前头没长眼,子宫要是穿孔医生可不管。”
女孩子果真被钱老姐的狮子吼吓住,在我眼前的屁股终于不再乱扭。计划生育的人流室,钱老姐一直是人鬼共镇。几个月来,我眼看上床就乱嚷乱叫、混不吝的大妞们是如何一个接一个被钱老姐喝住,顺利做完手术后,再一骨碌爬起来,给她递烟、留电话,还称兄道弟。这小姑娘就像黄嘴丫儿还没褪尽的小麻雀,治她根本不在话下。
我抓紧时间,从小号到大号使用扩宫棒,一点一点地扩张宫颈管,扩张到7号半时,已经可以将小指粗的7号吸管顺利探入宫腔,在马达的带动下,吸管像一台小型电动吸尘器,开始对宫腔内容物进行逐排抽吸。
最开始是胎囊局部的滑溜感,之后是蜕膜的绵厚感,再之后,是碰触子宫肌层时,手挠石灰墙一般的生涩感,这就是传说中的“肌声”,伴随这种特殊手感的出现,医生就知道吸得差不多了。我撤出吸管,改用锐利的刮匙清理两个不易清理干净的子宫角部,再换6号吸管,降低负压,做最后一次清理。整个人流手术,从探宫腔、扩宫颈,再到吸宫、刮宫,都是盲目操作,子宫里面的情况一点看不见,全靠医生的手感,可以说我就是在闭着眼睛“瞎刮”。
床上的小丫头虽然身体不敢乱扭,但我仍然听见她非常克制的苦痛表达,开始只是隐隐约约的呻吟,逐渐升级到她无法忍受的程度时,她都会在模糊不清的发音之后,跟闹猫一样,又像婴儿的啼哭,揪心地喊出一个“妈”字。这让我心中一颤,手却不敢停下。
钱老姐教过我,做人流要快,不可妇人之仁,快刀斩乱麻赶紧做完手术才是对病人真正的仁慈,因为人流一结束,病人立马不疼。
那以后,无以计数的没有全身麻醉的人流手术中,我听到最多次数的呼喊都是“妈”或者“娘”,几乎没有人喊“亲爱的”“宝贝儿”“老公”或者什么“达令(darling)”之类的,偶尔听到有姑娘喊一个听上去颇像男人名字的字符,姑且认为那就是她的爱人吧。
在遭遇这一自己找上门,虽然内心恐惧万分却又无从躲闪的疼痛时,在孤零零最无助时,带给女性最深安慰的不是男人,而是母亲。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注定要经受这些苦痛,或者长痛娩出生命,或者短痛扼杀生命,千百年来的梦魇轮回,似乎从未停歇。
我摘下手套,站起身来看到她煞白的小脸和额头上一层细密的汗珠,因为杜冷丁的作用,她的眼睛半睁半闭。我说:“做完了,感觉好点没?”
她不回答我,好像还在蒙眬状态,接着喊:“妈,好疼啊。”接着又是一声“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