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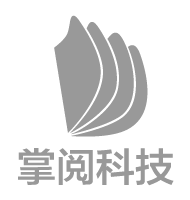
|
书名:明天过后
作者:【美国】斯蒂芬·金
译者:姚向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08-01
ISBN:9787572606816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克里斯·洛茨
明天只有那么多个。
——迈克尔·兰登
我不喜欢一上来先道歉,搞不好甚至有规则禁止我这么做,就像句子不能以介词结尾。但是,读完我目前所写的三十页纸,我觉得我不得不道个歉了,因为有个词我用了一遍又一遍。我从老妈嘴里学到了很多四字母词的用法,才几岁就已经用得很溜了(读者很快就会注意到这一点),但这个词有五个字母。它就是“后来”(later),也就是“后来呢”“后来我发现”和“后来我才意识到”的那个“后来”。我知道重复多了会让人烦,但我别无选择,因为故事发生那会儿我还相信圣诞老人和牙仙
 呢(尽管我在六岁时就起了疑心)。现在我二十六岁了,这确实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对吧?我猜等我四十来岁时——我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活到那个年纪——回头再看二十二岁的我,会意识到当时有很多道理我还不明白。现在我知道了,永远还有一个后来,至少在我们死前都是这样。到了那个时候,我猜一切都会变成从前。
呢(尽管我在六岁时就起了疑心)。现在我二十六岁了,这确实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对吧?我猜等我四十来岁时——我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活到那个年纪——回头再看二十二岁的我,会意识到当时有很多道理我还不明白。现在我知道了,永远还有一个后来,至少在我们死前都是这样。到了那个时候,我猜一切都会变成从前。
我叫杰米·康克林,从前有一次我画了一张感恩节火鸡,自己觉得特别厉害。后来——不久之后的后来——我发现我的画更像是从牛屁眼里拉出来的东西。有时候真相确实伤人。
我觉得这是个恐怖故事。请读者自行决定吧。
我和老妈一起从学校走回家。我的一只手拉着她,另一只手紧紧抓着我的火鸡,那是我在感恩节前的一个星期画的。那时我上一年级,对自己的火鸡可自豪了,走起路来都觉得虎虎生风。火鸡是怎么画的呢?你把手放在一张美术纸上,再用蜡笔照着描一遍,这样你就有了尾巴和身体。火鸡脑袋就全凭你自己发挥了。
我给老妈看我的火鸡,她全程对对对,好好好,宝贝你真厉害,但我不认为她真的仔细看了。她多半在琢磨怎么卖她手上的某本书呢,用她的话说就是“强行推销”。老妈是个文学经纪人,明白了吧。以前做这个的是她哥哥,我的哈利舅舅,但老妈去年接管了他的生意——说来话长,而且有点扫兴。
我说:“我用的是森林绿,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你知道的,对吧?”这时我们就快走到我们家所在的那栋楼了,它离学校只有三个街区远。
她还是说对对对。接着她说:“小子,等咱们到家了,你自己去玩吧,看《巴尼与朋友》或者《魔法校车》也行。我有一亿个电话要打。”
我也跟老妈说对对对,她戳了我一下,咧开嘴笑了。我很高兴自己能逗老妈发笑,虽然我只有六岁,但我已经知道她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了。后来我发现,老妈之所以这么严肃,也是因为她比较担心我,她认为她养大的这个孩子也许精神不正常。就在我的故事开始的这一天,她终于能确定我其实没疯了。这无疑让她如释重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压力重重。
“你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那天晚些时候她对我说,“除了我。也许甚至都不该告诉我的,小子。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假如你是个孩子,而说话的是你老妈,那么无论她说什么你都会点头答应。当然了,除非她说的是“现在该睡觉了”或者“吃完你的西蓝花”。
我们走进公寓楼,电梯还是没修好。你可以说假如电梯是好的,那么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我不这么认为。有些人喜欢说什么生活就是我们做出的一个个选择和我们走上的一条条道路,我觉得他们全是在放狗屁。无论走楼梯还是坐电梯,我们都必须从三楼出来。要是无常命运抬起手指着你,那么所有的道路都只会通向同一个终点,这就是我的看法。等我年纪再大一些之后,我也许会有别的看法,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不太可能。
“去他妈的电梯,”老妈说完,连忙又补了一句,“小子,你没听见我刚才说了什么。”
“听见什么?”我问,她再次朝我笑了笑。告诉你吧,这是那天下午她的最后一个笑容了。我问她要不要我帮忙拎包,她的包里和平时一样装着一份底稿,那天的底稿很有分量,看上去像是至少有五百页(天气好的时候,老妈总是一边坐在长椅上读底稿,一边等我放学)。她说:“算你有心了,但我总是怎么对你说的来着?”
“在生命中,我们必须背负自己的重担。”我说。
“一点不错。”
“你在看雷吉斯·托马斯的书吗?”我问。
“正是。老朋友雷吉斯,咱们能付房租多亏了他。”
“是关于罗阿诺克
 的吗?”
的吗?”
“杰米,这难道还需要问吗?”我不由得窃笑。老朋友雷吉斯写的东西永远和罗阿诺克有关,那是他在生命中背负的重担。
我们爬楼梯来到三楼,除了走廊尽头的我们家,这一层还有另外两套公寓,不过我们家的公寓是最漂亮的一套。伯克特夫妇站在3A的门口,我立刻知道出事了,因为伯克特先生在抽烟。我以前从没见过他抽烟,而且我们这栋楼本身就禁止抽烟。他眼睛充血,一头灰发乱糟糟地支棱着。我总是称呼他先生,但他实际上是伯克特教授,在纽约大学教什么超级睿智的课程。我后来知道他教的是英国与欧洲文学。伯克特太太穿着睡袍,光着脚。她这件睡袍相当薄,我透过衣服几乎什么都能看见。
老妈说:“马蒂,出什么事了?”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我就冲上去给他看我画的火鸡,因为他显得很难过,而我想哄他开心。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真的特别自豪。“伯克特先生,快看!我画了只火鸡!快看,伯克特太太!”我把火鸡举起来,挡住自己的脸,因为我不想让她认为我在看她的身体。
伯克特先生没搭理我,我觉得他甚至没听见我在说什么。“蒂亚,我有个坏消息。莫娜今天上午去世了。”
老妈的底稿包掉在了她的双脚之间,她抬起一只手捂住嘴。“天哪,不!这不是真的!”
他哭了起来。“她夜里起床,说想喝杯水,之后我就又睡着了。今天一早起来,我看到她躺在沙发上,毯子拉到下巴那儿,于是我轻手轻脚去厨房煮咖啡,因为我觉得好闻的味道会弄……弄……弄醒……会弄醒……”
说到这儿,他完全崩溃了。妈妈搂住他,就像我弄疼自己的时候拥抱我那样,尽管伯克特先生已经有一百岁了(七十四岁,我后来得知)。
这时伯克特太太对我说话了。我很难听清她说的话,但她的声音还是比其他死人的声音清晰,毕竟她才刚死不久。她说:“詹姆斯
 ,火鸡不是绿色的。”
,火鸡不是绿色的。”
“但我的就是。”我说。
老妈还抱着伯克特先生,像哄小孩似的前后摇晃。他们没听见伯克特太太在说什么,因为他们不可能听见,而他们没听见我说话,是因为他们在做大人的事情:老妈在安慰人,伯克特先生在痛哭流涕。
伯克特先生说:“我给艾伦医生打了电话,他来看过,说她应该是泡湿了
 。”我记得他好像是这么说的。他哭得太厉害了,很难确定他具体说了什么。“他打电话给殡仪馆,他们把她运走了。现在她不在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记得他好像是这么说的。他哭得太厉害了,很难确定他具体说了什么。“他打电话给殡仪馆,他们把她运走了。现在她不在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伯克特太太说:“要是我丈夫再不注意,他的烟头就要烧到你母亲的头发了。”
她没说错,确实烧到了。我能闻到头发烤焦的气味,就是美容院里的那股味儿。老妈太有礼貌了,所以什么都没说,但她想办法让伯克特先生松开了她,然后接过他手里的香烟,把它扔在地上踩灭。我觉得这么做很恶心,超级没格调,但我什么都没说。我能感觉到这是个特殊场合。
我还知道,要是我再和伯克特夫人搭话,老妈和伯克特先生肯定会被吓坏的。任何小孩,只要脑子没问题,都会懂得一些最基本的道理。你要说“请”,你要说“谢谢”,你不能在公共场合露出私处,你不能张着嘴嚼东西。另外,假如死人站在想念他们的活人身旁,你绝对不能和他们交谈。但我要澄清一下,算是给我自己辩解:刚看见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已经死了。后来我会越来越擅长分辨两者之间的区别,但当时我还在学习。我能一眼看穿的是她的睡袍,而不是她本人。死人看上去和活人一样,只不过他们总是穿着去世时穿的那身衣服。
与此同时,伯克特先生在讲述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告诉老妈他如何坐在沙发旁边的地板上,握着妻子的手,直到医生赶来。随后他继续那么坐着,直到殡仪馆的人来接走她。他的原话是“运送遗体”,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老妈解释给我听我才明白。刚开始我以为他在说什么美容师,也许是因为他烧老妈头发时的那股怪味。他本来已经渐渐不哭了,但这会儿又号啕大哭了起来。“她的戒指不见了,”他边哭边说,“不仅是结婚戒指,连订婚戒指也不见了,就是镶着大钻石的那枚。我翻过她那边的床头柜,每次她往手上抹那个特别难闻的关节炎药膏,就会把戒指放——”
“确实很难闻,”伯克特夫人承认道,“羊毛脂其实就是羊用来保护毛皮的分泌物,但真的非常有用。”
我点点头,表示我明白,但没说话。
“我也找了卫生间的洗手池,因为有时候她会把戒指放在台面上……我到处都找过了。”
“戒指会自己冒出来的。”老妈安慰道。现在她的头发已经安全了,于是她又把伯克特先生搂进怀里。“戒指会自己冒出来的,马蒂,你不需要担心。”
“我太想她了!我已经在想她了!”
伯克特夫人抬起手,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我敢保证,再过六个星期,他就会去请多洛雷丝·马高恩吃午饭。”
伯克特先生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老妈轻声细语地安慰他,每次我擦破了膝盖,或者像另外一次,我想给她泡杯茶,却把热水洒在了自己手上,她就会这么安慰我。简而言之,他们相当闹腾,于是我抓住机会开口,但压低了嗓门。
“伯克特夫人,你的戒指在哪儿?还记得吗?”
死人必须对你说实话。六岁的时候,我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当时我以为成年人无论死活都会说实话。当然了,那会儿我还相信金凤花
 是个真实存在的姑娘呢,你想说我傻就说好了。至少我没有相信三只熊真的会说话。
是个真实存在的姑娘呢,你想说我傻就说好了。至少我没有相信三只熊真的会说话。
“走廊壁橱最高的那层架子上,”她说,“在最里面,剪贴簿后面。”
“为什么放在那儿?”我问。老妈怀疑地瞪了我一眼。在她看来,我正在和空荡荡的门洞交谈……不过当时她已经知道我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了。有次在中央公园发生了一件事,不是什么好事,后面我会说到的。总之,在那之后,我不小心听见她和一个编辑打电话,说我有点“仙儿”。我吓得要死,以为她想给我改名叫“仙儿”,那可是个女孩的名字啊。
“我完全不知道,”伯克特太太说,“当时我应该已经中风了。血水正在淹死我的思想。”
血水正在淹死我的思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说法。
老妈问伯克特先生要不要来我们家喝杯茶(“或者喝点更有劲儿的”),但他说算了,他想再去找找他妻子的戒指。老妈打算叫中餐外卖当晚饭,于是问他要不要顺便给他带点,他说那敢情好,谢谢你,蒂亚。
老妈说没什么(她说“没什么”的次数和说“对对对”“好好好”的次数一样多),还说我们六点左右给他送过来——不过要是他想来我们家一起吃,我们也会非常欢迎他的。他说算了,他想在家里吃饭,但希望我们能陪他吃。他说的不是“我家”,而是“我们家”,就好像伯克特太太还活着似的。她已经死了,虽然她还在这儿。
“到时候你肯定已经找到她的戒指了,”老妈抓住我的手,“杰米,走吧。咱们晚些时候再来看伯克特先生,这会儿就别打扰他了。”
伯克特太太说:“杰米,火鸡不是绿色的,而且你画的那东西根本不像火鸡,更像是一个肉球上插着几根手指。你不是伦勃朗。”
死人必须说实话,假如你想知道问题的答案,这自然很好,但如我所说,真相有时候确实会伤人。我正要对她发火,但她忽然哭了起来,我也就不可能生气了。她转向伯克特先生,说:“现在谁会来提醒你别忘记穿腰后的裤带环?多洛雷丝·马高恩?气得我都要笑出来了。”她亲吻他的面颊,或者说,她对着他的面颊亲了一下,我分不清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我爱你,马蒂。死了也还是爱你。”
伯克特先生抬起手,挠了挠她嘴唇碰到的地方。我猜他只是觉得脸上有点痒吧。
所以,对,我能看见死人。自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能看见死人,但情况和布鲁斯·威利斯那部电影
 里演的不一样。能看见死人有时候很好玩,有时候很吓人(比如中央公园那家伙),有时候让我烦恼,但大多数时候,我就只是能看见死人而已。这和其他事情没什么区别,比如天生左撇子,比如才三岁就会演奏古典音乐,比如不幸得上早发型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那就是我的哈利舅舅,他发病那年只有四十二岁。我当时六岁,觉得四十二岁已经很老了,但即便我还小,我也明白,四十二岁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实在是太年轻了。对忘记各种东西的名字来说,四十二岁也还是很年轻——出于某些原因,每次我们去看哈利舅舅的时候,最让我害怕的永远是这件事。他的思想没有淹死在脑血管爆裂流淌出来的血水里,但依然是淹死了。
里演的不一样。能看见死人有时候很好玩,有时候很吓人(比如中央公园那家伙),有时候让我烦恼,但大多数时候,我就只是能看见死人而已。这和其他事情没什么区别,比如天生左撇子,比如才三岁就会演奏古典音乐,比如不幸得上早发型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那就是我的哈利舅舅,他发病那年只有四十二岁。我当时六岁,觉得四十二岁已经很老了,但即便我还小,我也明白,四十二岁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实在是太年轻了。对忘记各种东西的名字来说,四十二岁也还是很年轻——出于某些原因,每次我们去看哈利舅舅的时候,最让我害怕的永远是这件事。他的思想没有淹死在脑血管爆裂流淌出来的血水里,但依然是淹死了。
老妈和我继续走向3C,老妈开门,我们走进去。开门需要一点时间,因为门上有三把锁。她说过,想要住在这种有格调的地方,这就是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公寓有六个房间,而且俯瞰着公园大道,老妈管这儿叫公园宫殿。有个清洁女工每星期来家里打扫两次。老妈在第二大道的停车场里有辆路虎,有时候我们会去哈利舅舅在斯宾昂科的房子。多亏了雷吉斯·托马斯和另外几位作家(不过主要靠的是亲爱的老雷吉斯),我们才能住得如此舒服。可惜好生活并不持久,事情的发展轨迹也让人情绪低落,我很快就会说到的。回顾往事时,我偶尔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本狄更斯小说,只是多了些骂人话。
老妈把底稿包和手提包扔在沙发上,一屁股坐下来。沙发摩擦后发出放屁的声音,平时这个声音总会让我和老妈大笑,但那天我们都没有笑。“我他妈天哪,”老妈举起一只手,做个停止手势,“你——”
“对,我没听见。”我说。
“很好。我需要弄个电击项圈什么的,每次在你面前说脏话就会电我一下,让我长个记性。”她努出下嘴唇,吹开刘海,“雷吉斯的新书,我还有两百页要读——”
“这本叫什么?”我知道书名里肯定有“罗阿诺克”这四个字,他每本书的书名都是这样。
“《罗阿诺克的鬼姑娘》,”她说,“属于他写得比较好的那种,有很多性……咳,有很多亲吻和拥抱。”
我皱起了鼻子。
“抱歉,小子,但女士就喜欢小鹿乱撞和大腿滚烫。”她望向装着《罗阿诺克的鬼姑娘》的底稿包。底稿总是扎着七八根橡皮筋,里面总会有一根突然崩断。在这种时候,老妈就会爆出她最带劲的粗口,其中有几句我一直用到了今天。“不过这会儿我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喝杯葡萄酒,也许喝一整瓶。莫娜·伯克特是个超大号的讨厌鬼,没了她,他很可能会过得更好,但这会儿他正肝肠寸断呢。老天在上,他最好还有亲戚,一想到要当总安慰师,我就腿肚子发抖。”
“她很爱他。”我说。
老妈怀疑地看着我。“是吗?你猜的?”
“我知道她爱他。她说了些我画的火鸡的坏话,然后她哭了,还过去亲他的脸。”
“詹姆斯,那是你想象出来的。”她敷衍道。当时她已经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我很确定她知道,但成年人想相信一件事情总是非常困难。至于为什么,听我来告诉你。他们小时候发现圣诞老人是假的,金凤花姑娘不是真的,复活节兔纯属瞎扯(仅举三例,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在这之后,他们就会产生某种情结,不再相信他们没法亲眼看见的任何东西。
“不,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她说我永远也当不了伦勃朗。伦勃朗是谁?”
“一个画家。”她再次吹开刘海,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干脆剪掉刘海或换个发型。她当然可以换个发型,因为她非常好看。
“等会儿咱们过去吃饭,你可千万别和伯克特先生说你看见了什么。”
“当然不会,”我说,“可是她说得对。我画的火鸡烂透了。”这让我觉得很难过。
我的情绪肯定表现在了脸上,因为她向我伸出双臂。“小子,你过来。”
我走过去拥抱她。
“你画的火鸡很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火鸡。我要把它贴在冰箱上,永远也不取下来。”
我用尽全力抱紧她,把脸埋在她的肩窝里,这样就能闻到她的香水味了。“妈妈,我爱你。”
“我也爱你,杰米,乘以一百万倍。现在去玩吧,或者看看电视。我先打几个电话,打完就叫外卖。”
“好。”我走向我的房间,走到半路又停下了,“她把戒指放在走廊壁橱最高的那层架子上了,就在剪贴簿后面。”
老妈瞪着我,瞠目结舌。“她为什么要放在那里?”
“我问过她了,她说她不知道,还说那会儿血水正在淹死她的思想。”
“唉,我的天。”老妈低声说,抬起手捂住喉咙。
“咱们吃外卖的时候,你得想个办法告诉他,这样他就不需要担心了。我能点左公鸡吗?”
“当然,”她说,“但要配糙米饭,白米饭不行。”
“好好好。”我说。然后我就跑去玩乐高了,最近我在搭一个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