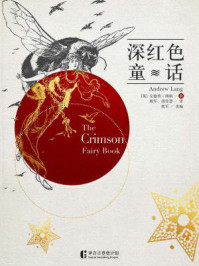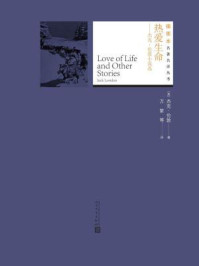“如果让一只虫从虫罐里跑掉,那么整罐虫都会尾随逃走。”这是路姑妈常说的话。她知道很多实用的格言,有些是传统名言,有些则是她自创的。比方说,我听过“口舌是颈项的敌人”一说,却没有听过“袋中猫绝对不止一只”,也没有听过“在兔子从帽子里跑出来之前,不要计算它们的数量”。路姑妈认为做人应该谨言慎行,但只限重要的事情。
因此,我一向不太跟阿瑟提起母亲。如果我提起了母亲,阿瑟很快就会发现我的真面目。邂逅他不久后,我捏造了一位母亲,说她是死于罕见疾病的温婉女性,印象中病名是红斑狼疮。
幸亏他对我的过去始终缺乏兴趣,只忙着诉说他的经历。我听说过他母亲的点点滴滴:她坚称自己知道怀上阿瑟的那一瞬间,立刻决定将仍在子宫里的阿瑟献给英国国教教会。当她撞见四岁的阿瑟把玩性器官时,她威胁要剁掉他双手的拇指。我知道阿瑟鄙夷母亲,不屑她如此重视勤劳和成就,其实阿瑟自己一样重视那些事物。我知道阿瑟畏惧母亲的一丝不苟,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他被迫为母亲拔除花坛边缘的杂草。我听阿瑟说他母亲不喜欢饮酒,还说自己早已遗忘父亲担任费雷德里克顿法官时的官邸,那官邸的娱乐室吧台有刻着迷你苏格兰人头造型的黄金酒瓶盖,看起来异常像乳头,或者那只是我自己的想象。我知道他母亲写过几封歇斯底里的信,以各种理由宣告和他脱离母子关系,例如政治、宗教和性。她得知我们同居后,给阿瑟寄过一封这种信。她从未原谅我。
这一切丑恶而不公的事情我一概真诚地聆听,部分原因是我希望了解他,主要还是出于习惯。在我的人生路上,我当过一段时间的好听众。我刻意锻炼倾听的能力,那时我觉得自己最好精通此道,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特长。我倾听任何人谈任何事,在适当的时机喃喃应声安抚对方,用语模棱两可,像枕头一样充满同情心。我甚至在门后、公交车上、餐厅里偷听别人的交谈,但那和聆听完全不同,毕竟偷听不是双向的交流。总之,聆听阿瑟说话对我而言易如反掌,结果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他母亲的事,而他对我的母亲则所知有限,倒不是说我因此占了什么优势。知识不见得是力量。
但我确实跟他提过一件事,一件应该在他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母亲以琼·克劳馥
 的名字为我命名。这是母亲让我百思不解的事情之一。她用琼·克劳馥的名字为我命名,是希望我像她在荧幕上扮演的角色一样美丽、有抱负、铁面无情、有能力摧毁男人吗?还是因为她希望我出人头地?母亲说琼·克劳馥奋发向上、意志坚强,从一无所有到功成名就。母亲赋予我别人的名字,是要我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吗?仔细想想,琼·克劳馥其实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本名是露西尔·费伊·勒萨埃尔,这个名字与我匹配多了。满头大汗的露西。我八九岁的时候,母亲会打量着我,若有所思地说:“我竟然帮你取了琼·克劳馥的名字。”我的胃会紧缩下坠,羞愧难当。我知道自己挨了骂,却至今仍不确定原因。但琼·克劳馥不是只有风光的一面。事实上,她有悲剧的气质。她有严肃的大眼睛、不快乐的嘴和高耸的颧骨,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或许这就是母亲话中的含义。或者,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琼·克劳馥身材纤细。
的名字为我命名。这是母亲让我百思不解的事情之一。她用琼·克劳馥的名字为我命名,是希望我像她在荧幕上扮演的角色一样美丽、有抱负、铁面无情、有能力摧毁男人吗?还是因为她希望我出人头地?母亲说琼·克劳馥奋发向上、意志坚强,从一无所有到功成名就。母亲赋予我别人的名字,是要我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吗?仔细想想,琼·克劳馥其实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本名是露西尔·费伊·勒萨埃尔,这个名字与我匹配多了。满头大汗的露西。我八九岁的时候,母亲会打量着我,若有所思地说:“我竟然帮你取了琼·克劳馥的名字。”我的胃会紧缩下坠,羞愧难当。我知道自己挨了骂,却至今仍不确定原因。但琼·克劳馥不是只有风光的一面。事实上,她有悲剧的气质。她有严肃的大眼睛、不快乐的嘴和高耸的颧骨,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或许这就是母亲话中的含义。或者,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琼·克劳馥身材纤细。
我不瘦。这是母亲始终不太能谅解我的许多事情之一。起初,我只是丰满。在母亲的相簿中最早期的快照里,我是健康宝宝,重量不比多数婴儿大多少。照片唯一奇怪的地方是我从不看镜头,只忙着将东西塞进嘴巴,例如玩具、手和奶瓶。这些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排放,尽管我的身材没有日渐浑圆,却也没摆脱一般人所谓的婴儿肥。相簿里的照片只拍到我六岁的时候,之后便没有了。那必然是母亲停止对我怀抱希望的时候,因为照片都是由她拍摄的。也许她不想再记录我的成长。她已经认定我不会成材。
我很快便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母亲为我报名舞蹈课程。舞蹈学校里有一位弗莱格小姐,她的苗条程度几乎不亚于我母亲,对我凡事都看不顺眼。她教踢踏舞和芭蕾。我们的教室位于肉铺楼上的长方形房间。我永远记得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布满灰尘的楼梯,肉铺的锯木屑和生肉味逐渐转为疲惫双脚的闷热潮湿的气味,夹杂着一丝弗莱格小姐亚德利牌古龙水的香气。母亲送我去上舞蹈课,一半是因为当时流行让七岁小孩学舞(好莱坞音乐剧仍然当道),一半是希望跳舞能让我减少几分丰满。她没有跟我说过这句话,而是跟弗莱格小姐说的。那时她还不说我“胖”。
我很喜欢舞蹈学校,而且舞技不错,只是弗莱格小姐有时会狠狠地将教鞭往地上一抽,说:“亲爱的琼,真希望你别踩那么用力。”就像那个年代的多数小女生,我将芭蕾舞者视为完美的化身,那是女生可以从事的工作。我常将短小的鼻子靠在珠宝店的橱窗上,瞪大眼睛看八音盒上的陶瓷娃娃,亮晶晶的女性人偶穿着坚挺的粉红裙,硬邦邦的陶瓷头颅上戴着玫瑰。我一边看,一边幻想自己凌空飞跃,被一位瘦削的穿黑色紧身裤的男舞者举起;而我体态轻盈如风筝,佩戴着蕾丝花边头饰,发丝缀满水钻,闪亮如希望。我认真上课,无比专心,甚至常在家里练习,用蕾丝浴室窗帘包住身体跳舞。那条窗帘原是家里不要的,当母亲正要将窗帘塞进垃圾桶时,我向母亲苦苦哀求,于是她把窗帘洗干净了给我——她不喜欢尘土。我渴望拥有缎面芭蕾舞鞋,但弗莱格小姐说我们年纪太小,脚骨尚未变硬。因此我只能穿黑色软鞋,鞋带是毫无浪漫可言的松紧带。
弗莱格小姐善于发明,我想,按照这年头的说法应该是创意十足。教小朋友基本舞步并没有挥洒创意的空间,因为舞步大致上是靠练习,但她会举办年度春季舞蹈表演。表演主要是为了让家长心动,也是为了吸引小女孩,好让她们央求父母允许她们参加来年的课程。
弗莱格小姐筹划全部节目。她也布置舞台、制作道具、设计舞服,将舞服图样交给母亲们,交代她们缝制服装的注意事项。我母亲不喜欢缝纫,但她会为了这个活动卖力地裁布、钉大头针,一如其他人的母亲。也许那时她还没有放弃我,也许她仍然在为我尽心。
弗莱格小姐按照学生年龄安排表演节目,和舞蹈课分班的方式相同。共有五个班:小小班、高大班、中班、大班、少年班。尽管她看起来难以亲近,双手修长骨感,头发绾成发髻,眉毛细长(后来我才明白那是眉笔画的),但她也有温柔的一面,她将情感发挥在创意里。
我在小小班。我本人并不符合这个班级的名称。我不仅比班上所有的同学都重,也比她们都高。但我不在乎,甚至根本不曾注意到这些事情,因为我每天为舞蹈表演而兴奋。我在地下室练习几小时。原本我在客厅演练,不料意外碰碎了母亲的白金双色的菠萝造型台灯,那是灯组里的一盏。之后母亲只准许我在地下室练舞。我会在洗衣机旁边旋转,默哼着舞蹈配乐;我向火炉行屈膝礼(那个年头仍然使用煤炭);我在晾在晾衣绳上的对折床单间舞进舞出。当我精疲力竭时,便爬上地下室的楼梯,气喘吁吁、浑身煤渣地迎面见到衔了一嘴大头针的母亲。我全身被刷洗干净后,母亲会让我站在椅子上,叫我慢慢转圈。即使是试穿舞衣,我也很难静止不动。
母亲的不耐烦和我的不相上下,但烦躁的原因与我的不同。她可能已经后悔送我进舞蹈学校。首先,我没有消瘦半分;其次,我比原先吵闹两倍,尤其是在排练踢踏舞的时候,我会穿上鞋尖和鞋跟都有铁片的皮鞋,违反母亲的禁令在走廊的硬木地板上练舞;还有,她舞衣做得不顺利,她遵照指示缝制,却缝不出应有的效果。
我们共有三件舞衣。小小班有三支舞曲:《郁金香时刻》是荷兰日常练习芭蕾舞的舞曲,我们得和舞伴排好队形,上下摆动手臂模仿风车;《起锚》是一支有快速旋转和敬礼动作的踢踏舞曲(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军事主题仍然流行);《欢乐蝴蝶》是优雅的舞目,细腻轻快,最接近我心目中舞蹈应有的模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支舞,还有我最喜欢的舞衣:一件像正牌芭蕾舞者穿的薄纱短裙、一件细肩带的紧身马甲、一副有闪亮昆虫触角的头饰、一对用衣架做的彩色玻璃纸翅膀,翅膀由弗莱格小姐提供。我最心仪的就是那双翅膀,但我们得等到正式表演时才能穿戴翅膀,以防损坏。
就是这一套舞衣令我母亲心烦。其他舞衣比较简单:荷兰舞衣是长长的蓬裙搭配黑马甲和白袖子,而且我的位置是在舞台靠后。《起锚》穿的是有海军穗带饰边的水手装,这一套也不成问题,因为它是高领长袖,腰身宽松。由于个子高,我站在后排。我没有当上主角,获选的三位主角都有秀兰·邓波儿式的鬈发,她们要站在用奶酪箱子做的小台子上跳单人舞。但我不太在意这些,一心只想成为挑大梁的蝴蝶,这样才能和班上唯一的男生表演双人舞。他的名字是罗杰。我有点爱上他了。我希望与他搭档跳双人舞的女生生病,然后他们就得派我顶替。我不只熟记自己的舞步,也将她的部分大致背了下来。
我站在椅子上,母亲将大头针戳到我穿的舞衣上,叹了口气,要我慢慢转身,然后她皱着眉头别上更多大头针。让她烦恼的问题很简单:粉红短裙会让我的腰、手脚裸露在外,看起来颇为滑稽。我是以一个像我母亲或弗莱格小姐那种焦虑、过于守旧的成人视角,重现了当年场景,才得知这一点的。我的大腿摇晃不稳,日后将发育成乳房的部位隆起两坨脂肪,上臂丰腴,腰部松垮,看起来一定很下流,有点少年老成,几乎是有伤风雅,有如姿色正在衰颓的脱衣舞娘。像我那样的小孩在一九四九年年初,会被认为不宜穿那么少的衣服亮相。怪不得我会爱上十九世纪:根据那个年代的某些明信片来看,肉感即是美德。
母亲为舞衣受了不少折腾。她将舞衣放长,多加一层薄纱掩饰我的轮廓,为马甲缝上衬垫,却是徒劳。当她总算准许我用梳妆台上的三面镜检视自己时,连我也被镜中人小小吓了一跳。尽管我年龄幼小,不在乎身材,但镜中人并没有我要的模样。我看起来不像蝴蝶,可是我知道只要佩戴上翅膀一切便会改观。即使在那个年纪,我也期待魔法式的转变。
彩排是在下午,正式表演则在同一天傍晚。时间排得这么紧凑,是因为表演地点不在肉铺楼上(那里太小),而在只租借了星期六一天的学校体育馆。母亲提着装了舞衣的硬纸板衣箱,送我去彩排。舞台很狭窄,踩起来声音空洞,可是柔和的紫色天鹅绒帘幕弥补了舞台的缺点。我一逮到机会便摸了一把帘幕。帘幕后回荡着孩子们的兴奋之情。那里有许多母亲。有些母亲自愿充当化妆师,为自己的女儿和别人的女儿化妆,给她们的嘴巴涂上暗红色的口红,用黑色睫毛膏让睫毛硬挺成尖刺。打扮好的女孩倚墙而立,以防毁了扮相,她们一动不动,呆滞得像神殿里的祭品。年纪大一点的学员们到处溜达、闲聊。她们并不重视这场表演,毕竟她们以前参加过,再说要晚一点才轮到她们彩排。
《郁金香时刻》和《起锚》顺利排演完毕。我们在后台更衣,大家七手八脚,紧张地咯咯笑,为彼此钩上钩子、拉上拉链。唯一的更衣镜前面围了一群人。与我们交替出场的高大班在台前跳《胡闹小猫咪》时,弗莱格小姐站在一双双翅膀间审视大家,挥着教鞭打拍子,偶尔叱喝几声,情绪很亢奋。我在穿蝴蝶舞衣时,见到母亲站在弗莱格小姐旁边。
母亲应该待在外面,坐在我带她去坐的第一排折叠椅上,手套搁在腿上,抽着烟,摇晃一只穿着露趾高跟鞋的脚。但她这会儿正在跟弗莱格小姐说话。弗莱格小姐转头看看我,向我走来,母亲尾随在后。弗莱格小姐低头打量我,抿起嘴巴。
“我了解你的意思。”她向母亲说。事后我愤恨地回想那一幕,总觉得要不是母亲介入,弗莱格小姐也不会注意到我的扮相有何不妥,但那八成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弗莱格小姐看到的情况、她们俩看到的情况,是欢乐、精致、充满灵气的《欢乐蝴蝶》即将沦为可笑而不得体的表演,和被一个小胖妹破坏的画面;这小女孩不像蝴蝶而像大毛毛虫,最精准的说法应该是像白色的蛆。
弗莱格小姐无法忍受这一点。对她来说,舞台的效果就是一切。她希望得到好评,她要大家发自内心的赞赏,不要别人怜悯或强忍笑意的言不由衷。现在的我同情她的处境,但当年的我不能体谅她。不管怎样,她都没有失去创意。她弯下腰,一只手搭着我赤裸浑圆的肩膀,将我拉到角落。她跪下来,强势的黑眼睛直视我的眼睛,糊掉的眉毛扬起又落下。
“亲爱的琼,你想不想扮演特别的角色?”她问。
我犹疑地向她微笑。
“亲爱的,你愿意帮我做一件事吗?”她和蔼地说。
我点头,因为我乐于助人。
“我决定稍微改变节目。”她说,“我决定增加一个新的角色。你是班上最聪明的女生,所以我选择你来扮演特别的新角色。亲爱的,你愿意帮忙吗?”
依据我对她的了解,我知道她和蔼的态度很可疑。但我照样中计。我同情地点头,很高兴自己被选中。也许我会被挑去和罗杰跳蝴蝶双人舞;也许我会得到更大、更有分量的翅膀。我热切地答应帮忙。
“很好。”弗莱格小姐说,一手抓住我的手臂,“来换你的新服装。”
“我要演什么?”我在路上问。
“亲爱的,你要演樟脑丸。”她一派安详地说,仿佛那是全天下最自然的事情。
由于她极具创意巧思,加上以往可能有过类似的经验,总之她有应付这种状况的一条基本原则:若是免不了出糗,不如假装你有意为之。我很久以后才学会这种做法,体悟到这种处世之道;但当时我很难过,其实应该说是满心凄凉,弗莱格小姐竟然要我脱掉云朵般的裙子和闪亮的头饰,换上高大班跳《泰迪熊野餐》的白色泰迪熊装。她还要我在脖子上挂一块写着“樟脑丸”的大牌子。“亲爱的,这样大家才知道你演的是什么东西。”她准备利用彩排和正式表演间的空当,亲手为我做牌子。
“我可以戴翅膀吗?”我问,意识到她要我做出的是多么重大的牺牲。
“哪有长了翅膀的樟脑丸?”她装出打趣但实事求是的口吻。
她的点子是,蝴蝶们一做完跳跃的动作,我就穿着白色服装,挂着牌子,笨手笨脚地进入蝶群中间,而蝴蝶们四散而去。她说表演会很可爱。
“我喜欢原来的编舞。”我试探地说,“我想按原来的样子跳。”我快哭了。我八成已经流出眼泪。
弗莱格小姐脸色一变,面孔凑到我眼前,因此我能清楚看见她眼睛周围的皱纹,闻到她嘴里的酸牙膏味。她缓慢而咬字分明地说:“你照我的吩咐做,不然就不让你上台。听懂了没?”
我无法承受不能上台的打击,只好屈服,但我付出了代价。我被迫穿着樟脑丸服装站在弗莱格小姐旁边,她搭着我的肩膀向小小班的同学说明编舞的改变,引介我崭新的重要角色。蝶群穿着纤巧的裙子,戴着闪亮的翅膀,像窈窕的淑女。她们看着我,搽了口红的嘴唇露出鄙夷的神态。她们没有听信弗莱格小姐的话。
我跟着母亲回家,因为她的背叛而拒不说话。尽管那时是四月,却飘起轻雪,我很高兴她的白色露趾鞋一定会让她的脚湿掉。我走进浴室锁上门,让她不能进来,然后不可自抑地哭倒在地上,脸贴着松软的粉红色浴室脚垫。之后我搬动洗衣篮,站在上面照浴室镜子。我的妆一塌糊涂,脸颊上的黑色污痕像沾满煤渣的泪水,紫色口红洇开了,嘴唇发肿。我到底哪里不好?我又不是不会跳舞。
母亲隔着上锁的浴室门恳求了一会儿,继而出口威胁。我出了浴室,但拒绝吃晚餐:总要有人和我一起受折磨。母亲用旁氏冷霜为我卸妆,训斥说“这下子又得重新上妆”,然后我们返回学校体育馆。(父亲在哪里?他不在场。)
我嫉妒地站在翅膀之间,红着脸穿着闷热可憎的服装,听着开场前的咳嗽声和折叠椅拖过地板的声音,看着蝴蝶们窸窸窣窣地跳出我记忆中的舞步,我确信她们没有人比我更熟悉那些动作。最糟的是,我仍然不懂自己为何受到这种待遇,为什么她们明明是羞辱我,却说成器重我。
轮到我出场时,弗莱格小姐将我推向舞台。我跌跌撞撞地上场,东张西望一番,依照她的指示尽量装出樟脑丸的模样,然后开始跳舞。我没有舞步可言,因为她没有教我。我一边跳,一边编舞。我挥动手臂,撞上蝴蝶,转着圈使出浑身力气在舞台的薄地板上跺脚,跺得舞台晃动。我尽情投入角色,那是愤怒与毁灭之舞,在皮毛之下,泪水沿着我的脸颊淌下,蝴蝶会死亡。事后,我脚疼了好几天。“我才不是这副德行。”我不断地跟自己说,“是她们逼我扮演这个角色的。”尽管泰迪熊戏服将我整个人包覆起来,在我周身晃荡,令我冒汗,我却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一丝不挂,仿佛这可笑的舞蹈正是我的真面目,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我就是那副德行。
蝶群依照暗号惊惶逃走。我十分讶异地发现自己被撇在舞台中央,眼前的观众哈哈大笑,报以热烈掌声。甚至当纤瘦的美丽女孩们列队出场回礼时,笑声和掌声仍然持续不断,好几个人叫道:“樟脑丸太棒了!”那些人一定是父亲,不是母亲。我不懂为何有人喜欢我这丑陋宽大的衣服,而不是其他人的美丽舞衣。
表演结束后,大家称赞弗莱格小姐的“樟脑丸”创意无比高明。连母亲也眉开眼笑。“你表演得很好。”她说。但那一夜我仍然为失去的翅膀哭泣。我永远没有机会佩戴翅膀,因为我决定割舍心爱的舞蹈学校,不参加秋季班。没错,我比其他女生更引人注目,但那似乎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注目。更何况,谁会想娶一颗“樟脑丸”?日后,母亲常常用其他各种形式向我提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