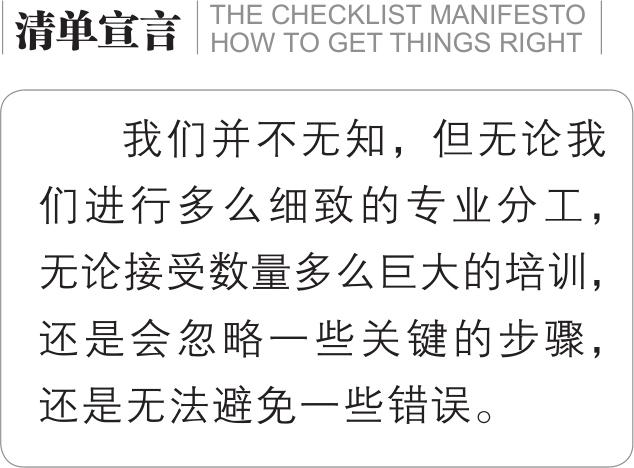·我们的身体可能以13 000多种不同的方式出问题。在重症监护室中,每位病人平均24小时要接受178项护理操作,而每一项操作都有风险。
·大量复杂的知识会让我们不堪重负。请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请承认,无论我们进行多么细致的专业分工和培训,还是会忽略一些关键的步骤,还是无法避免一些错误。
医学学术期刊《胸外科年鉴》(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上曾刊登过一篇论文,作者用干瘪晦涩的学术语言描述了一场发生在阿尔卑斯山一个奥地利小村庄里的噩梦。一对夫妻带着自己3岁大的女儿去屋后的林子里散步,结果一不留神孩子滑进了一个只结了一层薄冰的池塘。他们纵身跳入池塘试图将女儿拉上来,但孩子很快就沉入了水底。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把孩子救上岸。这对夫妻随即拨打了急救电话,急救人员立刻通过电话指导他们对孩子实施心肺复苏。
8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了,但他们发现孩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她的血压和脉搏都测不到,呼吸也停止了。孩子的体温只有19摄氏度,瞳孔已经放大,对光刺激没有任何反应,这说明她的大脑已经停止了工作。
但急救人员并没有放弃,他们依然给女孩实施心肺复苏。一架直升机将孩子火速送往附近的医院。一路上,急救人员不停地按压女孩的胸腔,等直升机到达医院后,他们直接将女孩推进了手术室,并把她抬到医院的轮床上。一个外科小组随即赶到,以最快的速度为孩子接上人工心肺机。
人工心肺机的个头和一张办公桌相当,外科医生必须将孩子右侧腹股沟的皮肤切开,将一根硅胶导管插入股动脉,让血液流入机器,并把另一根导管插入股静脉,使氧合后的血液被送回体内。一位体外循环灌注师打开人工心肺机的血泵,调整氧含量、温度和流量等参数。女孩的血液开始经体外循环,心肺机的管子也随之变成了鲜红色。直到一切就绪后,急救人员才停止按压女孩的胸腔。
把女孩送到医院的时间和为她接入人工心肺机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是1.5小时。不过,在“2小时关口”就要到来之际,女孩的体温上升了6摄氏度,她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这是她身上第一个恢复功能的内脏器官。
6小时后,女孩的核心体温已经达到正常的37摄氏度。医生试图用机械式呼吸机替换人工心肺机,但是池塘里的水和杂物对孩子的肺造成了严重损伤,输入的氧气无法经由肺部进入血液,所以医生只能为她接上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设备。为此,医生必须用一把锯子打开女孩的胸腔,并且将便携式体外膜肺氧合设备的导管直接插入女孩的主动脉和跳动的心脏中。
待体外膜肺氧合设备启动后,医生将人工心肺机的导管从女孩的身体里移除,然后对血管进行了修复,并将腹股沟上的切口缝合。外科小组随后将女孩送到了重症监护室,她的胸腔依然打开着,上面覆盖着无菌塑料薄膜。在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里,重症监护团队一直用纤维支气管镜吸除女孩肺里的积水和杂物。一天后,她的肺恢复良好,可以直接使用机械式呼吸机了。于是,医生又把她送回手术室,将插在她身体中的体外膜肺氧合设备的导管拔掉,修复血管,并将胸腔闭合。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女孩的肝、肾和肠等器官都恢复了功能,但脑还是没有反应。CT扫描显示,女孩的整个脑部都有肿胀的迹象,这是弥漫性损伤的特征,但脑部没有任何区域死亡。所以,医生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在女孩的颅骨上钻一个小孔,放入一个探头以监控其脑压,并通过引流脑脊液和使用药物等手段不停地对其脑压进行调整。在随后的一周多时间里,女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但最终,她渐渐地苏醒了过来。
先是她的瞳孔对光线有反应了。然后,她能够自主呼吸了。终于有一天,她张开了双眼,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溺水两周后,这个女孩出院回家。虽然右腿和左臂变得不太灵活,说起话来还有些模糊,但只要经过大量的康复治疗,她就可以在5岁前完全恢复。生理检查和神经检测结果都显示,她和其他女孩没什么两样,完全是一个健康的正常人。
这个故事之所以令人惊奇,并不只是因为医生能够把一个进了鬼门关2小时的小女孩拉回人间,更因为他们能够在混乱的医院里有条不紊地成功实施那么多复杂的治疗步骤。
人们常常会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场景: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急救人员用力按压其胸部,并对其实施人工呼吸。随着溺水者一阵咳嗽,肺部的积水被咳出,心跳恢复正常,神智也变得清晰了。但在现实中,急救可没有这么简单。
为了挽救这个小女孩的生命,数十位医护人员要正确实施数千个治疗步骤,比如在插入血泵导管的时候,不能把气泡注入病人的体内,要时刻保证各种导管、女孩敞开的胸腔以及她与外界接触的脑脊髓液不被细菌感染,他们还要使用一堆难伺候的设备,让它们正常运转。上面提到的每一步都很艰难,而要将这些步骤按照正确的顺序一个不落地做好更是难上加难。在整个过程中,医护人员没有任何犯错的余地。
实际上,很多因溺水而心脏停止跳动的孩子没有被挽救回来,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跳停止太久了,而是因为其他各种原因,比如机器坏了,手术团队动作不够快,或者有人没洗手而导致患者发生了感染。虽然这些案例没有写进《胸外科年鉴》,但它们非常普遍,只不过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我觉得我们都被青霉素忽悠了。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1928年的这项重大发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前景:只要服用一粒小药丸,或者打一针,就能治愈很多疾病。毕竟,青霉素治愈了许多原本无法医治的感染性疾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相似的简单方法治愈各种不同的癌症呢?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简单的方法来治疗烧伤、心血管疾病和中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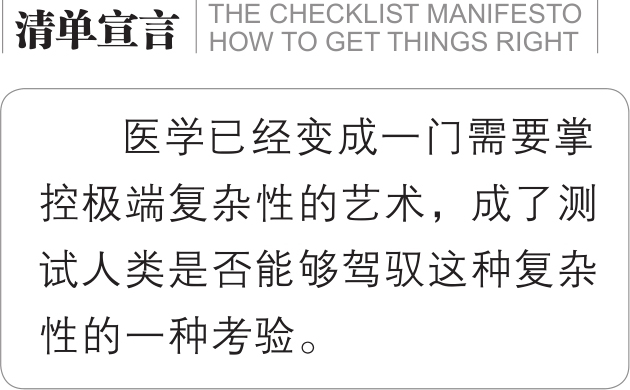
现代医学并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先进。虽然在过去的100年间医学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但是我们却发现,大多数疾病都有各自的特点,它们的共同之处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而且许多疾病仍然难以治愈。即使曾经用青霉素创造过无数奇迹的感染科医生,也面临非常严峻的情况:并非所有细菌菌株都对抗生素敏感,而那些敏感的也会很快发展出耐药性。今天,我们需要使用非常个性化的治疗手段,有时候甚至需要使用多种手段来治疗感染。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特定菌株的药敏性特征、病人的病情及受影响的器官系统。如今的治疗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离青霉素为我们展现的前景越来越远。医学已经变成一门需要掌控极端复杂性的艺术,成了测试人类是否能够驾驭这种复杂性的一种考验。
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九版)中,我们可以找到13 000多种不同的疾病、综合征和损伤类型。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可能以13 000多种不同的方式出问题,而科学几乎给上述每一种情况都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算我们无法治愈疾病,也能尽量减少疾病给患者带来的损伤和痛苦。不过,每种疾病的治疗方法都是不同的,而且基本上都不简单。现在,医生们手边就有6 000多种药物和4 000多种治疗手段可供选择,每一种都有不同的要求、风险和注意事项,这让医生们很难不出错。
我们医院在波士顿的肯莫尔广场(Kenmore Square)有一家附属社区诊所。“诊所”这个名称可能会让人觉得这家医疗机构很小,其实不然。这家诊所始建于1969年,现在的名称为“哈佛先锋”(Harvard Vanguard)。该诊所为各个年龄段的人们提供各类门诊服务,但就算只是提供门诊服务也不轻松。
为了跟上医学飞速发展的步伐,这家诊所建立了20多个科室,雇用了600多名医生和其他1 000多名专业人士。他们涉及的专业多达59种,其中有很多专业在诊所建成的时候还没诞生。如果你乘电梯到五楼,从电梯口一路走到普外科,会依次经过多个科室,如普内科、内分泌科、遗传科、手外科、化验实验室、肾科、眼科、整形外科、放射科和泌尿科。这还只是位于一条走廊两边的科室。
为了应对疾病复杂性这个问题,不同专业的医务人员进行了分工。尽管如此,我们的工作依然非常繁重。就拿我自己某一天的工作来说吧。
 急诊室让我去查看一名25岁的女病人。病人右下侧腹部越来越痛,还伴有发烧、呕吐等症状。我怀疑她得了阑尾炎,但她是个孕妇,所以不能让她接受CT扫描,这么做可能会威胁胎儿的安全。
急诊室让我去查看一名25岁的女病人。病人右下侧腹部越来越痛,还伴有发烧、呕吐等症状。我怀疑她得了阑尾炎,但她是个孕妇,所以不能让她接受CT扫描,这么做可能会威胁胎儿的安全。
 随后,一名妇科肿瘤医生让我去手术室看一看。一位女病人的卵巢上长了一个肿块,医生在切除这个肿块的时候发现,这可能是胰腺癌转移形成的。他想让我检查一下病人的胰腺,看看是否要一并切除。
随后,一名妇科肿瘤医生让我去手术室看一看。一位女病人的卵巢上长了一个肿块,医生在切除这个肿块的时候发现,这可能是胰腺癌转移形成的。他想让我检查一下病人的胰腺,看看是否要一并切除。
 邻近医院的一名医生打电话给我,说要让一名重症病人转到我们医院。这个病人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这个肿瘤已经阻塞了她的肾脏和肠子,并造成了大出血,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出了他们可以掌控的范围。
邻近医院的一名医生打电话给我,说要让一名重症病人转到我们医院。这个病人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这个肿瘤已经阻塞了她的肾脏和肠子,并造成了大出血,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出了他们可以掌控的范围。
 后来,我们医院的内科又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看一位61岁的病人。他的肺气肿非常严重,所以医生无法对他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因为担心他的肺容量不够大,手术风险性高。但是他现在得了很严重的结肠感染,也就是急性憩室炎,医生用了3天抗生素都无济于事。所以,手术是他能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后来,我们医院的内科又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看一位61岁的病人。他的肺气肿非常严重,所以医生无法对他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因为担心他的肺容量不够大,手术风险性高。但是他现在得了很严重的结肠感染,也就是急性憩室炎,医生用了3天抗生素都无济于事。所以,手术是他能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可能是觉得我的工作还不够乱,另一位同事让我去帮忙看一位52岁的患者,他患有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慢性肾衰竭,而且严重肥胖。他得过中风,现在又得了绞窄性腹股沟疝。
可能是觉得我的工作还不够乱,另一位同事让我去帮忙看一位52岁的患者,他患有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慢性肾衰竭,而且严重肥胖。他得过中风,现在又得了绞窄性腹股沟疝。
 还有一名内科医生让我一起给一位直肠瘘病人做诊断,她身体状况很好,但因为这个病可能要进行一次手术。
还有一名内科医生让我一起给一位直肠瘘病人做诊断,她身体状况很好,但因为这个病可能要进行一次手术。
正如各位看到的那样,我要在一天的时间里处理那么多不同而且复杂的病例。上述6个病人所患的疾病完全不同,此外,我还要进行26次不同的诊断。也许会有人觉得其他医生可能没那么忙,但实际上,我的每个同事每天都要面临许多复杂而棘手的问题。
根据哈佛先锋诊所病历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一年内,仅仅在门诊诊疗过程中,每个医生平均就要诊断250种疾病,而患有这些疾病的病人们还有其他900多种不同的健康问题需要医生仔细考虑。每个医生平均要开300种药物和100多种不同的化验单,还要使用40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如给病人接种疫苗、接骨等。
在所有医生中,普内科医生面临的问题最繁杂。他们每人平均每年要诊断371种疾病,要考虑其他1 010种健康问题,要开出627种药,还要使用36种治疗方法。只要想一想他们需要掌握多少种不同门类的知识,就会令人头脑发胀。而这还只是门诊的工作量,医疗管理系统并没有记录医生为住院病人提供服务时需要完成的各种工作。
但就算是只考虑门诊,统计数据也并不完整。因为在使用系统的时候,医生常常会使用“其他”这个选项。如果病人很多,而你的进度已经落下2小时,候诊的病人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这时候你往往不会在浩瀚的数据库中慢慢寻找相应的诊断代码,而是会选择“其他”这个万能选项草草了事。但话说回来,即便你有时间,也未必能够从系统中找到你想要记录的病症。
大多数美国医院使用的电子病历系统跟不上医学发展的速度,没有把新近发现的或刚刚和其他疾病区分开来的疾病包括在内。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患有肾上腺神经节细胞瘤的病人,这是一种罕见的肾上腺疾病。我还碰到过李–佛美尼综合征(Li-Fraumeni syndrome)患者,这是一种可怕的遗传病,会让病人周身器官都发生癌变。但是,在医疗管理系统的下拉菜单里找不到上述两种疾病的名称,于是,我只能选择“其他”选项了。科学家几乎每周都会有新的医学发现,会找到新的癌症亚型,会制订新的诊断标准,还会发明新的治疗手段。医疗的复杂程度与日俱增,连计算机系统都跟不上了。
但是医疗的复杂性并不只是源于知识的飞速积累,实践问题也是重要的原因。各位已经看到了医务人员面临的问题多么复杂棘手。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重症监护室(ICU)。
“重症监护”这个词听起来不太容易让人理解,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更喜欢用“重症护理”一词,不过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太清楚。但如果我们用“生命支持”这个非医学名称的话,一切就明明白白了。如今,人们可能会遭受许多可怕的病痛,如挤压、灼伤、炸伤、主动脉破裂、结肠破裂、严重心脏病发作、重度感染等。但不可思议的是,即使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病痛,很多人还是能活下来。要知道,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状况,在过去都能轻而易举地夺走人们的生命。而现在,重症病人存活下来已经变得司空见惯,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重症监护,因为相关医疗技术让我们能够用人造的方法替代人体失效的功能。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我们需要有大量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作为支撑。
如果病人的肺部出问题,我们需要机械式呼吸机,或许还需要将病人的气管切开。如果病人的心脏出了问题,我们需要主动脉内气囊泵。如果病人肾脏机能失效,我们则需要血液透析机。如果病人昏迷不醒,无法进食,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将硅胶导管插入病人的胃部或小肠,这样我们就能将由特殊配方制成的流质食物直接通过导管灌入病人的消化道;要是这位不幸的病人连肠胃都被破坏了,那么我们会将氨基酸、脂肪酸和葡萄糖直接注射进病人的血液里。
在美国,每天有将近9万人住进重症监护室,每年有500多万人需要接受重症监护。 几乎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机会光顾这个没人想去的地方。现代医疗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重症监护室里的生命支持系统,如早产儿、重伤患者、中风患者、心脏病患者,以及接受脑部、心脏、肺部等部位大手术的病人。在医院的各种治疗活动中,重症监护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在60多年前,重症监护室基本上不存在。但如果你到现在的医院去看一看, 在每天接受诊治的700位病人中,差不多会有155位接受重症监护。这些病人平均会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上4天时间,存活率大约是86%。 所以,进入重症监护室,接入机械式呼吸机和各种电线、导管并不意味着被判了死刑。不过,待在那里的几天会是你人生中情形最为危急的几天。
以色列科学家曾对重症监护病人在24小时内接受的各项护理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 每位病人平均每天要接受178项护理操作,如服药和吸除肺部积液等,而且每项操作都有风险。令人惊讶的是,医护人员操作的错误率只有1%。即便如此,这也意味着每位病人平均每天要承受两次左右的失误操作。 只有不断降低医护人员操作的错误率,提高成功率,重症监护才能成功挽救更多病人,但这很难做到。
对于一个昏迷的病人来说,仅仅在床上躺上几天就可能会出问题。
他的肌肉会萎缩,骨质会变得疏松,身上会长出褥疮,血管则开始阻塞。医护人员必须帮助病人活动他那软弱无力的四肢以避免发生痉挛。此外,医护人员还必须给病人皮下注射降低血液黏稠度的药物,每过几小时就帮他们翻个身,在给他们擦身和换床单的时候还不能碰掉导管或电线。他们每天要给病人刷两次牙,以防止口腔内繁殖的细菌引发肺炎。如果病人还要使用呼吸机、血液透析机,或者有开放性伤口的话,重症监护的难度就更大了。
不妨听我讲述一个故事,大家对重症监护的困难就会有直观的认识了。
有个病人名叫安东尼·德菲利波(Anthony DeFilippo),他已经48岁了,是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埃弗里特的豪华轿车司机。他因为患有疝气和胆结石而在一家社区医院接受手术。不幸的是,在手术期间,他出现了大出血的危急情况。虽然值班外科医生最终止住了大出血,但他的肝脏受到了严重损伤。在术后的几天里,他的病情不断恶化,社区医院已经没有能力对他进行医治了。于是,我同意他转院,并接手负责他的治疗,希望能稳定住他的病情。某个周日凌晨的1:30,他被送到了我们的重症监护室。他那乱蓬蓬的黑发紧紧贴在被汗水打湿的额头上,他的身体在颤抖,心率高达每分钟114次。因为高烧、休克和供氧不足,他神志不清、语无伦次。
“我要出去!”他大声叫道,“我要出去!”德菲利波不断用手撕扯他的衣服、氧气面罩和覆盖在腹部伤口上的敷料。
“德菲利波,没事的,”一位护士对他说,“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医院里。”
德菲利波是个大个子,他一把推开护士,翻身就要下床。我们立刻加大了输氧量,把他的手腕绑在床沿上,并试图和他讲道理。他最终精疲力竭,任由我们抽血和注射抗生素。
化验报告显示,他的肝功能衰竭,白细胞数量异常的高,这说明发生了感染。没过多久,我们发现他的肾功能也衰竭了,因为他的尿袋里一滴尿液也没有。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的血压不断下降,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也不再那么吵吵嚷嚷,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意识。他的每一个器官,包括他的大脑都开始衰竭。
我给他的姐姐打电话,并将德菲利波的病情告诉了她。她焦急地说:“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
我们的确尽了全力。我们给他注射了麻醉剂,一位男住院医生将一根呼吸管插入了他的气管,另一位女住院医生将各种设备连接上他的身体。她将一根5厘米长的细细针头插入德菲利波右手腕的桡动脉,并且用丝线将与针头相连的导管缝在他的皮肤上。随后,她将一根30厘米长的中心静脉置管插入他左侧颈部的颈静脉。当导管缝好后,X射线成像结果显示,导管的顶端正好位于它应该在的位置,也就是心脏入口处的腔静脉中。随后,她将另一根稍粗一点的透析导管穿过德菲利波的右胸上侧,插入他的锁骨下静脉。
我们将呼吸导管的另一头接上呼吸机,并将呼吸频率调整到每分钟14次。我们不断调整呼吸机的压力和流速,就像工程师在操控面板前不断调整参数一样,直到德菲利波血液中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达到我们预先设定的水平为止。
我们通过插入桡动脉的导管来监测他的动脉血压,并不断调整药物使其达到理想水平;还通过插入颈静脉的导管测量静脉压来调整静脉输液的速度,将插入锁骨下静脉导管的另一头插入血液透析机。这个人工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能把他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并将透析后的血液送回病人身体。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细微的调整来控制他的血钾水平以及血液中碳酸氢盐和氯化钠的含量。德菲利波就像我们手中可以操控的一台机器一样。
他当然不是一台简单的机器。我们面临的困难就好比仅仅依靠几个简单的仪表和操控装置,就要把一辆从山上飞奔而下的18轮汽车安全开到山脚下。光是维持德菲利波的血压就需要几万毫升静脉注射液和一架子的药物。呼吸机的功能已经发挥到了极限。德菲利波的体温已经上升到40摄氏度。 在与他病情相仿的重症病人中,只有不到5%的人能够走出重症监护室。只要我们稍有闪失,这一点点的生存概率就会荡然无存。
在随后的10天里,情况渐渐好转起来。德菲利波的主要病因是手术过程造成的肝损伤。由于他肝内的胆总管被切开了,所以胆汁不断漏出来。而胆汁具有腐蚀性,它能消化食物中的脂肪,也能把人体内部各种脏器都消化掉。德菲利波的身体太虚弱了,经不起修复手术的折腾。所以,一旦他的病情稳定下来,我们就请放射科医生帮忙采取临时性措施。他们在X射线的帮助下,将引流支架穿过腹壁,并将其放入切开的胆总管,这样就能把胆汁引出来。由于病人体内漏出的胆汁太多,他们不得不放置3个引流支架,一个在胆总管里,两个在胆总管周围。胆汁被排出后,德菲利波的烧退了。他的输氧量和补液量都下降了,血压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他渐渐开始恢复。但到第11天,就在我们准备把机械式呼吸机撤掉的时候,德菲利波的体温骤然升高,血压骤降,血氧水平再次大幅下降。他的皮肤上都是汗水,身体却在不断地打冷战。
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我们怀疑发生了感染,但X射线检查和CT扫描都找不出感染源在什么地方。尽管我们给德菲利波使用了4种抗生素,他还是高烧不退,最终导致其心脏发生了纤维性颤动。蓝色警报启动了。一大群医护人员闻讯赶来,对其实施电击除颤。这一举措奏效了,他的心跳又恢复到了正常的频率。又过了两天时间,我们才找出问题的原因。我们怀疑接入德菲利波体内的某根导管被感染了,所以为他换上了新导管,并将撤下的导管送到实验室进行培养。48小时后,结果出来了,所有导管都发生了感染。很可能是一根导管在接入时被细菌污染了,随后细菌通过德菲利波的血液蔓延到其他导管。就这样,所有导管都成了毒源,不断地将大量细菌引入德菲利波体内,使他高烧不退,病情恶化。
这就是重症监护室里的现实, 我们能拯救病人的生命,也同样能威胁他们的生命。 中心静脉置管感染非常普遍,我们也将其视为一种常见的并发症。
在全美各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医护人员每年要为病人插入500万根静脉置管。 美国2008年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显示,静脉置管插入10天后,就会有4%的病人发生感染。在美国,每年有8万人 发生此类感染,死亡率为5%~28%。 感染威胁性的大小取决于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那些挺过去的病人平均要在重症监护室里多待一周时间。但这里的威胁还远不止这些。 在美国,插入导尿管10天的重症监护病人有4%会发生膀胱感染,而接入呼吸机10天的病人有6%会发生细菌性肺炎,死亡率为40%~45%。 总而言之,有将近一半的重症监护病人会发生严重并发症。此类情况一旦发生,他们的存活率将大幅降低。
又过了一周时间,德菲利波才从感染中恢复过来,我们这才把呼吸机撤掉。但他还要耐心等上两个月才能出院。德菲利波的身体在出院后依然非常虚弱,这让他失去了工作和家庭,他也不得不搬到姐姐那里生活。我们为他插入的胆汁引流管依然在他的腹部上挂着。当德菲利波恢复元气后,我们会对他实施手术,帮他重建胆总管。但不管怎样,他顽强地活了下来,而大多数病情和他一样严重的病人最终都没能挺过来。
这就是现代医疗面临的主要困惑: 为了挽救垂死的病人,我们要掌握正确的知识,并确保每天对病人实施的178项治疗措施都不出错。 请注意,在治疗过程中你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比如一些监视器的警报会莫名其妙地响起,临床的病人可能会吵吵闹闹,还会有护士把头探过来问你是否可以帮把手,把病人的胸部打开。这些都会让原本已经非常复杂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即便是进行分工都未必能应付得过来。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现代医疗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专业分工,让每个人的专业领域变得越来越窄。在我讲述德菲利波的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是我在无时无刻地照料他,是我在进行各类繁杂的操作。不,这些其实是由重症监护医师做的。作为一名普外科医生,我希望自己能够应付大多数临床状况。但是重症监护的繁杂和细致让我不得不把工作交给专科护理专家。欧美的大多数主要城市都开设了有关特殊护理的培训课程。在如今的美国医院里,有一半重症监护室要依靠这些专科护理专家。
专业分工是现代医学的金科玉律。在20世纪初,人们只需要在高中毕业后读一年医学专业就可以行医了。而到了20世纪末,如果你想当医生,无论是在儿科、外科,还是在神经科单独执业,都必须完成4年的医学本科学习,然后还要接受3~7年的住院医生培训。不过,这些准备似乎已经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医疗了。如今,大多数年轻医生在结束住院医生培训后还要接受1~3年的专业进修培训,如有关腹腔镜手术、小儿代谢疾病诊治、乳腺癌放射学或重症监护等的培训。今天的年轻医生往往已经不再年轻。一般来说,他们要到34~35岁才能开始独立执业。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超级专家主导的时代。医生们在各自的狭小领域内不断磨炼自己的技艺,直到自己在这个领域比其他人干得更好。与一般专家相比, 超级专家有两大优势:他们知道更多重要的 细节,而且学会了如何掌控特定工作的复杂性。 但无论是在医疗行业,还是在其他领域中,一些工作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即使是最能干的超级专家也难免会犯错。
可能没有哪个领域的分工细化程度能够比得上外科手术了。我们可以把手术室看作操作极为频繁的重症监护室。在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只负责消除病人的疼痛和稳定他们的体征。但麻醉医生可分为小儿麻醉医生、心脏麻醉医生、产科麻醉医生、神经手术麻醉医生等。相似地,“手术室护士”这一称谓已经名存实亡,因为他们的专业也要进一步细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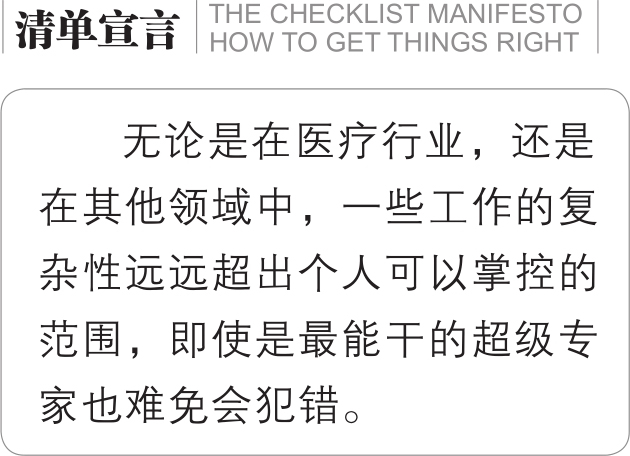
外科医生当然也要顺应潮流,其专业细分程度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以后会有左耳外科专业和右耳外科专业。虽然我们是在开玩笑,但谁也保不准以后外科医生不会有看左耳的和看右耳的之分。
我是一名普外科医生,但是现在除了在非常偏远的农村地区,你根本找不到什么外科手术都能做的医生。于是,我决定将我的专业聚焦在肿瘤外科手术上,但这个目标还是太大。所以,虽然我已经尽全力掌握各种普外科手术技术,特别是与急救相关的技术,但我还是不得不把目标集中在内分泌腺肿瘤切除手术上。
近几十年,专业分工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为外科手术技术的飞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前,即使是小手术,死亡率也都高达两位数,而且病人往往恢复得很慢,常常会留下残疾。但在今天,手术后病人当天出院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不过,如今的手术数量也在迅猛增长。 一个美国人在一生中平均要接受7次手术,而美国的外科医生们一年要做5 000万台手术。 所以,手术伤害的绝对数量依然居高不下。 在美国,每年有25万人没能走下手术台,不仅如此,许多研究都显示,至少有一半致死因素和严重并发症都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并不无知,但无论我们进行多么细致的专业分工,无论接受数量多么巨大的培训,还是会忽略一些关键的步骤,还是无法避免一些错误。
成功和失败并存的现代医疗向我们发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专业分工都不足以解决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如果超级专家都会失败,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 渐渐地,我们看到了问题的答案,但它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一个和医疗完全没有关系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