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日以来,思虑甚枯,唯念于教师职务,得少尽精力,使醇醇诸稚,展发神辉,亦此生一乐。顾力不逮思,实难从玄,今日所呈现象,每不满昨日所怀。所幸心存希望,即是一缕动机,此机勃发,或有美满光明之时也。
1913年10月12日给顾颉刚的信
偶思教育之要点,当无逾养成儿童正确精新之思想能力。国人旧时思想陈腐已极,匪可应用于当世。而儿童之环境之遗传,均不出此陈腐之思想。言教育不探其本,何效可获?徒推求于学生课文如何能背诵默写,学校规则如何能强令恪守,抑亦枝叶之事耳。
1916年4月14日日记
说到怎样教,对学生还得有所认识。不认识他们身体发展的情形,怎能培养好他们的体质?不认识他们获得知识和掌握技能的过程,怎能培养好他们的知识技能?不认识他们躬行实践该取什么途径,怎能培养好他们的道德品质?不认识他们的思想形成和感情深化的过程,怎能培养好他们的思想感情?这些都必须认识,不然,任你辛辛苦苦地教,实际上只是盲目地教——也就是没有尽教师的责任。所以,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之类非钻研不可。钻研这些学科越深,认识学生身心就越真,教起来就越有把握。
《教师怎样尽责任》
教师教学生靠语言,讲一堂课,谈一番话,语言是不可少的工具;可是要知道,决不能光靠语言。教师讲了一大堆有道理的话,可是他的实际生活并不那样,他的话就不会对学生起多大作用;或者讲了什么是不好的,可是他的实际生活里就很有那种不好的成分,那就会给学生很坏的影响:他们至少要想,原来话是可以随便说的,说的话跟实际生活是可以正相反背的。唯有教师的话跟他的实际生活完全一致,不但像通常说的“说得到做得到”,而且要做得到才说,情形就大不相同。那时候学生非常信服,愿意照着教师的话积极地实行,因为面前的教师就是光辉的榜样,他们觉得跟着教师走是顶大的快乐。我国古来有所谓“身教”,就是说教师教学生不能光靠语言,还得以身作则,真正的教育作用在语言跟实际生活的一致上。这样看来,教师必须以身作则,小学生守则才能有效地实施。
《教师必须以身作则》
我想现在如其真心要向这些教师说法,不必讲什么设计教育法、道尔顿制和教育测验等等,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用处,这些东西的确是可贵的宝贝。但是,最要紧的是使他们的日常生活上轨道。所谓上轨道,指最平常的而言,就是一言一行,都没有消极的影响,一饮一啄,都要有正当的意义罢了。这虽是最正常的,也是最根本的。如果能做到这样,再加上教法的研究,原理有了解,固然是教育所需求的教师;即使退一步,没有深切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只要能做到这样,也不失为中庸的教师,因为他们没有残害学生的思想和情感。
《教师的修养》
通常说教育工作分“言教”和“身教”,以“身教”为贵。这是不错的。不过仔细想想,要是自己不明白某些道理,不擅长某些方法,怎么能说给学生听?这是一层。要是光能说明某些道理和方法,而在平日的实践中并不按照自己所说的道理和方法行事,那给与学生的不良影响是不必细说的。所以又是自己的实践必须跟说给学生听的一致,这是又一层。从以上说的两层看来,“言教”并非独立的一回事,而是依附于“身教”的;或以言教,或不言而教,实际上都是“身教”。“身教”就是“为人师表”,就是一言一动都足以为受教者的模范。
知识学问无止境,品德修养无止境,这是古今中外凡是有识见的人一致的认识。所以就个人来说,谁也不该固步自封,说我是够了,凭我现在这一身本领,可以应用一辈子了。至于教育工作者,担负的既然是教育工作,就不能不就当前国家的形势,就受教育者的前途,考虑该怎样“自处”。当前国家的形势怎样?两个文明必须大力推进,四化建设必须赶速完成,全国各族人民都在为此而勤奋努力,各方各面都开展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受教育者的前途怎样?回答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唯有投身到上面所说的洪流中去,各自尽一份应尽的力量。受教育者的前途既然是这样,教育工作者自当从这些方面训练他们,熏陶他们。就教育工作者个人方面来说,当前国家的形势既然如此,自己是全国各族人民中的一分子,本该德才兼备,知能日新,一心为公,实事求是。何况自己担负的是教育工作,无论言教或是不言之教,总之要把自己的好模样的去教人,才能收到训练和熏陶的实效。把自己的好模样之教人就是“为人师表”。
“知也无涯”,没有接触过的事物不能知,没有探索过的道理不能知。现在是20世纪80年代,人类的进步事业飞速发展,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奥秘都有极其丰富的发见发明。但是决没有到了尽头,很可能没有发见发明的比已经发见发明的还多得多。所以谁也不能是全知全能的人,只能当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人。教育工作者当也如此。不过教育工作者必须为当前的受教育者着想,将来攀登新高峰窥见新奥秘的正是他们,非趁早给他们打基础不可。基础怎么打?还是身教为要。事事不马虎,样样问个为什么,受教育者看在眼里,印在心里,自然而然会养成钻研探索的良好习惯。至于一切事物后来居上的道理、历史洪流好比接力长跑的道理等等,虽然只能言教,如果例证确凿、说理透彻,受教育者也会受到良好影响。我以为在当今的时代,这是教育工作者为人师表的极其重要的一项。
《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
最近听吕叔湘先生说了个比喻,他说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可不是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吕先生这个比喻说得好极了,办教育的确跟种庄稼相仿。受教育的人的确跟种子一样,全都是有生命的,能自己发育自己成长的;给他们充分的合适的条件,他们就能成为有用之才。所谓办教育,最主要的就是给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适条件。
办教育决不类似办工业,因为受教育的人绝对不是工业原料。唯有没有生命的工业原料可以随你怎么制造,有生命的可不成。记得半个世纪以前,丰子恺先生画过一幅漫画,标题是《教育》。他画一个做泥人的师傅,一本正经地把一个个泥团往模子里按,模子里脱出来的泥人个个一模一样。我现在想起那幅漫画,因为做泥人虽然非常简单,也算得上工业;原料是泥团,往模子里一按就成了产品——预先设计好的泥人。可是受教育的人决非没有生命的泥团,谁要是像那个师傅一样只管把他们往模子里按,他的失败是肯定无疑的。
但是比喻究竟是比喻,把办教育跟种庄稼相比,有相同也有不相同。相同的是工作的对象都有生命,都能自己成长,都有自己成长的规律。不同的是办教育比种庄稼复杂得多。种庄稼只要满足庄稼生理上生长的需要就成,办教育还得给受教育者提供陶冶品德、启迪智慧、锻炼能力的种种条件,让他们能动地利用这些条件,在德智体各方面逐步发展成长,成为合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
对受教育者能提供充分的合适的条件,让他们各自发挥能动作用,当然比把他们往模子里按难得多。但是既然要办教育,就不怕什么难,就必得把这副难的担子挑起来。
《吕叔湘先生说的比喻》
我如果当小学教师,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是在嘴唇边,油腔滑调地喊一声;而是出于衷诚,真心认他们为朋友,真心要他们做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成长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得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不然,我就够不上做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
我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表演一两回,而不能终身以之,那是扮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都必须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但硬是要养成,决不马虎了事。譬如门窗的开关,我要教他们轻轻地,“砰”的一声固然要不得,足以扰动人家的心思的“咿呀”声也不宜发出;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又如菜蔬的种植,我要教他们经心着意地做,根入土要多少深,两本之间的距离要多少宽,灌溉该怎样调节,害虫该怎样防治,这些都得由知识化为实践,直到他们随时随地种植植物,总是这样经心着意,才认为又养成了一种好习惯。这种好习惯不仅对于某物本身是好习惯,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对于开门关窗那样细微的事,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还肯作奸犯科,干那些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对于种植蔬菜那样切近的事,既因工夫到家,收到成效,对于其他切近的事,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认识,具体的如社会现象的剖析,还肯节省工夫,贪图省事,让它马虎过去吗?
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认作终极的目的。我要从这方面养成小朋友语言的好习惯。有一派心理学者说,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所以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一个词儿,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怎么写,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一句句子,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讲,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该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一篇故事,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一首诗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什么,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的目的。
我决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这样唱的时候,完全失掉语言之自然,只成为发声部分的机械运动,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既然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那么,随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么意义?
现当抗战时期,课本的供给很成问题,也许临到开学买不到一本课本,可是我决不说:“没有课本,怎么能开学呢!”我相信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许多功课都是不一定要利用课本的,也可以说,文字的课本以外还有非文字的课本。非文字的课本罗列在我们周围,随时可以取来利用,利用得适当,比较利用文字的课本更为有效,因为其间省略了一条文字的桥梁。公民、社会、自然、劳作,这些功课的非文字的课本,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书铺子里没有课本卖,又有什么要紧?只有国语,是非有课本不可的;然而我有黑板和粉笔,小朋友还买得到纸和笔,也就没有什么关系。
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者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我决不举起手来,在他们的身体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觉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隔一两天也就没有痕迹;这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的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身体上的痛或红肿,固然不久就会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却是永不会磨灭的。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并且,当我打他们的时候,我的面目一定显得很难看,我的举动一定显得很粗暴,如果有一面镜子在前面,也许自己看了也会嫌得可厌。我是一个好好的人,又怎么能对着他们有这种可厌的表现呢?一有这种可厌的表现,以前的努力不是根本白费了?以后的努力不将不产生效果吗?这样想的时候,我的手再也举不起来了。他们的顽皮和愚笨,总有一个或多个的原由;我根据我的经验,从观察和剖析找出原由,加以对症的治疗。哪还想有一个顽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周围吗?这样想的时候,我即使感情冲动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也就立刻转到心平气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来出气了。
我还要做小朋友家属的朋友,对他们的亲切和忠诚和对小朋友一般无二。小朋友在家庭里的时间,比在学校里来得多;我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必须与他们的家属取得一致才行。我要他们往东,家属却要他们往西,我教他们这样,家属却教他们不要这样,他们便将徘徊歧途,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费。做家属的亲切忠诚的朋友,我想并不难;拿出真心来,从行为、语言、态度上表现我要小朋友好,也就是要他们的子女弟妹好。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弟妹?还肯故意与我不一致?
《如果我当教师》
我如果当中学教师,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犹如我决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读书”一个样。书中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学生方面说,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说成“读书”,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好像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功夫。因此,说成“教书”,也便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好像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并没有什么分别。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这里我不敢用一个“教”字。因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这么一套本领,双手授予学生的意思;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领,能够说已经完整无缺了吗?我能够肯定地说我就是一个标准的健全的公民吗?我比学生,不过年纪长一点儿,经验多一点儿罢了。他们要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经验,我就凭年纪长一点儿、经验多一点儿的份儿,指示给他们一些方法,提供给他们一些实例,以免他们在迷茫之中摸索,或是走了许多冤枉道路才达到目的——不过如此而已。所以,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
我不想把“忠”“孝”“仁”“爱”等等抽象德目向学生的头脑里死灌。我认为这种办法毫无用处,与教授“蛋白质”“脂肪”等名词不会使身体得到营养一个样。忠于国家忠于朋友忠于自己的人,他只是顺着习惯之自然,存于内心,发于外面,无不恰如分寸;他决不想到德目中有个“忠”字,才这样存心,这样表现。进一步说,想到了“忠”字而行“忠”,那不一定是“至忠”;因为那是“有所为”,并不是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为了使学生存心和表现切合着某种德目,而且切合得纯任自然,毫不勉强,我的办法是在一件一件事情上,使学生养成好习惯。譬如举行扫除或筹备什么会之类,我自己奋力参加,同时使学生也要奋力参加;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自己看作切身的事,竭知尽力地图谋最好的解决,同时使学生也要看作切身的事,竭知尽力地图谋最好的解决: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养成学生的好习惯,综合起来,他们便实做了“忠”字。为什么我要和他们一样的做呢?第一,我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应当“忠”;第二,这样做才算是指示方法,提供实例,对于学生尽了帮助他们的责任。
我不想教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情。设立学生自治会了,组织学艺研究社了,通过了章程,推举了职员,以后就别无下文,与没有那些会和社的时候一个样:这便是有名无实。创办图书馆了,经营种植园了,一阵高兴之后,图书馆里只有七零八落的几本书,一天工夫没有一两个读者,种植园里蔓草丛生,蛛网处处,找不到一棵像样的蔬菜,看不见一朵有劲的花朵:这便是有名无实。做这种有名无实的事比不做还要糟糕;如果学生习惯了,终其一生,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这样有名无实,种种实际事务还有逐渐推进和圆满成功的希望吗?我说比不做还要糟糕,并不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主张不要成立那些会和社,不要有图书馆种植园之类的设备。我只是说干那些事都必须认真去干,必须名副其实。自治会硬是要“自治”,研究社硬是要“研究”,项目不妨简单,作业不妨浅易,但凡是提了出来的,必须样样实做,一毫也不放松;有了图书馆硬是要去阅读和参考,有了种植园硬是要去管理和灌溉,规模不妨狭小,门类不妨稀少,但是既然有了这种设备,必须切实利用,每一个机会都不放过。而且,那决不是一时乘兴的事,既然已经干了起来,便须一直干下去,与学校同其寿命。如果这学期干得起劲,下学期却烟消云散了,今年名副其实,明年却徒有其名了,这从整段的过程说起来,还是个有名无实,还是不足以养成学生的好习惯。
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国文科在训练思维、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理化科在懂得自然,进而操纵自然之类;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每一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辐”,许多的辐必须集中在“教育”的“轴”上,才能成为把国家民族推向前进的整个“轮子”。这个观念虽然近乎抽象,可是很关重要。有了这个观念,我才不会贪图省事,把功课教得太松太浅,或者过分要好,把功课教得太紧太深。做人做事原是不分科目的,譬如,一个学生是世代做庄稼的,他帮同父兄做庄稼,你说该属于公民科、生物科,还是数学科?又如,一个学生出外旅行,他接触了许多的人,访问了许多的古迹,游历了许多的山川城镇,你说该属于史地科、体育科,还是艺术科?学校里分科是由于不得已;要会开方小数,不能不懂得加减乘除;知道了唐朝,不能不知道唐朝的前后是什么朝代;由于这种不得已,才有分科教学的办法。可是,学生现在和将来做人做事,还是与前面所举的帮做庄稼和出外旅行一个样,是综合而不可分的;那么,我能只顾分科而不顾综合,只认清自己的那门功课的目标而忘记了造成健全的公民这个总的目标吗?
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决不专作讲解工作,从跑进教室始,直到下课铃响,只是念一句讲一句。我想,就是国文课,也得让学生自己试读试讲,求知文章的意义,揣摩文章的法则;因为他们一辈子要读书看报,必须单枪匹马、无所依傍才行,国文教师决不能一辈子伴着他们,给他们讲解书报。国文教师的工作只是待他们自己尝试之后,领导他们共同讨论:他们如有错误,能给他们纠正;他们如有遗漏,给他们补充;他们不能分析或综合,替他们分析或综合。这样,他们才像学步的幼孩一样,渐渐地能够自己走路,不需要人搀扶;国文课尚且如此,其他功课可想而知。教师捧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学生对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一边是念一句讲一句,一边是看一句听一句;这种情景,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多么滑稽又多么残酷啊!怎么说滑稽?因为这样之后,任何功课都变为国文课了,而且是教学不得其法的国文课。怎么说残酷?因为学生除了听讲以外再没有别的工作,这样听讲要连续到四五个钟头,实在是一种难受的刑罚,我说刑罚决非夸张,试想我们在什么会场里听人演讲,演讲者的话如果无多意义,很少趣味,如果延长到两三个钟头,我们也要移动椅子,拖擦鞋底,作希望离座的表示;这由于听讲到底是被动的事情,被动的事情做得太久了,便不免有受刑罚似的感觉。在听得厌倦了而还是不能不听的时候,最自然的倾向是外貌表示在那里听,而心里并不在听;这当儿也许游心外骛,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也许什么都不想,像老僧入了禅定。叫学生一味听讲,实际上无异于要他们游心外骛或者什么都不想,无异于摧残他们的心思活动的机能,岂不是残酷?
我不怕多费学生的心力,我要他们试读、试讲,试作探讨,试作实习,做许多的工作,比仅仅听讲多得多,我要叫他们处于主动的地位。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事物,我决不滔滔汩汩地一口气讲给他们听,他们尝试过了,我才讲,可是我并不逐句逐句地讲书,我只给他们纠正,给他们补充,替他们分析和综合。
《如果我当教师》
我如果当大学教师,还是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依理说,大学生该比中学生更能够自己看书了;我或者自己编了讲义发给他们,或是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或别的书给他们作课本,他们都可以逐章逐节地看下去,不待我教。如果我跑进教室去,按照讲义上课本上所说的复述一遍,直到下课铃响又跑出来,那在我是徒费口舌,在他们是徒费时间,太无聊了;我不想干那样无聊的勾当。我开一门课程,对于那门课程的整个系统或研究方法,至少要有一点儿是我自己的东西,依通常的说法就是所谓“心得”,我才敢于跑进教室去,向学生口讲手画,我不但把我的一点儿给与他们,还要诱导他们帮助他们各自得到他们的一点儿;唯有如此,文化的总和才会越积越多,文化的质地才会今胜于古,明日超过今日。这就不是“教书”了。若有人问这叫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为学。”
据说以前的拳教师教授徒弟,往往藏过一手,不肯尽其所有地拿出来;其意在保持自己的优势,徒弟无论如何高明,总之比我少一手。我不想效学那种拳教师,决不藏过我的一手。我的探讨走的什么途径,我的研究用的什么方法,我将把途径和方法在学生面前尽量公开。那途径即使是我自己开辟的,那方法即使是我独自发现的,我所以能够开辟和发现,也由于种种的“势”,因缘凑合,刚刚给我捉住了;我又有什么可以矜夸的?我又怎么能自以为独得之秘?我如果看见了冷僻的书或者收集了难得的材料,我决不讳莫如深,决不提起,只是偷偷地写我的学术论文。别的人,包括学生在内,倘若得到了那些书或材料,写出学术论文来,不将和我一样的好,或许比我更好吗?将书或材料认为私有的东西,侥幸于自己的“有”,欣幸于别人的“没有”,这实在是一种卑劣心理,我的心理,自问还不至这么卑劣。
我不想用禁遏的办法,板起脸来对学生说,什么思想不许接触,什么书籍不许阅读。不许接触,偏要接触;不许阅读,偏要阅读。这是人之常情,尤其在青年。禁遏终于不能禁遏,何必多此一举?并且,大学里的功夫既是“为学”,既是“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材料是越多越好;如果排斥其中的一部分,岂不是舍广博而趋狭小?在化学试验室里,不排斥含有毒性的元素;明知它含有毒性,一样地要教学生加以分析,得到真切的认识。什么思想什么书籍如果认为要不得的话,岂不也可以与含有毒性的元素一样看待,还是要加以研究?学生在研究之中锻炼他们的辨别力和判断力,从而得到结论,凡真是要不得的,他们必将会直指为要不得。这就不禁遏而自禁遏了,其效果比一味禁遏来得切实。
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凡是在我班上的学生,我至少要知道他们的性情和习惯,同时也要使他们知道我的性情和习惯。这与我的课程,假如是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似乎没有关系,可是谁能断言确实没有关系?我不仅在教室内与学生见面,当休闲的时候也要与他们接触,称心而谈,绝无矜饰,像会见一位知心的老朋友一个样。他们如果到我家里来,我决不冷然地问:“你们来做什么?”他们如果有什么疑问,问得深一点儿的时候,我决不摇头说:“你们要懂得这个还早呢!”问得浅一点儿的时候,我决不带笑说:“这还要问吗?我正要考你们呢!”他们听了“你们来做什么”的问话,自己想想说不出来做什么,以后就再也不来了。他们见到问得深也不好,问得浅也不好,不知道怎样问才不深不浅,刚刚合适,以后就再也不问了。这种拒人千里的语言态度,对于不相识的人也不应该有,何况对于最相亲的朋友?
我还是不忘记“教育”那个总目标;无论我教什么课程,如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决不说除此之外再没有我的事儿了,我不作纵情任意,或去嫖妓,或去赌博,或做其他不正当的事。我要勉为健全的公民,本来不该做这些事;我要勉为合格的大学教授,尤其不该做这些事。一个教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的教师,他的行为如果不正当的话,其给与学生的影响虽是无形的,却是深刻的,我不能不估计它的深刻程度。我无法教学生一定要敬重我,因为敬重不敬重在学生方面而不在我的方面,可是我总得在课程方面同时在行为方面,尽力取得他们的敬重,因为我是他们的教师。取得他们的敬重,并不为满足我的虚荣心,只因为如此才证明我对课程同时对那个总的目标负了责。
无论当小学中学或大学的教师,我要时时记着,在我面前的学生都是准备参加建国事业的人。建国事业有大有小,但样样都是必需的;在必需这个条件上,大事业小事业彼此平等。而要建国成功,必须参加各种事业的人个个够格,真个能够干他的事业。因此,当一班学生毕业的时候,我要逐个逐个地审量一下:甲够格吗?乙够格吗?丙够格吗?……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我才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我帮助学生总算没有错儿,我对于建国事业也贡献了我的心力。
我决不“外慕徙业”,可是我也希望精神和物质的环境能使我安于其业。安排这样的环境,虽不能说全不是我所能为力,但大部分属于社会国家方面,因此我就不说了。
《如果我当教师》

在上海半淞园与中国公学中学部友人合影(右三为叶圣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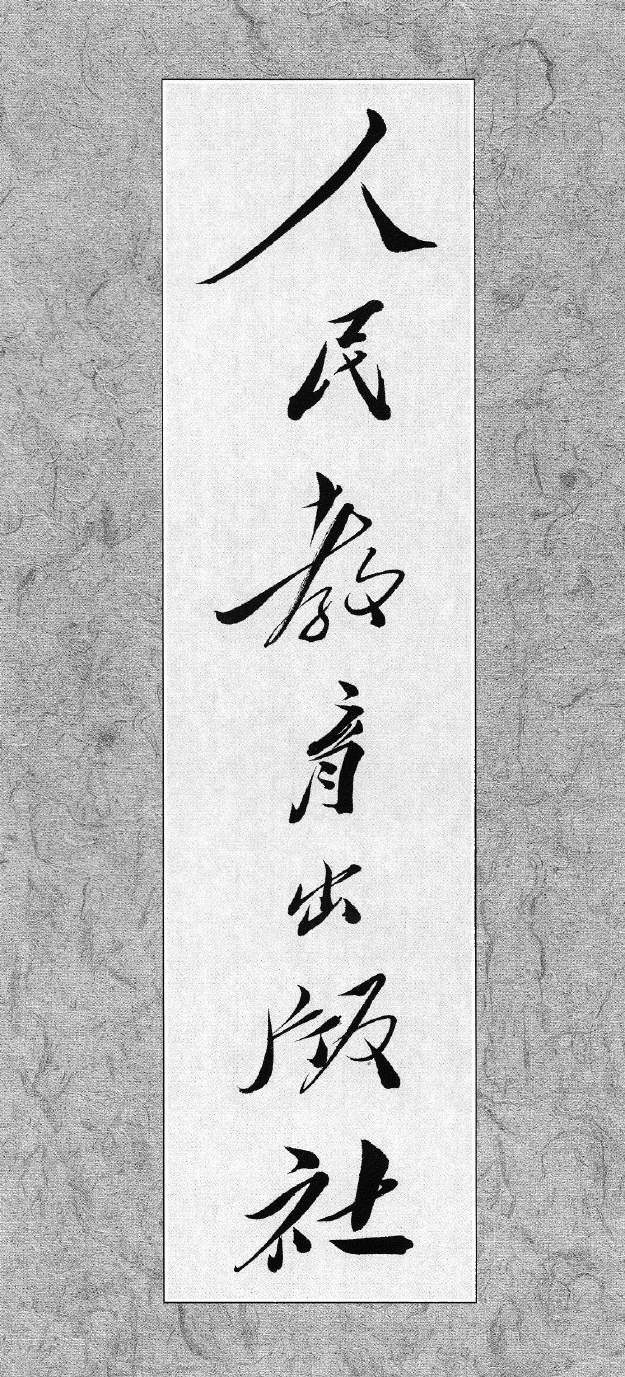
毛泽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的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