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一座藏书百万册的城市度过了此生最难忘的时光之一。也许正因为有如此多的藏书,这座城市决定活在过去。
我还记得在牛津的第一个早上,当时我带齐了所有证件,深深地为自己的研究资助而骄傲,想长驱直入博德利图书馆,花上几个小时畅游一番。可是在门厅就被拦住了,一个工作人员在听到我的一番解释之后,把我带到了旁边一间办公室,似乎我行迹太可疑,动机太不纯,所以最好关起门来处理,免得影响其他参观者和学习者。办公桌的另一边坐着一位光头男子,他询问我时跟我毫无眼神交流。我一一回答,证明我来此地确有正当理由。他让我出示各种证件,很有礼貌,但有点让人害怕,我又一一出示,他将信息输入到庞大的数据库中。漫长的沉默过后,手指还搭在键盘上的他令人瞠目结舌地秒回中世纪,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宣誓时间到。”他递给我一沓塑封卡片,每张卡片上都写着一种语言的誓词。我按要求宣誓:我将遵守各项规定;不偷窃或损坏图书;不纵火,也不帮人纵火,只为带着邪恶的喜悦看着熊熊火焰吞噬馆藏珍宝,将它们化为灰烬。所有预备步骤似乎都符合入境时的扭曲逻辑,就像在去美国的飞机上你会收到那种超现实主义的移民表,问你是否打算刺杀美国总统。
不管怎样,光宣誓还不够,还要通过各种探测器,让他们检查我包里的东西,将包寄存在行李室,才能最终通过入口处的金属十字转门。做各种检查时,我想起中世纪的图书馆要将书拴在书架或书桌上,以防被盗。我想起历史上对窃书贼奇思妙想的诅咒,文字充满黑暗的想象力,莫名地吸引我,也许是因为发明一个到位的诅咒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我应该去编一本合集,从刻在巴塞罗那圣佩德罗·德拉斯·普埃列斯修道院图书馆的威胁性文字开始。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在《阅读史》中引用过这段话:“凡是偷窃书籍,或是有借无还者,他所偷的书将变成毒蛇,将他撕成碎片。让他中风麻痹,四肢坏死。让他痛不欲生,呼天抢地。让他的痛苦永无止境,直到崩溃。让永远不死的蠹虫啃啮他的五脏六腑。直到他接受最后的惩罚,让烈焰赤火煎熬他,永恒不停。”
在《阅读史》中引用过这段话:“凡是偷窃书籍,或是有借无还者,他所偷的书将变成毒蛇,将他撕成碎片。让他中风麻痹,四肢坏死。让他痛不欲生,呼天抢地。让他的痛苦永无止境,直到崩溃。让永远不死的蠹虫啃啮他的五脏六腑。直到他接受最后的惩罚,让烈焰赤火煎熬他,永恒不停。”
那天早上,我拿到了图书证,后来才知道那是牛津大学级别最低的图书证,我可以进图书馆和学院,但只能在指定时间进入指定区域;可以看书和杂志,但只能阅读,不能外借;可以观看学术生活的奢华仪式,但不敢妄想参与其中。很快,我查到刘易斯·卡罗尔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加执教二十六年。于是,我意识到一个天大的误会:《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品,实际上,它惟妙惟肖地描述了我在牛津头几周的经历。那些可以透过锁眼看到的让人心痒难耐的地方,需要喝下神奇药水才能进入。我的脑袋撞到天花板,卧室憋得人透不过气,以至于我特别想把手伸出窗外,把脚伸到烟囱外面。各种隧道、指示牌、古怪的点心、逻辑难以捉摸的对话。热衷于无法预料的仪式的不合时宜的人物。
我还发现在牛津,所有关系——友情、博士研究的合作或抄袭、性关系及其他变体——都是季节性的,随校历的节奏走。我在学期中间来是个错误。这时,学生懵懂摸索的阶段已经过去,基本需求已经得到解决。住在加尔文式的公寓也没能让我更好地融入。公寓的行为规范和城市本身一样很不友好,回寝时间也是修道院式的。我还记得晚上七点集体厨房的凄惨模样,八个冰箱一字排开,其中一个冰箱的一层贴着我的房间号,就像书脊上的签名,甚至蛋格也被平均分成两个一组。所有这些安排都把人框在编了号的区域里,不许越界,不许拿别人的东西吃。你下楼吃晚饭,制造出一点点垃圾,扔到公共垃圾袋里,再回到那个属于你的铺着地毡的窄小房间。
我太需要找人说话了,便开始求人跟我说话。赛克勒图书馆是我的大本营,我先从这儿开始我的第一次语言学尝试。门房看起来很快活,脸红红的——肯定是喝酒喝的,笑呵呵的,可以信任。阿什莫林博物馆的一名女保安怀疑的眼神吸引了我,我也去搭腔了。我向他们打听这座城市有什么秘密,图书馆里有哪些外人不知道的事,各种神秘现象该如何解释。于是,我从这些“哨兵”口中听到了引人入胜的故事。
我问他们,为什么借个书手续惊人地烦琐——图书管理员记下你要什么书,然后跟你约好一两天后,你在某个时间到某个阅览室去取。如果临近周末,等待的时间还会被拉长到三天,甚至四天。我提出疑问:书究竟在哪儿?于是,他们跟我说了地上城与地下城的故事。
他们告诉我,博德利图书馆的管理员每天要收到一千本全新的出版物,必须给它们腾出位置,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又会有一千本书到来。每年图书馆都要增加约十万本新书和二十万本新杂志,也就是说,每年要增加三千多米长的书架。而法律规定连一张纸都不可以扔掉。20世纪初,图书馆大楼被源源不断送来的图书淹没,也是从那时起,图书馆开始建造地下书库和有地下传递带的隧道网。冷战时期,到处都是核武器防空洞,地下迷宫空前繁荣。然而,地下室已不足以承载如此大量的纸质书,市政排水系统也因此受到威胁。于是图书馆又开始将书运到郊外,如附近废弃的矿井和工厂仓库。他们还告诉我:有专门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押送,尽管穿着荧光条制服的他们看上去更像起重机操作工。
因为这番对话——我所感受到的第一丝善意,我开始跟牛津达成和解。一个人散步时,我感觉我听到了脚下图书传送带的回声,它陪伴着我。我想象着书在潮湿的隐秘隧道中,就像童年时《布偶奇遇记》
 中的布偶,或电影《地下》
中的布偶,或电影《地下》
 中的人物。我放松下来,不再那么警惕。牛津的各种古怪都有其客观原因。作为一个笨拙的陌生人,我觉得更舒服,甚至更自由了。而且,带着耐心,我还找到了其他令人难忘的不适之处。
中的人物。我放松下来,不再那么警惕。牛津的各种古怪都有其客观原因。作为一个笨拙的陌生人,我觉得更舒服,甚至更自由了。而且,带着耐心,我还找到了其他令人难忘的不适之处。
晨雾中,走在影影绰绰的街道上,我感觉整座城市都漂浮在书的海洋上,好似一块飞行中的魔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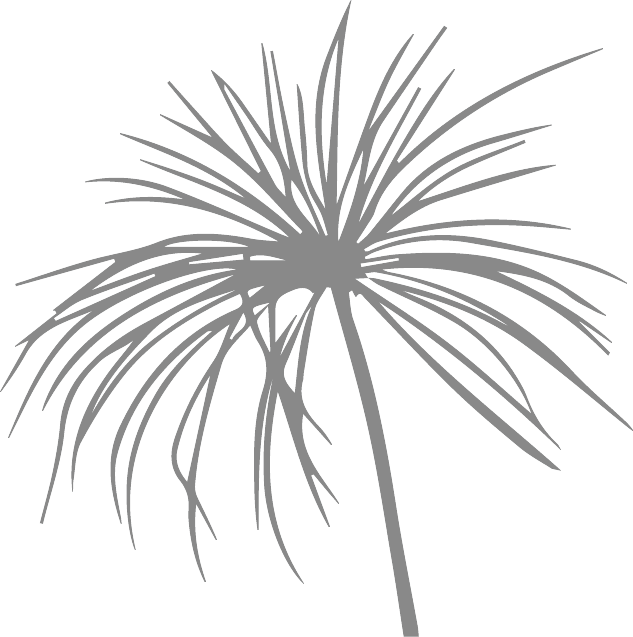
一个单调的雨天早上,墙上沾着水迹,女保安朋友告诉我,她工作的阿什莫林博物馆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家公共博物馆。我兴趣盎然。待在事情肇始之地总是令我很激动,因为那里有过创举。
这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小小颠覆,当时几乎无人察觉。1677年,伊莱亚斯·阿什莫尔
 将个人收藏的古钱币、版画、珍稀的地质样本、异域动物的标本等奇珍异宝赠给了牛津市。从此,它们不再是私人收藏,不再是传给子孙后代、彰显社会地位的家族奢侈品,而属于所有学生和拜访牛津的好奇游客。
将个人收藏的古钱币、版画、珍稀的地质样本、异域动物的标本等奇珍异宝赠给了牛津市。从此,它们不再是私人收藏,不再是传给子孙后代、彰显社会地位的家族奢侈品,而属于所有学生和拜访牛津的好奇游客。
当年的世界十分保守,创新并不受欢迎,往往得打着复兴传统的幌子。因为渴望重现过去的辉煌,阿什莫尔赠给公众的藏品这一没有称呼、没有先例的新鲜事物被冠名为“博物馆”,由此臆想出亚历山大港和牛津之间的对应关系。图书馆已经有了,缺的是博物馆。他们以为在复兴历史,其实创造的是不同的产物,它融合了古代思想和当代志向,后来大获成功。作为展览场所的博物馆概念在欧洲落地生根,它不再是亚历山大港那种学者的聚居地。
1759年,大英博物馆在伦敦开幕。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没收了王宫卢浮宫,包括宫内的所有艺术品,将其改为博物馆,成为新的激进主义的象征。革命者们希望废除历史是单一社会阶级的财产这一想法,过去的物品不应只供贵族把玩。法国大革命将历史从贵族的手中夺了回来。19世纪末,去博物馆欣赏古代用品、古代大师的画作、手稿和初版书成为欧洲人的时尚消遣方式,而远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也对此进行了效仿。1870年,一群企业家创建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则是第一家现代艺术私人博物馆。一位名叫所罗门·R.古根海姆
 的矿业家及其后代效法前人,目前正经营着庞大的跨旅游业、商业乃至房地产业的古根海姆世界连锁博物馆。基于伊莱亚斯·阿什莫尔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亚历山大港的文化遗产织出了一张覆盖全球的巨网。博物馆已被誉为“21世纪的大教堂”。
的矿业家及其后代效法前人,目前正经营着庞大的跨旅游业、商业乃至房地产业的古根海姆世界连锁博物馆。基于伊莱亚斯·阿什莫尔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亚历山大港的文化遗产织出了一张覆盖全球的巨网。博物馆已被誉为“21世纪的大教堂”。
这里隐藏着有趣的悖论:让所有人都能热爱过去,这本身具有深刻的革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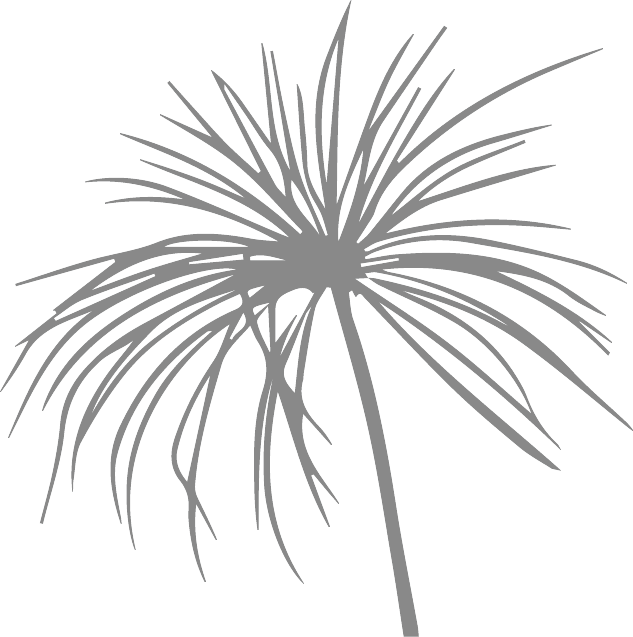
近东——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小亚细亚和波斯——已知最古老的图书馆也对窃书贼和毁书人进行了诅咒。
“将泥板据为己有的人,无论是偷的,还是抢的,或指使奴隶偷的,让沙玛什
 挖掉他的眼睛,让纳布和尼萨巴把他变成聋子,让纳布将他的身体溶在水里!”
挖掉他的眼睛,让纳布和尼萨巴把他变成聋子,让纳布将他的身体溶在水里!”
“摔坏泥板的人,将泥板泡在水里的人,或将泥板上的文字抹掉,使其无法辨识的人,让天上和地上的男神和女神诅咒他,狠狠地、无情地诅咒他,只要他活着,咒语就无法破解,让他的名字和种子从地球上永远消失,让他的肉被狗吃掉。”
读完这些咬牙切齿的威胁,我们可以猜到遥远的藏书对主人是何等重要。当时还没有图书贸易,想要书,要么自己抄(因此你需要一个职业抄写员),要么作为战利品从别人那儿抢来(因此你需要在危险的战役中打败敌人)。
我们这里所说的书,其实是书的远祖,发明于五千年前,其实是用黏土做成的泥板。美索不达米亚河岸没有纸莎草,石头、木头或皮革等其他材料也很稀少,但那里黏土应有尽有。因此,苏美尔人在脚下的黏土上写字。他们将黏土制成约二十厘米长的四方形泥板,跟我们的七英寸平板电脑差不多大,表面平整,可以用来书写。他们基于在软泥板上压出凹槽发展出一种书写风格。水会抹去泥板上的文字,但焚书无数的火却会使泥板像进了陶窑似的,变得更持久耐用。考古学家们发现的大部分泥板,恰恰是因为火灾才得以保存下来。书籍里藏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幸存故事。在极少数情况下——美索不达米亚和迈锡尼的火灾、埃及的垃圾场、维苏威火山爆发——是破坏力拯救了它们。
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很寒碜,书库很小,书架靠墙,上面是一排排的泥板,一块挨着一块,立在架子上。其实,近东古代史专家更愿意称其为“档案”。泥板上保留了发票、交货单、收据、清单、结婚文件、离婚协议、法庭记录和法律条文,文学作品很少,基本上只有诗歌和圣歌。在今天的土耳其,赫梯王国首都哈图沙王宫的发掘现场,人们找到的好几块泥板属于一种奇怪的类型:对抗性无能的祈祷文。
在哈图沙图书馆——以及更早一些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尼普尔——已经出现了记载藏书总目的泥板。那时候还不时兴给书起名,作品只好用首句或概述进行区分。为了防止内容很长的文本四处散落,人们要在泥板上标数字,有时还会标上作者名和其他辅助信息。书目的存在向我们表明,早在公元前13世纪,图书馆的藏书就开始不断增加,读者不可能将放置在书架上的泥板一眼扫到底。此外,这也是理论上的重大进步:对藏书有整体意识,既是成就,也是抱负。书目不只是简单的图书馆附录,更是图书馆的思想理念、内在联系,是它的巅峰。
近东的图书馆向来不是公共图书馆,它要么属于培养抄写员的精英学校——他们需要模板供学习使用,要么是国王御用。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是托勒密之前最伟大的藏书家。他说的话被记录在了泥板上:建尼尼微图书馆,供“朕阅读及思考用”。亚述巴尼拔会写字,这在当时的君主中很不常见,他常以此自夸:“历代先王们,无人会写字。”在他的图书馆里,考古学家们发掘出约三万块泥板,只有五千块是文学作品。近东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往往跟其他泥板混在一起,既有文件档案,也有跟预兆、宗教、魔法相关的文字。
作为距亚历山大图书馆最近的前辈,骄傲的亚述巴尼拔国王的图书馆不具有世界性,收藏其中的是一系列用于典礼和仪式的实用型文本和文件。就连收藏文学作品也是出于实用目的——国王需要了解作为民族根基的神话。近东的所有图书馆,无一例外,均不复存在,被湮没在遗忘之中。那些伟大帝国的文字被深埋于被摧毁的城市旁边的沙漠里,残篇即便重见天日也无法被破解。遗忘是如此彻底:当游客们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城市遗址上看到楔形文字时,许多人以为这只是门框、窗框上的装饰。沉寂了许多个世纪之后,还是研究者们凭借一腔热情挖掘遗迹,终于破解出了泥板上被遗忘的文字。
而雅典、亚历山大港和古罗马的书籍从未完全沉寂过。许多个世纪以来,它们始终在窸窸窣窣地与人交谈,既讲述神话和传说,也谈论哲学、科学和法律。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也在以某种方式参与到谈话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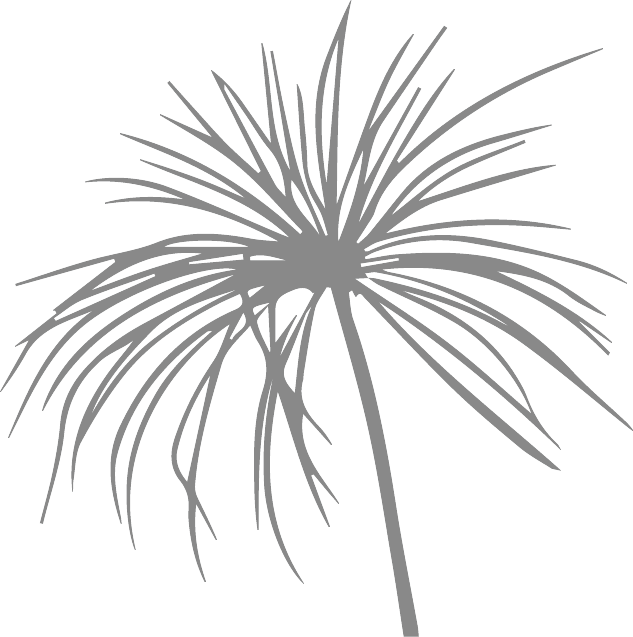
亚历山大图书馆还有些前辈在古埃及,只是在全家福上它们的模样看起来最为模糊。法老时代就有私人藏书馆和神庙图书馆了,但相关记载都含糊不清。史料中提到了档案库(存放行政管理文件)和传统书库(存放传统古籍,抄写、解释、保护圣书的地方)。关于古埃及图书馆更确切的细节是由一位古希腊旅行者提供的。他的名字叫阿布德拉的赫卡提乌斯,在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参观过底比斯的阿蒙神庙,还有人为其讲解。他在迷宫般的大厅、庭院、走廊和房间里转了一圈,认为这是具有异国情调的经历。他在一道回廊上看见了神圣的图书馆,将它描述为“呵护灵魂的地方”。除了将图书馆视为灵魂诊所这一理念很美之外,我们对古埃及藏书几乎一无所知。
和楔形文字一样,象形文字也被遗忘了一千多年。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走过漫长岁月的象形文字会变成一堆完全无法理解的符号?在古埃及,只有很少的人会读书写字(抄写员会,他们是国王和王室成员之下最有权势的群体)。想当抄写员,你需要掌握成百上千种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需要掌握成千上万种符号。学习的过程很漫长,还要去专门的学校,只有富家子弟才负担得起,类似于我们现在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的MBA班。王国会在培养出来的抄写员中遴选出高级公务员和祭司。之后,他们会参与法老们的王位争夺战,趁机贯彻自己的想法,从中渔利。我不禁想引用一段非常久远的古埃及人的文章,但它的内容在今天读来却莫名地亲近。文章说,一位名叫杜阿-赫蒂的富豪花大价钱让儿子佩皮去念培养抄写员的学校,儿子却不好好念书。于是,他对儿子说了这番一听就是老父亲会说的话:“你要好好念书。我见过铁匠干活,手指就像鳄鱼爪子。理发师给人理发,要一直忙到天黑,还要走街串巷,招揽顾客……砍甘蔗的人要去三角洲,砍得胳膊都抬不起来,被蚊子叮得满身包,恨不得被苍蝇吃了……你瞧,干什么工作都会有人管,除了做抄写员。抄写员自己管自己。你要是学会读书写字,会过得比刚才提到的做这些职业的人都好。你要跟人上人在一起。”
不知道佩皮会不会把老父亲的唠叨听进去,会不会一边抱怨,一边学习,向古埃及社会精英阶层迈进。如果会,他需要苦读若干年,练习写字,还会挨打——老师们恶名在外,个个都很凶,最后总算能显摆抄写员那套帅气的行头:不同粗细的笔、带沟槽的调色板、颜料包、混合颜料用的龟甲,还有作为结实垫板的名贵木板,用来垫在莎草纸下方。那时候人们不习惯用桌子,写字都是盘腿坐,垫着写。
我们知道的是古埃及最后一代抄写员的经历,他们见证了埃及文明的衰落。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
 颁布敕令,宣布基督教成为唯一国教,强制民众信奉,并禁止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信奉其他宗教。古代神祇的庙宇全部被关闭,除了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菲莱岛上的艾希斯神庙。一群祭司逃到那里,他们掌握着复杂的书写奥秘。但皇帝已经明令禁止他们再传播知识。他们中的一个名叫内斯密特-阿霍姆(Eesmet-Akhom)的人在神庙墙上刻下了最后一篇文章。这是最后一篇象形文字的文章,以“永远”这个词结尾。若干年后,查士丁尼一世
颁布敕令,宣布基督教成为唯一国教,强制民众信奉,并禁止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信奉其他宗教。古代神祇的庙宇全部被关闭,除了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菲莱岛上的艾希斯神庙。一群祭司逃到那里,他们掌握着复杂的书写奥秘。但皇帝已经明令禁止他们再传播知识。他们中的一个名叫内斯密特-阿霍姆(Eesmet-Akhom)的人在神庙墙上刻下了最后一篇文章。这是最后一篇象形文字的文章,以“永远”这个词结尾。若干年后,查士丁尼一世
 诉诸武力,关闭了祭司们负隅抵抗的艾希斯神庙,反叛者们集体沦为阶下囚。古埃及埋葬了几千年来与之共存的古老神祇,连同崇拜物和语言。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象形文字就彻底消失了。后来又花了十四个世纪,人们才重新找到破解象形文字的密码。
诉诸武力,关闭了祭司们负隅抵抗的艾希斯神庙,反叛者们集体沦为阶下囚。古埃及埋葬了几千年来与之共存的古老神祇,连同崇拜物和语言。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象形文字就彻底消失了。后来又花了十四个世纪,人们才重新找到破解象形文字的密码。
19世纪初,围绕破解埃及象形文字展开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竞赛。欧洲最优秀的东方学者们接受挑战,找寻失落的文字。他们互相盯着,唯恐被人占了先机。几十年里,科学界充满了兴奋、悬念、嫉妒和对荣誉的渴望。发令枪是1799年7月在距亚历山大港四十八公里处打响的。前一年,梦想着追随亚历山大脚步的拿破仑率军抵达埃及。他们本想扰乱对手英军,结果饱受沙漠炙烤。远征失败了,但它却让欧洲人爱上了法老时代的古董。在拉希德港(法国人叫它罗塞塔)附近建军事要塞时,一名士兵发现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奇怪的文字。深色的石碑很重,陷在泥里,铁锹撞上它时,这名士兵一定叽里咕噜地骂了几句,却不知道他正要发掘出一件不同寻常的古董。不久,它将以罗塞塔石碑之名举世闻名。
这块值得纪念的石头是古埃及的一块残碑,托勒密五世命人将祭司诏书用三种语言——象形文字、埃及草书
 (古埃及文字发展的最后阶段)和希腊语——刻在上面,有点像今天自治大区法律出台时,也要用另外三种官方语言
(古埃及文字发展的最后阶段)和希腊语——刻在上面,有点像今天自治大区法律出台时,也要用另外三种官方语言
 同时发布。在罗塞塔工作的工程师团队的一位上尉意识到这块残碑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命人将这块七百六十公斤重的石碑运到开罗的埃及研究所。研究所刚刚成立,会聚了与法国远征军同行的学者和考古学家。后来,他们做了拓片,分发给想接受识字挑战的学者。再后来,英军上将纳尔逊将拿破仑的军队逐出埃及,抢走了罗塞塔石碑——尽管法国人恨得牙痒痒的——运回大英博物馆,成为今天最受欢迎的展品。
同时发布。在罗塞塔工作的工程师团队的一位上尉意识到这块残碑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命人将这块七百六十公斤重的石碑运到开罗的埃及研究所。研究所刚刚成立,会聚了与法国远征军同行的学者和考古学家。后来,他们做了拓片,分发给想接受识字挑战的学者。再后来,英军上将纳尔逊将拿破仑的军队逐出埃及,抢走了罗塞塔石碑——尽管法国人恨得牙痒痒的——运回大英博物馆,成为今天最受欢迎的展品。
那是1802年,那一年,智力竞赛开始了。
试图破解未知语言的人们一头扎进这一堆乱七八糟的单词里,追着它们的影子走。如果没有任何抓手帮助理解,如果连神秘的句子在说什么事情都不知道,那么这个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可如果这篇神秘的文字有已知语言的译本,研究者就不会完全找不着北,毕竟地图已经在手,往未开拓的区域走便是。因此,语言学家们迅速推断出,罗塞塔石碑上的希腊语片段将会打开古埃及失落语言的大门。破译的过程激发出新一轮的密码学研究热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促使埃德加·爱伦·坡写出了短篇小说《金甲虫》
 ,柯南·道尔写出《跳舞的小人》
,柯南·道尔写出《跳舞的小人》
 。
。
19世纪初,语言学家们被残缺的碑文弄得晕头转向,迟迟未能解开古埃及之谜。象形文字部分少了开头,希腊语部分少了结尾,他们几乎无法在原文和译文中建立明确的对应关系。然而,19世纪20年代前后,拼图开始一点点地完成,马其顿国王的名字成为关键。在象形文字部分,有些符号被刻在椭圆里(考古学家们称之为“椭圆框”)。他们迈出的第一步是假设椭圆里的文字是法老的名字。英国人托马斯·杨
 破解出了“托勒密”的名字,法国人尚-弗朗索瓦·商博良
破解出了“托勒密”的名字,法国人尚-弗朗索瓦·商博良
 随后破解出了“克里奥帕特拉”的名字。有了被破解的第一批发音,掌握多种语言的商博良发现谜一般的埃及文字和自己掌握的科普特语有相似之处。从这一直觉出发,他执着地研究多年,比较碑文,努力破译,编纂了一本埃及象形文字词典和一本语法书。但没过多久,四十一岁的他英年早逝。几十年挨冻受穷,长日辛苦的研究摧毁了他的健康。
随后破解出了“克里奥帕特拉”的名字。有了被破解的第一批发音,掌握多种语言的商博良发现谜一般的埃及文字和自己掌握的科普特语有相似之处。从这一直觉出发,他执着地研究多年,比较碑文,努力破译,编纂了一本埃及象形文字词典和一本语法书。但没过多久,四十一岁的他英年早逝。几十年挨冻受穷,长日辛苦的研究摧毁了他的健康。
托勒密的名字就是打开锁的那把钥匙。在缄默了许多个世纪后,埃及莎草纸和石碑重新开口说话了。
今天,有个名叫罗塞塔项目的倡议,致力于保护人类的各种语言免遭灭绝。项目总部位于旧金山,负责该项目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计算机专家设计出了一种镍盘,将同一篇文章的一千种语言的译本微雕在了镍盘上。即便记得某种语言的最后一个人去世,平行译本也会帮助我们找回它的音和义。镍盘是另一种全球性的便携式罗塞塔石碑,用来抵御不可逆转的对语言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