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人年轻的妻子百无聊赖,正孤枕独眠。十个月前,商人从地中海的科斯岛出发,前往埃及,此后便杳无音信。而他的妻子年方十七,尚未生育,独守空房,寂寞难耐,渴望生活中有新鲜事发生,但她又不能擅自离家,免得被人说闲话。她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可做,只能靠折磨女奴取乐。刚开始她还觉得有点意思,但这很难填补漫长的时间。所以,她喜欢有其他女人来家里做客,敲门的人是谁根本无所谓。毕竟时间如铅块,重重地压在身上,让人绝望地想找人把它打发掉。
女奴前来通报,希利德婆婆来了。她好歹能开心一会儿了——希利德婆婆是她的奶妈,说话口无遮拦,下流话说得眉飞色舞,让人忍俊不禁。
“希利德妈妈!你有好几个月没来我家了。”
“你知道的,孩子,我住得远,而且力气已经比蚂蚁还小了。”
“好吧,好吧,”商人的妻子说,“你还有力气好好搂抱不止一个男人呢!”
“你就笑话我吧!”希利德回答,“这种事是留给你们这些姑娘家做的。”
希利德婆婆坏笑着,狡猾地扯了几句闲话,总算道出她上门的真正目的。那个又帅又壮,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两次夺得摔跤奖牌的小伙子看上了商人的妻子,想她想得发疯,想成为她的情人。
“你别生气,听听我的建议。他正心痒痒得很,你就跟他耍一耍嘛!难不成就待在这儿独守空房?”希利德诱她上钩,“等你明白过来,都人老珠黄了,好好的一朵鲜花都枯萎了。”
“别说了,别说了……”
“你丈夫在埃及干吗呢?他也不给你写信,肯定是去偷腥,把你给忘了。”
为了攻破姑娘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她绘声绘色地列举了埃及,特别是亚历山大港能给离家的负心汉提供的一切:数不清的财富、令人愉悦的温暖气候、体育馆、各种演出、一大群哲学家、书、金子、葡萄酒,还有如星光闪耀的迷人女子。
这是公元前3世纪一个古希腊短剧的开头,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我大致翻译了一下。这种小品肯定不会上演,只能当剧本读,文字幽默,有时带点流浪汉小说的味道,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禁忌世界的窗户。在那里,有挨打的奴隶、残忍的主人、皮条客、被青春期的孩子逼到绝望边缘的母亲,还有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女人。希利德是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拉皮条的女人之一,她们从事淫媒,深谙行业机密,毫不犹豫地拿目标人物的软肋开刀——全世界的女人都怕变老。然而,生性狡猾的她这回栽了跟头。对话以女子的嗔怪结束,她要为出门在外的丈夫守贞;也许是因为偷情的风险太大,她不乐意。你脑子坏掉了?她质问希利德。不过,她也给奶妈倒了杯酒,以示安慰。
除了幽默和新鲜的腔调,这个剧本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它为我们揭示了普通人眼中当年亚历山大港的模样——它是享乐之城与书之城,性之都与文字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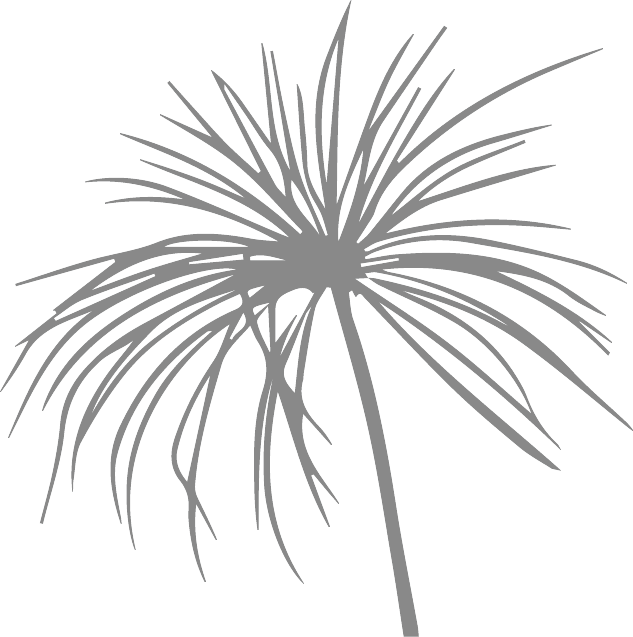
亚历山大港的传说远没有结束。希利德引诱商人妻子的这段对话发生两百年后,这里上演了一出伟大的旷世恋情,一段发生在克里奥帕特拉
 与马克·安东尼
与马克·安东尼
 之间的爱情故事。
之间的爱情故事。
当年的罗马虽然是最伟大的地中海帝国的中心,但它黑乎乎的街道依然如迷宫般弯弯曲曲的,路面泥泞不堪。当马克·安东尼乘船第一次抵达亚历山大港时,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让人心醉神迷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宫殿、神庙、宽阔的街道与纪念碑散发着伟大的光芒。罗马人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充满信心,自诩未来的主人,却没能抵挡住昔日辉煌、没落奢华的诱惑。在激情、骄傲与谋算之下,有权有势的将军和埃及的末代女王情投意合,在政事和床笫之间结盟,这让传统的罗马人大感羞耻。更有甚者,还有传言说马克·安东尼想把帝国的都城从罗马迁到亚历山大港。要是当年这对情侣打赢了控制罗马帝国之战,那么今天,游客们要想在永恒之城
 中与斗兽场和诸多广场合影留念,恐怕要组团去埃及了。
中与斗兽场和诸多广场合影留念,恐怕要组团去埃及了。
克里奥帕特拉跟她的城市亚历山大港一样,集文化和性感于一身。普鲁塔克
 说,她其实并非国色天香,路过的人并不会为她驻足。但她聪明,口才好,魅力十足,嗓音甜美,让人听得身上酥酥痒痒的。普鲁塔克还说,她说话时还会根据她说的语言来调整音调,宛如一件有很多根弦的乐器。她可以不用翻译就跟埃塞俄比亚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米提亚人和安息人自由交谈。她聪明机智,消息灵通,在国内外的多次权力争夺战中胜出,尽管她在决定性战役中落败了。问题是,人们都是从敌方角度去谈论她的。
说,她其实并非国色天香,路过的人并不会为她驻足。但她聪明,口才好,魅力十足,嗓音甜美,让人听得身上酥酥痒痒的。普鲁塔克还说,她说话时还会根据她说的语言来调整音调,宛如一件有很多根弦的乐器。她可以不用翻译就跟埃塞俄比亚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米提亚人和安息人自由交谈。她聪明机智,消息灵通,在国内外的多次权力争夺战中胜出,尽管她在决定性战役中落败了。问题是,人们都是从敌方角度去谈论她的。
在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中,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马克·安东尼以为自己即将统治全世界时,他想要送一件伟大的礼物给克里奥帕特拉,给她一个惊喜。他知道情人日日挥霍无度,黄金、珠宝、美味佳肴根本入不了她的眼。有一次他们饮酒至天明,她以一种挑衅的炫耀之姿,将一颗硕大无比的珍珠用醋溶解,一口饮下。于是,马克·安东尼挑选了一件让她无法不屑一顾的礼物:他将二十万卷书堆在她的脚下,赠给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亚历山大港,激情可以用书点燃。
两位于20世纪故去的作家成为这座城市隐秘角落的向导,使亚历山大港的神话越发古色古香。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
 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公务员,希腊人,在英国政府驻埃及公共事业部农田灌溉处工作,从未受到过提拔。晚上,他将自己沉浸在欢愉之中,混迹于风月场所,周遭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堕落灵魂。他对全城的妓院了如指掌,那里是他唯一的避难所,因为他是个同性恋,“谁都不认可,谁都强烈鄙视”——他这般写道。卡瓦菲斯遍读经典作家的作品,而他的诗人身份几乎无人知晓。
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公务员,希腊人,在英国政府驻埃及公共事业部农田灌溉处工作,从未受到过提拔。晚上,他将自己沉浸在欢愉之中,混迹于风月场所,周遭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堕落灵魂。他对全城的妓院了如指掌,那里是他唯一的避难所,因为他是个同性恋,“谁都不认可,谁都强烈鄙视”——他这般写道。卡瓦菲斯遍读经典作家的作品,而他的诗人身份几乎无人知晓。
今天,在他最广为人知的诗歌作品里,伊萨卡、特洛伊、雅典、拜占庭那些真实和虚构的人物一一登场。其他看起来更个人的诗歌作品,主要挖掘自他的成长经历——怀念青春岁月,初尝人间享乐,感慨时间流逝,言辞间带着讽刺与心碎。主题上的差别其实只是表象。阅读和想象中的过去跟自身成长记忆一样,让他激动不已。在亚历山大港闲逛时,他看见逝去城市的脉搏依然在现实的城市中跳动。亚历山大图书馆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回声、呢喃与窃窃私语,仍然回荡在空气中。对他而言,如今活着的人们痛苦、孤独逡巡其间的冰冷街道,正是因为有了那群了不起的幽灵才有了生气。
《亚历山大四重奏》
 中的人物——贾斯汀、达利,尤其是自称认识卡瓦菲斯的巴萨泽——都时常想起“这座城市的老诗人”。劳伦斯·达雷尔
中的人物——贾斯汀、达利,尤其是自称认识卡瓦菲斯的巴萨泽——都时常想起“这座城市的老诗人”。劳伦斯·达雷尔
 是一个被国内的清教主义及其氛围憋得透不过气来的英国人,他用四部小说进一步弘扬亚历山大港神话中性与文学之都的美誉。劳伦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时期来到亚历山大港。当时,埃及被英军占领,是间谍活动和阴谋活动的老巢,也是一如既往的享乐之城。亚历山大港的各种色彩和它们所唤醒的各种感官反应,谁都没有他描写得那么真切。夏季天很高;静得出奇;烈日炙烤;蓝色明亮的大海、防波堤和黄色的海岸;城里的马留提斯湖,有时如海市蜃楼般模糊不清;港口的海水与湖水间,有数不清的聚集着灰尘、乞丐和苍蝇的街道;棕榈树、豪华饭店、大麻和醉酒;充满电荷的干燥空气;柠檬黄和深紫色的黄昏;五个种族、五种语言、十几种宗教;五支舰队在油油的海水中的倒影。达雷尔写道:在亚历山大港,肉体醒了,感受到铁窗的禁锢。
是一个被国内的清教主义及其氛围憋得透不过气来的英国人,他用四部小说进一步弘扬亚历山大港神话中性与文学之都的美誉。劳伦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时期来到亚历山大港。当时,埃及被英军占领,是间谍活动和阴谋活动的老巢,也是一如既往的享乐之城。亚历山大港的各种色彩和它们所唤醒的各种感官反应,谁都没有他描写得那么真切。夏季天很高;静得出奇;烈日炙烤;蓝色明亮的大海、防波堤和黄色的海岸;城里的马留提斯湖,有时如海市蜃楼般模糊不清;港口的海水与湖水间,有数不清的聚集着灰尘、乞丐和苍蝇的街道;棕榈树、豪华饭店、大麻和醉酒;充满电荷的干燥空气;柠檬黄和深紫色的黄昏;五个种族、五种语言、十几种宗教;五支舰队在油油的海水中的倒影。达雷尔写道:在亚历山大港,肉体醒了,感受到铁窗的禁锢。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这座城市。在《亚历山大四重奏》的最后一部小说里,克莉描绘了一幅凄凉的场景:被扔在沙滩上的坦克像恐龙的骨架,大炮像石化森林中倒下的树,贝都因人在地雷阵中迷失了方向。她总结道:这座向来任性的城市如今好比巨大的公共便盆。1952年之后,劳伦斯·达雷尔再也没有回到过亚历山大港。苏伊士运河战争标志着中东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此居住了几千年的犹太人和希腊人于战后逃走。从那里回来的游客告诉我:世界的感官之都已经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