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群神秘的人策马走在古希腊的道路上,农民们在田间地头或自家门前怀疑地打量着他们。经验告诉他们,只有危险人物才会外出旅行,比如士兵、雇佣兵和奴隶贩子。农民们皱着眉,嘴里嘟囔着,目送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他们不喜欢拿着武器的外乡人。
骑手们继续骑行,没有留意这些乡下人。几个月来,他们爬上高山,越过沟壑,行过山谷,蹚过河流,从一个岛航行到另一个岛。自从接到这个奇怪的任务,他们的肌肉变得更结实,耐力也增强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必须冒险在一个战火不断的世界穿过各种危险地带。他们是一群猎手,在寻找一种非常特别的猎物,它们安静、狡猾,不会留下半点痕迹或足印。
如果这些令人不安的密使能坐在码头酒肆,喝着红酒,吃着烤章鱼,跟陌生人聊天醉饮——出于谨慎,他们从不这么做——他们大可以讲述了不起的旅行经历。他们曾踏足饱受瘟疫之苦的土地,穿越满目疮痍的焦土,见识过滚烫的余烬、战时叛军和雇佣兵的暴行。由于那时候广阔的地域都没有地图,他们迷过路,几天几夜都漫无目的地在烈日下或风暴中疾走。他们不得不饮下恶臭的水,喝完腹泻不止。每当下雨,骡子和大车就会陷入泥沼,他们一边怒吼一边骂骂咧咧地拉车,直到双膝跪地,啃了一嘴泥。当夜幕降临,又没有任何栖身之处时,他们只能裹着斗篷防蝎子。他们被虱子咬得发疯,被四处出没的强盗吓得心惊肉跳。很多次,他们骑马走在广阔的荒凉地带,一想到一群强盗正屏住呼吸潜伏在某个路口,打算一跃而上,冷血地结果他们的性命,劫掠他们的财物,再将尚有余温的尸身遗弃在那些灌木丛中,便觉得血液都要凝结。
他们当然会感到害怕。埃及国王在让他们跨海去执行任务之前,将巨资托付给了他们。那时候,亚历山大大帝
 刚驾崩几十年,携巨款出门极其危险,无异于自杀。尽管窃贼、各种传染病、海难都会让这一昂贵的使命血本无归,法老依然坚持从尼罗河畔的埃及派人跨越国界,远去四面八方。占有的欲望令他辗转反侧,他狂热地、迫不及待地渴望他的秘密猎手们替他将猎物收入囊中,不管要面对怎样未知的危险。
刚驾崩几十年,携巨款出门极其危险,无异于自杀。尽管窃贼、各种传染病、海难都会让这一昂贵的使命血本无归,法老依然坚持从尼罗河畔的埃及派人跨越国界,远去四面八方。占有的欲望令他辗转反侧,他狂热地、迫不及待地渴望他的秘密猎手们替他将猎物收入囊中,不管要面对怎样未知的危险。
坐在自家门前窃窃私语的农民、雇佣兵和强盗要是知道这些异国骑手在寻找什么,一定会惊讶得目瞪口呆,感觉不可思议。
书。他们找的是书。
这是埃及王室的最高机密。上下埃及
 的统治者,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愿意豁出性命(当然是别人的性命,国王们向来如此),去为亚历山大图书馆找到世界上所有的书。法老所追寻的梦想是建立一座尽善尽美的图书馆,收藏有史以来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
的统治者,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愿意豁出性命(当然是别人的性命,国王们向来如此),去为亚历山大图书馆找到世界上所有的书。法老所追寻的梦想是建立一座尽善尽美的图书馆,收藏有史以来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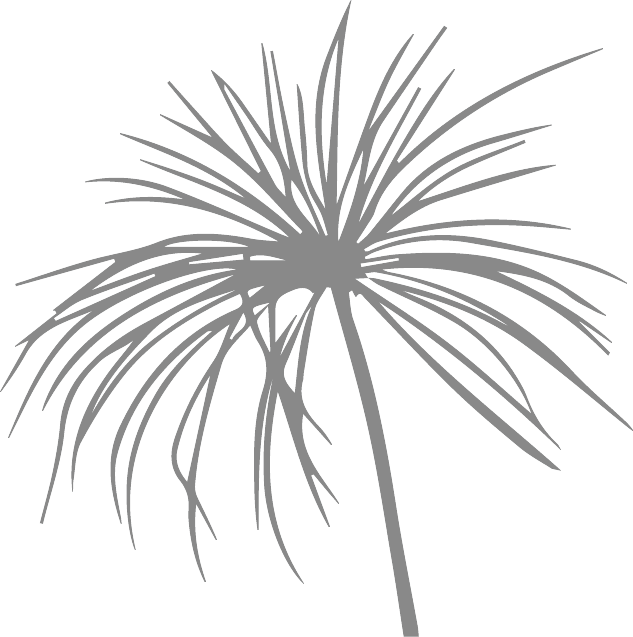
我总是害怕提笔写下一本新书的开头,害怕迈出这一步。当我已经跑遍所有的图书馆,在本子上记满兴奋的笔记,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甚至愚蠢的借口不动笔时,我还会拖延几日,也由此彻底明白自己是个胆小鬼。我就是感觉力有不逮。作品的基调、幽默感、诗句、节奏,还有前景,全都有了。待写的章节在事先拟好的文字中隐约可见。可是,该怎么写呢?眼下,我还有一大堆疑问。每写一本书,我都要回到起点,像所有第一次一样心脏怦怦直跳。玛格丽特·杜拉斯说,写作就是试图发现如果我们开始书写,我们会写出什么——从动词原形到条件式,再到虚拟式——如同感受到大地正在脚下裂开。
说到底,写作跟那些我们没学会就开始做的事没什么两样,比如说外语、开车、当妈妈、活着。
在被疑虑折磨得奄奄一息后,在拖了又拖,不能再拖,借口找了又找,不能再找之后,终于,在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开始面对一张孤独的白纸。我已经决定要以神秘的猎书人作为开卷画面。我感觉自己和他们一样。我喜欢他们的耐心与坚韧,他们投入的时间,以及这趟寻书之旅的漫长且刺激。多年来,我做研究,查出处,收集文献,试图理解史料。当真相揭晓时,那些经抽丝剥茧找到的确凿历史实在太令我震惊,以至于它们变成故事,不请自来地进入我的梦境。我想要化身猎书人,奔波在古欧洲危险动荡的道路上。如果以他们的寻书之旅开始这本书,是否可行?未尝不可。但我要如何在想象力的血肉中保住史料的骨架?
这个开头似乎和寻找所罗门国王的宝藏或遗失的约柜
 的故事一样神奇,但史料表明,妄自尊大的埃及国王的脑袋里确实动过这个念头。也许在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是唯一也是最后一次,将世界上所有的书尽数收入世界图书馆这一梦想有可能成真。今天,我们会觉得这是博尔赫斯那些古怪抽象、引人入胜的短篇小说中的情节,又或者是他天马行空的幻想。
的故事一样神奇,但史料表明,妄自尊大的埃及国王的脑袋里确实动过这个念头。也许在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是唯一也是最后一次,将世界上所有的书尽数收入世界图书馆这一梦想有可能成真。今天,我们会觉得这是博尔赫斯那些古怪抽象、引人入胜的短篇小说中的情节,又或者是他天马行空的幻想。
在建设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际图书贸易。书可以在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里买到,但在年轻的亚历山大港是买不到的。据史料记载,国王们凭借自己高高在上的权势,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去网罗书籍——买不到就没收;如果需要砍下百姓的头、毁掉他们的庄稼才能得到一本垂涎已久的书,那国王就会如此下令,并号称国家的荣耀远比这些琐碎的顾虑更为重要。
为了达到目的,坑蒙拐骗自然也是在所不惜。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在戏剧节上首次演出后被收藏在雅典档案馆中,而托勒密三世对这些官方版本觊觎已久。于是,法老的使者们前去借阅这些珍贵的莎草纸书卷,以便交给抄写员一字不差地誊写一份。雅典当局狮子大开口,索要十五塔兰特
 银的押金,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金。埃及人照付不误,鞠躬行礼,千恩万谢,许下庄重的誓言——十二次月圆月缺前定将原物奉还,并立下重咒,若损毁书籍便不得好死。然后呢?他们当然是舍了押金,直接将手卷据为己有。雅典官员们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伯里克利
银的押金,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金。埃及人照付不误,鞠躬行礼,千恩万谢,许下庄重的誓言——十二次月圆月缺前定将原物奉还,并立下重咒,若损毁书籍便不得好死。然后呢?他们当然是舍了押金,直接将手卷据为己有。雅典官员们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伯里克利
 时代名震一时的都城雅典已变成王国的外省城邦,无法与埃及相抗衡。埃及控制了粮食贸易,而当年的粮食相当于今天的石油。
时代名震一时的都城雅典已变成王国的外省城邦,无法与埃及相抗衡。埃及控制了粮食贸易,而当年的粮食相当于今天的石油。
亚历山大港是王国的主要港口与新兴发展中心。古往今来,达到如此规模的经济大国总会为所欲为。任何船只,不管从哪里来,只要停靠于此,就要立刻接受盘查。海关官员则会查封他们在船上找到的所有书,命人用新的莎草纸一一誊抄,然后留下原本,归还抄本。这些在登船时抢来的书最终会被放置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书架上,并加上一个小小的标识——“船上图书”,以注明来源。
当一个人位居世界之巅时,对他人提出任何要求都不为过。据说托勒密二世曾派使者前往各个国家,给君主或统治者送去封着火漆的信,让他们送来所有藏书——王国境内诗人和散文家写的书、演说家和哲学家写的书、医生和占卜者写的书、历史学家写的书和其他所有书。
此外,正如开篇画面所描绘的那样,国王们遣秘密猎手携重金,走过世界上那些危险四伏的陆路与海路,购买所到之处能找到的所有书,越多越好,还要最古老的抄本。这么大的胃口,如此高的价钱,自然也招来了心术不正与弄虚作假之徒。他们提供珍本的赝品,将莎草纸做旧,把很多本书拼凑成一本以增加篇幅,总之想出了各种巧妙的手段。有个聪明人很有幽默感,他特意写了一些看起来不得了的书,来满足托勒密王朝历代国王们对书的占有欲。这些伪作的书名都很有趣,拿到今天也会很畅销,比如《修昔底德
 未尽之言》。你可以将修昔底德换成卡夫卡或乔伊斯,想象一下造假者打着这些人的名号写回忆录和无法言说的秘密,并带着这些假书出现在图书馆时,会引发多大的期待。
未尽之言》。你可以将修昔底德换成卡夫卡或乔伊斯,想象一下造假者打着这些人的名号写回忆录和无法言说的秘密,并带着这些假书出现在图书馆时,会引发多大的期待。
尽管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购书者们都很谨慎,不想上当受骗,但他们更怕百密一疏,错过一本好书,让法老震怒。国王不时就会带着阅兵似的自豪劲儿来检阅收藏的书卷。他会问负责整理图书的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
 现在有多少本书了?德米特里则告诉他数字:“国王陛下,已经有二十万本了。我会努力尽快补至五十万本。”亚历山大港对书的渴求变成了疯狂的热情。
现在有多少本书了?德米特里则告诉他数字:“国王陛下,已经有二十万本了。我会努力尽快补至五十万本。”亚历山大港对书的渴求变成了疯狂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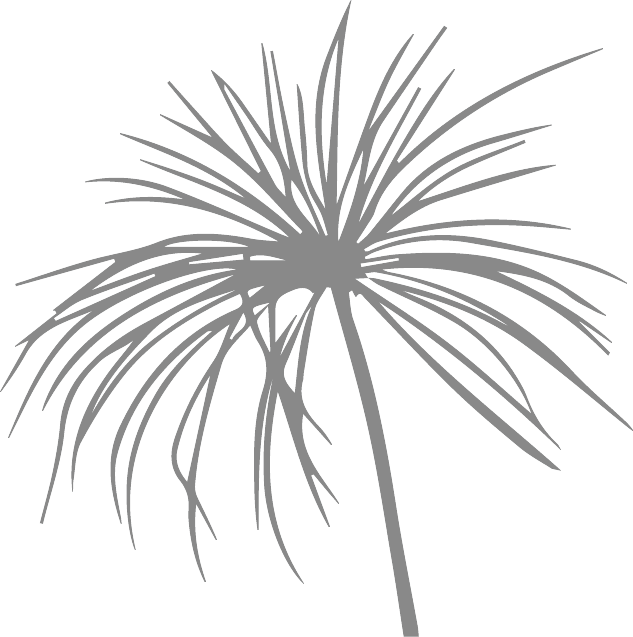
我出生在很容易买到书的国家和时代,在我家里,书堆得到处都是。集中干活那段时间,我会从不同的图书馆借回大几十本跟研究有关的书,我通常把它们垒得高高的,堆在椅子上,甚至地上。而倒扣在桌上的书就像一个双坡屋顶,需要找栋房子来挡风遮雨。如今,为了避免两岁的儿子把书弄坏,我把书堆到沙发背上。坐在沙发上休息时,我的后颈会碰到书角。如果将书价和我所在城市的房租做个对比,不难发现,书才是最花钱的租客。但我觉得,从大开本的摄影集到陈旧的胶装书——它们跟扇贝似的,总想合上——书总会让家里显得更温馨。
为了摆满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书架,那些秘密猎手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故事十分迷人,就像不远万里去西印度群岛寻找香料的故事一样,充满奇遇与冒险。而如今,书是如此普通,缺乏新科技的光环,以致有许多“先知”跳出来预言书会消失。每隔一段日子,我就会在沮丧的报纸文章上读到预言书会消亡,会被电子设备取代,并在众多娱乐选择前败下阵来的论调。最危言耸听的言论是,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时代的结束,书店和图书馆将迎来真正的末日——书店纷纷关门,图书馆无人问津。他们似乎在暗示:书很快就会被摆在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橱窗里展示,而在它近旁的便是史前矛尖。我想象着那些画面,环视家中数不清的一排排书和黑胶唱片,自问道:令人怀念的旧世界就要消失了吗?
真的吗?
书已历经时间的考验,证明了自己是一名长跑运动员。每次我们从革命的美梦中醒来,或从灾难的噩梦中醒来时,它都还在。正如翁贝托·埃柯
 所言,书跟勺子、锤子、车轮或剪刀属于同一个类型:一旦被发明出来,便无须改变。
所言,书跟勺子、锤子、车轮或剪刀属于同一个类型:一旦被发明出来,便无须改变。
当然,科技令人眼花缭乱,它有足够的威力将旧物拉下神坛。然而,我们都会怀念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照片、档案、旧行当、回忆,因为它们会迅速变旧,许多产品很快就过时了。首先是歌曲磁带,然后是电影录像带,我们徒劳地收集着科技执意使之过时的东西。DVD出现时,他们说,总算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存储问题。可是后来,他们又故技重演,用体积更小的磁盘来诱惑我们,我们永远都需要购买新的小玩意。吊诡的是,我们还能阅读十多个世纪前被耐心抄写下来的手稿,却看不了仅仅数年前被制作出来的录像带或碟片,除非家里的储藏室像废旧用品博物馆一样,保留了每一代电脑和播放器。
别忘了,几千年来,在一场未被历史记载的战争里,书是我们的同盟。这是一场保存我们那些宝贵创造物的战争:那些会随风而逝的话语;那些让混乱的世界具有意义、给予我们活下去的信念的虚构类作品;还有从我们无知的坚石上一点点刮下,真真假假、永远只是暂时正确的知识。
因此,我决定投入到这项研究中去。首先要面对的是问题,一大堆问题: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历史上发生过哪些不为人知的兴书之事或毁书之事?哪些书永远遗失了?哪些书得以幸存?为什么有些书会变成经典?多少书被水淹、被火烧、被岁月湮没?有多少书被愤怒地销毁?多少书被满怀热情地抄写?它们是同一批书吗?
本书想继续猎书人的冒险,而我则成为他们不可能的旅伴,去寻找失落的手稿、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即将沉寂的声音。也许,猎书人只是在给妄自尊大、心怀执念的国王跑腿。也许,他们并不理解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或许荒唐可笑。夜宿荒郊野外,篝火渐渐熄灭时,他们会小声嘟哝:“豁出命去替疯子实现梦想,这种日子真是受够了!”他们一定更希望被派到努比亚沙漠平叛或去尼罗河上的驳船验货,在那儿更容易获得晋升。但我认为,他们像寻找散落的珍宝似的寻找所有书的踪迹时,正在为我们今天的世界奠定根基,只是他们并不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