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氏谓“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其说之妄,刘氏已明辨之矣。兹所亟待讨论者,禹与夏果有无关系?顾氏曰:“ 何以《诗》《书》 (除《尧典》《皋陶谟》《禹贡》) 九篇说禹,六篇说夏,乃一致的省文节字而不说出他们的关系? ”(密圈照原文)吾为之下一总解答曰:此因《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非夏禹事迹之总记录,因禹与夏之关系非“必当入于其作者之观念中”者。一言以蔽之,此 因《诗》《书》中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 。试即《诗》《书》中言夏言禹之篇什而考察之:
(1)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信南山》)
(2)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文王有声》)
(3)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韩奕》)
顾氏曰:“《诗经》中有一个例,凡是名词只有一个字的,每好凑成两字,凡两字以上的名词不删……如‘王命仲山甫’‘命程伯休父’,名词虽在二字以上也不加省节了。《十月之交》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读此很可见 人名为单字 ,则加维字于人名……务使一句凑成四字。‘维禹甸之’‘维禹之迹’正是此例。禹若果是人王,亦应照了‘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他为‘后禹’(至少也要像《国语》和《尧典》的称他为‘伯禹’)。禹若果是夏王,亦应照了‘夏后’‘夏桀’之例而称他为‘夏禹’。”
夫《诗》三百篇非出一人之手,又非同时同地之文,而各个作者之属词造语之方式不能一律,故有所谓“作者之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author)。今于三百篇中,取数首相同之语调以例其他,则必须假定各个作者所用之语调皆如一。此 大前提已不成立 。兹退一步承认顾氏所称之例,而“维禹甸之”“维禹之绩”等语,果违此例否耶?顾氏不云乎,“人名为单字,则维字加于人名”,禹正单字之人名也。其缀以维字,正犹番、蹶、楀之例也。吾侪不因番、蹶、楀上未加周字,遂谓其非周人,独以禹上未缀夏字,遂谓其非夏主乎?顾氏之根本错误,在以“夏禹”二字为一名(term),而以“仲山甫”“程伯休父”之例律之。 不知夏乃禹之国号而非禹之名 ,“ 夏 ”“ 禹 ” 二字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 ,非如“仲山甫”之不可析为“仲”与“山甫”,及“程伯休父”之不可析为“程伯”与“休父”也。且也,“夏”“禹”二字既无不可分离之关系,而“维”与“夏”声调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仄声),维字置于句首,又有顿首语气(此顾氏言之),是故此处“维”字与“夏”字实不能相代。
至因《诗》三百篇中未尝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禹为“后禹”“伯禹”,未尝照“夏后”“夏桀”之例,称禹为“夏禹”,遂谓禹非夏王,此犹为妙不可言之奇论。吾侪读《乐府诗选》《玉台新咏》《明诗综》《清诗别裁》,其中亦未尝有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刘邦为“帝刘邦”,称朱元璋为“帝朱元璋”,亦未尝有遵“夏后”“夏桀”之例,称刘邦为“汉刘邦”,称朱元璋为“明朱元璋”,然则刘邦、朱元璋非汉帝、明帝矣,嘻!
(4)惟帝降格有夏,有夏诞厥逸。(《书·多方》)
(5)有夏不适逸……殷革夏命。(《书·多士》)
按此处言夏皆指夏桀事。若作“惟帝降格夏禹,夏禹诞厥逸”“夏禹不适逸……殷革夏禹命”岂不与事实相违反乎?
顾氏曰:“《多士》《多方》并言夏殷,言殷则必举成汤,言夏则从不举禹,这是什么道理?”
考《多士》《多方》之称夏殷事,乃周公将桀之所以亡,汤之所以得天下,与纣之所以亡,武王之所以得天下相比论,以明周之取商,正如商之取夏,皆奉天命,而非违义。前者(《多士》)所以抚慰殷之遗民,后者(《多方》)则因淮夷叛后,告谕“四国多方”,皆有为而发。其 所言与夏桀以前之事完全无关,安能将禹事牵入 !
(6)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克用三宅三俊。……呜呼!其惟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书·立政》)
顾氏曰:“这一段是把夏商对举的,都是说夏商起的时候如何好,后来的时候如何坏。何以在商则举出创业的成汤与亡国的纣,而在夏则但举出亡国的桀而不举出创业的禹?做《立政》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禹的(篇末即言‘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但他何以不把禹汤并举,何以篇末又单举禹呢?”
读者须注意,《立政》一篇乃周公陈说往事以为成王鉴戒,并 非欲于夏商事为本末毕具之叙述 。且随口宣言,既常有无意中缺漏,而又经史官之转载,残佚自不能必无, 安能持此以判断当时之历史观念 !且谓在商举汤、纣,则在夏亦须兼举禹、桀, 此不过词章上求偶俪之陋技,而非吐辞所必循之公例。 观《立政》篇中又云:“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 ,立政立事,牧夫准人……”正与上引“ 古之人迪惟有夏 …… 亦越成汤 ”同一辞气。此处并言商周,而亦于周则举文王,于商则不举汤, 可见《立政》作者惯用此种语调 , 其省略并非有特别原因 。至篇末言“陟禹之迹”,乃所以回应篇首,正见禹与夏之有关系也。
以上已将顾氏所举为证据者,悉加评骘。此外《诗》《书》中言夏言禹者尚有九条,兹并加稽验,观其有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需要。
(7)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长发》)
此处可作“昆吾夏禹”耶?否耶?读者自能辨之。
(8)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诗·长发》)
(9)是生后稷,缵禹之绪。(《诗·閟宫》)
(10)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诗·殷武》)
(11)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植嘉谷。(《书·吕刑》)
(12)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书·立政》)
吾前言之矣,“禹”“夏”两词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故言禹不举夏,不能为禹与夏无关系之证。且此处前三条,若将夏字加入,则声调(euphony)及音节(metre)皆失其宜矣。
(13)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书·洪范》)
此处禹尚未即天子位,若称夏禹则失辞矣。
(14)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荡》)
夏后统指夏代(《论语》以“夏后氏”与“殷人”“周人”对举,此其证也)。言夏代之亡可为殷代之鉴,故云“不远”也。若作“在夏禹之世”,则毫无意义矣。
(15)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书·召诰》)
此处夏殷对举,皆统指其全代。若改作“夏禹”便不可通。若因其言夏不举禹,遂谓禹与夏无关系,然则此处言殷亦未尝举汤,岂汤与殷亦无关系欤?
综上观之,《诗》《书》中九篇说禹,六篇说夏,其中 有十三篇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可能 (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及十五条), 其余亦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 。顾氏又引《论语》上未言禹与夏之关系为证,按《论语》上言禹者仅三条:
(1)禹,吾无间然矣。
(2)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3)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
前一条言禹之行为,绝无举及其国号之需要。后二条两单名对举,更不能将“夏”字添入。
是故, 关于禹与夏之关系,《诗》《书》《论语》均不能施用默证 。换言之,即 吾侪不能因《诗》《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 。而顾氏所谓“禹与夏的关系……直至战国中期方始大盛,《左传》《墨子》等书即因此而有夏禹的纪载。……禹与夏没有关系,是我敢判定的”云云, 绝对不能成立 。(以上评顾氏文中“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一节。)其他由根本观念推演而出之妙论,自然“树倒猢狲散”,本可不必再浪费笔墨以辨之。惟以其影响于一般仅从报章杂志中求智识之青年对于古史心理,甚巨且深,故不殚更赘数言。
顾氏以禹、夔、饕餮在字义上为虫兽之名,而假定禹为动物,刘掞藜氏已明辨其谬(《读书杂志》第十三期第二页第四格)。吾侪更当注意者,顾氏谓夔、饕餮为兽,遂“推之于禹”亦当非人,此 种类推法 (analogy), 史上绝不能用为证据 。(参看J.M.Vincent: Historical Research ,pp.257-259.New York Holt and Co.1911.)彼又谓:
在传说中,鲧为治水的人。《说文》云:“鲧,鱼也。”《左传》云:“尧殛鲧,其神化为黄熊。”(下引朱熹语云:“熊乃三足鳖。”)则鲧为水中动物,禹既继鲧而兴,自与相类,故《淮南子》即有禹化为熊的故事。
夫鲧训为鱼,而不能谓名鲧之人即鱼也。此理刘氏阐之已详,兹不赘。鲧化为熊之神话,乃指其死后之事,与生前无涉。若因神话言其死后化为动物,遂谓其非人,则《成都记》亦云“杜宇死,其魂化为杜鹃”,岂蜀帝杜宇为鸟而非人欤?即退一步言,古代有鲧为水中动物之神话,而因禹与鲧相类,遂谓古代亦以禹为水中动物, 此种类推法之结果,亦不能据为典要 。至《淮南子》乃汉人之书,且多妖言,决不能用以证春秋以前之历史观念。
顾氏又曰:“《天问》言治水有‘鸱龟曳衔,鲧何听焉’及‘应龙何画’之问,《山海经》本此,遂言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可见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很多,引禹为类,并不为过。”
此用类推法, 与前者同一谬误 。且即用类推法,亦必须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试问总理治水之禹,与神话中画地之应龙、曳衔之鸱龟(按王逸注云,“鲧治水,绩用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此言固不能据为典要,然顾氏谓鸱龟为治水中动物,其言亦无确据也), 安能引以为类 !
顾氏又曰:“《左传》与《天问》均说鲧化熊。《天问》又说‘伯禹腹鲧’,又说‘焉有龙虬,负熊以游’,觉得伯禹与龙虬有合一的可能,觉得第一条理由又得一凭藉。”(按第一条理由谓禹为似蜥蜴之动物,刘掞藜氏已驳之。)
顾氏谓鲧为熊之说不能成立,前已明之。《天问》云:“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按腹,王逸古本作“愎”,言伯禹与刚愎之鲧何以变化而不相同,有何神圣之处足供附会。“龙虬负熊”之熊,与鲧有何关系?(若因神话谓鲧化为熊,言熊便是指鲧,然则凡言杜鹃者便指蜀帝杜宇耶?)而“负熊”之龙虬与禹又有何关系?愿顾氏明以教我!
顾氏复下一假定曰:
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 平水土 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流播的地域既广,遂觉得禹平水土是极普遍的,进而至于说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对于禹有一个地王的观念。
中原民族自周昭王以后,因封建交战而渐渐与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来,始有禹名见于《诗》《书》。又因后土之祀,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
关于此假定,吾侪可分五层评论。
(一)请问“ 商周间的新民族 ” 是否 “ 有平水土的需要 ”?顾氏曰:“楚越间因土地的卑湿,有积水的泛滥,故有宣泄积水的需要。因草木的畅茂,有蛟龙的害人,故有焚山泽、驱龙蛇的需要。”焚山泽乃益事,与禹无涉,兹且不谈。至谓楚越积水泛滥,则不能不请其“拿证据来”。顾氏引《天问》“地何以东南倾”“东南何亏”及《汉书·地理志》“江南卑湿”三事,遂谓周代楚越之地,与孟子所谓尧时“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竟这等相似”。按古人所谓“地不满东南”,乃因我国东南部地势倾陷,为江海所归,此与陆地上积水泛滥,自是二事。且《天问》所谓“东南”并未明言何地,安得随意指为楚越。读者更须特别注意:《汉书》只言“江南卑湿”,而顾氏则云:“楚越间地势卑湿,积水泛滥,故有宣泄的必要。”此 全为凿空附会之谈,实犯史法上“从抽象名词推理 ”(reasoning from abstract terms) 之大病 (参看 Historical Research ,pp.259-260),夫吾人今日犹恒谓“粤地卑湿”“南方卑湿”,然则广东亦“积水泛滥,有宣泄之必要”耶?
(二) 禹若为楚越民族所虚造之神话中人物,则决不能于华夏之历史观念中有立足之地 。何也?春秋以前,吴越荆楚诸族,乃中原人民所鄙为“蛮”“夷”而不侪于人类,而又中原之世敌也。夫以自命堂堂之华胄,而乃取彼“蠢尔蛮荆,大邦为仇”之民族之神话中人物,与中原历史观念根本相凿枘者,举而加诸乃祖乃宗(后稷)之上,与之配祀,垂为型仪,律 以古代夷夏之防之严 ,及 以夷变夏之大惧,此必无之事也 。
(三) 禹之神话盛于楚越,不能为禹之观念创自楚越之证。安知非由于楚越与中原民族接触后,禹之史迹输入,因从而放大附会耶 ?禹之神话之所以盛于楚越,吾 尝求其故 ,盖有二焉:(1)南方民族富于想像,独擅构造神话之能力。(参看顾实《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见东南大学《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三期。)(2)越欲借华夏自重,以洗刷蛮夷之名,而自认为禹后(此正犹刘渊之自认为汉高祖后),益有制造禹迹以弥缝之之必要。此禹致群神会稽,道死葬会稽等传说所由起也。
(四)绳以逻辑。顾氏之假定之能否成立,根本上全视乎能否证明周昭王以前中原民族无禹之观念,及周昭王以前楚越已有禹之观念。二者缺一,则其假定无根可据。关于后者, 顾氏未道及只字。吾尝代之向汉以前之载籍搜索,毫无影响可寻 。关于前者,顾氏之言曰:
《周颂》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语,可见其作于成康之后,昭穆之世。细绎《周颂》的话,他们也说山河,但没有道出个禹字。也说耕稼,但又没道出一个禹字。也说后稷,但又没有道出他和禹曾有过什么关系。一比了商鲁《颂》、大小《雅》对禹的特别尊崇,就显出《周颂》的特异。《周颂》为什么特别不称禹?原来作《周颂》时尚没有禹的伟大神迹传到周民族来。
《周颂》中有一首称《成康》,只能证明此首作于成康之后,不能证明《周颂》三十一篇作于成康后若干时。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此三十一篇皆作于大小《雅》、周鲁《颂》之中各诗前,昭穆之世。
是故吾侪不能用《周颂》以证昭穆之世之历史观念
。兹退一步承认此层,
顾氏之论据亦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
。夫欲因《周颂》中称山河、稼穑、后稷而不举禹,遂断定其时无禹之观念,则必须证明凡言山河、稼穑、后稷,非将禹举及不可。然此论绝对不能成立。试观大雅及商鲁颂之“崧高维岳”“帝省其山”“瞻彼旱麓”“景员维河”“思乐泮水”“江汉浮浮”,并言山河而亦未将禹举及。然则作此诸诗时亦无禹之观念耶?《诗》三百篇中之言后稷者,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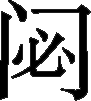 宫》将后稷与禹对举,然则除《
宫》将后稷与禹对举,然则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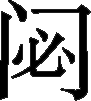 宫》外,其余言后稷各诗之作者亦皆无禹之观念耶?禹乃治水者而非耕稼者,言稼穑自无举禹之需要,此更无论矣。至是,吾侪可下一结论曰:
《周颂》之不称禹,乃因无称禹之需要,并无“特异”,并非“特别的不称禹”。故不能因其不称禹,遂谓其时无禹之观念。
宫》外,其余言后稷各诗之作者亦皆无禹之观念耶?禹乃治水者而非耕稼者,言稼穑自无举禹之需要,此更无论矣。至是,吾侪可下一结论曰:
《周颂》之不称禹,乃因无称禹之需要,并无“特异”,并非“特别的不称禹”。故不能因其不称禹,遂谓其时无禹之观念。
(五)顾氏谓“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又谓禹“又因后土之祀,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并引上列顾氏所立假定中语)。前者乃将“敷”“甸”二字穿凿附会之结果,后者乃由于误读《国语》,并经刘掞藜氏驳证。(见《读书杂志》第十三期第四页及第十六期第四页。)
综上五层观之, 顾氏所设之假定绝对不能成立 。(以上评顾氏文中“禹的来源在何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