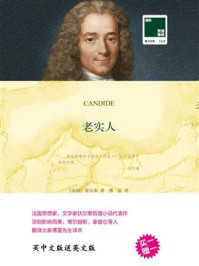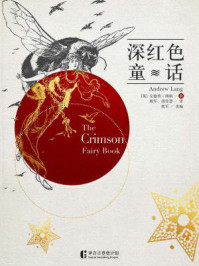华盛顿 1941年7月26日
一个湿热难耐的星期六下午,但首都的街道热闹得很,到处都是奔忙的行人和急躁的出租车司机。每个人都像是在执行特别重要的任务。欧洲战局日益扩大,紧急的态势似乎终于影响到了华盛顿。麦格林教授从一辆停在白宫外的出租车上下来,扫了一眼四周,竟没看到一个穿美军制服的人,倒是有很多人提着鼓鼓囊囊的公事包,像是有明确的目的,要去做什么事。他猜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军人。
一年前,罗斯福叫麦格林向威廉姆斯学院告个无限期的长假,作为亚洲问题顾问加入自己那个名不副实的智囊团;但他担心在政策上与总统的其他顾问起冲突,最后还是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同意偶尔给总统出出主意。这是他今年第三次应召进入白宫。他很懊恼又得放下手头的工作离开威廉斯敦,但想到自己说不定可以帮着扭转历史进程,又觉得很荣幸。
到目前为止,总统已采纳他的建议,继续与日本人认真谈判,没被战争部长
 史汀生、内政部长伊克斯和中国游说团诱使,“对日本人来硬的”。一定又出现了新的危机,他猜可能与上个月希特勒突然入侵苏联有关。他在东京的一个线人曾来信表示,这场入侵让陆海两军吵得很厉害,陆军想进攻西伯利亚,而海军则倾向于向南进军,抢占石油和其他资源,看样子,陆军会赢。
史汀生、内政部长伊克斯和中国游说团诱使,“对日本人来硬的”。一定又出现了新的危机,他猜可能与上个月希特勒突然入侵苏联有关。他在东京的一个线人曾来信表示,这场入侵让陆海两军吵得很厉害,陆军想进攻西伯利亚,而海军则倾向于向南进军,抢占石油和其他资源,看样子,陆军会赢。
总统隔着桌子伸出手来,满面笑容,热情地招呼他的老同学。“我知道你刚满六十岁。恭喜啊!你这爱尔兰暴脾气,熬到这岁数真是奇迹了。”他回忆起他们在学校的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聊了几分钟,他提醒麦格林自己还有一年才满六十,然后话题一转,又调侃了一番教授的那本新书。书中提到一个观点:美日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分歧,美国与日本一样难辞其咎。曾对他的其他作品给予高度认可的评论家们预言,这本书会葬送他的职业生涯。
“我不是在为日本辩护,”他说,“几乎可以说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推到了快跟我们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英国——还有我们——为了不让他们成为经济上的对手,做的那些事必然导致日本侵略“满洲”
 和中国。”除了这个原因,还有经济大萧条、人口暴增、发掘新资源和新市场来维持一流强国地位的迫切需求,最后还有来自苏联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的威胁。
和中国。”除了这个原因,还有经济大萧条、人口暴增、发掘新资源和新市场来维持一流强国地位的迫切需求,最后还有来自苏联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的威胁。
“弗兰克,你可别告诉我,你现在看每张床下都躲着赤色分子
 。”
。”
“只要他们确实存在,我就不会置之不理,总统先生,”他把身子往前凑了凑,“我不明白为什么您身边那么多顾问都在叫嚷着黄祸论
 ,却不担心日本会是军事上的对手。您拿到的那些情报说日本飞行员效率低下,真是乱弹琴;而且,日本的战船和飞机也不是什么劣等货。我那天看到一幅漫画,画着矮小的龅牙日本士兵和水兵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让人觉得他们是嘲笑的对象,不是什么可怕的对手。总统先生,千万不要低估他们。我担心史汀生先生和赫尔先生潜意识中种族优越感作祟,向您施压,迫使您对日本人采取极端手段,最后把他们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却不担心日本会是军事上的对手。您拿到的那些情报说日本飞行员效率低下,真是乱弹琴;而且,日本的战船和飞机也不是什么劣等货。我那天看到一幅漫画,画着矮小的龅牙日本士兵和水兵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让人觉得他们是嘲笑的对象,不是什么可怕的对手。总统先生,千万不要低估他们。我担心史汀生先生和赫尔先生潜意识中种族优越感作祟,向您施压,迫使您对日本人采取极端手段,最后把他们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看看这个。”罗斯福递给他的是美方截获的日本外务大臣发给日本驻维希大使的一份电报的译文。不论维希政府如何决断,日军都将于7月24日进兵印度支那。罗斯福从皱着眉头的麦格林手中抽回那份情报。“当然,你没看过这个。”他在长长的烟嘴上安了一支香烟。“维希政府在期限前一天,决定不做抵抗,让日军进驻。”他又递过来另一份情报,这是日本驻维希大使发给日本外务大臣的,“赫尔看到这个,骂骂咧咧地冲进来。”
麦格林看到上面写着:“法国之所以这么痛快地接受日本的要求,是因为见识到了我们的决心有多坚定,我们的意志有多坚决。简而言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麦格林一言不发,慢慢地把情报递了回去。
“赫尔要我再向日本实施一道新的禁令,狠一点的,史汀生老伙计觉得我们应该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麦格林握紧拳头,“总统先生,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是的,一切与美国的贸易都将终止。”
“但是,总统先生,美国是他们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啊!”
“这我很清楚,弗兰克。”
“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宣战。”
“那倒不至于。”
“可日本人肯定会那样想。请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考虑一下。他们通过和维希法国
 谈判进入印度支那。我知道您看不上维希,但那毕竟是一个我们承认的国家,日本人的做法合乎国际法。”
谈判进入印度支那。我知道您看不上维希,但那毕竟是一个我们承认的国家,日本人的做法合乎国际法。”
“那是武装占领,弗兰克,你这口气像是他们的律师。”
“我希望自己像个历史学家。冻结资产会被东京解读成ABCD
 列强包围日本帝国的最后一步,在他们看来,这是否定他们作为亚洲老大的正当地位,是关乎存亡的挑战。”
列强包围日本帝国的最后一步,在他们看来,这是否定他们作为亚洲老大的正当地位,是关乎存亡的挑战。”
“我希望他们把这看作是对侵略者的教训。”
“请考虑一下后果,总统先生。这样做会让我们在东京的朋友乱了阵脚,我们有很多很有影响力的好朋友,天皇的首席顾问木户侯爵向来热爱和平,天皇本人也是,还有总理大臣近卫也想要和平。这人在某些方面是个十足的傻瓜,但我相信格鲁大使已经向您汇报过,他和多名日本要员一直在努力争取让我们两国达成合理的协定。”
罗斯福吃吃地笑起来:“弗兰克,你可真是一股清风!”
“有时候我觉得您认为我送的是一股热风,一堆空话。”
“你给我指出了很多值得琢磨的问题,”总统严肃地说,“我很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又给我上了一堂历史课。”他们握了握手,“对了,你那个儿子,威尔,已经成了乔治·马歇尔
 的得力干将。我觉得他以后会比你强的。”
的得力干将。我觉得他以后会比你强的。”
“但愿吧。”
“你那个小儿子也来找过我。他像你,弗兰克。”
麦格林一脸茫然,罗斯福乐了:“我只是远远地见了他一面,他当时和美国和平动员协会的人一起在前面抗议示威。”
麦格林能感觉到自己尴尬得脸都红了。
“别太当回事,弗兰克。赤色分子总好过年纪轻轻就成了共和党人。”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再次感谢你,”他郑重地说,“你今天跟我讲的每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我们这个可怜的世界是受政治现实支配的。即使我不总是采纳你的建议,我也希望你知道我真的考虑过。相信我,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再说一遍,你给我指出了很多值得琢磨的问题。谢谢。”
麦格林离开白宫的时候,心里在想,可怜的富兰克林,虽然才干超越华盛顿一干人等,但注定要沦为政治动物。一个地大物博、从不忌惮外族的国家的元首怎么可能理解日本的处境:一个地少人多的海岛帝国,资源匮乏,还要提心吊胆地提防残忍无道的邻国苏联·罗斯福很清楚美国阻止日本移民这项政策助长了仇恨和不信任的风气,但他意识不到这是大张旗鼓的种族歧视,理所当然会激怒骄傲的日本人。对希特勒的怕和对英国的爱误导了他,令他完全站在了丘吉尔一边,而那个老家伙是不会让民主越过苏伊士运河的。
麦格林为了说服他的这个老同学摆出的那些具有战略高度、涉及长远利益的理由,罗斯福怕是不会采纳,他更关心短期的利益博弈。麦格林骂了一句,骂完又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富兰克林就是有一种讨人喜欢的特质。麦格林想起了1932年的那个秋天,当时罗斯福州长在与胡佛竞选总统的过程中途经威廉斯敦,马萨诸塞州州长伊利作为威廉姆斯学院的校友请他在他的敞篷汽车上跟学生们讲几句话。车停在小教堂边的山上。学生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共和党人,喝着倒彩,不让罗斯福开口。当时离车很近的麦格林和小马克都注意到了伊利怒不可遏的表情,而罗斯福只是和蔼地笑笑,就好像在说:“这跟我料想的一样,我知道会在乡村俱乐部学院受到这样的待遇。”他在麦格林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无论怎么热情洋溢的演讲都没这个小小的举动这般令他折服。见学生们这样无理取闹,麦格林火冒三丈,他把马克拽到下一个街角,那里聚集着河畔工厂的几百名工人。汽车缓缓驶过,富兰克林摘下他那顶不久就将举世瞩目的卷檐软呢帽,笑了,那是一种包容一切的微笑。麦格林一直忘不掉工人们满脸的崇敬,以及随后爆发出的诚挚而热烈的掌声。这样的罗斯福是他在哈佛的那段时间里从未见识过的罗斯福,纵使他们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他仍旧不离不弃支持拥戴的也正是这样的罗斯福。
麦格林招了辆出租车,十分钟后就到了弗洛斯和正的公寓,这地方与马萨诸塞大道上的日本大使馆隔了几个街区。尽管这五年过得并不顺,但弗洛斯的脸上没什么精神压力的痕迹。她很幸运地遗传了克拉拉淡泊宁静的好性情。正在墨西哥处理贸易事务,灰心丧气地过了两年,然后被再次降级派到哈瓦那当一个小小的副领事,似乎再无出头之日,然后到了1941年初,接到一个意外的消息,说要把他调回华盛顿,他兴高采烈地赶过来,被浇了一盆冷水,原来调他过来纯粹只是因为他英语好。作为野村大使的其中一名主翻译官,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熟悉与日美谈判有关的各种文件,美国和日本两边的文件。野村是一名海军大将,他很少向正咨询,指望自己是总统的老熟人这层关系能派上用场。“我是日本的朋友,”罗斯福在欢迎他到任的时候说,“你是美国的朋友,你了解我们国家,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然而,很不幸的是,和野村谈的几乎一直是国务卿赫尔,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老顽固,他深信日本人不值得信赖。
正曾经想提醒大使,赫尔那副友好的样子只是假象,他已经完全被自己那几个亲华派幕僚洗脑。正很清楚,谈判局势在恶化。他想起他那位丝绸商人祖父曾经跟他讲过“黑船”的故事,当年载着美国红毛鬼的黑船不请自到,霸道地入侵他们神圣的国土。老人用他那不再嘹亮的嗓音哼唱起一首歌:
他们来自幽冥之地,
长着鹰钩鼻的巨人像山里的小鬼;
这些巨人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发。
他们从我们的圣主那里窃取了承诺
欢天喜地跳着舞驾船而去
驶向遥远的幽冥之地。
祖父说,美国人走了又来,但他们从来都不了解这片神圣的土地。这片圣土上的人民从这些红毛鬼身上只学到了那些让他们贪婪、永不满足的劣根性。正在想,船还在来来往往,但两个地方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少数人——比如他——已经发现两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但红毛鬼和神的孩子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正内心觉得两国势必会开战。那到时候弗洛斯和他们五岁的儿子正雄会怎样?他不断地安慰弗洛斯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们两个国家不可能起冲突;但她心里清楚得很,她装作相信他那套乐观的说辞,依旧表现出一副乐天派的样子。
晚饭后,威尔也来了。别看他走路步态傻呆呆的,浑似詹姆斯·史都华,其实那是假象,他在壁球场上的对手最后都沮丧地发现外表靠不住;同样让人上当的还有他那慢吞吞的,甚至有点土里土气的话风,和他辩论的对手也已经认识到这点。他以名列前茅的好成绩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成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法兰克福特的书记员。去年,法兰克福特建议他接受任命加入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参谋部。他认为战争无法避免,于是就同意了。他很崇拜罗斯福,认为新政是大势所趋。要说有什么是他信奉的,那就是站在赢的一方;你必须遵守比赛规则,不论输赢都要保持风度,但赢总归要比输好。威尔几乎一直都在赢。而且,他在全国壁球锦标赛上拿了冠军后,着实低调谦虚,最后和手下败将成了好朋友。威尔试图把这经验传授给马克,两兄弟感情很好,但实用的忠告马克从来都听不进去,在威廉姆斯学院,他不肯加入联谊会,热衷于跟校园里的每一个怪人厮混,简直让人觉得他总是跟自己过不去,非得挑最难走的路去走不可。
威尔热情地跟父亲打招呼。“我知道你今天又去了总统办公室。”父亲和总统的交情令威尔很自豪,但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肯像哈里·霍普金斯那样成为总统的正式顾问。明明可以穿行在权力的走廊里,为什么偏要选择留在一个区区小学院里?
威尔从父亲嘟嘟哝哝的应答中猜到他没能说服罗斯福放弃禁令。他自己那边一整天都乱哄哄的,大家都在忙着制订应急计划。马歇尔和海军的同级将领、海军上将史塔克,一直都建议总统暂时不要有极端的举动,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应对太平洋战争。两人都主张集中精力对付希特勒,马歇尔上将曾经给威尔看过海军作战计划处出的一份警告——这样的禁令可能会导致日本为抢占石油资源提前攻打马来亚
 ,使美国过早地被卷入太平洋战争。
,使美国过早地被卷入太平洋战争。
当着正的面,他们说话一贯谨慎,谁都没有提起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话题主要围绕着马克。麦格林抱怨他反复无常,还犟得要死。在威廉姆斯学院,他坚持要打工,还一定要住校,住在穷孩子的宿舍里。大二结束,他就宣布要搭便车去加利福尼亚,然后直到开学前一天才回来。到了第二年夏天,他又不肯去他们家在斯夸姆湖的别墅,扒火车跑到别处去了,一张接一张地给弗洛斯寄空白明信片,让家里人知道他在哪里。在威廉姆斯学院,他通过创业赚了很多钱:运营纽约专列,开办打字社,经营学生书店。标准石油公司的猎头邀请他毕业后去他们公司担任要职。可他不领情,又整个夏天扒着火车到处跑,之后还去纽约投奔了共产党。现在,他白天卖胜家缝纫机,晚上帮着组织街头集会。尤其让麦格林恼火的是,玛吉也步他后尘,跑到纽约当《先驱论坛报》的小记者去了。
听到麦格林抱怨马克看来注定要被冲动牵着鼻子走,弗洛斯忍不住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他问。
弗洛斯想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教授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他自己被冲动牵着鼻子走造成的。他和马克实在太像了:两人都很急躁,但从来不记仇;都很叛逆,很固执,很没耐心;老爱打抱不平,急躁又冲动;出生在天主教家庭的爸爸在七年级的时候,被一个修女不分青红皂白地用金属尺打了一顿手板后,从此再也不愿去教区学校,一根筋地要去公立学校,后来又因为不肯上圣母大学惹得他父亲火冒三丈,他离开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奔赴最逊的东部,去上最逊的学校。
正没有表达意见,只是静静地听麦格林抱怨,心里在想自己和父亲之间存在的分歧。也许他当初不该违背父亲的忠告,一意孤行地娶了弗洛斯。刺耳的电话铃声把他拽回到现实。他接起电话一听,脸色煞白。他说他们收到报告:总统刚刚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他向家人告辞,匆匆忙忙赶去大使馆。
在回酒店的出租车上,麦格林在默默地诅咒那些傻瓜,是他们怂恿总统犯下了这样一个愚蠢的错误。他所热爱的这两个国家势必会两败俱伤,罗斯福和天皇都被各自的文化和政治体制缚住了手脚。就连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也不是罪魁祸首,他们也只是身陷封建制度囹圄的普通人。史汀生、赫尔和伊克斯都不是元凶,尽管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对手逼到了墙角,要是不屈服,几乎没有出路,只能开战。
麦格林担心自己的孩子。弗洛斯真是太不幸了!玛吉和马克这两人精力过剩,做事莽撞,总是闯祸。也许只有明智的威尔才能够保全自己,他在华盛顿跟着马歇尔不会有事。
然后,他想到了日本。户田一家和他其他的朋友都逃脱不了厄运了。日本这样一个小国怎么对抗得了美国这样的强国?它会一败涂地,它的人民,军人也好,平民也好,都将遭受无法想象的悲惨命运。
弗洛斯在等正回家,心里在犯愁。如果真的爆发战争,他们一家三口会怎样?交战期间他们会被扣押起来吗?要真是这样,对正来说可真是太痛苦了,他会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家人。
在纽约的马克和玛吉在星期天吃早餐的时候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同住在河滨大道附近西边第143街上的一幢小房子的底楼。两人都意识到这是迈向战争的一大步。玛吉有个按捺不住的想法——虽然战争很可怕,但她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两年前,麦格林带她去了趟欧洲,让她认识了西格丽德·舒尔茨,她便知道自己必须也成为一名驻外记者,不然不会甘心。看着娇小的西格丽德勇敢地对抗纳粹的新闻代表,玛吉萌生了效仿她的念头。战争会为她在欧洲和亚洲都创造机会。
可马克很困惑,也很沮丧。在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前,他真正的生活始于黄昏。在为和平奋斗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地方如纽约这般让他兴奋。除了参加附近的美国和平动员协会的街头集会,马克还作为代表出席一个全国性的左翼和平研讨会,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和其他大型场馆举行的重要集会。在这些场合,他遇到了许多有意思的激进青年,但是他想结识一名美丽的女共产党人的梦想一直都没有实现。他能在这个圈子里找到的最好的对象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工会组织者,大家都叫她“红罗莎”。她的野性活力令他神魂颠倒,但自从她把性病传染给他之后,他的激情就熄灭了。为什么突然甩了她?作为绅士,马克不能说出实情。同志们纷纷谴责他是负心汉。
他加入共产党,是因为这是唯一一个真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党派,也是唯一一个对抗反犹太主义和吉姆·克劳法
 并且公开支持和平的党派。但是,在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后,这个党立即把美国和平动员协会变成了一个战争组织,马克对此提出抗议。他仍旧信奉和平。你怎么能星期六还称它是帝国主义战争,到了星期日就改口成了民主战争?一名很有说服力的官员从市区赶过来做了一通思想工作,才把马克留住。连着几星期,他趁地铁员工晚上下班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交通公司的各车段卖《工人日报》。他一开始还挺喜欢这种挑战的,不久就有了五六个固定的客户,这了不起的功绩又使他成了党内的宠儿;但即便这样,他在组织纪律的约束下还是干得很不开心。他的主要兴趣转移到了新恋情上。他的新女友叫米丽娅姆,是他在塔利亚电影院搭上的一个犹太姑娘。他每星期都要带她来两次第143街的那幢小房子。玛吉并不赞成马克和她交往,因为这姑娘在饼干厂工作,但每次马克招待女朋友的时候,她都会很主动地出去,让他们享受二人世界。
并且公开支持和平的党派。但是,在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后,这个党立即把美国和平动员协会变成了一个战争组织,马克对此提出抗议。他仍旧信奉和平。你怎么能星期六还称它是帝国主义战争,到了星期日就改口成了民主战争?一名很有说服力的官员从市区赶过来做了一通思想工作,才把马克留住。连着几星期,他趁地铁员工晚上下班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交通公司的各车段卖《工人日报》。他一开始还挺喜欢这种挑战的,不久就有了五六个固定的客户,这了不起的功绩又使他成了党内的宠儿;但即便这样,他在组织纪律的约束下还是干得很不开心。他的主要兴趣转移到了新恋情上。他的新女友叫米丽娅姆,是他在塔利亚电影院搭上的一个犹太姑娘。他每星期都要带她来两次第143街的那幢小房子。玛吉并不赞成马克和她交往,因为这姑娘在饼干厂工作,但每次马克招待女朋友的时候,她都会很主动地出去,让他们享受二人世界。
“我要出去一下。”马克说着便出了门,他又是去华盛顿高地,又会在那里逛很久。他已经厌倦了这个党派,厌倦了卖缝纫机,而且他开始后悔自己当初太迷恋米丽娅姆。她是个可爱温柔的姑娘,他也很喜欢听她讲在饼干厂里工作遭遇的种种凶险,比如如何摆脱老男人色眯眯的纠缠;但现在,她谈到了结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