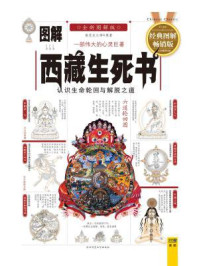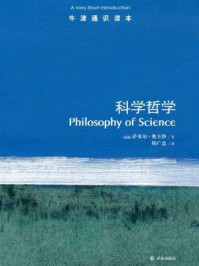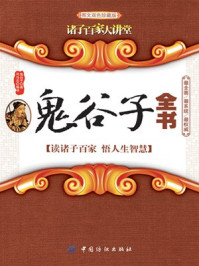弗朗茨·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1886—1929),犹太哲学家,现代犹太哲学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对犹太哲学乃至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罗森茨维格于1886年12月25日出生在德国卡塞尔(Kassel)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在他童年时代一般性的犹太传统教育以及非犹太性质的普及性教育是并存的,后者对他的影响恐怕更大。从1905年开始,他相继在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学习医学,在此期间,影响他的是希腊哲学以及以尼采、歌德为主的现代哲学和文学。1907年冬,罗森茨维格终于放弃了医学转而到柏林大学攻读现代历史和哲学。1908年秋,罗森茨维格从柏林回到弗莱堡大学,并接触到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1912年夏,罗森茨维格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黑格尔与国家》。长期的非犹太教育的影响使得罗森茨维格对犹太传统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在1913年达到了顶峰,再加上受皈依基督教的朋友的影响,他甚至想以犹太人的身份皈依基督教。虽然这一年秋天的一次赎罪日仪式使得他回心转意、迷途知返,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终身都保持着对基督教的一份好感。1913年秋至1914年,罗森茨维格在柏林犹太教科学学院学习期间遇到了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老师,赫尔曼·柯恩(Hermann Cohen),此时的柯恩已经不再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领袖,而是重拾自己信仰的犹太哲学家。有着相似经历的罗森茨维格对柯恩崇敬有加,并期待着在后者的指导下实现思想上的飞跃。然而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战争打断了他的学习,但却并未中止他的哲学思考,利用战争的间隙,罗森茨维格撰写了大量的笔记和书信,使得他的哲学思想逐渐成型,因此,后人曾称之为“战壕里的犹太思想家”。1917年3月,他写成了《适逢其时》( It Is Time ),并题献给他最崇敬的老师科恩。在此书中,他详细阐述了他的犹太教育思想,并计划建立一所犹太教科学研究院(Academy for the Science of Judaism)。1918年初,罗森茨维格还两次回到柏林,和父母以及科恩商讨建立犹太研究院的有关事宜,也正是在此期间,罗森茨维格因缘际会偶然发现了柯恩的《源于犹太教的理性宗教》(中文译本《理性宗教》)一书的复写稿,这本书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本书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心路历程,罗森茨维格决定动手写作《救赎之星》。由于战争的影响,写作的历程异常艰苦,罗森茨维格不得不将自己的思想记录在明信片或家信中,逐一寄回家乡,才使得这部著作得以断断续续地进行。终于,战争结束了,战败的德国虽然万马齐喑,但却给了罗森茨维格充分的写作时间和空间。1919年2月16日,这部洋洋几十万字的巨著宣告完成。虽然写作完成,但罗森茨维格清醒地意识到这本内容奇特的书很可能引起包括犹太教、基督教等在内的广泛争议,因此,他并未将此书立即出版。1921年7月,他曾应一个出版商的邀请,写成《论健康的与不健康的思维》( Das Büchlein vom gesunden und kranken Menschenverstand )这个哲学小册子,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救赎之星》的梗概。然而,就在该书即将付印前夕,他又放弃了出版的念头,收回了书稿。因此,《救赎之星》直到几十年过后才首先在英国问世(1953年),书名用的仍是上述小册子的名字,而德文原版直到1964年才得以正式出版。1920年3月,罗森茨维格与艾蒂·罕缔结良缘。同年8月1日,他就任法兰克福犹太讲习所所长。1921年11月(或12月)的一天,罗森茨维格莫名其妙地跌倒了数次,在被送往医院检查后,他被确诊患上了慢性偏瘫症。从此以后,这个挥之不去的病魔紧紧缠绕着罗森茨维格。病痛中的罗森茨维格表现得极为顽强和乐观。他经常拖着孱弱的病体参加各种各样的实践和学术活动,还书写了大量的书信阐述自己的观点,帮助思想上面临困惑的犹太青年们。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夫人的帮助下翻译了中世纪的犹太诗人、哲学家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的诗歌,并且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ber)一起将希伯来语《圣经》译成德文。1929年12月10日凌晨,罗森茨维格与世长辞。
《救赎之星》是罗森茨维格的代表作,是其思想的最集中体现,在这里就以《救赎之星》为主,简单介绍一下罗森茨维格的主要思想。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救赎之星》的主要思想,那就是: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走进生活。围绕着这一主旨,罗森茨维格重点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考察了人类历史上所出现的种种试图摆脱死亡的思想形式,并指出它们并未完成自己的任务;二是借助“救赎之星”的概念阐明人类获得真正生命的途径;三是通过考察亚欧的诸种宗教,指出只有犹太教与基督教才是真正的救赎之希望。
《救赎之星》一开篇就指出,死亡是人类自诞生那天起就挥之不去的梦魇,它时时刻刻缠绕着人类,无孔不入地炫耀着自己的威力,得意洋洋地嘲笑着人类短暂易逝的生命。在这篇充分体现其文学天赋和想象力、极富感染力的文字中,罗森茨维格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凸现了人类生存的内在矛盾,并指出,正是基于解决这一矛盾的需要才诞生了哲学。在罗森茨维格看来,哲学,就其根本任务来说,既不是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也不是回答人是否能够认识世界的问题,而是教会人们如何摆脱对于死亡的恐惧,并进而获得真正的生命。显然,罗森茨维格对哲学的这种看法是同人们对于哲学、包括哲学对于自身对传统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由此出发,罗森茨维格又进一步区分了新旧两种哲学。所谓的旧哲学,指的是从公认的“哲学之父”古希腊的泰勒斯开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为止的西方哲学;而所谓的新哲学,是黑格尔之后的,以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为代表的哲学。新旧哲学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因此,罗森茨维格把新哲学的思维方式又称为“新思维”。总体上来看,旧哲学认为,消除人类对于死亡恐惧的唯一办法是将个体消融到“全”(All)之中,此时的个体不再是个体,而变成了“全”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借着“全”的力量对抗死亡,甚至获得永生。罗森茨维格认为,旧哲学的解决之路仅仅是动听的谎言。因为这套解决办法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个体无法独自面对死亡,只有“全”才有这个能力,个体在“全”面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可怜虫,毫无独立的价值。作为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的生与死的考验的士兵,罗森茨维格清楚地知道,当死亡真正降临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面对死亡,始终是个体的事情。因此,旧哲学的解决办法在当人真正地直面死亡时毫无效力。而新哲学则与此不同,它给予了个体以充分独立的地位,它虽然仍然无法单枪匹马地对抗死亡,但至少它不需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放弃自身,它有着自身的价值,这价值虽然不一定很大,但却无法抹杀,也不可替代。新旧哲学的这种根本上的不同,造就了它们表现形式的不同。首先,在起点上,旧哲学表现为抽象的概念,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演绎过程,最终下降到具体的环节。而新哲学则直接从具体的个体出发,从具体经验上升到存在,到全体,这里凸现的是个体性的、当下性的经验。其次,从理论到构造上来看,旧哲学强调的是统一性,用一条原则统一起整个的世界。而新哲学则强调关系性,即:“全”是由处于不同关系中的个体所组成的,其中的每一个体都具有着独立的地位。这种关系,罗森茨维格名之为“对话”关系,对这种关系的阐述构成了整部《救赎之星》的基本内容。第三,旧哲学和神学的关系始终紧张,除非迫于外在压力,否则哲学不关心神学问题。而新哲学必定关心神学问题,并且只有在犹太-基督传统中,旧哲学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总而言之,《救赎之星》开篇提到的种种旧哲学所不能或不愿意解决的问题,都要在新哲学-新思维中才能找到答案。在提出了问题和解决思路之后,罗森茨维格详细阐述了以“救赎之星”为核心的思想。
“救赎之星”的形象来自于犹太人耳熟能详的“大卫之盾”。大卫之盾是用两个三角形重叠而成的六角星。罗森茨维格用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代表上帝、世界和人,而用另一个三角形的角代表创造、启示和救赎。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六个最基本的概念或元素。上帝通过“创造”产生世界;上帝通过“启示”选择了人;上帝以及人的创造性的工作产生“救赎”活动。我们知道,旧哲学也探讨上帝、世界和人,但罗森茨维格认为,经过康德的批判,这三者都变成了“先验幻象”,罗森茨维格称之为“无”。在康德那里,这样的无是否定性的,而柯恩则认为,这样的无并非一无是处,反而卓有成效地昭示了有(存在)。罗森茨维格由此出发,借助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将这三个无变成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神的概念、元逻辑学的(metalogic)的世界概念及元伦理学(metaethics)的人的概念。到此为止,罗森茨维格确定了第一个三角形中的三个角。接下去需要确定的就是另外三个角,即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罗森茨维格深受他的老师柯恩的影响,将三者之间的关系定义为相互关系。对上帝来说,上帝本身就具有创造性、启示性、救赎性,因此,上帝本身就是造物主、启示者和救世主;世界本身具有被创造性和被救赎性,人本身具有被启示性、救赎性与被救赎性。因此,大卫之星只是一个象征,三者的关系并非是如图形所示的几何联系,其关系是相互的、复杂的。同时,在创造、启示和救赎之间本身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从时间上讲,三者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从三者的作用上来看,创造是基础,创造需要启示,启示是关键,同时创造和启示又都需要救赎,救赎是目的,因为只有在救赎中创造才最后完成,启示才最后实现。
从对“救赎之星”的解释不难看出,罗森茨维格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一开始就提出的目标,即摆脱对于死亡的恐惧,救赎就是完成这一工作的最终保证。谈论救赎是宗教的基本话题之一,由此,罗森茨维格过渡到了《救赎之星》的第三部,即涉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部分。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涉及救赎,为什么罗森茨维格认为犹太-基督宗教才是最终的归宿?通过考察古代亚洲的诸宗教(其中涉及了中国的宗教),他认为亚洲宗教中的神是僵死的、无生命的,极其容易走向宗教的反面即无神论;通过考察古希腊的宗教,他认为希腊的诸神虽然永生但却与死无关,因而也不能作为活生生的人的信仰;通过考察伊斯兰教,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成了的宗教,因而是僵化的、无法给予人以活生生的指导的宗教。总而言之,这些宗教形式都无法从当下的、活生生的人的具体经验出发,而犹太-基督传统则不同,它让永恒进入时间,从而实现人的救赎。不难看出,这种对于个体当下的经验的强调是《救赎之星》开篇所凸现的新思维的逻辑延伸。由此出发,罗森茨维格将这一选择的原因归结为个体经验,并进一步指出,虽然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建筑在个人经验基础上的,但两者又有所不同,即:犹太教是永恒的生活,而基督教是永恒的道路。所谓永恒的生活,意思是犹太人活在永恒的当下,外在于世界、国家的历史,上帝已经将救赎置于犹太人的生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高于所有其他民族,是其他所有民族的目标。所谓永恒的道路,意思是基督教是通向救赎的道路,它在历史之中,它负担着拯救、引导其他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责任。
总而言之,《救赎之星》以传统的象征性符号阐发的是罗森茨维格的新思维,是现代犹太哲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承先启后之作,它上承柯恩对于犹太传统的重视,又不囿于柯恩对于传统的理性化解释,以对个体经验的强调唤起了现代犹太哲学对于关系、对话等概念的重视,成为布伯、列维纳斯等人思想的先驱。在更广泛的哲学史上,罗森茨维格的新思维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方法,并辅以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对人类思想中非理性成分的重视,开启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先声。
本书的翻译过程可谓相当漫长。如果算上最早的准备工作,已有十余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关于现代犹太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亟待填补的大量空白,面对这种情况,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傅有德教授开始组织力量,有计划地翻译犹太哲学与宗教名作,罗森茨维格的《救赎之星》就是其中的一部。这部著作的翻译一延再延,直到今天才得以告竣,其中原委颇为复杂。首先是因为原书遣词怪异,行文似“天马行空”,致使原本深奥的文义更加难以把握,使译者望而却步;其次是因为译者的更换,原来的两位译者先后退出,新的译者又需要时间熟悉作者的思想和文本。目前的译文是由傅有德和孙增霖合作完成的。其中,傅有德负责本书第三部的翻译及全书的统稿工作,孙增霖完成了第一、第二部的翻译。
 对于罗森茨维格这样的颇具诗人气质的哲学家,我们在充分感受到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恣肆汪洋的文字魅力之余,也深感翻译上的困难重重。因此,只能尽自己的努力使译文尽可能地贴近原文,个别地方实在无法用简单的汉语表述的就用附注的形式稍加解说,力图给读者一个清楚明白的交待。当然,尽管我们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可以预料的是译文中仍然会有许多疏漏、不足之处,在此请各位方家不吝指正,以使我们有机会在将来进一步完善这项工作。
对于罗森茨维格这样的颇具诗人气质的哲学家,我们在充分感受到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恣肆汪洋的文字魅力之余,也深感翻译上的困难重重。因此,只能尽自己的努力使译文尽可能地贴近原文,个别地方实在无法用简单的汉语表述的就用附注的形式稍加解说,力图给读者一个清楚明白的交待。当然,尽管我们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可以预料的是译文中仍然会有许多疏漏、不足之处,在此请各位方家不吝指正,以使我们有机会在将来进一步完善这项工作。
译 者
2010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