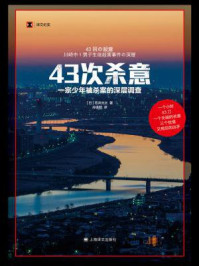小时候缺乏和大自然的直接联系。有同学把天牛和蝉一类的昆虫抓到教室里,都会大吃一惊。上学路上有几个水坑和土堆,就觉得是崇山峻岭。南方的家乡有山有水,但自己频繁地草率地路过,不太花时间去欣赏,进步的车轮好像不经过那里。
那时候觉得自然就是自然而已。
去年被困在了北京,于是今年回家过年的愿望到达了顶峰,不论如何都要回去。此前两年,情感在疫情中被压缩又被抽空,很少出现这种纯粹的向往之情。回去发现马路下面都被挖空,做成地下商场,郊区的山都被铲平,要建新区,钢铁厂的大烟囱和江水一样,日夜不息。我目睹这些变化,却不真的在意,也不介意小镇青年啊乡愁啊这些越来越被贬低的坏词。去他们的,我只想回到家人身边,紧紧抓住吃每一道好菜的权利。
在大的时代奔腾里,小地方给我们安慰。
书店搬家后就有了露台,我抢了几个角落,作为植物的培养基地。种的植物都很平常,月季、茉莉、琴叶榕、仙人掌一类,种法也很粗放,经常被同事嘲笑,怎么那么不修边幅。有的同事也会把他们的植物搬出来,离职后大多便不带走,我自然就收养过来。别的同事们再看到我给它们浇水,渐渐不再面露诧异的表情,好像接受了我开这样的小差。慢慢地,人换了几茬,花盆也比植物多,我不再新添什么,光照顾比较能忍耐的那几株。
有的植物长得快,被阳光一照,叶子和花都日新月异,这样反而没什么成就感,人力所能做的,只是保证水肥不停而已。还有的,一年到头没什么动静,很长时间才抽出一片叶子,或是一朵花,这时候只能付出日复一日的等待,情感劳动的含量还更高。有一株柠檬需要人工授粉,我试了几次都不得要领,偶然一次似乎成功了,经过几周的缓慢生长,最后竟然长出一只鸡爪般的佛手柑。这算是这个露台上几年来最大的新闻。
我把这点简单重复的劳动藏在工作里,就像是植物的呼吸。
把几件不搭界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说,像是自己思维上的一个毛病。在不同的问题上腾挪,会带来暂时的轻松,也有可能提供另类的灵感,帮助我们从沉痛的现实里起飞。我从记忆里偷来这几个瞬间,也是想给眼下越来越喘不上气来的生活找办法,绕开那些逻辑上严丝合缝的二元对立。不管是公园和野外,还是家乡与露台,本质上都不构成什么像样的宣言或者反对,大概只算一口叹息、一个转身、一次闭眼,把注意力从那些效率惊人、尺幅巨大的事物上移开。往回看,向下走,获得片刻的清明。
有一年的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上,陈丹燕老师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她去过那么多地方,得了那一年的旅行写作奖,在台上却说,“世界其实是一个小地方”。一个当然是鼓励我们不用怕,尽管去冒险,再有一层更打动我——也可能是我的演绎,新知其实就那么多,也没那么难获得,不比自己心里的小世界更难撼动。
世界首先内在于自己,然后才大于自己。
关于世界每况愈下的描述已经很多了,很难在这个方面再添新意。战争再次出现,每一个人都开始和仇恨沾边,而锁链并没有断,同时铐住了解铃和系铃人。之前以为乱象只是话语的分裂,现在看是话语的消灭,不仅让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更让你们停止靠近,停止了解。的确像是回到了一个世纪之前。于是想起茨威格所经历的19至20世纪的版本,“我们竟将如此层出不穷的变故挤塞到一代人生活的短暂时间之内,那当然是一种极其艰难和充满险恶的生活——尤其是和我们的祖先们的生活相比”。
这种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停止对新世界的赞美,事实证明它未能提供更多生存的可能。但是接下来去哪里呢?并没有人知道。可见的出路大多只是故伎重演。只好先允许自己叹息、转身、闭眼,在更小的尺度上生存,同时渴望在心里凿出一条很深的地道,通往这世上最不可撼动的那一层。在公园里,我最喜欢的事之一,就是对着那些几百岁的老树发呆,它们什么都不说,却一定什么都懂,真想喊它们起来做个访谈。
这时候觉得自然是对扭曲世道的更正。
于是,单读的理念也应该改为,在狭隘的世界,做个宽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