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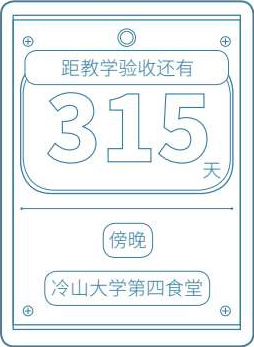
“啧啧,这社会真是疯了,要我说啊,咱这地方就是因为没宗教,所以才有这么多没底线的事。”在傍晚的学校食堂,秦子一边用筷子挑面,一边用手机刷着社会新闻,感慨道,“一个人要是被宗教约束着,就不会做那么多坏事。”
坐在对面的荒白教授看了秦子一眼,没说话,低头吃饭。
秦子捕捉到了教授一闪而过的神情,放下手机笑问:“怎么?您不同意?现在这社会这么堕落,您还一天天地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要热爱这里。我问您,您自己热爱这里吗?”
教授听出了秦子语气中的挑衅,抬头平静地说:“我热爱啊。”
“那您不妨具体说说,您到底热爱这片土地的什么啊?”
教授放下筷子,扶了扶眼镜。“好,就从你刚才提到的宗教来说吧。我热爱这里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片世俗的土地。”
“呵……”秦子发出不逊的声音。
教授问:“秦子同学,你知道什么状态下的人会倾向于拥抱宗教吗?”
秦子摇头。
“生活中充满不确定性的人会拥抱宗教。当一个人被各种不可抗力左右时,他就会去宗教里寻找庇护,从神仙那里寻找一个笃定的答案。比如,南方某个沿海城市经济发达,思想开放,曾经引领发展潮流,但求神拜佛的风气旺盛,你知道为什么吗?”教授说到这儿,探过身子,压低嗓音。
“不知道……”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过去这个沿海城市里生活着很多渔民,而在技术条件落后的时代,出海打鱼非常危险。渔民有句话叫‘强山不强水’,意思是爬山遇到困难尚且能勉强一下,但在水里就没办法了,淹死就是淹死了。在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下,底层渔民倾向于向宗教寻求保佑,这就给这个城市带来了自下而上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在于,这个城市后来虽然发展起来了,但没什么实业,立足之本是金融和贸易,而这些很容易被不确定性因素左右。很多当地老板赚了大钱,但却没有安全感,因此他们格外在意宗教。这些占据大量资源和话语权的精英一旦热衷于求神拜佛,整个社会的风气就又被自上而下地影响了。”教授在说这些时,一直盯着秦子,“最终,这个现代化的城市里弥漫着求神拜佛的风气,大街上都能看到算命先生的门前排起长队。”
秦子抬手做了一个请继续的手势。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除此之外,一个人对宗教的态度会受到遗传的影响。”
秦子一愣。“什么?这也能遗传?”
教授点头。“是的,双生子研究表明,基因遗传对一个人看待宗教的态度有很大影响,有时甚至是主要的因素。”
“这……”
见秦子的气势已经弱下来,教授继续说道:“你知道为什么中国是个世俗国家吗?”
秦子探过身去。“不知道……”
教授低声说道:“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我的推测,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有着悠久的农耕传统。”
“您又来了,讲个道理要先绕八百里……”
“在遥远的古代,世界上有三种主要生产方式,分别是农耕、游牧、渔猎。虽然我们总说过去的传统农业靠天吃饭,但就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来说,农耕是最强的,渔猎是最弱的。”教授用筷子指着自己碗里的米饭说,“如果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越多,人就越倾向于拥抱宗教,那么生产方式最稳定的农耕就是最世俗的。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
秦子看着教授,不说话。
教授说:“刚才我提到人对宗教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由遗传决定,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推论,一个民族长久以来的生产方式会通过历史的筛选效应影响这个民族的宗教取向。对华夏民族来说,农耕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民间虽然有各种信仰,但世俗力量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这是因为在相对稳定的农耕文明中,劳动力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被内卷化的精耕细作瓜分干净。在这种情况下,把精力和资源过度投入宗教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这与农耕这一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是相悖的。”
秦子眯起眼。“我怎么觉得您说得这么玄乎呢?”
教授说:“你看过《齐民要术》吗?你要是看过,就会发现贾思勰的这本农书记载着大量农业精耕技术,当时的农民在仔细摸索各种轮作方式,还有播种密度和产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南北朝也正是中国的精耕技术逐渐成熟的阶段。但你别忘了,彼时也正是中国的世俗力量和宗教势力殊死搏斗的时代。”
秦子猛然一惊,道:“对啊!三武灭佛……”
教授的声音更低沉了:“所谓灭佛战争,其实从逻辑的底层来看,根本就是世俗政权和宗教团体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源的争夺。秦子,你要庆幸中国的世俗力量取得了胜利,否则,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时代,中国是否会变成一个超大号的复活节岛也犹未可知。”
听到这儿,秦子的冷汗都下来了。“我看过戴蒙德教授的《崩溃》,波利尼西亚人因为宗教狂热,最后把自己的家园变成了……”
教授的语气仿佛是在讲恐怖故事。“是的,变成了一个荒芜的食人乐园。”
秦子沉默了。
教授缓缓吐出一口气,说:“中国之所以是个世俗国家,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建立在历史悠久的农耕传统之上,勤劳务实的基因在这里传承扩散,崇奉鬼神的血脉则处于边缘,这就是为什么‘子不语怪力乱神’且‘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会被历代中央帝国推崇备至。”
秦子说:“可是有些中国人也信鬼神啊,比如说……”
教授举手打断。“当然是有的,但那只是主流世俗之外的杂音,中国历史上真正完全陷于宗教的中央政权只有一个,就是上古时代的殷商。”说到这儿,教授拿出手机给秦子看了一张照片。
秦子吓了一跳。“这是……?”照片里,一件青铜器里装着一颗人头。
“这是一种叫甗(音同演)的炊具,殷墟出土……这个残暴的王朝必须毁灭,否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长久地被宗教束缚,颤抖着匍匐在鬼神的脚下。”教授举着手机意味深长地说,“牧野之战后,中国人逐渐摆脱了对鬼神的疯狂崇拜,转而用礼制去构建一个世俗社会。在之后3 000多年的时间里,世俗力量一直死死地压制着宗教势力,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政教合一的全国性政权。”
秦子说:“也不一定吧,教授,我记得清帝国的国教就是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
教授点头道:“《啸亭杂录·章嘉喇嘛》提到,清朝之所以宠幸黄教,也就是格鲁派,并不是真心崇奉其教义,而是蒙古诸部对其崇信已久,朝廷这么做可以赢得信众的忠诚,以巩固边疆。尊重但保持控制和审慎便是中国世俗王朝对宗教的主流态度,这为中国孕育了深厚的世俗传统。你很难想象,在政教合一的国家,人们能高喊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口号,当然,‘赛先生’也没有辜负我们,生产力的爆发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便是‘赛先生’给这片世俗土地的回报。”

图1 装着人头骨的甗
秦子不再说话。
教授收拾碗筷,一边起身一边说:“至于你之前说的道德和宗教之间的话题,我觉得两者之间未必有什么直接关系。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在于是否信仰宗教,更多地在于其自身的选择。秦子,你知道在我看来,什么是最大的道德吗?”
秦子摇头道:“不知道。”
“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丰衣足食,生活幸福,就是最大的道德。”说到这儿,教授指着秦子的碗,“我看你就是吃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