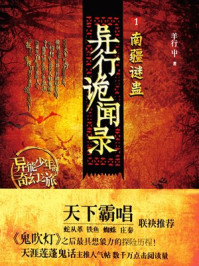民国十六年(1927年),天津。
嘹亮的小号声响起,乐队仿佛被打了一针吗啡,立时兴奋起来。尤其坐在角落里的两个贝斯手,如从冬眠中苏醒的动物,到了春意盎然的发情期一般。他们也不知从哪儿掏出沙锤和手鼓,随着节奏左右摇摆,胖乎乎的身子竟也扭得像弹簧一样。与此同时,一个英国小伙迈着轻快的步子踏上舞台,开始演唱《花生小贩》
 。
。
他头戴巴拿马草帽,穿着肥大的黄色短袖衬衫、白绸缎裤子、帆布马鞍鞋,为了增强表演效果,还在脸上涂了鞋油,试图搞出在沙滩长期日晒的感觉,不料颜色涂得过重,适得其反,整张脸都黑了。他嗓音也很一般,远远称不上甜美,但载歌载舞非常卖力,虽说有些高音唱不上去,依旧扯着脖子在努力地唱着:“Mani……Mani……”
不过没关系,这蹩脚的表演足以令舞厅里的年轻人沸腾。尤其是在被迫欣赏了好几首男低音之后,无论是来自泰晤士河畔、密西西比河畔的小伙,还是来自塞纳河畔、莱茵河畔的姑娘,都感到生无可恋,所以对他们而言这首跑调的哈瓦那民歌已是天籁之音。姑娘小伙们露出笑容,跟着音乐手舞足蹈。不远处,他们的父母、姨妈、姑妈之类的长辈们却面沉似水,正用谴责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仿佛在感叹——上帝啊!这些年轻人脑袋进水了吗?怎么喜欢殖民地的野蛮歌舞?
没办法,青年人和老年人永远玩儿不到一起,分歧总是难免的。何况这里既不是英国伦敦,也不是法国巴黎,更不是哈瓦那的海滩,而是中国天津。
对异国人士而言,租界里衣食住行样样齐备,唯独西式娱乐场所不算多,要想不分国籍、不论年纪且不失身份地找点儿乐子,大伙只能在同一幢建筑里将就。这家俱乐部有二十多年历史,名叫“康科迪亚俱乐部”,但是天津人更习惯叫它“德国俱乐部”。因为它坐落于德租界,原本只对德国侨民开放,直到九年前德国在世界大战中落败,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德租界,将其改为特别行政第一区,这家俱乐部也收归政府,随即转租给一位俄国商人,从此开始全面对外营业。
为了吸引更多客人,俱乐部的经营者煞费苦心,在后院增添了网球场、旱冰场,还在周末开办舞会,聘请乐队伴奏,喜欢唱歌的客人可以上台一展歌喉。不过众口难调,乐队既要照顾老爷太太们的艺术情趣,又要给姑娘小伙们送上欢乐,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有人戏称这里的氛围就像美国的两党选举,每当有一半人欢呼雀跃,另一半人准在咬牙切齿。好在楼上另有其他娱乐项目,台球、扑克牌、国际象棋,甚至还有百家乐、轮盘赌。当老绅士们脆弱的耳朵和心脏忍受不了新潮音乐时,他们可以转移到别的房间,或者到露台上吸支烟,顺便聊聊生意——俱乐部不仅是娱乐中心,也是社交中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家俱乐部已不再属于租界,但外国客人仍占绝大多数。没有任何规定限制中国人,可是进入这里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套体面的西装,而且西装口袋里还得塞着足够多的钞票以及一张证明自己很有地位的名片。这条不成文的规定把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挡在了门外,不过仍有一些符合条件的中国人来——这不,当歌舞进行到高潮时就有两个中国青年手拉手走进来。
两人都是男性,都在二十岁左右,身材相仿,穿着同样的西装,系着同样的领结,扎着同样的皮带,就连皮鞋尺码也一样,确切地说这两套服饰只属于其中一人——利盛商行的少东家沈海青。
利盛商行是全国知名的贸易行,其业务涉及外贸、金融等领域,在天津的影响力足可与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跨国公司比肩,在上海等地也设有分支机构。利盛的老板郑秉善出生于江浙的诗书世家,年少时被清政府选中,派往美国留学。他勤勉刻苦成绩优异,于耶鲁大学毕业。归国后曾经效力洋务机构,后来不满清政府腐败,选择弃官从商,和妻弟沈乃器一起创办了利盛商行。郑秉善不但有超凡的商业头脑,而且为人豪爽、交际广泛,无论身处南方还是北方,甚至在国外,都是政界、军界乃至工商业巨头们的座上客。可惜郑家财齐人不齐,郑秉善中年断弦,一直没有续娶,如今年逾半百无儿无女。妻弟沈乃器在一场海难中与妻子双双殒命,只留下一个独生子,便是沈海青。
作为郑秉善唯一的外甥、利盛商行未来的继承人,沈海青享受着大少爷的待遇,在新式学堂读书,喝过两年洋墨水,说一口不算太糟糕的外语,兜里总是揣着数目不小的零花钱,出入高级娱乐场所。
至于与沈海青同来的另一个小伙,身份就有些尴尬了。他是个相声艺人,自幼无父无母流浪江湖,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晓得,如今在“三不管”卖艺,认识的人都称呼他的艺名“小苦瓜”。
海青与苦瓜因相声结识,又莫名其妙卷入一桩连环杀人案,阴错阳差地破了案,稀里糊涂成了好朋友。有钱人家的少爷和穷说相声的交朋友,这未免有些惊世骇俗,但这世上奇怪的事有很多,比如两位男士当众手拉着手,这景象就很引人瞩目。
其实海青也不想拉着手,但没办法,只有这样才能让苦瓜摆脱玻璃旋转门——当这小子转到第四圈的时候,门童打量他俩的眼光已经不对劲儿了。
“等等!”苦瓜抱怨道,“我还没玩够呢!再转一圈……”
“再转就晕了。”
“我学过翻跟头,晕不了。”
“你不晕,我晕!”
苦瓜被海青拉着紧走几步,终于把旋转门忘到脑后,但紧接着他又被眼前的事物吸引——真皮沙发、弹簧地板、石膏雕塑、水晶吊灯、绚丽的灯光、西式的乐队,还有数不清的各色头发的外国人……“三不管”的穷艺人哪儿见过西洋舞会?
他搞不清状况,瞠目结舌半晌,忽然一拍脑门儿:“明白啦!他们在办喜事,不是给老人庆寿,就是娶媳妇儿。”
“不对。”
“那就是办丧事,有人死啦!”
“别胡说……”
“谁胡说?我懂!吹唢呐,唱大戏,肯定是红白事。”
“不是唢呐,是小号,那人也不是在唱戏……”
“怎么不是?黑脸的,包公戏。”
“外国哪有包公?包龙图打坐在哈瓦那吗?那是个白人,我猜他是想把皮肤弄成古铜色,不小心把颜料涂多了,变成黑人了。他在唱歌,让大家跳舞,你没看见他们都很高兴吗?”
“哦!老喜丧!丧事喜办……”
“别瞎嚷!”海青一把捂住苦瓜的嘴,“听好了,咱们是凭我舅舅的名片才进来的,要是胡说八道被人家轰出去,不单我跟着你丢脸,舅舅的名誉也受损,以后我们还怎么来?”
“知道呀!”苦瓜推开他的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舞会,找乐子,这就跟看戏、看电影,或者到‘三不管’听你说相声一样,都是消遣。”
“洋人真怪,咱们都是看别人演,他们却自己蹦蹦跳跳。”
“舞会也是一种社交。”
“什么跤?”苦瓜不懂“社交”这样的新名词,“摔跤吗?他们都站着,没瞧见有摔躺下的呀。”
“我说的是社交!就是交朋友,通过跳舞结识朋友。”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吗?”
“可以,但是……”
“我也凑凑热闹。”
不待海青解释完,苦瓜已经一猛子扎进跳舞的人群。他哪会跳拉丁舞?跟着节奏手忙脚乱地蹦了两下,索性甩开胳膊,迈开步子,扭起了大秧歌。秧歌的动作很大,三扭两扭就碰到旁边一个金发青年。那外国小伙不禁抱怨了两句,可是一看苦瓜怪异的动作,不禁哈哈大笑,还招呼朋友也来看。不一会儿工夫,周围十几人都在“欣赏”苦瓜的舞姿,一开始他们只是嘲笑,可渐渐觉得这傻里傻气的舞蹈挺有趣,而且很容易,竟也模仿着扭起来。苦瓜更加自我陶醉,甩开膀子越扭越起劲儿,就像领舞一样。
海青看不下去了,扯住苦瓜胳膊,不由分说把他拖出人群:“我得找根绳子把你拴起来,别再给我丢人现眼啦!”
“这有什么丢人的?跳舞嘛。”苦瓜意犹未尽,“你这西装我穿着不舒服,要是穿大褂我扭得更好,还能翻跟斗呢。”
“好好好,你的跟斗翻得比孙悟空还好,不过现在你要克制住翻跟斗的欲望。我带你过来不是为了玩儿,你不是说想见见那位通灵大师吗?他就在那边……”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上星期沈海青陪同舅舅参加舞会。郑秉善是为了结交一位新上任的德国外交官,听说那位外交官有个女儿,所以叫海青来给人家当舞伴。不料那位小姐没来,生意的事海青又不感兴趣,便在俱乐部里闲逛,偶然遇到一位通灵术大师。这位大师与众不同,他的通灵术并非与死人的魂灵沟通,而是声称能找到心灵相通的两个人。托苦瓜之福,海青见识过相面算卦的勾当,自然嗤之以鼻。大师却信誓旦旦,摊开一副扑克让他抽,海青随便抽了一张,大师看后说有个戴维斯小姐与他心灵相通,并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海青会说英语,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电话,还真找到了那位戴维斯小姐,竟然隔空猜到他摸到的牌是红桃4。海青激动不已,与那位小姐探讨了生日、命运、星座、幸运数字等有趣的话题,颇有找到知己的感觉。
此后三天郑秉善赴德国谈一笔生意,没了舅舅的管束,海青又可以随心所欲。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三不管”找苦瓜玩儿。提及通灵术的奇遇,海青十分笃定,苦瓜却不信,一口咬定是“腥的”
 ,还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色唐金”
,还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色唐金”
 ,于是海青给苦瓜换上自己的西装皮鞋,把他领进俱乐部。
,于是海青给苦瓜换上自己的西装皮鞋,把他领进俱乐部。
此刻苦瓜顺着海青手指的方向望去,见一个男子坐在大厅角落的沙发上——此人中等身材,着黑色晚礼服,戴一顶很夸张的大礼帽,还套着高领披风。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他戴着黑布面罩将上半张脸遮住,只露两只眼睛,不过从高耸的鼻子、棕色的眼眸以及两撇棕色小胡子判断,这一定是个外国人。
“就是这家伙?”苦瓜有些疑惑,“怎么瞅着像变洋戏法儿的?你没搞错吧?他是‘金字’的,不是‘彩字’的?”
“我也搞不清这属于戏法儿还是算命,总之很灵验。”
“没关系,甭管土布还是洋布,反正就是这块料!我就不信外国跑江湖的有什么不一样。”
两人渐渐凑近,见那位大师面前摆着一副扑克牌,印着花色和数字的正面朝下,扣在桌子上。旁边有几个围观的人,其中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姐正和他交谈。小姐说着从牌堆里抽出一张黑桃K。大师接过那张牌贴在额头上,做闭目冥想状,过了片刻睁开眼对金发小姐说了几句话。
“他叽里呱啦说的什么呀?”苦瓜没上过学,连中国字都写不出几个,哪懂外语?
海青给他翻译:“他说此时此刻有一位姓威廉姆斯的先生跟你心灵相通……”
“威什么玩意儿?”
“威廉姆斯,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姓。”
“哦,是个复姓。”
“随便你怎么想吧。”海青懒得再跟他解释,“他说威廉姆斯先生和这位小姐心意相通,知道小姐心中所想,能在电话里猜出小姐抽到那张牌的花色和数字。”
“哦?他通过电话叫别人猜牌,还让客人自己打这通电话,这把戏我还是头一回见。”
“所以才神奇嘛。”
这时又见大师凑到金发小姐耳畔低声嘀咕了几句,苦瓜不禁蹙眉:“说悄悄话,这我可真不晓得他玩儿什么花样了。”
“我大概能猜到,他会告诉那位小姐威廉姆斯先生的电话号码,并嘱咐不能透露给其他人,而且只能拨打一次,否则就不灵验了。上星期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金发小姐似乎不太相信大师的话,但也礼貌性地道谢,一脸怀疑地朝吧台走去——那边正好有两部电话。大师没有把黑桃K放回牌堆里,随手抛到一边,继续跟其他人攀谈。随即又有个胖胖的法国贵妇凑上去抽牌,这次是方片A,通灵的过程跟刚才一样。海青翻译道:“他说有一位赵小姐跟太太您心灵相通……”
“赵小姐?还有中国人?”
“当然。毕竟这儿是天津,多数电话号码属于中国人。”
胖妇人也从大师口中得到号码,兴致勃勃地朝另一部电话奔去,一时间没人再抽牌,大伙的目光都投向打电话的两人。大师俨然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仰坐在沙发上,捻着油亮亮的小胡子。片刻工夫,只见金发姑娘拿着听筒的手颤抖起来,放声大叫:“Oh my gosh!(我的天哪!)”再看那位胖妇人,稍等片刻也拨通了,没说两句便一脸喜色——显然两人都灵验了。
众人亲眼得见,跃跃欲试者多起来,这时有个穿绣花旗袍、满身珠光宝气的中国妇女被两个朋友推到前面。大师见她有点儿羞涩,起身脱帽致意:“太太您好,不要怕,这很有趣……”
“咦?这家伙会说中国话。”苦瓜感到惊奇。
海青也很意外:“不知道呀,上次我见他是外国人就用英语和他交谈,没想到他会中文。”
“说得还挺流利,不过……”苦瓜仔细听了几句,觉得大师说中文的口音怪怪的。
这次有了变化,大师没有立刻通灵,而是说起了恭维话,称赞中国女人多么漂亮,中国文化多么悠久,中国菜肴多么美味,直至金发姑娘放下听筒,空出那部电话,他才请中国太太抽扑克牌。结果是黑桃2,大师将牌贴在额头,沉默片刻道:“有位奥斯卡先生跟您心灵相通,他能猜出这张牌……什么?不!打电话又不是幽会,我不会告诉您先生……您不会外语?别担心,与您心意相通的人肯定也会说中国话。别犹豫了,这是一种心灵交流,兴许能给您带来好运,我告诉您奥斯卡的电话号码,但这关乎隐私,您不能透露给别人……”他在中国太太耳边嘀咕了一阵,又把黑桃2抛到一旁,于是中国太太也在他的鼓励下去打电话。
海青见苦瓜瞧得出神,用胳膊肘捅了捅他:“看三遍了,发现毛病没有?”
“没有。”
“哈!你也有甘拜下风的时候。”海青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
“谁说我服他?”
“你不是找不出毛病吗?”
“别急,兔子尾巴长不了,早晚会露出破绽。”
两人不再交谈,认真观察大师。想尝试的客人一个接一个,大师却不慌不忙,电话只有两部,他总是等空出一部电话再接待下一位客人,每次都灵验。有人抽到梅花10,他说心灵相通的是施先生;有人抽到黑桃Q,心灵相通者是沃德先生;抽到红桃10,找琼斯女士;抽到梅花5,找周先生;抽到方片J,打电话找褚小姐……
“哼!”苦瓜突然发出一阵冷笑,“总算叫我看穿啦!我就知道他这玩意儿不地道。”
海青一怔:“你发现什么了?”
苦瓜没理他,径自走到桌前,抱拳行礼:“辛苦辛苦!”
海青差点儿笑出声——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这“辛苦”二字是江湖人“盘道”的开场白,外国人怎会懂?
大师有些迷惑,迟缓片刻才回答:“晚上好,先生。”
苦瓜一点儿也不客气,伸手将桌上的扑克牌一翻,从里面挑出一张梅花3,递到大师面前。大师见他破坏规则,却也没说什么,接过那牌正要往额头上放,苦瓜笑呵呵道:“别急!先让我猜猜看,是不是有位姓杨的先生与我心灵相通?”
大师握着扑克的手定住了,凝然注视着苦瓜。
“猜错了?那再换一张。”苦瓜又拿起一张方片8,“这张是叫我找一位姓王的小姐吧?”
大师依旧沉默,虽然戴着面具看不见表情,但他棕色的眼眸游移不定,显得有些慌张。
苦瓜不依不饶,晃着手中的牌笑道:“快告诉我王小姐的电话号码吧,我都等不及了。我不和女士们抢那两部电话,可以去隔壁的西餐馆借电话。”
大师终于有了反应,他把牌往桌上一丢,揉揉太阳穴:“抱歉!我有些头晕,通灵术很耗精神,该死……哦,我是说恐怕得回家休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Ladies and gentlemen(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安……”说罢他连扑克牌都没收,把礼帽往头上一扣,站起身快步离去,那急匆匆的背影宛如一只受惊的黑兔子。
围观之人不明所以,都觉得扫兴,瞥了苦瓜几眼各自散去。海青也搞不清状况:“怎么回事?”
“我揭了他的门子,还不赶紧溜?”
“你是说他是……”
“‘腥’的!一腥到底,假到不能再假啦!”
海青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
苦瓜满脸不屑:“很简单,电话另一边是他同伙,猜扑克靠的是暗号,只要记熟就行。扑克牌有黑桃、红桃、梅花、方片四种花色,每种十三张,每张的花色数字都有对应的姓氏,刚才我留心观察,早就发现门道,不过是想多看几次确认一下。果不其然,有人摸到方片A,他说拨电话找赵小姐,有人摸方片J,他说拨电话找褚小姐,拿到梅花10就找施先生。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什么一目了然?越听越糊涂。”
“笨蛋!张王李赵这样的姓满大街都是,褚姓、施姓却不多见,怎就偏巧赶上这么两位?我虽没念过书,不会写字,但《百家姓》总还听说过,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褚姓正好排第十一,扑克牌里的J也是第十一;方片A就是方片1,赵姓也排第一,这难道是巧合?施姓排在第二十三,如果减去前十三个姓,正好是第十,刚才那张牌就是梅花10。很明显,方片的牌都是女的,十三张牌对应从赵到蒋这前十三个姓,梅花是男的,十三张牌对应的是从沈到曹十三个姓,完全按《百家姓》顺序排列。”
“原来如此。”海青渐渐领悟——窥破机关似乎不难,可谁又能有这奇思妙想,把一个外国灵媒与中国的《百家姓》联想到一起?
苦瓜又道:“同样的办法,黑桃、红桃对应的是洋人,我不懂洋人那些乱七八糟的姓,但也一定有规律吧?”
“让我想想。”海青低头思索着,“我摸到红桃4,电话打给戴维斯(Davis)小姐,摸到红桃10找琼斯(Jones)女士,黑桃2是奥斯卡(Oscars)先生,看来红桃对应女性,黑桃对应男性,按26个英文字母排列。不过……”黑桃K怎么会是威廉姆斯(Williams)先生?最后一张不应该是Z为首的姓氏吗?黑桃Q是沃德(Ward),怎么都是W字头?对啦!U、Y、Z打头的姓非常罕见,X打头的姓根本没有。俱乐部里外国人比中国人多,说出中国罕见的姓客人不懂,可要是说出生僻的欧美姓氏就容易惹人怀疑。所以他把U、X、Y、Z四个字头舍去,在前面另找四个字头,编出威廉姆斯和沃德这样一长一短两个姓就能把相邻的两张牌区分开。想到这儿,海青不禁欣喜,就像破解了什么重大谜案一样,“我明白啦!果然很简单,就是按照字母排序……可要是摸到两张王牌呢?”
苦瓜微微一笑:“我也不知道,但一定有办法区分,天津有那么多洋人,再挑两个日本人的姓也不是难事。”
“哈哈,有道理!”
“弄明白暗号剩下的事就好办了,电话另一头的人跟他是同伙,打电话的客人说找某女士、某先生,等于自己报出暗号,那边就知道客人拿的是什么牌了,当然百试百灵。其实他告诉众人的电话号码只有俩,两个号码交替使用,所以才悄悄说,还嘱咐不能告诉其他人,就是怕大伙发现号码一样。凡是抽过的牌他都暂时放一边,以免碰巧连续抽出同一张,那会连续报出同一个姓,引人怀疑。他一边装神弄鬼,一边留心观察,等周围的客人走得差不多了,换一批新客人时再把那些牌放回去。至于另一头的同伙,至少是两男两女,既会中国话又会外国话,就守在两部电话机旁……”
“所以当你说要借别处的电话时,他自知情况不妙,两个号码都占线,第三人拨号肯定打不通,而且密码也被你看穿,他这戏法儿变不下去了,只能溜之大吉。”
“没错。我觉得这办法一点儿也不高明,竟然需要四个伙计、两部电话,太麻烦啦!凭这把戏到‘三不管’‘撂地’,没半天工夫就会被人识破,也只能在这种地方骗骗你这样的少爷秧子。”
海青白了他一眼:“我觉得关键是你们‘三不管’没有电话。”
“我们不稀罕。”苦瓜嘴硬道,“挂上电话线,翻跟头不方便。”
“你怎么总想翻跟斗?”
“叫你气的!亏你还跟我混过,这么简单的把戏都能把你唬住,还什么铜铃术、铁铃术的,丢不丢人?实话实说吧,你叫那家伙骗了多少钱?”
“没有啊。”
“什么?!”
“一分钱也没骗走,他耍这套把戏根本不找客人要钱。”
苦瓜的笑容倏然收敛:“你要小心了。”
“小心什么?”
“骗局没结束,他肯定还有其他手段,你多留神吧。”
“不会吧……”
苦瓜一脸严肃道:“这可不是开玩笑。但凡江湖作艺的,无论哪国人,不是图名就是图利。那家伙为的是什么?说图名,他弄块黑布遮着半张脸,谁晓得他是谁?怎么替他扬名?说图利,他又不收半文钱,这合乎情理吗?你仔细想想,四个同伙,两部电话,他下的本钱可不小,既不‘置杵’又不‘扬蔓儿’,吃饱了撑的呀?老话说得好,事出反常必有妖,他肯定还有别的幺蛾子。”
“未必。可能是闹着玩,他们外国人喜欢‘恶作剧’,比如我跑去跟你说相声,不也是纯粹‘玩儿票’,不图名不图利吗?”
“不一样!如果纯粹为了玩,应该轻松自在,为什么戴面罩?难道怕见人?就算是故作神秘,机关被我点破,摘下面罩哈哈一笑也罢了,为什么夹着尾巴逃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狼狈而逃必有亏心的地方。据我的经验,‘三不管’里凡是表面不要钱的买卖,‘开杵门子’
 来比明着要得更厉害。杀人不动刀,都是‘绝户杵’
来比明着要得更厉害。杀人不动刀,都是‘绝户杵’
 !你们文明人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跟吃饭有关系……”
!你们文明人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跟吃饭有关系……”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对!甭管午餐还是晚餐,没有免费的,也包括早点。‘杵门子’埋得越深,打的‘杵’越多,这里面肯定还藏着其他门子。我不晓得你们电话里说些什么,反正得多留神。虽说你家有钱,扔个百八十块银圆不在乎,也不能叫人当猴耍。你要是再遇见这个人,千万别理他!”
“好,我听你的。”海青点点头。
苦瓜这才稍放下心来:“走!咱接着跳舞。”
“跳可以,你别再扭秧歌了!”
“我不会他们的舞。”
“我教给你……”
两人正要往舞台方向去,忽听见有人呼唤:“海青,是你吗?”
海青扭头一看:“埃里克!”
来者是个外国人,个头不高,棕色头发,约莫二十岁,却已有些谢顶,前额光秃秃的,但是身材非常匀称,脸上泛着健康的光芒。海青见到他非常高兴,冲上前给个拥抱:“没想到是你,我们的大英雄凯旋了!”
“好久不见。”这个外国人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我算什么大英雄?太抬举我了。”
“你现在是世界名人!”
“嘘!别声张,我还真怕有记者认出我,很麻烦的……这位是你朋友?”外国人的目光转向苦瓜。
“哦,他是……”海青心里犯难,怎么介绍呢?苦瓜究竟姓什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难道说姓苦?海青灵机一动,“是我的好哥们儿,你就叫他‘曼伦’(Melon)就行。”
苦瓜一愣,朝海青咬耳朵:“我怎么叫曼伦?”
“这是你的英文名字。”
“什么意思?”
“就是瓜。”
“呃,随便吧……”苦瓜含糊着答应,想要抱拳行礼,忽然意识到应该用新式礼节,于是伸右手和那外国人握了握,“您好。”
“非常荣幸。”外国人握手的力道很大。
海青拍着外国人的肩膀,带着一脸骄傲的表情介绍道:“曼伦,你今天算是大开眼界啦!这位也是我朋友,他叫埃里克·利迪尔,是奥林匹克冠军。”
“什么军?”苦瓜没听明白,“当兵的?”
利迪尔一头雾水:“我没参军啊。”
海青对牛弹琴很是扫兴,赶紧解释:“他不是军人,是奥林匹克冠军,运动会,运动!”
“哦……”苦瓜笑了,“当官的。”
“不。”利迪尔皱起眉头,“我不从政,不感兴趣。”
海青一脸尴尬:“抱歉,恐怕咱们有点儿语言障碍,稍等……”忙不迭把苦瓜拽到一旁,“不懂就别瞎说,好吗?”
“运动不就是当官吗?”苦瓜眨了眨眼,“我常听说,某人想当官就花钱运动运动。”
“不是一回事。埃里克不喜欢政治,跟当官的没丝毫关系。他虽然是苏格兰人,但出生在天津,还有个中国名字叫李爱锐。他喜欢体育,跑得很快。”
“哦?”苦瓜眼睛一亮,“跑得快?比我还快吗?”他少时流浪江湖曾以偷盗为生,有一身飞贼的本事,虽然现在不再做此勾当,但自信跑得很快。
海青笑了:“他肯定比你快。埃里克三年前参加巴黎奥运会,在400米比赛中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
“什么意思?”
“他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之一,绰号‘飞毛腿’。”
“我不服,现在就跟他比比……”
“求求你,别再惹是生非了。”海青简直欲哭无泪,正好看见有个服务生举着饮料托盘走过,赶紧拿了一杯香槟塞到苦瓜手里,“现在把你的嘴堵上,别乱插话。”
“好吧好吧……”
海青这才回到利迪尔身边:“没想到你又回中国了,在英国当金光闪闪的体育明星不好吗?”
“一点儿都不好。”利迪尔耸耸肩,“我生在中国,在这儿很快乐,这里更像我的家。没人在乎你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也没人在乎你是不是牧师的儿子。你没瞧见巴黎、伦敦那些记者采访我时的表情,哈!他们还以为我茹毛饮血,天天光着脚在修道院里敲钟呢。”
“哈哈哈。”海青被他逗乐了,“今后有何打算?”
“其实我去年就回来了,一直在燕京大学进修,前不久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天津有一所中学已决定聘用我。”
“恭喜恭喜,利迪尔老师。”
“还是按中国的称呼,叫我李老师吧。”利迪尔整了整衣领,颇为自豪,“再没什么比教授孩子们知识更有意义、更让我感到快乐了。”
“你一定是教体育喽?”
“不,是物理和化学,没想到吧?不过在教书之前我得先完成一项任务,同样很有意义。”
“什么任务?”
“翻修英租界的球场。”
“我家附近那个网球场?”海青的家在英租界爱丁堡道,离网球场不远,那座球场已有二十多年历史,还是清朝的时候建的。
“对,就是那座。工部局打算把它扩建为占地四万平方米的大体育场,他们请我参与设计。为此我还特意参考了伦敦斯坦福球场的图纸,一定会干得更出色。名字我都想好了,它是体育精神的象征,属于民众的乐园,所以叫‘民园国际运动场’,以后天津也能承办国际赛事了。”
“真叫人期待啊!”海青兴奋地叫起来,“到时候也能在那儿看到你的比赛?”
“当然,绝对是我的主场……对啦!明晚陪我参加一个聚会,怎么样?”
“什么聚会?”
“新兴商会的刘会长邀请几位名流到他家吃饭,除我之外都是各国商界人士,你应该认识刘会长吧?”
“刘文卿?”
“是的。”
作为利盛商行的少东家,海青当然认识不少工商业名流,但他一脸苦涩:“认识倒是认识,我舅舅跟他很熟,可我不喜欢这种聚会。”
“我也不喜欢。”利迪尔撇撇嘴,“但没办法,修建体育场不仅是英租界的事,还关乎社会各界,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明天参加聚会的人都多多少少提供过帮助,我作为设计者总得露个面,你若是参加咱还能聊点儿有趣的话题,要是我自己面对那些人……哦,太无聊了,能期待的只有食物,但愿他家有个好厨师。”
海青暗忖,舅舅经常指责他不务正业,希望他多参加工商界的社交活动,虽然舅舅现在不在家,可还有管家老吴在耳边絮絮叨叨,若参加这次聚会可以搪塞老吴,过后再怎么玩儿老吴都无话可说了,于是笑道:“好吧,我陪你去。”
“太棒啦!”利迪尔豪爽地把手一挥,“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再叫几个朋友,不妨叫曼伦也参加。”
海青吓得一头冷汗:“不必了,他很忙的。”苦瓜参加商界聚会将是什么情景?简直不敢想象。
“那就算了……我叔叔在楼上打台球呢,我得去陪他,咱们明天再聊。说定了,下午四点,你知道刘会长家在哪儿吧?”
“知道,离我家不远。”
“好的,再见。”
“明天见。”海青挥挥手,回头再一看,险些把鼻子气歪——苦瓜正站在一名端托盘的服务生身边,一杯接一杯地喝香槟,似乎已经连灌五六杯了。
“别喝啦!”他上前制止。
“怎么了?”苦瓜有些红头涨脸,“这东西甜滋滋的,还有股气儿往上顶,挺不错的。”说着又把手里那杯灌下去。
“你干吗喝这么多酒?”
“酒?这不是糖水吗?”
“当然不是,这是香槟酒,后劲儿很大的。”
听海青这么一说,苦瓜似乎也觉得身上发热:“糟啦!我不能喝酒的,明天还有重要的事。”
“什么事?”
“师叔推荐我到同乐茶楼演出,茶楼老板要亲眼看看我的本事,好决定以后用不用我。你不是还答应到时候给我捧场去吗?”
“什么?就是明天?”
“明天下午。”
海青急得跺脚:“你怎么不早说?”
“我给忘了,刚想起来,哈哈哈……”
“亏你还笑得出,快回家吧。”
“哈哈!你忘了,我也忘了,瞧这事儿闹的……明儿背贯口把词儿也忘了,后天连自己叫什么兴许都忘了,哈哈……这段子太有意思了,哈哈哈……”酒劲儿涌上来,苦瓜没由来地傻笑,仿佛把这辈子的高兴事儿都想起来了。
“哎呀!你喝多了。”
海青要搀扶他,苦瓜却连退两步,冲向跳舞的人群,扭起了秧歌,手里还攥着那只玻璃杯。这次他跳得更欢,动作更大,一边扭一边哈哈大笑,惹得所有客人侧目,在他的影响之下竟有许多年轻人也莫名其妙地跟着他扭起来。
再这样下去非闹出乱子不可,海青只得从背后抱住他:“你可真会给我找麻烦!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带你来了。”
苦瓜兀自傻笑:“你不带,我自己来,哈哈……我懂!社交嘛,就是喝香槟、跳舞、打扑克,这都是奥运会项目……放开我!曼伦先生要翻跟斗……”
服务生忍着笑凑过来:“先生,那只酒杯。”
“哦。”海青从苦瓜手里抢过玻璃杯,还给服务生,赧然道,“对不起,他赌百家乐输光了钱,所以多喝了几杯。”又从怀里掏出两张钞票放在托盘上。
“谢谢您的小费,需要帮忙吗?”
“帮我叫辆出租汽车。”
“好的,先生。”
对一般市民而言,雇洋车已是高消费,出租汽车莫说中国人,连一般的外国人都雇不起,整个租界才十几辆。可惜苦瓜人生中第一次坐汽车竟是在醉酒之后,无法享受这份惬意了。
“我真是自作自受啊!”海青拖着苦瓜,晃悠悠往外走。后面追来一个英国小伙,笑呵呵抓住他肩膀,操着浓重的外国腔调问:“刚才那舞挺带劲儿,跟拉丁不一样,叫什么名字?”
海青烦透了,猛力甩开他的手,没好气儿地吼了声:“扭秧歌!”说完拖着苦瓜挤进旋转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