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让勒德洛的仆人们把这个地方从上到下清理了一遍,让他们擦洗地板,粉刷石墙,然后挂上色彩丰富的暖色系壁毯。我让木匠把门重新装好以抵挡门外的风。我从酒商那里买下一大桶新酒,分装成两份以供王子沐浴之用;王后堂姐写信告诉我,西班牙公主希望每天都可以沐浴。我希望她在感受到侵袭勒德洛堡塔楼的寒风之后可以放弃这个奇怪的习惯。我已经命人做好了新窗帘,给她的被子加了衬里——我们希望王子每天晚上都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从伦敦的布料商那里订购了床单,他们给我寄来了能够买到的最优质的床单。我拖了地,把新鲜的香草撒在地板上,这样所有房间都弥漫着盛夏干草和草地花朵的气息。我清扫了烟囱,以便公主带来的苹果木能够燃烧出明亮的火光。我从乡下给整个小城堡订购了最好的食物:最甜的蜂蜜、酿造得最醇的麦芽酒、收获以后储存至今的水果和蔬菜、桶装的咸鱼、熏肉、上乘的大圈奶酪。我提醒他们,要保证新鲜猎物的持续供应,而且必须宰杀野兽和鸡肉以招待城堡的客人。我需要管理家里的几百名仆人,整个家庭的几十口人,确保所有人都分工完毕,准备就绪;然后我就开始等,我们所有人都在等,等这对新婚夫妇的到来。他们是英格兰的希望和光明。我需要打点他们的生活,他们要学会如何成为威尔士亲王和亲王妃,并尽快生一个小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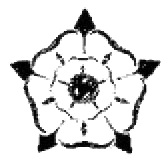
我的目光扫过小镇杂乱的茅草屋顶到达东边,希望看到王家护卫队飘动的旗帜往西边移动,看到卫兵们行进前往格莱福德大门。然而,我看到的只有一个骑马的人,他的马速度很快。我即刻意识到这是个坏消息: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金雀花家族亲属们的安危。我匆匆穿上披风,赶忙下楼到城堡的门口,心怦怦跳,准备好接受这个消息。他从宽阔大街的鹅卵石路上小跑过来,在我面前一跃下马,然后跪了下来,还给了我一封密封的信件。我接过信,撕开了封口。我一开始担心的是我的亲属埃德蒙·德拉·波尔因叛变而被捕,而我会被当成同伙。我惊恐万分,无法阅读信上潦草的笔迹。“信上说了什么?”我简单问道,“有什么消息?”
“玛格丽特夫人,我很抱歉告诉您,当我离开斯托顿的时候,您的孩子病得很严重。”他说道。
我眨着眼看了下那潦草的字迹,阅读了我管家给我写的便条。他告诉我,九岁的亨利生病了。他起了红疹,而且还发烧。七岁的亚瑟一直很健康,不过厄休拉的病情让人担心。她一直在哭,好像还会头痛,而且在管家给我写信时她确实在发烧。她才三岁,正处于婴儿向儿童过渡的危险期。管家对雷金纳德这个宝宝只字不提,我只好认为他在幼儿园里生活得很好,身体很健康。当然,如果我的孩子早已过世,那管家一定会告诉我的吧?
“一定不是汗热病。”我对送信员说。汗热病是我们所有人都恐惧的一种新病。这种病伴随都铎军队而来,当伦敦城的人聚在一起举行欢迎仪式时,这个病就几乎席卷了整个伦敦城。“快告诉我,他得的不是汗热病。”
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架。“但愿不是。我觉得不是。还没有人……”他突然不说话了。他想说还没有人死——这样可以证明不是汗热病。汗热病会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让一个健康的人在一天内去世。“您的大儿子病了三天他们才派我过来,”他说道,“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病了三天了。也许他还……”
“那雷金纳德宝宝呢?”
“跟奶妈一起在她的小屋里,不在房子里。”
我从他苍白的脸上看到了我自己的恐惧。“你呢?你还好吗,小伙子?没什么不适的症状吧?”
没有人知道两地之间的跋涉会让人多不舒服。有些人认为,送信员衣服里面带着的,纸上消息写着的,都是不祥的,所以给你带来警示的人也会给你带来死亡。
“我很好,上帝保佑,”他说道,“我没有起疹子,也没有发烧。不然我就不会来到您身边了,我的夫人。”
“我最好回家一趟。”我说道。我既要为都铎家族尽忠职守,又十分担心我孩子的身体,左右为难。“告诉马厩里的人,我会在一个小时内离开。我需要一名护卫和一匹能用的骑马。”
他点了点头,牵着他的马穿过有回声的拱道,进入了马场。我吩咐侍女们打包好我的衣服,在她们中间找个人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和我一同骑马,因为我们必须去斯托顿;我的孩子生病了,我必须陪在他们身边。我咬了咬牙,大声发布了命令,要求备好护卫的士兵,我们要带的食物,我打算在马鞍上拴一件防雨雪的油皮披肩,以及我要穿上的披肩。我不考虑要到哪里去,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让自己想起我的孩子们。
生活中险象环生,谁会比我更了解这个道理呢?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地了解:婴儿很容易死亡,孩子可能会得最罕见的疾病,王室的血脉极其脆弱,死亡就像一只忠实的黑色猎犬,紧紧尾随着我们金雀花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