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此时,凯瑟琳正乖乖地待在格林尼治宫,虽然她肿胀的腹部已经渐渐平坦,但她还是以严峻的决心等待着孩子的降生。可待产的时间终究还是结束了,她的肚子没有任何动静。她用玫瑰精油和香薰肥皂浸泡过的热水沐浴,穿上最好的礼服,鼓起勇气站出来接受大家的质疑和嘲讽。而我像一个凶悍的守护者一样站在她旁边,扫视所有人,看有谁敢对她长时间的消失评头论足。
她的勇气并没有得到回报。没人会关心一个生不出孩子的新娘。更有趣的事情还在继续,王室笼罩在丑闻中。
我的前任追求者威廉·康普顿,似乎为了安慰自己,开始与我的二表妹安妮调情,安妮是白金汉公爵
 两个美丽的姐妹之一,她才刚刚与乔治·黑斯廷斯爵士结婚。彼时我正全神贯注于凯瑟琳的悲痛,当我发现这件事时,事情已经演化得尤为恶劣。我的斯塔福德表亲在国王面前狠狠地侮辱了康普顿,并把安妮带出了宫。
两个美丽的姐妹之一,她才刚刚与乔治·黑斯廷斯爵士结婚。彼时我正全神贯注于凯瑟琳的悲痛,当我发现这件事时,事情已经演化得尤为恶劣。我的斯塔福德表亲在国王面前狠狠地侮辱了康普顿,并把安妮带出了宫。
这个行为有些过激,但反映出公爵典型的骄傲。毫无疑问,在他看来,他的妹妹可以犯下任何轻率的罪行:她是凯瑟琳·伍德维尔
 的女儿,和伍德维尔家族的大多数女孩一样,漂亮而任性;她对自己的新丈夫不满意,认为他会容许一切不端行为的发生。但是,在宫里的人持续不断的窃窃私语中,我开始察觉事情并不简单。这已经不是一个朝臣的逍遥法外的事件,或是一部宫廷爱情的剧集,而是代表一种挑战规则的欲望。对宫廷爱情总是充满热情的亨利似乎与康普顿站在同一战线,康普顿声称自己被公爵侮辱了,这位年轻的国王便大发雷霆,命令白金汉郡公爵远离宫廷,坚持维护看起来既羞怯又笨拙的康普顿——他像是只护犊子的母羊。
的女儿,和伍德维尔家族的大多数女孩一样,漂亮而任性;她对自己的新丈夫不满意,认为他会容许一切不端行为的发生。但是,在宫里的人持续不断的窃窃私语中,我开始察觉事情并不简单。这已经不是一个朝臣的逍遥法外的事件,或是一部宫廷爱情的剧集,而是代表一种挑战规则的欲望。对宫廷爱情总是充满热情的亨利似乎与康普顿站在同一战线,康普顿声称自己被公爵侮辱了,这位年轻的国王便大发雷霆,命令白金汉郡公爵远离宫廷,坚持维护看起来既羞怯又笨拙的康普顿——他像是只护犊子的母羊。
此时无论发生什么,都比不上威廉·康普顿与公爵妹妹的绯闻更令人不安。国王选择支持他的朋友而不是被戴绿帽子的丈夫,公爵即使受到侮辱也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和支持。有人在撒谎,把一切瞒着王后。侍女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她们什么都不会说。伊丽莎白·斯塔福德表姐保持着贵族的谨慎,因为正处于丑闻的中心的是她的亲戚。侍女摩德·帕尔女士说,这已经不仅仅是常见的八卦了。
凯瑟琳命人去取了王宫的账册,随后便看出来了:当她在产房苦等那个她早知不会降生的孩子之时,整个王宫都在纵情享乐,而安妮·黑斯廷斯正是这五朔节女王。
“这是什么?”她问我,指着五塑节早上安妮窗口唱诗班的开支,“这又是什么?”那是安妮的装扮费用。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任何看到账单的人都会明白,大笔的王室经费正在用于满足安妮·黑斯廷斯的娱乐活动。
“王室为什么要为威廉·康普顿和安妮女士的唱诗班买单?”她问我,“这在英格兰是件正常的事吗?”
凯瑟琳的父亲是个众所周知的花花公子。她明白国王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爱人,谁都不敢抱怨,尤其是妻子。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被自己的丈夫伤了太多次心,她和国王一样拥有王室血统,却受了太多委屈。即便如此,西班牙国王从未修正过自己的做法。伊莎贝拉遭受了地狱般的折磨,她的女儿凯瑟琳目睹了一切,发誓自己绝不会经历这种痛苦。她不敢想象,这位声称爱了自己很多年的年轻王子也会做出这样的事。她不敢想象,在她最悲伤最孤独的时刻,她年轻的丈夫却在跟自己侍女的亲戚调情。
“恐怕你的担心并非毫无依据,”我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告诉她最糟糕的情况并帮她想办法解决,“威廉·康普顿假装向安妮求婚,这事人尽皆知,但仅仅是一个掩护。安妮一直在和国王私下约会。”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她仍表现出王后应有的大方得体。
“而且我很抱歉要告诉你比这更糟糕的事了。”我说。
她吸了一口气。“说吧,玛格丽特,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
“安妮·黑斯廷斯告诉其他的侍女,这不仅仅是调情,也不仅仅是转瞬即逝的五朔节的求爱。”我看到她脸色苍白,嘴唇紧抿着。“安妮·黑斯廷斯说国王已经对她做出了承诺。”
“什么?他承诺了什么?”
我顾不上礼仪,坐在她旁边,搂着她的肩膀,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勒德洛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想家的公主。我说:“亲爱的……”
那一刻,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你要对我说实话,玛格丽特,我想听实话。”
“她说国王发誓自己爱上了她。她告诉国王,自己的婚约可以解除,而他的也是无效的。他们已经提及婚姻了。”
在漫长的沉默中,我祈求上帝,别让她因带来这样的坏消息而怪罪于我。她的身子渐渐无力地瘫软,脸颊满是泪水,悲伤地哭泣。我只能紧紧抱着她。
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她缓过神来,用手揉揉眼睛。我递给她一块手帕,她擦了擦脸,擤擤鼻涕。
“我早就知道。”她叹了口气,声音疲惫不堪。
“你知道?”
“他昨晚跟我说了一些话,我猜到了他的用意。上帝原谅他:他告诉我他很困惑。他告诉我,当他们同床时,她痛苦地喊叫说她受不了,他不得不温柔地对待她。她告诉国王,处女在第一次同床时会流血。”她脸上露出一丝厌恶和嘲笑,“显然,她让国王看到自己流了很多血,并说服国王,我在新婚之夜时已不是处女,我与亚瑟同过床。”
她努力保持镇定,却克制不住地颤抖。“她告诉国王,他与我的婚姻是无效的,因为我与亚瑟结过婚还同了床。在上帝看来,我将永远是亚瑟的妻子,而不是亨利的妻子。上帝永远不会赐给我们一个孩子。”
我很骇然。我茫然地看着她。我们之间的秘密被昭然天下,我竟没有言语去反驳。
“她自己就是一个已婚女人,”我断然说道,“她结过两次婚。”
凯瑟琳对我的质疑露出了悲伤的笑容。
“她说,我们的婚姻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这就是我们失去婴儿的原因。她告诉国王我们永远无法拥有孩子。”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然后松开。
“是的,”她若有所思地说,“她是不是既残忍又邪恶?”
我没有回答,她接着说:“这很严重,因为她告诉国王,我大了肚子但并没有生出孩子,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的婚姻违背上帝的原则。一个男人不应该娶他兄弟的遗孀,这是《圣经》中的话。”她冷笑着,“她甚至引用了《利未记》中的章节:‘倘若有人娶了自己兄弟的妻子,这是可耻的行为,他这样做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兄弟。他们二人必无后嗣。’”
安妮·黑斯廷斯突然说出这样的神学教义,着实让人大吃一惊。一定是有人教她在国王耳边吹风。“教皇已经特许过了,”我坚定地说,“你的母亲安排好了一切!无论你是否与亚瑟同过床,这件事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她点点头。“是的。但亨利已经被他那位老奶奶吓坏了。在我们结婚之前,她就用《利未记》警告过亨利。他的父亲一向不相信自己的运气。而现在这个斯塔福德家族的孩子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告诉亨利我们失去孩子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的婚姻受到了诅咒。”
“她说什么都不重要,”我对这个邪恶的女孩感到愤怒,“她的兄弟已将她从宫中带走,她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眼皮下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已经结了婚!不是自由身了!她决不能嫁给国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亨利怎么会相信她是处女!她已经两次结婚了!他们疯了吗,胆敢说出这样的话?”
凯瑟琳点点头。她在思考如何应对眼前的情况,我突然意识到这与她母亲的做派一脉相承——一个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永远企图翻盘的女人。如果她的帐篷被烧光了,那她就会建一栋石堡,她就是这样的女人。
“是的,我想我们可以摆脱她,”她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必须和她的公爵兄弟重归于好,让他回到宫里;他势力强大,我们不能与其为敌。老夫人已经死了,她不能在亨利身边阴魂不散,我们必须停止这个话题。”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我说。
“你会给公爵写信吗?”她问道,“他是你的表亲,不是吗?”
“爱德华是我的表亲,”我指出,“我们的祖母是有一半血缘关系。”
她笑了。“玛格丽特,我发誓你和每个人都有血缘关系。”
我点头。“我是。他会回来的。他忠于国王而且很喜欢你。”
凯瑟琳点点头。“他对我来说并不是威胁。”
“为什么这么说?”
“我的父亲以花心闻名于世;我的母亲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每个人都知道女人只是他的乐子,没有人跟他提过爱情。”她脸上露出一丝厌恶,仿佛国王和女人之间的爱总是声名狼藉。“除了对他的妻子,我的父亲永远不会提及‘爱’这个字眼。没有人怀疑他的婚姻,也没有人胆敢挑战我的母亲,伊莎贝拉女王。他们是秘密结婚,也没有得到教皇的特许——他们的婚姻是世界上最不确定的婚姻,但是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将共同走过一生。我的父亲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的情妇,但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过‘爱’这个字。从来没有人敢挑战西班牙女王的位子。”
我静静听着。
“我的丈夫才是我最大的威胁,”她疲惫地说,她美丽的面容仿佛只是张面具,“他以前是个被宠坏的傻孩子,但现在他的年纪应该足够他理智地处理与情人的关系。他绝不应该让任何人质疑我们的婚姻。如果有人这么做,就是在破坏他自己和我的权威。我是英国唯一的王后,他是唯一的国王。我是他的妻子,我们经过了加冕。这绝不应该受到质疑。”
“我们可以确保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我说道。
她摇了摇头。“但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产生了,”她说,“一位对妻子之外的人说‘爱’的国王,一位对自己的婚姻提出质疑的国王是在动摇自己王位的基石。我们可以阻止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个想法进入他愚蠢的脑袋的瞬间就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
我们沉默地坐了很久,想着亨利帅气的脸。“他因为爱情娶了我,”她无力地说,“这门婚事不是被指定好的,而是因为爱情。”
“这是一个不好的先例,”我自己就是一个在被指定的婚姻中成为寡妇的女人,“如果一个男人为爱而结婚,当他认为自己已经不再爱的时候,就可以取消婚姻吗?”
“他不再爱我了吗?”
我无法回答她。这问题对她来说太过悲伤。她的第一任丈夫那么深爱着她,除了她,绝对不跟别的女人发生关系,更不会爱上别的女人。
我摇摇头,因为我不知道。我怀疑亨利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很年轻,”我说,“冲动而精力旺盛——这几个特点结合起来就很危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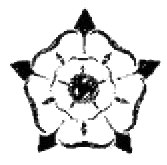
安妮·黑斯廷斯再也没有回到宫里来,她的丈夫将她送到了修道院。她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表亲爱德华·斯塔福德,白金汉公爵,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与我们重归于好。
凯瑟琳把亨利带回了她的身边,他们怀上了另一个孩子,这个男孩很好地证明上帝对他俩婚姻的认可。王后和我假装此事从未发生过,也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