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姆斯和我过得太幸福了,就连两个私生子从帕多瓦回来都没有给我们造成困扰。亚历山大现在已经被任命为了圣安德鲁斯大主教,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詹姆斯现在是默里伯爵,两人前来请安,我也仪态淡定地向他们问好。我向他二人展示了他们父亲的合法儿子,并告诉他们,这是亚瑟,苏格兰诸岛的亲王,罗撒西公爵。两个男孩跪在婴儿床之前,立下了忠诚的誓言,亚历山大眨了眨他架在鼻子上的圆眼镜后的近视眼,迟疑地开口道:“这头衔这么大,但他人可真小。”这让我好笑了一阵。
我丈夫任命亚历山大为大法官时,我甚至没有出言反对。“我需要一个我能完全信任的人。”他说道。
“他还不过是个大男孩。”我急躁地说。
“我们早先是在苏格兰长大的。”
“那好吧,只要他明白,他的一切所学都是为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利益就好。”我说道。
“我肯定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一刻都不曾忘记过这一点。”他啼笑皆非地说。
凯瑟琳终于给我回信了,亲笔书信,还盖有她的石榴纹章,这让我感到惊讶。这是一封私人信件,信上说她感到伤心欲绝,愧疚难当,她失去了她怀的孩子,她曾以为这会是个女儿,她觉得她未能给哈里带来一个孩子(如今哈里只缺一个孩子),唯一能让他们的幸福变得完满的孩子。
这让我十分震惊,我一下将我先前的义愤抛诸脑后。她让我停了下来,让我想起了我死去的小女儿,还有在她之前的儿子。我想起我还曾取笑她到了二十三岁才第一次做母亲,这实在是太残忍了。她读到这个笑话的时候,她才刚刚失去了她的孩子,这个玩笑太恶劣了。我现在内心充满悔恨,我感到羞耻,我放任了我对凯瑟琳的好胜心,这演变为了一股恶意。我拿着她的信,走进了礼拜堂,为那个夭亡的小孩子的灵魂祈祷。我为凯瑟琳的悲哀祈祷,我为我弟弟的沮丧祈祷,也为英格兰的王座祈祷。我祈求他们能拥有一个都铎儿子做继承人,祈求这个同我做了八年姐妹的年轻女人能有一个都铎儿子,我对她的情感在喜爱与嫉恨中轮番变换,但我始终把她放在我的心上,一直都为她而祷告。
随后我深深地埋下头,向被恶龙吞噬的圣玛格丽特低语,若如我所料想的那样,她必定知晓那在末路绝境里中获取救赎之幸福的神秘法门:玛格丽特完好无损地从恶龙腹中逃离出来,而我在饱受分娩之苦后生下了一个儿子与继承人——仅有的都铎儿孙与继承人。我从未希望凯瑟琳遭受厄运,也不希望哈里或者玛丽有任何不测——诚然,我真心为她的遭遇感到遗憾——但是我的儿子亚瑟是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继承人,在她生下男孩之前,他将一直是。她的儿子在出生之时便会取代我的儿子。如今,我有一个儿子而她没有,谁能为我怀有这样一丝隐秘的喜悦而责怪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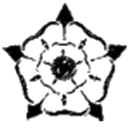
派往英格兰的大使写信说,虽然凯瑟琳失去了一个孩子,但是她——赞美上帝——怀的是双胞胎,所以她仍留有一个孩子。
“这真是不寻常。”我丈夫对我说道。我的所有侍女都退下了,他坐在我房间的壁炉旁边,大声地读着这封信。“她真幸运。”
我心底泛出怒气,这完全可以理解,想到我跪着为她祈祷,期盼她能从丧子之痛中振作起来之时,她的腹中却还保有一个男孩儿。这真是太可笑了,在她仍然怀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她竟然能给我写出一封那么悲惨的信。她这般无事生非做什么!
“你这话什么意思,‘不寻常’?”我没好气地问道,对我的丈夫心生不满,他对那些医师的作品总是这么感兴趣,他喜爱阅读他们写的恐怖书籍,观摩那些画有病变心脏与肿胀内脏的恶心图片。
“她流产时居然只失去了一个孩子,而不是两个,这让我惊奇,”他说道,继续读那封信,“上帝保佑她,我希望情况就是这样;但这的确非比寻常,双子之中失去其中一个而保住了另一个。我好奇她是怎么知道的。她不能让医师好好检查一番真是巨大的遗憾。这有可能仅仅是她还没有恢复月事,但如此一来她腹中便没有孩子。”
我双手捂住耳朵。“你不可以谈论英格兰王后的月事!”我抗议道。
他对我大笑,将我的手拉开。“我知道你怎么想,但她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女人罢了。”
“我永远也不会允许医师靠近我,即便是我在生产的时候快死掉了的情况下!”我坚决地说道,“在那样的时刻,一个男人怎么可以靠近一位王后?我祖母特别写信说王后应该尽在女人的服侍下,在一间封闭上锁的黑暗房间中分娩,甚至是前来为王后做弥撒的牧师都不能见到她——他必须隔着一道屏风将圣饼递过去。”
“但是万一生产中的女人需要医师的知识怎么办?”我的丈夫反问道,“万一出了状况呢?你的祖母不是就差点死在分娩中了吗?要是当时她有一位医师协助她,情况是否会好些?”
“一个男人怎么会知晓这些事呢?”
“噢,玛格丽特,别傻了!这些又不是神话故事。母牛会怀孕,母猪会生崽。你觉得王后生孩子会和其他的母兽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发出一声尖叫。“我不要听这个!这是邪说。是叛逆。两者都是。”
他把我的手从我惊恐的脸上拿了下来,温柔地轻吻我的手掌。“你不必听这些,”他说道,“我并非街上十字座前的预言师。我能知道一些事情而不用将它们大声讲出来。”
“不论怎么说,她一定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女人了,”我愤愤不平地说道,“失去了一个女儿,赢得了所有人的同情,然后还保有双胞胎中的那个儿子。”
“也许她是的,”他也承认道,“我自然也希望如此。”他背对我,脱下衬衫。他腰间的受难带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噪声。
“噢,快取掉那个可怕的东西。”我说道。
他看着我。“如您所愿,”他说道,“我愿做任何事来取悦这世界上第二幸运的女人——假若她能满意于永远处于第二位,就如她现在的地位,第二等的王后,在第二等的王国,等着她才出生的男孩儿被迫成为第二顺位的继承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抗议道。
他伸出双臂将我圈在怀里,并没有劳心回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