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写信给祖母,告诉她我的丈夫深陷在罪恶的泥沼之中。我跪在礼拜堂中好几个小时,思考自己该如何向她诉说才能让她切实感受到与我同等的怒火。关于他那受诅咒的命运,我的措辞异常谨慎,因为我不想提到他谋反的事实,以及他父亲死亡的真相。对我们都铎来说,谋反是一个尴尬的话题,鉴于我们从金雀花们手上夺取了王位,而那些曾受命于天的国王,每个英格兰人都发誓对他们尽忠。我相当肯定,在对理查德国王许下了牢不可破的忠心誓言之后,祖母仍然策划了反抗他的叛乱。而她无疑是他妻子的好朋友,还在她的加冕礼上为她牵裙摆。
所以我没有提及我丈夫曾经的谋反,但我向她强调了他罪孽深重,并且我又惊讶又不满地见到了他的私生子们。我不知该如何对待那名最年长的男孩,亚历山大,晚餐时他坐在他父亲旁边,他们如同家人一般入座,位次按照年龄排序,从十岁的亚历山大一直到坐在奶嬷嬷腿上的婴儿,她用银勺子把餐桌敲得梆梆响,银勺子的手柄上还有蓟花纹饰!王室的标记!詹姆斯表现得我似乎应该心怀喜悦地看着所有孩子都出现在皇家的晚宴上,仿佛这群漂亮的孩子值得我们引以为傲。
这是罪孽,我写道。同时也是对我这位王后的冒犯。若是父亲在我大婚之前就知晓他们的存在,他会下令让这些孩子离开我的城堡。他们应该远离我的封地。这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吗?怎么能指望我为他们提供住所呢?说实话,他们就不应该出生在世上,可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他们离开。
至少我能让他们远离我的宫殿。他们的育儿所和教室都在一座塔内,那位哲学家——我还得让他住在我的城堡里,这真是雪上加霜——在另一座塔内。我享有王后的套房、会见厅、私室以及卧房,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房间。我清楚地吩咐我的侍女还有国王的管事,只有我的侍女才能进入我的宫殿。不论父母是谁,任何年龄和性别的“小宝贝儿”都不能在此进出,好像我想要他们的陪伴似的。
我需要更多信息,需要知道我能做些什么。在等待祖母的建议期间,我咨询了我的随从女官凯瑟琳·亨德利夫人。她出身于戈登家族,是我丈夫的亲戚。她的埃尔斯语和国王一样流利——这些人都说得很流利——而且她认识这些人,她可能认识这群孩子的生母。我觉得这群孩子中有一半都和她是亲戚。这不是什么高贵血脉,是一个部落——他们都是一群野蛮的小杂种。
等到乐师开始演奏,我们坐下来摆弄针线活。我们正在绣一幅祭坛布,上面展示着圣玛格丽特遭遇恶龙的场景。我觉得自己同样身处于被迫面对一头罪恶火龙的困境中,而凯瑟琳能告诉我打败它的方法。
“凯瑟琳夫人,你可以坐在我身边。”我说道,于是她搬来一张小矮凳,坐在我旁边,开始料理我的刺绣的边角。
“你可以先放着不管。”我说,于是她顺从乖巧地放下了布料和针线,并小心地将针放回了银制盒子内。
“我想和你聊一聊国王的事。”我开口道。
她一副洗耳恭听的平静神色。
“关于那些孩子。”
她没有答话。
“这么多孩子。”
她点点头。
“他们必须离开!”我突然宣告。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殿下,这是国王和您才能决定的事情。”
“是的,可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以往是如何处理这类情况的。我无法命令他。”
“是的,您不能命令他。但我认为您可以问问他。”
“他们到底是谁?”
她思考片刻后说道:“您确定您想要知道?”
我坚定地点头,她看着我,眼里带有微弱的同情。“那我便如您所愿地告诉您吧,殿下。不过请谨记一点,陛下不过是一个刚过三十的男人。自他还是一个男孩儿,他便已经是苏格兰的国王了。他在烽火动荡中登上王位,又是一个激情澎湃且大权在握的男人,一个欲望极强的男人,他自然会有许多儿女。他的特别之处仅仅在于他将儿女一起养育在他最好的城堡之内,并且他深爱着他们。大多数男人在婚外有了孩子就丢给生母养育,或者甩手交给外人,对孩子不闻不问,陛下承认自己的子嗣,为此,他也许应该得到嘉奖。”
“不,这不应该,”我干脆地说道,“我的父亲只有我们几个子女。他一个情妇都没有。”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仿佛她更了解一切。我时常厌恶凯瑟琳·亨德利的这一点,她总是一副心里藏着秘密的样子。
“您的父亲是有福之人,他娶到他的妻子,您的母亲。”她说,“既然詹姆斯国王已经娶了您,他大概也不会再有其他情妇了。”
一想到有人在我的位置上比我更受喜爱,我心底里就不由得蹿出一股怒火。我一点都不想有人将我同其他女人作对比。我之所以如释重负般地离开英格兰,部分原因就是没人的目光能够再次在优雅的凯瑟琳与我之间来回,没人能够再次将我同我妹妹玛丽相比较。我讨厌被比较——此刻我却发现我的丈夫有半打情人。“亚历山大,那个年龄最大的男孩,他竟能被准许坐得如此靠前,他的生母,那个玛丽昂·博伊德是什么人?”我问道。
她挑眉看着我,仿佛在询问我是否确定想要知道一切。
“她是谁?她也死了吗?”
“没有,殿下。她是安格斯伯爵的一位亲戚。一个非常显耀的家族,道格拉斯家族,您应该也有耳闻。”
“她当我丈夫的情妇很久了吗?”
凯特琳思索着。“我想是的。亚历山大·斯图亚特已经十岁多一点了,是吧?”
“我怎么知道?”我尖锐地斥道,“我又没有盯着他。”
“是的。”她回答道,然后停了下来,没说话。
“继续,”我生气地说,“他是她给国王生下的唯一私生子吗?”
“并非如此,她和国王有过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儿夭折了。但她的女儿凯瑟琳和她的哥哥一起居住在此。”
“是那个头发漂亮的小女儿吗?大约六岁样子的那个?”
“不,那是玛格丽特,她是玛格丽特·德拉蒙德的女儿。”
“玛格丽特!”我惊呼道,“他给他的私生女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
她低下头,默不作声。侍女们望向她,好像为她被我困在窗边而惋惜。我脾气火暴,尽人皆知,没人敢把坏消息告诉我。
“他给每个孩子都冠上了自己的姓氏,”她小声地说,“他们都被称为斯图亚特。”
“要是他们全都是些王八的小崽子,为什么不用生母丈夫的姓氏呢?”我现在满腔怒火,“为什么陛下不下令让这些丈夫和他们的妻子孩子住在一起呢?让这些女人待在家里,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呢?”
她什么都没说。
“他还把一个男孩儿叫做詹姆斯。詹姆斯是哪一个?”
“他是珍妮特·肯尼迪的儿子。”她低声说道。
“珍妮特·肯尼迪?”我想起了这个名字,“那她在哪儿呢?不在这里吗?”
“嗯,不在的。”凯特琳迅速地说,好似这是不可能的事,“她住在达尔纳威城堡,非常遥远的地方。你永远都不会遇见她。”
至少这一点令人放心。“那陛下也不会再见她了吗?”
凯瑟琳捏起挂毯的一角,好像她希望做针线活似的。“我不知道,殿下。”
“那就是还在见她了。”
“我不能说。”
“那剩下的呢?”我继续我的提问。
“剩下的?”
“剩下所有的孩子。圣玛格丽特在上,肯定还有六个!”
她掰着手指,列举说道:“亚历山大和凯瑟琳是玛丽昂·博伊德的儿女;玛格丽特是玛格丽特·德拉蒙德的女儿;珍妮特·肯尼迪的儿子是詹姆斯;还有三个最小的,因为太年幼了,所以通常是和他们的母亲伊莎贝尔·斯图亚特住在一起,没有住在这座城堡里,分别是吉思、凯特琳和珍妮特。”
“总共有多少孩子呢?”
我能看出她在数。“总共有七个孩子在这儿。当然了,还有一些没有被承认的孩子。”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我不会让他们任何一人与我住在同一屋檐下,”我说道,“你明白了吗?你得告诉他。”
“我?”她从容不迫地摇头,“殿下,我不能告诉苏格兰的国王陛下,斯特灵城堡不欢迎他的孩子。”
“那么,我的内侍将不得不完成这件事。或者是我的告解神父,或者是某个能够告诉他的人。我做不到。”
我的话音陡升,然而亨德利夫人并没有因此而畏缩。“您必须自己告诉他,殿下,”她恭敬地说,“他是你的丈夫。不过如果我是您——”
“你不会是我,”我打断她说道,“我是一名都铎公主,都铎的长公主。没人能与我相提并论。”
“如果我有幸分处在您的位置的话。”她从善如流地改口道。
“你不过曾经是一个觊觎王位之人的妻子,”我刻薄地说道,“显而易见,你不会处于我的位置。”
她低头。“我只是想表达,假如我是一位国王的新妻子,我会向他询问这件事情,如同寻求帮助一般,而不是当作权利去要求。他对您很好,但他也很爱他的孩子们。他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博爱之人。你可以像请求帮助那样去询问。虽然……”
“虽然什么?”我质问道。
“他会感到难过,”她说,“他爱他的孩子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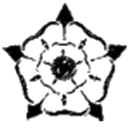
都铎儿女从不求助。身为都铎家族的公主,我要求捍卫我的权利。傲慢国的凯瑟琳可没有和任何人分享勒德洛城堡,除了我们金雀花家族的表亲,玛格丽特·波尔及她的丈夫,亚瑟的一名护卫,所有人都不会这样要求她。等到玛丽大婚——可能是嫁给一位西班牙王子——她会光荣地前往她的新国家。她不会遇到一堆私生子,混血种,还有妓女。我理应受到与这两位公主相等的待遇,要知道她们在出身或者年龄上都不如我。
我等到了第二天,在围观礼拜堂的弥撒仪式之后,在我们离开那个圣地之前,我挽着我丈夫的手臂,走在圣坛阶梯上,向他开口道:“我尊贵的丈夫,我认为让您的私生子住在我的城堡里不太合适。这是您赐封给我的城堡,我拥有的房产,而我不想要他们在这里。”
他牵起我的手,握在他手里,直视我的双眼,宛如在圣坛前许下婚姻的誓言一般。“我的小妻子,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心爱的孩子。我曾希望你或许能善待他们,再给他们添一位小兄弟。”
“我的儿子将是两位王室父母的合法婚生子,”我生硬地说道,“他不会生活在一群私生子陪伴中。他会有血统高贵的玩伴。”
“玛格丽特,”他说话的语气更加温柔了,“这些小天使对你没有任何威胁,他们的生母也并非你的对手。你是万人之上的王后,我有且仅有一位的妻子。你的儿子生来就将成为苏格兰王子,英格兰的继承人。他们住在这里,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我们一年只会来这里几次,你几乎不会见到他们。这对你不会有影响。但若是他们在这里,我便能知晓他们处在整个国家最安全的地方。”
尽管他轻轻地摇着我的手,但我笑不出来。尽管他的触摸是如此温暖,但我没有动容。我见识过祖父的私生子和表亲们给父亲带来的威胁。这些金雀花的姓氏源于一种生长起来便无法扼制的杂草,而我们都铎家族和这份血脉紧密相连,与那些血脉纯粹的后代,与那些混血种,与那些声称有亲缘关系的男孩,与那些已经成为鬼魂的男孩,甚至与那些毫无血缘关系的男孩紧密相连。我不会让我的城堡里住满这些来路不明的男孩。我的父亲砍掉了他妻子表亲的脑袋,才消除了关于谁才是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疑虑。凯瑟琳的父母要求在她从西班牙到达英格兰之前,这位表亲必须得死,我的要求不亚于她。我不会容忍王位有竞争者存在,即便现在我儿子尚未出生。我不要有竞争者出现。
“不。”我断然拒绝道,尽管我耳中听到了脉搏剧烈跳动的咚咚声,反抗他令我害怕。
他低头片刻,我认为我取得了胜利,然而我看出来了,尽管他一言不发,但他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他不过是在控制自己,抑制自己的愤怒。他再次抬头时,眼底一片寒意。“那好吧,”他说道,“但这显露了您的心胸狭隘,王后殿下。心胸狭隘,刻薄自私,而且糟糕透顶的,是您的愚蠢。”
“你住口!”我抽回手,气急败坏地斥责他,就在我要让他见识一名都铎儿女的怒火之时,他却稍微向我颔首,然后对圣坛深深鞠了一躬便走开了。他干脆地离开了,恰似他毫不在意我的不满,徒留我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话可讲,无人可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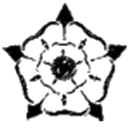
我又给祖母写了一封信。他怎么敢骂我愚蠢?他怎么敢——他留下满城堡的私生子,还因杀害了自己的父亲而良心不安——骂我愚蠢?到底谁更愚蠢?是一位捍卫自己作为王后的权利的都铎公主,还是白天见学者,晚上找妓女的臭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