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朝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边境地带前进,对留在身后的一切并没有感到多少遗憾。我的童年美好大多已经消逝。在过去的一年,我失去了我心爱的兄长,接着是我的母亲,和她一起走的还有我刚出生的小妹妹。然而,我发现在这段我即将迎来的新生活中,我并没有过多地思念他们。不同寻常的是,在我北上旅途中,我思念的人竟然是凯瑟琳。我想要告诉她我所受到的热切欢迎,每个城镇都献上了它们热情洋溢并令人难忘的问候,我还想问她长途骑行的不便之处以及衣橱紧缺的解决之法。我模仿她昂首挺胸的优美姿态,甚至还练习过她耸肩的小动作。我学着用西班牙语的口音说出“荒唐”这个词。我设想她会成为英格兰王后,而我会成为苏格兰王后,那民众定会比较我二人,所以我要学着如她一般典雅端庄。
我每天都能找到机会练习她的体态,因为我逐渐意识到王室人员最了不起的特点之一,便是在人们为你祈祷,或是与你说话,甚至是为你高歌那些为你而作的赞美诗的同时,你还能够保持淡定地思考一些趣事。有人为你的到来而感谢上帝时,打呵欠是很失礼的行为,于是我学会了一个既可以神游太虚但又不会陷入沉睡的小技巧。我像凯瑟琳那样端坐,背挺得笔直,头高高地抬起以拉长我的脖颈。大多数时候,我会将我的礼裙拉高约莫一寸,然后看着我的鞋。我订制了脚趾处绣有精细图样的宴会鞋,如此一来,虔诚的冥想过程可以变得更加有趣。
一路向北,每每到达一个漫长而无趣的驻留处,我都有大把的时间盯着我的脚趾,与此同时,这些贵族先生正向我歌功颂德。
父亲下过命令,我的旅程将是一场恢宏浩大的队伍行进,其中我的任务就是穿着各式各样的礼服,光彩照人,当民众为了都铎王室的来临,尤其是为我途经他们瘟病肆虐、肮脏狭小的城镇,纷纷感谢上帝之时,我要谦逊地垂下目光。这就是我看向脚趾的时机。我心里盘算着不久后我便能到达我自己的国家,苏格兰。到时我会成为王后,在之后我便能自己决定去向何方,同时暗自计算这些致辞还会耗时多久。
越往北走,郊外景色越令我惊奇。天空几乎就铺展在我们的头顶,如同一口敞开的大箱子。忽然之间,那地平线不断后退,变得遥不可及,我们在起伏的青山上上下下,映入眼帘的依然是延绵不断的群山,仿佛整个英格兰都在我们脚下翻滚连亘。在我们头顶的是北方的广袤苍穹。这里的空气湿润清新,几乎将我们淹没。我不由得感到我们不过是渺小的人,在这壮阔天地间爬行的一串小虾,是这接连的崇山峻岭间的小斑点,那些盘旋在我们上方的秃鹫,还有飞得比它们更高的白头海雕,将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我先前不知道路途竟是这般遥远,也不了解英格兰北部居然如此空旷,不见人烟:没有篱笆,没有沟渠,没有农田,完全没有开垦过,就是一片无人的村落、荒原,甚至没有绘制在地图上。
尽管如此,仍有在这片处女地上艰难谋生的人群。我们偶尔能远远地望见简陋的石塔,有时他们的警卫发现了我们,我们就会听见警钟敲响的声音。这都是些北方的野蛮人,他们驰骋在这片土地上,互相偷窃庄稼和马匹,围攻彼此的城堡,凭靠压榨他们的佃农、抢劫他人谋生。我们不会靠近那些人的基地,我们人多势众,装备精良,他们也不敢来犯;但是我的护卫长,萨里伯爵托马斯·霍华德一想到他们,那一口老黄牙就恨恨地磨出响动。他曾在这片村落作战,烧毁过那些破败的堡垒,以此惩罚这些人的野蛮、贫穷,还有他们对南方富饶安定的憎恨。
也恰恰是他阻止我订制我想要的东西,因为一切事务都要听从于他和他那位同样令人不快的妻子——艾格尼丝的指挥。不知为何,父亲喜欢并信任托马斯·霍华德,还命他护送我去爱丁堡,确保我的言行符合苏格兰王后的身份。我本以为,事到如今,不需要霍华德在我边上辅佐提议,我也值得信赖。他同时也是一个探子,因为他不止一次与苏格兰人打过仗,并且他在我们停驻的每个城镇都和那些北方贵族会面,研究苏格兰边境领主们的脾性,还要了解他们之中是否有人可以被收买,投入我方阵营。他向我们的贵族承诺,他们将用获得的武器和金钱用以维护英格兰抵御苏格兰的防御工事,哪怕我的到来将会带来永久的和平。
霍华德貌似不明白我和苏格兰国王的婚约将为这个世界带来何等改变。他表面上对我毕恭毕敬,脱帽致意,屈膝下跪,接受我桌上的菜肴,但仍有一点让我不喜欢他的礼仪,那就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神授君权的尊贵。这就好像他以为自己曾目睹父亲在博斯沃思战场的泥沼中,步履蹒跚地捡起了王冠,那么某天父亲也可能会再次失去它。
霍华德后来也反抗过我们,但他说服了父亲,说那是值得颂扬的忠诚,而非叛国。他说他曾为过去的那顶王冠效力,而他现在忠于当今的国王。哪怕英格兰的冠冕戴在一只来自非洲的狒狒头上,那么他也会对它忠心耿耿。这顶王冠,还有王冠带来的财富,才是霍华德的忠贞之源。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会拥戴我父亲和我。他若不是一名杰出的将军,我想我本不必忍受他的伴随。若是母亲仍然在世,她会指定她的族人陪伴我。若是我的兄长还活着,那我的祖母也不必留在王宫,保护我们剩下的唯一继承人。然而一切都乱了套,自从凯瑟琳来到宫里,带走了亚瑟,随后我的利益便失去了它应得的优先地位,这两个霍华德的行事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每到一个停歇的地方,我对他们的厌恶就加深一层,他们盯着我听取那些表忠心的颂词,还鼓动我发表讲话作为回复,尽管我十分明白,我需要表现出对约克郡的赞赏,对贝里克郡的着迷,这是我们极北之地的城镇,是靠近入海口的河湾上的一颗玲珑明珠。我无须被吩咐去赞扬这些堡垒;我看得到贝里克郡对我的殷勤友好,我感受得到在这些高大结实的城墙之内是多么的安全无虞。可是托马斯·霍华德几乎又口述了一遍那些我要对城堡统领说的感谢之词,他为自己对传统的了解而扬扬得意。一定程度上,他是爱德华一世的后代,这意味着他觉得自己能够出言指点我在马鞍上的坐姿,或者是指出我在晚餐讲话时,目光不应该流连菜肴,而应该望向大厅。
在我们到达苏格兰边境前,从贝里克出发后仅有两个小时,我就已经对两个霍华德厌烦透顶了。我决意等我一旦统领宫中事务,当务之急便是把他们遣送回国,并给我的父亲去信一封,说他们不具备作为我臣仆的能力。对他来说,这两人或许有用。他们可以为凯瑟琳效劳,她可以感受到托马斯·霍华德带来的快乐。她可以看看能否接受霍华德的忠心——无比效忠于王冠,甚至不介意它在戴谁的头上。此人阴沉严肃又野心勃勃,必能令她牢记:她亦曾嫁于一位威尔士亲王,如今却决心成为另一位威尔士亲王的妻子;这是霍华德们效忠的那顶王冠,也是凯瑟琳属意的那顶王冠。
然而,等到我们跨过边界,最终进入苏格兰时,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达尔基思堡的女主人,莫顿女伯爵悄声对我说:“国王快到了。”
这段旅程是如此漫长,我几乎快忘记了它的终点:苏格兰王位,蓟花王冠,还有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而非一个仅仅是通过大使赠送礼物和花言巧语赞美我的人——一个真实存在,正赶来同我相见的男人。
原定的安排是等我进入爱丁堡,他才会来与我会合,可是讨厌的传统规定,新郎——就像童话中的王子——不应按捺自己的急切,可效仿浪漫小说中的多情骑士,提前出发去见他的新娘。这又让我想起了亚瑟,他也曾冒雨前去多格莫斯高地,同不情愿的凯瑟琳相见。回想起他受到的冷遇和难堪,让我一时之间哭笑不得。但是这也表明,苏格兰国王知晓这些环节,表露出了他对我的兴趣,这令我心生好感。
尽管准备完全,但大家还是难免慌张起来,连侍女官艾格尼丝·霍华德来到我房间时,都流露出些许激动之情。我穿着一件深绿色的礼服,衣袖由金缕缝制而成,佩戴上我最为圆润华美的珍珠后,我们都静坐一旁,犹如等待画家为我们作画一般,聆听着乐曲,竭力装作没有在等待的神态。托马斯·霍华德进来了,环视房间,像在安排哨兵一般。他靠近我肩膀,在我耳边低声告诉我,稍后国王到来之时,我应该装出一副完全意外的惊讶模样,不要露出一点“久等了”的神色。我告诉他我知晓这一点,然后我们一起等待着。时间流逝,大门口终于传来一点声响,爆发出一阵欢呼,主宅大门吱呀作响地推开,楼梯上传来马靴哒哒的脚步声,接着哨兵一下推开门,他进来了:我的丈夫。
我一看见他差点尖叫出来。他长着一脸可笑至极的络腮胡,红得像狐狸毛,胡须多得几乎像整只狐狸搭在他身上。我一下站了起来,发出一声惊喘。艾格尼丝·霍华德狠狠看了我一眼,要是她站得离我近一点,我觉得她肯定会拧我一下,让我注意仪态。但这点失礼没有造成麻烦,国王牵起我的手,向我鞠躬,为惊吓到我而表示歉意。他把我瞪大的眼睛,微张的嘴巴当作对他意外到来的称赞,取笑他自己是爱的吟游诗人,然后他面带笑意,自信地向我的所有侍女问好,还对艾格尼丝·霍华德弯腰,并向托马斯·霍华德亲切致意,好似他们会成为挚友,且他已将托马斯两次入侵苏格兰的事情抛诸脑后。
他的穿着很漂亮,宛如一位欧洲君主,身上是镶着金边的红色丝绒,他还特别提到我们俩都选中了丝绒服饰。他上衣的剪裁类似骑马装,然而其布料却价值不菲,同时他背上还背着一把里拉琴,而非一把像是要去打猎的十字弓。我得说,尽管有一点点的惊讶,但假如他去哪里都背着他那把里拉琴,那他确实是一位吟游诗人。他还告诉我他热爱音乐、诗歌以及舞蹈,他希望我也喜欢这些。
我对他说我确实喜欢,随后他便鼓励我跳一支舞。艾格尼丝·霍华德站在我身旁,乐师弹起一首帕凡舞曲
 ,我深知自己舞姿优美非凡。享用晚餐过后,我们坐在彼此身旁,当前他正和托马斯·霍华德交谈,我正好能仔细地观察他一下。
,我深知自己舞姿优美非凡。享用晚餐过后,我们坐在彼此身旁,当前他正和托马斯·霍华德交谈,我正好能仔细地观察他一下。
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他年纪固然不小,已满三十,但他完全没有一个老男人的那种刻板与严肃。他有一张俊美的脸庞:高挑的眉毛,温暖的双眸中满是智慧。他敏捷的思维、炙热的情感,都在他那双黑眼睛里闪露,他的嘴唇线条分明,不知为何,让我有了去亲吻的心思。自然,他的胡子除外。他的胡须真是无法忽视。我怀疑是否有办法能穿过他的胡髯。万幸他梳理和清洗过,还喷了香水,不是那种乱得像老鼠窝的胡子。但是我还是想要他把脸刮干净,我忍不住思考自己是否要向他提起这件事,要我嫁给一个老得足以做我父亲的男人本来就是一件够糟糕的事了,难道还要来到一个没有我祖国辽阔的国家里,让他带着一脸狐狸尾巴与我共寝吗?
他在黄昏时分离开了,我对艾格尼丝·霍华德提起,她是否能告诉她的丈夫,我想要国王刮干净胡子。不出我所料,她立马告诉了他,仿佛我的偏好很荒唐无理似的,在入睡之前,我受了他们一通说教,他们说能成为一位王后就是我的福气了,没有哪位丈夫,尤其是受命于天的国王,会接受一个年轻女人对他外貌的建议。
“男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女人是在上帝完成了他最完美的造物之后的作品,没有女人能够批判男人的形象。”托马斯·霍华德如此告知我,仿佛他是位教皇。
“噢,阿门。”我闷闷不乐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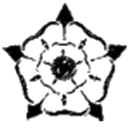
接下来的四天,在婚礼之前,我的新丈夫每天都前来拜访,不过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和托马斯·霍华德交谈,而不是与我讲话。这个老头在边境上同苏格兰人战斗,所有人都认为他俩会是终生仇敌,然而他们却形影不离,分享那些行军打仗的故事。我的婚约者,这个本该向我示爱讨好之人,却和我的护卫在一起回忆过去的战争,而托马斯·霍华德,这个本该留意我的安危之人,忘记了我的存在,给国王讲述他多年的行军生活。当他们共同绘制曾经的战场地图,或者詹姆斯国王描述他正在设计的武器以及为他的城堡建造的工事的时候,他们真是快活得不得了。他们二人的行为举止,都军人气势十足,仿佛女人同这个世界毫无关联,仿佛世间唯一有趣的任务便是侵略他人的土地,杀死其他人。哪怕我和我的侍女在场之时,若国王与托马斯一道走进来,他也只会花费一点时间来讨我喜欢,接着就问起托马斯是否见过这种新型枪支,什么达达尼尔枪,新式火炮,是否听闻过著名的苏格兰猛式大炮,那是欧洲体积最大的火炮,由勃艮第公爵进献给詹姆斯的祖父的贡品。这令人十分气恼。我相信即使是凯瑟琳也忍不下这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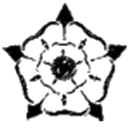
我们进入爱丁堡之日便是我作为都铎公主的最后一日,之后我会在新的国度加冕为后。国王将我扶上马,坐在他身后,好似我是一名普通少女,而他是我的御马官,又好似他俘虏了我,正要带我归家。进入爱丁堡时,我坐在他的身后,紧紧贴在他的后背,双臂环在他的腰上,就像一个从集会上回家的农家女。所有人都为此开心愉悦。大家喜欢我们做出的这幅浪漫图绘,仿若一幅骑士和被救少女的木版画,也喜欢看到一名英格兰公主如同一件战利品一般给带进他们的都城。这些苏格兰人都是不拘礼节又亲切友好的人民。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然而,在看到英俊国王的粗犷模样,他那满头红发和长长胡须,看到马背上坐在他身后的金发公主的那一刻,民众们神采飞扬的面容,不停挥舞还送出飞吻的双手,还有这些欢呼,都表现出了他们的激动喜悦。
整座城市由城墙包围,城墙上修建了结实高大的城门,城门之后是交杂错乱的简陋木屋和破败房舍,还有一些墙上刷着石灰、屋顶盖着厚厚茅草的高大房屋,以及少数新建的石堡。城市的一端有一面山势险峻的峭壁,在峭壁顶上屹立着一座城堡,它的四周都是垂直的悬崖,仅有一条狭窄小道通往山尖;不过,城市另一端地处河谷,有一座新修建的宫殿,外面的高山密林便是这片区域层层防御的城墙。从城堡沿着陡峭山坡一路向下到宫殿有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宽阔大道,长达一英里,商人和公会成员的豪华住宅正对着这条街,房屋的高层就在街道上方。这些豪宅的后方是美丽的庭院,以及通往内部宅院和大花园、果林、围场还有隐藏在后的房舍的晦暗狭巷,以及下山的秘道。
每个街角都有关于天使、女神和圣人为我祈祷爱与丰饶的布景或者假面剧。这是一座精致的小城,修造得又高又宽,城堡就像是屹立在它之上的高山,塔楼直冲云霄,旗帜在云层之中翻飞。这也是一座混乱的城市,由陋室破屋和高宅大院重建而成,由木头和石料搭造而成,灰石板房顶代替了茅草屋顶。但是每一扇窗户,不论是敞开,关闭,或是装有玻璃,都露出了一面旗帜或是涂上了各种颜色,并在凸出的阳台上挂上了各种长巾和花串。每一扇窄小的门口都挤满了一家人,向我挥手,而那些修有凸肚窗、高层阁楼和阳台的石砌房屋里都有孩子们探出身子来欢呼。所有人的喧闹声汇集在这小小的街道上,侍卫设法在人群中拨开一条道路时,他们的叫嚷实在声势滔滔。我们前后至少有一千匹骏马,马背上的苏格兰领主和英格兰贵族共同行进,以显示我为苏格兰带来的全新团结。我们沿着狭窄的鹅卵石街道蜿蜒前行,下山来到了荷里路德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