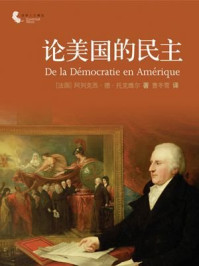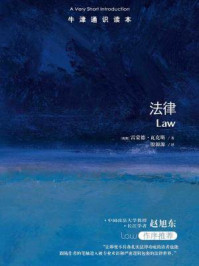意大利实证学派的理论看似纷繁而多元,实则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如下:实证学派认为,刑罚处罚的基础不应该仅仅是尊重社会的基本道德良知,更应该致力于设计一系列的刑罚措施,有效治理与防控那些不断出现的犯罪现象。遏制伴随社会经济结构改革而来的犯罪率,和可能因此反复出现的犯罪行为。笔者认为,实证学派的基本观点为:其一,实证学派将刑法研究的重心从抽象类型化的犯罪行为,转移到实实在在的客观犯罪现象上。但是,学派并非抛弃类型化犯罪理论,而是以此为前提,通过借助生物学、心理学等研究工具,对犯罪行为、犯罪现象、犯罪人互相影响而产生复杂变化的“犯罪生态”进行综合考察。其二,实证学派将古典学派对罪犯主观意愿、可归责性、道德感等展开的理论研究,通过提出“人格危险性”这一概念进行了理论内涵的拓展。所谓“人格危险性”,这一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对社会而言,普遍存在的危险”,这种普遍存在的危险,可能由于某种特定的诱因,而最终导致了某种相应犯罪行为的发生。其三,关于刑罚措施理论,实证学派认为,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侧重论证犯罪人精神理性的异常和严刑峻法的使用。面对19世纪末社会结构深刻的变革,严刑峻法并未能使得犯罪人远离犯罪,反而因为刑罚措施配置与适用不当,对罪犯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了双重伤害。因此,实证学派强调保安处分等刑罚处罚二元制的展开,尽可能使得刑罚措施得以合理而适当地施加于罪犯,并最终可以令罪犯有尊严地回归社会。
意大利实证学派的三位创始人,对于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看法本身不同程度体现了三位学者个人的学术特点,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实证学派理论的发展脉络,因此,笔者对三位学者的有关论述亦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学术考察。
龙勃罗梭作为犯罪人类学理论的代表,从犯罪人类学理论出发,认为古典学派理论假设中的犯罪人具有与正常人相同的智力和情感表达,并且古典学派认为犯罪行为是评价行为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这两种观点是缺乏现实依据的,是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形而上学。龙勃罗梭认为,犯罪人的反社会犯罪倾向首先应当归因于犯罪人群体的生理异常与心理异常,只有在定罪量刑过程中融入“危险人格”因素的考量,并运用妥当的罪犯矫正措施对犯罪人格进行积极的矫正,才会达到矫正罪犯,回归社会的矫正目标。“因此,现代学派是以一种新的科学——犯罪人类学为基础建立的:可以把犯罪人类学界定为犯罪人的自然史,因为犯罪人的自然史包含着犯罪人的器质性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生活,就像人类学包含着正常人和不同种族的人那样。”

笔者在研究中观察到,伴随着菲利理论体系的不断成熟与完善,不同历史时期,菲利对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的批判也呈现出不同的思考维度和观察视角。1890年,菲利通过一份专门论述刑事古典学派两位学者——贝拉利亚与卡拉拉的学术报告,完整展示了菲利学术研究早期的理论特征。菲利在这份报告中,将古典学派的理论观点概括为:“……首先,古典学派的理论如其他适合科学的理论体系一样,古典学派的理论建立在人类社会的经验直觉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其次,古典学派理论形成初期,也曾因为理论体系过于理想化而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 [7]
囿于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无论是贝卡利亚还是卡拉拉都未能令刑事古典学派理论焕发新的生命。古典学派的刑法学理论肇始于启蒙运动,易言之,是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潮在刑法学领域的一种体现。但是,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却因为无法从科学的实证主义之中,寻找到崭新的研究视角,而最终无法完成刑事法学理论更细致的系统性研究。菲利认为:“……如上所述,应当利用科学研究的实施和数据,分析犯罪。这个过程如同生物领域的科学研究,以及社会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一样。我们引入科学研究犯罪现象的方法,根本上,是为了改变传统意义上,刑事法律学科仅仅利用三阶层理论分析方法研究犯罪现象,转而提高刑法学研究的科学性。”
[8]
菲利指出,如同斯宾塞等提出的自然规律来认识人类本身一样,刑事法律科学的研究也应当是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思与呈现,并且,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体,都应当被纳入刑事法律科学所认知或表达的范围之内。菲利认为,犯罪学学科研究之中,必须首先应以科学研究放在第一位,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研究,确立一系列的检验标准,才可以被称作应用科学。

尽管,在菲利看来,刑事古典学派的研究存在上述局限性,但他也承认,刑事古典学派在一个多世纪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对意大利刑事立法的完善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菲利认为,其以古典学派刑事法律研究成果为基础,将科学实验的方法同法学理论研究相结合,为意大利刑事法律研究方法和范式带来了全新的革命,也更为有效将古典学派理论应用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菲利认为,将科学实验的方法同犯罪学理论研究融合起来,是自伽利略时代就已经完成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革命。因此,犯罪学研究、刑罚学理论研究都应当依托于实证研究方法的革新,才有能力对犯罪现象进行更为广泛的深入研究。 [9]
综上所述,古典学派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同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相结合,这样一种理论研究模式不仅是科学的,也是可行的,同时也是迫在眉睫的。“自贝卡利亚开始,刑事古典学派的对刑法理论的研究范围,集中在犯罪行为,罪行的研究。但是,请注意:古典学派理论体系自始至终,并没有针对犯罪人本身进行系统研究。……因此,我们的新学派与古典学派的学术研究重点各有不同。”
 除了对犯罪人进行唯一重点研究,实证学派也将对犯罪行为进行研究,只是与古典学派的研究角度不同。前者将犯罪行为看成“有血有肉的法律实体”,“即,我们去研究诸如小偷和谋杀犯的犯罪原因,需要研究实施犯罪的一系列行为,追根溯源,最终将整合犯罪的全部行为,进行刑法政策研究。”
除了对犯罪人进行唯一重点研究,实证学派也将对犯罪行为进行研究,只是与古典学派的研究角度不同。前者将犯罪行为看成“有血有肉的法律实体”,“即,我们去研究诸如小偷和谋杀犯的犯罪原因,需要研究实施犯罪的一系列行为,追根溯源,最终将整合犯罪的全部行为,进行刑法政策研究。”

也就是说,意大利实证学派将犯罪行为的研究,作为研究犯罪人、犯罪原因的切入点,并以这种更具社会学意义的犯罪行为作为研究枢纽,将全部犯罪现象纳入学派的研究范围之中。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对待犯罪人、犯罪行为,是抽象性的、逻辑性的、经验性的认知与评判,那么,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主审法官个人的主观感知因素占据了刑事审判的主要环节。在这样的审判过程之中,法官往往很难将犯罪人的犯罪原因、犯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犯罪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犯罪人所处的地域因素等统和为一个整体进行刑事审判。并且,从审判的开始,犯罪人就被假定为一个罪大“恶”极之人。与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不同,菲利认为,意大利实证学派首先是将犯罪人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同普通社会公众并无根本差异的个体,也就是,“犯罪人与我们一样,是彼此平等的权利主体。” [10] 因为,每一个杀人犯犯下故意杀人罪的前提,都是不尽相同的,有些犯罪原因或许是情有可原的。
当然,实证学派尽管尊重并在后来的“菲利草案”中,践行了古典学派的刑法学基础理论教义,但是,针对构成要件三阶层理论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菲利也有自己的观点、看法。他依据自己数十年对犯罪学、犯罪人类学、犯罪社会学深入浅出的细致分析,以及将刑事政策体系建构为“社会防卫体系”的设想,认为传统的构成要件理论需要将犯罪的事实进行公式化处理,需要从犯罪行为之中,“对称”地找出符合构成要件认定结构的三个元素: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如此一来,社会百态,每个同类型罪犯之间尚存在不同的个体化差异,当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无法做到“一一对称”地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结构时,理论的精妙严谨就沦落为僵化无序。因此,如何最大程度平衡刑事法律规则与“犯罪人个体化差异”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地成为犯罪人类学、犯罪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向了。菲利认为,抽象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往往只能解决“形式”上那些“看起来一致”的犯罪类型,甚至很多时候,依据构成要件理论逆推获得的证据往往大同小异。但那些因为犯罪人本身个体的差异存在的不同,就在这种“抽象定罪”过程中被忽略掉了。 [11]
论及犯罪人在服刑期间,如何通过配置科学合理的刑罚处罚措施,才能更有利于罪犯的矫正与再社会化,菲利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路径。他首先否定了监狱的效用,并指出监狱中普遍存在的,犯罪人之间“交叉感染”的负面效应:“……将罪犯关进监狱之中,使得更多没有基本人类良知和道德素养的人,相互感染;并使得这些罪犯可能走向更无法挽回的地步。将这些罪犯关闭在一个无法接触正常人类社会生活的监狱之中,每天在监狱工厂中不停工作,最后在刑期结束后,被释放回社会之中。罪犯在监狱中,并没有能变得更好,没有能获得刑满释放后,重新回归社会的生存能力。” [12]
菲利认为,自贝卡利亚提及关注罪犯个体基本权利之后,犯罪人因素被更广泛纳入刑事法律研究之中,备受重视。在这个意义上,实证学派对犯罪人个体的理论研究,乃至以社会防卫理念为核心,并将研究重点指向罪犯矫正,都堪称学术史的里程碑。“……在坚持传承古典学派的经典理论之上融合了科学实证主义理论,用实验归纳的方法对实际问题进行有效的归纳与总结。……之所以关注犯罪人,就在于犯罪人是活生生地存在于社会现实生活之中的……我们要将古典学派总结的理论,以及实证学派总结出的经验相结合,并有效地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尤其是,实证学派将关注如何改革监狱,如何使得监禁制度成为更有利于进行社会防卫的措施,并更加有效地对那些罪犯进行有的放矢的矫正。实证学派必然会使得犯罪学融入社会生活之中……刑事法律体系应当存在于预防与制裁之中,存在于法律判断与事实判断之中,存在于司法审判与执行之中。” [13]
笔者纵观意大利实证学派理论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针对其理论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也从未停止过。有的学者认为,实证学派是在保护犯罪人,从而纵容犯罪人进行犯罪。对此,菲利则认为,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为了罪犯的家庭,罪犯的子女可以不再进行犯罪活动,对那些成年的犯罪人进行适当的非监禁刑处罚,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在服刑期间,可以学会更多适应社会的技能,从而在出狱以后可以更好回馈社会。“……树木,只有在它刚刚种下时可以将它扶正,如果等到它长高了以后,再想扶正它,已经永远也不可能了。” [14] 也就是说,他认为对成年罪犯的矫正目标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子女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有的学者质疑实证学派通过人类学、心理学等方式,对罪犯进行综合矫正,是错误的,是过于理想化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其结果也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对此菲利认为,无论是罪大恶极的罪犯,还是涉世未深的未成年犯罪人,都是可以通过点滴的矫正、耐心的心理辅导,甚至是通过“音乐”等方式,使得罪犯在矫正以后,可以获得道德上的“自我救赎”。只要罪犯还存在一点基本的道德认知,那么,最终就可以通过综合矫正回归社会。反之,假如我们忽视了对诸如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辅导、教育等矫正途径,那么,最后很可能导致未成年犯罪人在出狱后,变成一个终生犯罪的犯罪人。
同菲利相较起来,加罗法洛更为认同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观点,其中,加罗法洛认为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他所坚持的理论同古典学派的理论并无二致:其一,“公正的惩罚是必要的惩罚”;其二,“古典学派正是通过公正的因素来限制社会防卫的运用。公正的因素引出两个原则,他们对目前刑事科学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特征来说关系重大。这两个原则是:(1)除非行为人对其行为负有道义责任,否则犯罪就不存在。因此,犯罪的严重性随着道义责任的轻重而变化。(2)刑罚严厉程度必须与犯罪的严重性成正比。”
 除此以外,加罗法洛作为实证学派的学者,同样否定道义责任论,他认为,以道义责任论的作为归责的基础并不能真正遏制犯罪的发生。相反,只有根据不同罪犯个体的特殊状况,所处社会阶层的不同,设计出符合罪犯矫正效果的制裁措施,方才得以实现“罪犯适应社会的可能性”,也才可以真正遏制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
除此以外,加罗法洛作为实证学派的学者,同样否定道义责任论,他认为,以道义责任论的作为归责的基础并不能真正遏制犯罪的发生。相反,只有根据不同罪犯个体的特殊状况,所处社会阶层的不同,设计出符合罪犯矫正效果的制裁措施,方才得以实现“罪犯适应社会的可能性”,也才可以真正遏制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
意志自由的关键就在于,行为人事实上具有决定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在决定行为、做出选择、最终决定如何实施行为时,一定是行为人认为最优的选择。针对实证学派的种种质疑,尤其是质疑实证学派似乎并未将社会道义责任的因素融入于对犯罪人进行刑法处罚的过程。对此,我们需要客观看待:将罪犯个性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整合起来进行定罪处罚,并依照上述关于意志自由理论的理解,是不可能没有任何道义责任的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