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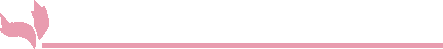

文│她和那只猫
新浪微博│她和那只猫
江稚鱼在二十八岁这年出了书。
签售会定在了来年开春,草长莺飞的三月。她怕冷,遂披了件薄薄的针织开衫,散着长发,坐在那里气质不输明星,引得不少读者红了脸颊,胆子大的则宣之于口。
“谢谢。”她把书合上递给读者,看向下一个人,“你好。”
“江老师,听说您的这本书是写给前男友的。”
她愣了一下。
来人是位男士,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手里抱着一台单反:“前几年有传言说你跟钢琴天才在交往,后来他出了意外,你立即和他撇清了关系,如今又写了本跟他有关的书,请问能借此机会解释一下吗?”
他的语速很快,咬字清晰,应该是个媒体人。江稚鱼鲜少谈及这些,关于此类问题都是提前打好招呼,现在算是突发情况,她微愣时,又听到他说:“江老师,难道传言都是真的?”
他摁下了快门,闪光灯亮起,江稚鱼脸色微白,握笔的手止不住地微微颤抖。工作人员冲上来架着男人离开,可现场已经乱作一团,签售会只得暂停。
江稚鱼独自在车上坐了许久。停车场的光线极暗,她的身影完全隐在阴影里,她伸手打开了音乐,是肖邦的《小狗圆舞曲》。
熟悉的曲调萦绕在狭小的空间里,副驾驶位上放着签售的书,她翻开,入目是一张两人的合照,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小字——春日快乐,江稚鱼。
她很小声地说:“春日快乐,程与淮。”
江稚鱼第一次见到程与淮,是在十七岁那一年。
那是三伏天的傍晚,她跟朋友有约,所以逃掉了钢琴课。她爬上培训机构的墙刚要往外跳,外面树下传来了说话声。
是一男一女。
那棵树枝繁叶茂,她看不清,只听到女孩说:“程与淮,晚上再见。”
之后,下面没声音了。
江稚鱼又等了一会儿,确定人都走了,才撑着墙头起身。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她一接通,朋友就吼道:“江稚鱼,你不会又放我们鸽子吧?”
她被吓了一跳,手机没拿稳,掉在了地上,人也摔了个四仰八叉。
江稚鱼趴在厚厚的草坪上痛呼,心里骂死了朋友。下一秒,一双白色运动鞋出现在她的视线里,看起来有些旧。
然后,那双鞋的主人说话了:“听够了?”
是刚刚那一男一女中的男生。
江稚鱼忍着痛爬起来,这才发现他很高,戴着黑色的鸭舌帽,薄唇轻抿,目光有些冷淡。
“我只是路过,什么都没听到。”她舔了舔嘴唇,有点心虚,她想他应该是不信的。
果然,他看了眼她身后的墙,又看了她一眼,然后走了。
她瘸着腿嘀咕:“要不是你们,我就不会摔下来了,最好别让我再见到你,否则我一定……”掌心的痛处被牵动,她轻轻“咝”了一声。
再见会怎么样呢?
江稚鱼没想过这个问题,可她很快又见到了程与淮。他抱着吉他在公园里卖唱,穿一件白色棉T恤,表情淡淡的,低声唱着英文歌。周围挤满了女孩子,其中就包括江稚鱼。
确切地说,江稚鱼是被朋友拉过来的。商场门口正对着公园,朋友一出来就看见了,激动地道:“刚听人说他经常在这里卖唱,又帅又有才华,鱼,你不觉得吗?”
江稚鱼只觉得有些丢脸。
没想到,不久后她却看到了程与淮出糗。
程与淮被几个男人堵在公园的小树林里,那些人都是附近的流浪歌手,见程与淮人气高,又是个大学生,便打算合伙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们已经威胁了一轮,穿着白衬衫的程与淮直愣愣地站着,树影婆娑,他清冷得像是地上的一轮月亮。
他没说话,那伙人恼羞成怒,刚揪住他的衣领,便听见一阵警车鸣笛声由远及近,他们撂下狠话就匆匆离开了。
程与淮从那片树林出来,迎着灯光便看到了蹲在不远处的江稚鱼,她收起了手机,警笛声随即停止。
他走近了,说道:“谢谢。”
“没事啊。”她站起身,语气里有几分兴高采烈,“上次的偷听是无意的,这次就当扯平喽。”
程与淮这才反应过来她是翻墙的女孩,但他似乎没打算解释,只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做的吗?在我能力范围内。”
江稚鱼本打算端着架子拒绝的,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我请你吃饭吧。”他又说。
“行吧。”她的脸有些红,好在在夜色的遮掩下不易被发现,但她依旧端着,“为了救你,我还没吃饭,那就勉强跟你去吃顿饭吧,这可不是我占你便宜哦。”
“嗯。”
程与淮带她拐进了附近的胡同。这种细长的巷子江稚鱼从没来过,昏黄的路灯将两人的影子缩小又放大。经过第三盏路灯时,她终于开了口:“程与淮,你不会为了赖掉一顿饭就把我卖了吧?”
“不会。”他说完,停顿了几秒,“况且你会报警。”
“我不是经常报警。”她瞪他,“还不是为了救你,不然你都被揍成猪头了。”
他不与她争辩,走出几步就停了脚步:“到了。”
那是一家露天烧烤,巷子两侧各摆了一排小桌子。顾客很多,程与淮找了个空位子,又起身拿了菜单递给她。
菜单上红红绿绿的一片,很多菜江稚鱼都没吃过,她怕出洋相,就把菜单丢给了程与淮:“还行吧,也不是太饿。”
“你平时吃什么?”
她想了一下,说:“鲍鱼、鹅肝和鱼子酱。”
程与淮抬头看她,她补了一句:“经常吃都腻了。”
他没再问,拿笔画了起来,江稚鱼托着下巴瞧他。他的睫毛很长,灯光打下来还投下了一片阴影,鼻梁也很挺。她脑海里响起朋友夸他真帅的话,是挺帅的,她想。
她正看得入神,程与淮忽然抬起头,她躲闪不及,就这么被抓个正着,心脏莫名其妙地怦怦乱跳。
“我刚才问你的这些……”
江稚鱼以为他是问够不够吃,下意识地点头:“够够够。”她的语气突然变得有些矫揉造作,“人家胃口小,点多了可吃不了。”
他沉默片刻,才说:“我是问,你吃辣吗?”
耳边的微风戛然而止,她咬着牙恶狠狠地道:“不吃。”
程与淮没再说话了。他的话本来就很少,席间基本是江稚鱼在说。
“你一直在那里卖唱吗?”
“嗯。”
“为什么?”
“缺钱。”
她没问他为什么缺钱,因为从他点的菜里就能看出来他是真的缺钱。五个菜中有四个素菜,唯一的荤菜就是两串羊肉。
江稚鱼挥手招来了服务员,又要了一堆荤串。吃到一半,她溜进去结了账。等程与淮再去的时候,老板娘笑眯眯地告诉他已经付过钱了。
出去后,程与淮把钱给江稚鱼,她没收。分别的时候,她忽然大发善心地问他:“你有想过换个兼职吗?”
江稚鱼说的兼职就是给她当家教,她开出了高于市场价三倍的价钱。
“为什么?”程与淮问。
她脸上是明媚的笑:“当然是因为你值这么多啊。”
他不信,直到翻开了她的课本,干净得一尘不染。
“的确值这么多。”他说。
她假装听不懂,清了清嗓子,道:“你会发现我很聪明。”
他忽略她的自夸,随手翻着课本:“你哪个学科成绩最好?”
“英语吧。”听起来高大上些。
于是,聪明的她做了一张英语卷子,只得了10分……
“是很聪明。”他夸奖,“有几道挺难的题你都蒙对了答案。”
江稚鱼纵然脸皮厚,也有些难为情,那两个小时的补习时间她听得格外认真。补习结束后,程与淮把试卷收回书包里,她才后知后觉地起身送他下楼。
客厅的角落里放着她经常使用的钢琴,程与淮的目光落在上面,江稚鱼问:“你喜欢钢琴?”过了很久,他才“嗯”了一声。
她罕见地没接话,眼里流露出不好的情绪。程与淮后来才知道缘由。
那天,给他开门的是江稚鱼家的阿姨,他跟在阿姨后面上楼。二楼的书房没关门,里面传出中年男人的声音,男人已经在发火的边缘:“江稚鱼,我给你找的家教你不要,你自己去找什么大学生,你是补习还是欣赏?好好的钢琴说不弹就不弹,你到底要任性到什么时候?”
程与淮停下脚步,忽然想到第一次见她,就是她从音乐培训机构翻墙出来。紧接着,江稚鱼的声音响起:“钢琴是我喜欢弹的吗?是你强加给我的!”
阿姨诚惶诚恐,走过去敲了敲门:“程老师到了。”
里面的声音停止了,接着,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走出来,程与淮往旁边挪了几步,男人看都没看他一眼。
他进去时,江稚鱼正坐在椅子上翻着书,依旧笑嘻嘻的,眼里没有半分怒气。
那两个小时,程与淮十分耐心,话稍多了些,还难得有几分温柔。
补习结束的傍晚,江稚鱼照例送他下楼。穿过花园时,风车茉莉的枝丫掠过他的黑发,落了一朵在他的肩上。
江稚鱼伸手替他摘下,却不料他忽然回头,她压住跳到嗓子眼的心,摊开掌心,露出那朵白色的小花:“刚才落你身上了。”
“谢谢。”
她把花朵放进口袋,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听到了?”
程与淮不愿说谎,回答了“是”。
“那你今天是在可怜我吗?”她的神情忽然有些悲悯。
“没有。”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江稚鱼,我给你唱首歌吧。”
程与淮唱了首粤语老歌。
他没拿吉他,是用的客厅里的钢琴。傍晚的微风从半开的窗子溜进来,亲吻着他柔软的黑发,余晖洒满他的背,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江稚鱼轻抿着嘴唇,直到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他起身,携着一身橘光走到她面前,破天荒地安慰她:“江稚鱼,你其实挺优秀的。”
后来程与淮每次来为她补习,她父亲竟然再没开过口。江稚鱼松了口气,也没再故意考低分来气他。她甚至更刻苦,不仅是因为父亲,也想告诉程与淮她的确很优秀。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时,她考了省内第七名的好成绩。她打电话给程与淮,他在电话那头淡淡地说:“恭喜。”
江稚鱼握着手机娇嗔道:“还是你教得好嘛。”
“你聪明。”
“你猜我报的哪里的学校?”
他还没说,电话里先出现了一道温柔又年轻的女声:“与淮,你看见我的头绳了吗?”
那样好听的声音,江稚鱼曾坐在墙头上听到过,是那日树下的女生。后来江稚鱼在学校里也见到她了,大四学姐,学校里一众男生的白月光。她站在江与淮身边,两人般配得如同天上的星星与月亮。
关于他们的故事,江稚鱼听室友讲过很多遍。两人曾就读同一所高中,她喜欢音乐,程与淮就陪着她考上了同一个音乐学院,后来她在迎新晚会上弹奏的《小狗圆舞曲》就是送给他的开学礼物。
江稚鱼忽然想到很久以前,她考进班级前二十名,无赖一般向程与淮讨要奖励,程与淮弹的就是这首曲子。
他说那是他最喜欢的曲子,他想去马略卡看看春天,如果有可能,再养一只狗。他说这话的时候,眼里一片温柔。
现在想想,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
江稚鱼后来见到程与淮的次数越来越少,听说大学毕业后,他打算去国外进修音乐,与他女朋友一起。
江稚鱼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办公楼,他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旁边还有一位老师,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叮嘱他结婚时可一定要发请柬。
程与淮笑笑,说一定会的。
他与老师告别后,从台阶下来就看到了江稚鱼,他走过去跟她打招呼:“好久不见。”
他的刘海剪短了,衬得他的五官越发立体、成熟,身上是一件宽松的白衬衫,露出一截锁骨。
“好久不见。”她扫了眼他手里的档案袋,“要走了吗?”
“是。”他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说话时语气很温柔。
江稚鱼猜测是他女朋友打来的,她别过脸,压下喉咙里的酸涩。
程与淮挂掉电话后说:“我先走了。”
“好,再见。”
江稚鱼站在原地,看见程与淮的女朋友在不远处的树下朝他挥了挥手。对方长发及腰,明眸皓齿。她过来顺势挽着他的胳膊,而他看向她的每一眼都带着爱意。
那天晚上江稚鱼做了个梦,梦见程与淮把这份爱意给了她,他问她最喜欢的人是谁,她红着脸说“海底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
可梦终归是梦,醒来后,江稚鱼看见程与淮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两张机票上的十指紧扣。
可惜,海底月捞不起,心上人也不可及。
江稚鱼毕业那年,程与淮在钢琴圈崭露头角。
镁光灯定格在他周遭,他一身黑色西装,格外清冷矜贵。有记者采访时开起玩笑:“听说您想和女朋友一起去马略卡,是打算成为下一个肖邦吗?”
他笑了笑,用流利的英文回答:“肖邦是我努力的目标。马略卡也很美,不过那里没有属于我的春天。”
江稚鱼在屏幕前反复揣摩那句话,又想起半年前看到的那个八卦。有人匿名说江稚鱼的女朋友为了钱跟他分手了,她当时还和爆料者吵了大半夜,如今心里却是五味杂陈。
江稚鱼思来想去,最后还是飞去见了程与淮。坐在星级餐厅里,她打量着他,他相比之前瘦了,下颌线很明显,身上的艺术气息更浓郁。
“怎么了?”他忽然问。
“没事。”
程与淮话不多,都是江稚鱼在讲,最后她问:“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
“我分手了,应该不算太好。”他这么一说,江稚鱼就想到了那个八卦,正思忖着,听到他又说,“应该比你盘里的鹅肝好。”
江稚鱼低头看去,盘子里的鹅肝已经面目全非,她悄悄红了耳朵,但还是端着架子道:“现在国内流行这样吃,你没回国,可能不知道。”
程与淮欲言又止,忍了又忍,最后还是说:“江稚鱼,国外不是深山老林不通信号。”
江稚鱼:“……”
两人从餐厅出来后,刚好路过冷饮店,程与淮进去买了两瓶水,江稚鱼在门口等着。两个黑人小哥迎面走来,一个朝她伸出右手,一个在旁边拍照。她下意识想握住,程与淮刚好出来,把她往自己身边拉。
黑人小哥骂了几句,用的意大利语,江稚鱼听不懂,她问程与淮什么意思,他拉着她往前走,走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才松开:“握手要给钱。”
她“啊”了一声,撇撇嘴:“我还以为追我的人都排到了米兰。”
“这么失落?”
程与淮低头轻笑,黑发白衣,背后是飞翔的鸽子与神圣的教堂。一片喧嚣中,江稚鱼只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在人山人海中,隔着岁月漫长,年少时的喜欢也变得连绵不绝。
他把水递给她:“半年前我在运河边看见了一个人,侧影跟你挺像,当时还以为是你。”
他目光真诚,她缴械投降:“是我。”
程与淮出国之后,她隔一段时间就会飞到米兰,赌一赌碰上他的概率。如果见不到,她就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着他呼吸过的空气。
江稚鱼又说:“我来,是因为我喜欢你。”
程与坏最后还是说了抱歉,他告诉她,他目前还没准备好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江稚鱼挥挥手:“没关系,我拿得起放得下。”
可其实,从很早开始,她就放不下。
回去之后,江稚鱼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没有再跟以前一样偷偷飞去米兰看他,关于他的消息,还是无意间从手机上弹出的时事新闻上看到的。新闻上写着程与淮受邀去保加利亚演出,遭到两个暴徒抢劫,他的头部被暴徒用金属管重重一击。
江稚鱼疯狂给他打电话,不断按着重播键,可一直没人接,最后她推掉了国内的工作,飞去了米兰。
程与淮的情况不太好,大脑严重受创,右臂也因此失去活动能力。醒来后,他终日缄默寡言,房间里只有江稚鱼的声音。他唯一一次主动开口,却是劝她不必留在这里。
江稚鱼背对着他插花,装作没听到,从高中开始,她就喜欢耍赖。程与淮也深知这一点,又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她才转身:“我没奢望你能和我在一起,难道连喜欢也要被剥夺吗?”
她盯着他,眼窝里还有泪,说出来的话也是心酸到极致。程与淮心里很乱,过了好半天才说了一句:“对不起。”
后来他再没提过这件事,江稚鱼也变得忙碌起来,总是在打电话,眉头紧皱着。程与淮问起,她却笑着说没事。
米兰的冬季多雨,程与淮从梦中醒来时,江稚鱼正趴在床上睡觉,一旁的手机还亮着。他拿起来,见是一些关于手臂康复的医疗文献,划了几下,通篇都是难懂的专业术语。
他不知怎么就想到了出事后,江稚鱼在他床边哭得稀里哗啦,还有他劝她离开的那个下午,她也满眼是泪。
他压下心中的酸涩,迎着台灯昏黄的光,长久地盯着睡着的人。她向来炽热又明朗,她的爱也一样,披荆斩棘地在他的生活里开了一线天光。
转眼到了年底,江稚鱼托江父联系到了神经外科方面的一位专家,她跟程与淮坐飞机过去,但检查结果仍然让他们感到失望与遗憾。
从医院出来后,江稚鱼说:“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他们去了马略卡,她拉着他去参观了卡尔特会修道院,那是肖邦和他的爱人居住过的地方,也是程与淮最喜欢的地方。整栋建筑被橄榄树和杏树包围,小屋的墙上挂着肖邦的画像,下面放着一台使用过的钢琴。
江稚鱼说:“我本以为会治好你的手臂。”
她垂头丧气地咬着唇,看得程与淮有些难受,他伸出左手牵住她,开口时声音有些哑:“江稚鱼,谢谢你。”
他们在马略卡长住下来,江稚鱼养了一只狗,是隔壁老妇人送给她的。
江稚鱼坐在院子里逗弄小狗,程与淮就在靠窗的屋子里弹琴。他尝试着用左手和右手一根手指弹奏,日益熟练,盛夏时还参加了小镇举办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上台前,江稚鱼抱着小狗为他加油,程与淮笑笑:“你怎么比我还紧张?”
“当然是害怕你成为高不可攀的大钢琴家。”
他气笑了,故意逗她:“我现在退出应该还来得及。”
江稚鱼皱眉轻拍他胳膊:“说什么呢你。”
工作人员在喊程与淮,他紧跟着上台。演奏很顺利,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后过了很久,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程与淮用左手呈现的超凡效果让评委们震惊,他们用意大利语赞美他是坚强的贝多芬。程与淮演奏的视频在网络上的反响也很大,网友们没找到程与淮的社交账号,江稚鱼的账号倒是被扒出来了,春日里的那张合照下面是清一色的祝福。
江稚鱼将手机熄屏,朝程与淮笑:“他们吹彩虹屁,说你是走上神坛的男人。”
“那你赚了。”
“真自恋!”她挪到他身边,看向他手里的国际钢琴大赛邀请函,“什么时候呀?”
“二月。”
比赛地点在国内某一沿海城市,江稚鱼查了一下,那天正好是元宵,他们提前回了国,在国内过了除夕。
等到比赛那天,江稚鱼早早就准备好,一路上反复叮嘱他。这一次她格外紧张,早上起来右眼皮就不停地跳,心里也七上八下,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像踩在绵软的云上。
她在云上看见了弹钢琴的程与淮,与往日不同,曲子弹了一半,他的右臂再也没能抬起来。紧接着,她从云朵上摔了下去。
江稚鱼很久后才找到程与淮,他坐在音乐厅的角落里,低垂着头。她走过去坐在他旁边,音乐厅的灯逐一熄灭,他们的身影完全隐沉在黑暗里。
后来的那段日子,江稚鱼总觉得像做了一场灰色的梦,梦里是铺天盖地的谩骂,是荒诞不经的造谣,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恶意。
到最后,她支撑不住了。那天,她收到一个匿名包裹,里面是一只血淋淋的黑猫,她被吓得发起了高烧。
程与淮报了警,做完笔录已经是夜里。江稚鱼迷糊着醒来,脸上是不正常的红:“我不想待在这里了,我们回马略卡好不好?春天快要到了。”
他哑着嗓子说“好”。
可最后,他失约了。他换了手机号,抹去了有关她的一切消息,她怎么也找不到他。
之后,江父开了一场发布会,那些污蔑她的人纷纷道歉,世人也开始同情起她,日子变得和之前没什么两样,只是程与淮仍旧没回来。
江稚鱼后来又去了马略卡,他们租的那栋房子有了新的主人,隔壁的老妇人也搬走了,那只小狗则在他们离开后不久就死掉了。
一切似乎都变了。
她走过高低起伏的巷子时,看见一对挽着手的情侣正沿着墙边前行。街角的广播在放着肖邦的曲子,那天阳光很好,好到她总是想到他们的过去。
她还记得除夕那天,临近新年钟声响起时,她问程与淮的愿望是什么,他说了一句,却刚好被倒计时声音盖过。
墙壁上的花朵刚好落下,她的眼泪也落下。
最后她想,他的愿望应该是希望他们永远在一起。
程与淮去见江父时,是在他和江稚鱼约定去马略卡的前一天。
那天刚好立春,他坐在包间里,温润的日光落在他身上,暖洋洋的。包间外的大树上,树叶正在蔓发,一切仿佛都是重新开始的模样。
江父推门进来,坐在他对面:“有段时间没见了。”
是有段时间了,上一次是程与淮给江稚鱼补习功课,那天下午他到得早,江稚鱼在午睡,他敲响了江父书房的门。
“好久不见,江先生。”
“别来无恙。”江父虚盖着茶杯说道,“可否听我讲个故事。”
他讲的故事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一次音乐宴会上,女钢琴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歌坛新晋小生。喜爱音乐有共同语言,加之年龄相仿,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相爱的第五年,歌坛小生喝醉后靠在女钢琴家肩上的照片被媒体刊登在报纸上,引得女钢琴家父亲勃然大怒,她被迫嫁给了门当户对的青年才俊。婚礼当天,歌坛小生以好友身份出席。
之后本该开启各自的生活,然而两年后,歌坛小生抑郁成疾,最终抱憾离世。女钢琴家得知消息后不顾世俗非议为他扶灵送他最后一程。葬礼结束后,女钢琴家驱车离开,途中因伤心过度遭遇车祸,最后救治无效身亡。
“那个钢琴家是江稚鱼的妈妈,也是我的妻子。”
那一年,江稚鱼才两岁,还不理解离开的意思,只是看着躺在纯白床单上的妈妈不停地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醒过来?”
他没办法告诉她,她妈妈再也不会醒来了。
“之前您严格要求她练琴,也是因为您妻子吗?”程与淮问。
“是。”江父望着窗外。
出事那天,她被推进手术室前,看着他笑笑,那是她第一次对他笑,看起来像是终于解脱了。她用尽了力气缓慢地说:“如果我走了,你要照顾好稚鱼,好吗?”
他哭得像个孩子。她一语成谶,没能走出手术室。
“稚鱼随她妈妈,有时候我看着稚鱼弹琴,总是会想起几十年前的她。”他苦笑道,“我对她严格说到底也不过是出于自己的私心,总是沉溺在过去。”
那时江稚鱼正值叛逆期,他仿佛又要经历一次失去的痛苦,这种心情在得知她认识了学音乐的男孩后达到顶点,直到程与淮敲响了书房的门。
“江稚鱼很早就喜欢你,她做的那些事情我也都看在眼里,当然,我是不支持的。你去国外进修的资助金是我私下捐赠的,所以她更加反感我。你那时说理解与爱是相互的,我后来想通了些,只要她平安喜乐就好。”他的目光落在程与淮的右手上,“我只有这一个女儿,我拼了半辈子,也不过是想让她过得好一些,可如今,我真不知如何和她母亲交代。”
程与淮和江父聊了很久,傍晚时才起身。江稚鱼发来了消息,问他东西收拾好没。他站在树下,刚刚立春,风里还是卷着冬天的凉气,他的影子也显得很孤独。良久后,他回复:“江稚鱼,对不起。”
他本打算回到马略卡之后就向江稚鱼表白,他们重新租一个大点的房子,把那只小狗养大。可他无法忘记江父推开椅子向他下跪的那一幕,他所有的话语堵在了喉咙里。
如同他很早就说过的,理解与爱是相互的,可那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或许分别与爱也不一定是相背的。
他会一直记得,马略卡的春日里,她抱着一只小狗,让他弹奏肖邦的《小狗圆舞曲》,脸上是明媚的笑。
原来,那是他与她共度的最后一个春天。
(编辑:白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