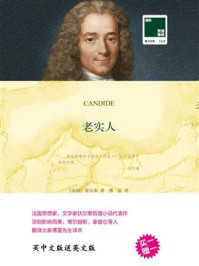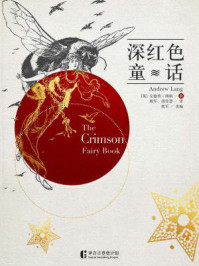瑞那夫人天性纯朴,加上眼前的幸福,心情好得像天使般温柔,只有想到侍女艾莉莎,心头的甜蜜才有点变味。这位姑娘新近得了一笔遗产,去向谢朗神甫做忏悔时,吐露出想嫁给于连的打算。神甫真心为弟子红运高照而感到高兴,哪知于连对提婚之议,一口回绝,使教士极为惊讶。
“我的孩子,你对自己的心思,也要注意一下,”教士皱着眉头说,“这笔财产,可保温饱而有余。假如是为了舍身奉教,而不屑一顾,我当然要向你致贺。我在维璃叶当本堂神甫,于今已有五十六年。然而,根据种种迹象看,我的职务快保不住了。这件事,很伤我的心,不过好歹每年还有八百法郎收入。我讲这一细节,是想告诉你,不要对神甫一职抱什么幻想。如果想攀附权势之辈,那肯定会万劫不复。要想发迹,势必会损害穷苦人民的利益,去奉承区长、市长、名流,投他们所好,为他们效劳:这种行为,社会上称为处世之道,对一个世俗中人,与灵魂的得救倒也并非完全水火不容。但处于我们的位置,就应该有所选择:不是追求尘世的富贵,就是向往天国的福祉,别无折中的办法。小朋友,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三天之后,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我很难过,看到你心灵深处郁积着一股热情,表明你还没有那种教士必备的克制功夫和舍身精神。以你的聪明,我可以预言你前途似锦,不过,允许我说句老实话,”善良的神甫说到这里,眼角噙着泪水,“作为一名教士,对你的灵魂能否得救,我不无担忧。”
于连为自己动了感情而深感羞愧,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自己受人关爱。他喜极而泣,便跑到维璃叶后山的大树林哭了个痛快。
“为什么我会这样呢?”临了,他自问道,“我觉得,我可以为了善良的谢朗神甫百死而不悔,然而,他刚才向我指明,我不过是傻瓜一个。我本想瞒骗他,而他却把我看透了。他对我所说的那郁积的感情,正是我求富贵的渴望。原想着牺牲五十路易的年金,他会对我的虔诚说句其志可嘉的好话,可偏偏在这当口,他认为我不配当教士。”
“今后,我就凭自己性格中坚毅可靠的那部分为立足根本。”于连继续想道,“谁还能说我曾号啕大哭以求一快,曾对说我是傻瓜的人表示过敬爱!”
三天后,于连终于找到了托词,他本该一上来就想好的。这个托词,纯系诽谤,但诽谤又怎样?他故意闪烁其词,向神甫承认,心中有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因为涉及第三者,使他一开始谈论婚事,就不予考虑。这无异于说艾莉莎品行不端了。谢朗神甫在于连的神态中发现一种热衷浮华的情绪,这种凡俗之心与年轻修士身上的虔敬之道,是大相径庭的。
“小朋友,”谢朗神甫又说,“与其做一个没有信仰的教士,还不如老老实实做个博学多识、受人尊敬的乡绅。”
于连对这些劝诫,回答得很得体,至少在措辞上他夸夸其谈,把一个怀有宗教热忱的年轻神学士所能使用的词汇全都用上了,但他说话的声调和眼底包藏不住的火焰,使谢朗神甫深以为忧。
对于于连的未来,似乎不宜做太坏的评估,因为他兼具圆滑与审慎,把一套虚伪的论调编得找不出漏洞,在他这个年纪,已实属难得。至于声调和手势,是因为他一直混在乡民中间,还没见过大场面。以后,一旦有机会接近上流社会的先生,那无论是姿势还是措辞,就会粲然可见了。
瑞那夫人感到纳闷的是:其侍女新近得到一大笔钱,却不见她心情更快活。只看到她三天两头去见神甫,回来时总眼泪汪汪的。后来,艾莉莎把自己的婚事跟女主人说了一下。
瑞那夫人听后,以为自己得了病。人像发热一样,夜不成眠。只有看到侍女或于连在侧,才觉得活了过来。她日夜想着他们,想着他们婚后的幸福光景。一个小家庭就靠五十路易来维持,固然是穷,但在她心目中却颇具迷人的色彩。那时,于连很可能到专区首府布雷去当律师,离维璃叶只有十五里路,在这种情况下,偶尔见一面的希望还有。
瑞那夫人真以为自己快要疯了。她告诉了丈夫,后来果真病倒了。当天晚上,侍女进来服侍,她发现那女孩在抽泣。最近,她恨透了艾莉莎,刚才还数落了她几句,这会儿觉得不好便开口请侍女原谅自己脾气不好。不料艾莉莎泪水冒得更凶了,说要是太太允许,她想把自己的不幸事儿说一说。
“那你就说吧。”瑞那夫人答道。
“唉,太太,想不到他会拒绝我。一定有人跟他说了我的坏话,他就信了。”
“是谁拒绝呀?”瑞那夫人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还有谁,太太,除了于连先生,”侍女抽噎着说,“神甫先生也拗不过他。因为神甫觉得,他不该拿当过女佣为借口回绝一个正经姑娘。说穿了,于连先生的父亲,也不过是个木匠。就他自己,没进太太家之前,又是什么样儿呢?”
后面的话,瑞那夫人都没听进去。她亢奋已极,神志几乎都不管用了。她让侍女把于连回绝的话说了又说,据说态度之硬,已无反悔的余地。
“我愿意替你做最后一番努力,”女主人对侍女说,“由我出面,跟于连先生说说看。”
第二天午饭后,瑞那夫人心里不无快意,去为她的情敌做说客。谈了一个小时,看到艾莉莎的婚议和财产一再遭到婉拒。
于连慢慢地不再做千篇一律的回答,对瑞那夫人的好言规劝,能很机智地挡回去。几天陷于绝望,瑞那夫人抵御不住了,任幸福的激流洋溢她的心田。等她恢复神志,在卧房安歇下,便遣开众人,这时,她自己都大吃一惊。
“莫非我爱上于连了?”她终于这样自问。
这个发现,换了别的时光,她一定会愧疚不已,坐立不安,而此刻,对她不过是很别致的人生一境,而且好像有点事不关己似的。风波过后,只觉得心疲身软,连最强烈的感情也无能为力了。
瑞那夫人想做点事,不料却昏昏沉沉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倒也不十分惊恐。她太幸福了,很难把事情往坏里想。天真、纯朴、善良的内地女子,绝不至于为了感受新的情致或忧苦而折磨自己的灵魂。于连到来之前,她整个身心都被一大堆家务事吸引了去——在远离巴黎的地方,这就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命运。瑞那夫人对于激情,跟我们对彩票的看法一样:肯定会上当,只有疯子才去碰这种运气。
晚餐钟响,于连领着小孩回来了。瑞那夫人听到于连的声音,脸顿时涨得绯红。自从心有所爱以来,她学乖了,把脸红的原因,说成是头痛得厉害。
“女人就是这样,”瑞那先生呵呵一笑,“像台机器,这里那里,时时需要修补修补!”
这类打趣的话,瑞那夫人虽然早已听惯,但说话的声调,还是觉得非常刺耳。为了消闲遣闷,转而打量于连的长相,即使他是天底下最难看的男人,此刻也会讨得她的欢心。
瑞那先生刻意模仿宫廷显贵的习尚,每当春回大地,初逢佳日,就率全家搬到苇儿溪小憩。这个村子因一则中世纪的传闻,事关嘉白丽哀凄艳的遭遇而遐迩闻名。当地有一座哥特式古老礼拜堂,如今已断垣零落,却不失为一大景观。离废墟几百步远处,瑞那先生拥有一座古堡,内有两对塔楼和一座仿蒂琉璃宫庭院的花园。花园四边,广植黄杨;园内小径,栗树夹道——而且,栗树之属,一年要修剪两次。旁边有块地,种的是苹果树,是闲行漫步的好去处。果园尽头,有八九棵挺拔的胡桃树,枝叶茂密,绿荫蔽空,离地高十余米。
看到这几棵树,瑞那夫人常止不住要赞赏几句,她丈夫则说:“这些树真可恶,麦子在树荫下就是不长,每棵树叫我少收几担粮。”
田园景色,这一次对瑞那夫人似乎有耳目一新之感。赞之赏之,竟至陶醉。洋溢的感情,给了她机智和决断。到苇儿溪的第三天,瑞那先生因公务赶回小城,瑞那夫人便自己出钱,雇来一批工匠。是于连给她出了个主意,铺设一条沙石小路,以环绕果园并连接高大的胡桃树,这样孩子清晨散步,鞋子就不会被露水沾湿。这个方案从设想到施工,还不到二十四小时。这天,瑞那夫人跟于连一起指点工人干活,过得很愉快。
维璃叶市长从城里回来,大感惊异:路已经修好了!丈夫的到来,使瑞那夫人吓了一跳:因为她已忘了还有他这个人!此后两个月中,市长先生一讲起此事就非常生气,说她胆大妄为,这么大的改造工程,未与他商量就擅自做了。不过,瑞那夫人是自掏腰包,这点还觉得差强人意。
长日易度,白天瑞那夫人跟孩子们在花园里跑来跑去,捕捉蝴蝶。他们用薄纱做大网罩,去捉可怜的“鳞翅目昆虫”。这个佶屈聱牙的学名,是于连教给她的。因为瑞那夫人托人特地从贝藏松购来戈达尔的生物学著作,于连便跟她讲了不少有关这类昆虫的奇异习性。
这些可怜的蝴蝶,他们毫不留情地用别针钉在一张硬纸板上,这也是于连想出来的办法。
瑞那夫人与于连之间,终于不愁没有话题了。以前,碰到沉默的时候,于连像活受罪,现在就不必担这份心了。
他们话题不断,而且兴致极好,虽然谈的都是无伤大雅的事。生活变得忙碌而愉快,颇合大家口味,只除了艾莉莎,觉得活儿多得干不完。侍女说:“即使在狂欢节,维璃叶有舞会,太太也没这么用心打扮过。现在倒好,她一天要换两三套衣服。”
我们无意讨好任何人,但也不必讳言,瑞那夫人肤白如雪,她为自己剪裁了几件袒胸露臂的轻衫。身姿停匀,披上薄罗轻衫,真是娇艳惊人。
“夫人,你从没这么年轻过。”维璃叶的友人来苇儿溪赴宴,见到女主人时都这么说。(这在当地算得上一种恭维。)
说来奇怪,读者诸公也许不信,瑞那夫人这么精心打扮,似乎并无直接的目的,只是兴之所至而已。她无暇多想,时间不是消磨在跟孩子和于连一起捉蝴蝶,便是与艾莉莎共同制作新衣。她只回了一次维璃叶,因为想去采购密罗兹运来的夏季新装。
回到苇儿溪,瑞那夫人带来一位有亲眷关系的少妇。这位戴薇尔夫人是瑞那夫人从前在圣心修道院的同伴。瑞那夫人结婚后,跟戴薇尔夫人不知不觉热络了起来。
戴薇尔夫人听表妹讲的一些趣事——真乃疯头疯脑的想法——常常大笑不止。女主人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想不出这些念头。”这些出人意料的想法,即巴黎人所谓的风趣,瑞那夫人面对丈夫,就像做了什么蠢事一样,会觉得难以启齿,而跟戴薇尔夫人,则勇气大增。刚开始讲还有点腼腆,等两位夫人一起待久了,瑞那夫人神情就活跃起来,长长的一上午一眨眼就过去了,彼此心情非常愉快。知情识趣的戴薇尔夫人在这次拜访中,发觉她表妹虽不像从前那么无忧无虑,但生活肯定比从前快活得多。
至于于连,到了乡间,像回到了童年,跟他学生一样兴高采烈,跑着跳着去捉蝴蝶。受过种种约束,玩过种种计谋之后,如今洒脱自在,远离他人的视线,而且凭本能觉得对瑞那夫人不必害怕,尽可纵情于生活的欢快之中。尤其青春年少,置身于世上最美的群山之间,其乐何如!
戴薇尔夫人到后不久,于连就觉得可以跟她做朋友,便急巴巴地领她到新修沙径的尽头,大胡桃树的底下,把这一带的秀丽景色,指点给她看。以风光而论,这儿如果不比瑞士的山川或意大利的湖泊更美,至少也不相上下。向前走几步,沿着陡斜的山坡,很快就能登上一片高峻的悬崖。悬崖周边,都是橡树;崖石外突,几乎遥临河面之上。于连站在悬崖峭壁之上,快活,自在,甚至像是家中之王,陪伴着两位女性朋友,沉醉在她们对美景的礼赞之中。
“我觉得这仿佛就是莫扎特的音乐。”戴薇尔夫人称赏道。
维璃叶周围的乡野,不可谓不美,但兄长的嫉妒,父亲的横暴与呵责,在于连眼里,已无由见其妍丽。在苇儿溪,就没有这些苦涩的回忆,而且生平第一次,没碰到什么仇敌。瑞那先生留在城里的日子——这是常有的事,于连就可以大胆读书了。不像从前,他只能在夜里看书,还得小心提防,把花盆扣过来罩住灯光。很快,夜晚也不用苦读,可以安心睡觉了。白天,在教课之余,他夹了那本书来到岩壑之间,那本作为他行为的唯一准则,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的书。书中不仅有幸福与陶醉,也有失意时的慰藉。
拿破仑关于妇女的言论,对其治下某些流行小说的评说,使于连第一次获得某些有关的见解。其实,这些见解,对跟他同龄的年轻人来说,早已算不得新鲜了。
酷暑来临。晚上,到离房子不远处一棵繁茂的菩提树下乘凉,已成习惯。大树底下,浓荫幽深。一天晚上,于连一边讲,一边比方,向两位少妇侃侃而谈,自觉津津有味。他说着挥动起手臂来,不小心碰到瑞那夫人的纤纤素手,那手是搁在花园漆椅的椅背上的。瑞那夫人把手很快缩了回去,但于连想,他有责任叫这只手不缩回去。想到有一种职责要履行,事若不成就会徒留笑柄,甚至滋生自卑,于是,所有乐趣,顿时从他心头消散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