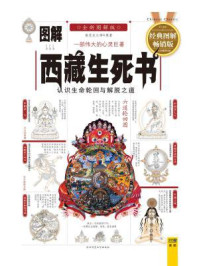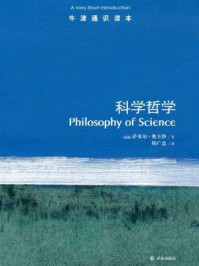知性思维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黑格尔说:“知性的定律是同一律,单纯的自身联系。”
 这种同一律同时也就是形式逻辑的主要规律,它的基本要求,就是以自身同一的观点来思考对象。知性思维在对混沌的表象进行抽象时,遵循的正是这种定律。它强调,某一规定即是某一规定,而不是其他。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单纯化”的方式。正是这一原则赋予思维以确定性:“无论在理论的或实践的范围内,没有理智(指知性——引者),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
这种同一律同时也就是形式逻辑的主要规律,它的基本要求,就是以自身同一的观点来思考对象。知性思维在对混沌的表象进行抽象时,遵循的正是这种定律。它强调,某一规定即是某一规定,而不是其他。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单纯化”的方式。正是这一原则赋予思维以确定性:“无论在理论的或实践的范围内,没有理智(指知性——引者),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
 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知性思维是形式逻辑原则在认识过程中的具体化。
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知性思维是形式逻辑原则在认识过程中的具体化。
然而,知性思维与形式逻辑的原则及方法并不完全相同。如所周知,形式逻辑所研究的,主要是思维的形式、结构,它并不涉及思维的具体内容。而知性思维的对象,则并不仅仅是思维的形式与结构,它同时包括感性直观所提供的各种有关客体的具体材料。换言之,知性思维并不停留在形式的推论上,而是着重于对感性内容的分析、抽象,等等。正是以具体事物为对象这一特点,决定了知性思维不仅要运用一般的形式逻辑的方法,而且必然直接或间接地与实践活动相联系,因为对象的内在性质既不是感性直观所能提供的,也不是单纯的思辨推论所能揭示的,它往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过程才能逐渐暴露出来。这一点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自然科学的实践亦即实验,实验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选择性、分析性:它总是在撇开对象的某些因素的前提下,亦即在纯粹的(理想化)的形态下突出、强化对象的另一些性质。可以说,只有在实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抽出事物的各个规定而精确地加以考察。例如,要把握某种客体的化学性质(亦即该对象的某一方面的规定性)就必须诉诸化学实验。在这里,知性离开了实验即寸步难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实验列为悟性(知性)活动的要素。
 从这方面看,如果把知性思维完全等同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则势必抽去其具体内容及客观基础,从而使之流于空疏。
从这方面看,如果把知性思维完全等同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则势必抽去其具体内容及客观基础,从而使之流于空疏。
将知性思维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等量齐观,
 是知性思维经常遭到的又一误解。从形式上看,知性思维与形而上学的方法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在抽象性、坚硬性(固定性)等方面,二者往往是相近的。但相似、相近不等于相同。如果作一番比较具体的分析,那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把形而上学方法与知性思维混为一谈的根据之一,即是认为二者均坚持抽象的同一,这样,欲区分二者,便不能不对知性思维的同一(亦即形式逻辑的同一)与形而上学的同一作一比较。知性的同一,如果以形式逻辑公式来表示,即是A=A,它强调的是对象的自身同一。所谓自身同一,即是肯定该物即是该物,而不是他物。至于对象本身的内在差异,知性并不加以否定,它只是不作研究而已。从逻辑上说,承认事物的内在差别与知性的同一并不矛盾,例如,说“A=A”与说“包含差别的A=包含差别的A”并不相互矛盾,而这两个命题都同样为知性思维所承认。如前所述,知性思维的成果是自身同一的抽象规定。从整个认识过程来看,这种自身同一的规定恰恰是以潜在的形式包含着内在差异(否则,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行程,就成了仅仅对各种抽象规定作机械组合的过程),因而知性思维对这些规定的揭示与肯定,同时也就以潜在的形式承认了其中蕴涵的内在差别。与此不同,形而上学的同一则完全否认了内在差别的存在,在它看来“包含差别的同一”这种提法本身是悖理的,同一只能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如汉代的哲学家董仲舒认为:“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
是知性思维经常遭到的又一误解。从形式上看,知性思维与形而上学的方法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在抽象性、坚硬性(固定性)等方面,二者往往是相近的。但相似、相近不等于相同。如果作一番比较具体的分析,那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把形而上学方法与知性思维混为一谈的根据之一,即是认为二者均坚持抽象的同一,这样,欲区分二者,便不能不对知性思维的同一(亦即形式逻辑的同一)与形而上学的同一作一比较。知性的同一,如果以形式逻辑公式来表示,即是A=A,它强调的是对象的自身同一。所谓自身同一,即是肯定该物即是该物,而不是他物。至于对象本身的内在差异,知性并不加以否定,它只是不作研究而已。从逻辑上说,承认事物的内在差别与知性的同一并不矛盾,例如,说“A=A”与说“包含差别的A=包含差别的A”并不相互矛盾,而这两个命题都同样为知性思维所承认。如前所述,知性思维的成果是自身同一的抽象规定。从整个认识过程来看,这种自身同一的规定恰恰是以潜在的形式包含着内在差异(否则,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行程,就成了仅仅对各种抽象规定作机械组合的过程),因而知性思维对这些规定的揭示与肯定,同时也就以潜在的形式承认了其中蕴涵的内在差别。与此不同,形而上学的同一则完全否认了内在差别的存在,在它看来“包含差别的同一”这种提法本身是悖理的,同一只能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如汉代的哲学家董仲舒认为:“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
 质言之,阴与阳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事物中,它们只能或者前后相继,或者分别存在于左右两方。严格地说,只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绝对同一,才是与辩证法所说的具体同一相对立的抽象同一。
质言之,阴与阳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事物中,它们只能或者前后相继,或者分别存在于左右两方。严格地说,只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绝对同一,才是与辩证法所说的具体同一相对立的抽象同一。
与“同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关,知性思维与形而上学在如何看待不同规定的区别这一问题上,也有着本质的不同。恩格斯说:“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起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别作为补充。”
 知性思维在坚持自身同一的同时,确实有执着各规定的分别而撇开它们的联系这一面。但是,首先,撇开联系并不意味着排斥联系,知性强调各规定之间的区别,旨在克服感性表象的混沌性:在表象中,各规定的特殊性质往往被整体上的混沌性、模糊性所掩盖,为了使这些规定以确定的形式呈现出来,就不能不暂时撇开它们之间的联系而着重考察其彼此界限,换言之,知性思维所坚持的区别性,实质上即是确定性,它的对立面主要不是各规定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是感性的混沌性、模糊性。知性虽然对诸规定的相互关系不加讨论,但它也并不否认这种联系的存在。其次,知性思维所说的区别,本身具有过渡的性质。知性思维专注于各规定的确定性(区别性),而一旦对规定本身的特殊性质加以深入的探究,则它与其他规定之间的固有联系即将逐渐呈现出来,这就在客观上为把握它们之间总体上的联系提供了前提。正是基于知性思维的这一特点,黑格尔把知性称为“使各规定性过渡的唯一的威力”,
知性思维在坚持自身同一的同时,确实有执着各规定的分别而撇开它们的联系这一面。但是,首先,撇开联系并不意味着排斥联系,知性强调各规定之间的区别,旨在克服感性表象的混沌性:在表象中,各规定的特殊性质往往被整体上的混沌性、模糊性所掩盖,为了使这些规定以确定的形式呈现出来,就不能不暂时撇开它们之间的联系而着重考察其彼此界限,换言之,知性思维所坚持的区别性,实质上即是确定性,它的对立面主要不是各规定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是感性的混沌性、模糊性。知性虽然对诸规定的相互关系不加讨论,但它也并不否认这种联系的存在。其次,知性思维所说的区别,本身具有过渡的性质。知性思维专注于各规定的确定性(区别性),而一旦对规定本身的特殊性质加以深入的探究,则它与其他规定之间的固有联系即将逐渐呈现出来,这就在客观上为把握它们之间总体上的联系提供了前提。正是基于知性思维的这一特点,黑格尔把知性称为“使各规定性过渡的唯一的威力”,
 也正是知性的这种过渡性质,决定了它并不构成关于外部世界的最后定论。与此相反,形而上学并不是从克服感性的模糊性与笼统性、保证思维的确定性这一角度强调事物各规定之间的分别,而是把区别本身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而加以无限夸大,以此排斥相互联系的原则。在它看来,对象的诸规定之间既然有确定的界限,那么它们必然就是彼此隔绝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
也正是知性的这种过渡性质,决定了它并不构成关于外部世界的最后定论。与此相反,形而上学并不是从克服感性的模糊性与笼统性、保证思维的确定性这一角度强调事物各规定之间的分别,而是把区别本身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而加以无限夸大,以此排斥相互联系的原则。在它看来,对象的诸规定之间既然有确定的界限,那么它们必然就是彼此隔绝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
 这就完全勾销了事物之间的关联。如果说,在知性思维中,客体之诸方面的区别具有相对的(过渡的)特点,那么,形而上学则赋予这种区别以绝对的、最终的性质,从而使之泛化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
这就完全勾销了事物之间的关联。如果说,在知性思维中,客体之诸方面的区别具有相对的(过渡的)特点,那么,形而上学则赋予这种区别以绝对的、最终的性质,从而使之泛化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
在肯定知性思维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本质差异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停留于知性思维,否认其过渡性(亦即否认从知性向理性转化的必要性),把知性思维的成果视为完成了的、最终的认识形式,那就不可避免地将走向形而上学,例如,把知性的同一绝对化,使之成为思维的唯一原则,那就容易转化为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把抽象规定之间的区别推向极端,则势必导致孤立、静止的思维方式,如此等等。为了避免从知性思维向形而上学的转化,就必须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将知性“隶属于辩证法之下”,
 换言之,也就是自觉地把知性思维作为辩证思维(理性思维)的一个从属环节。
换言之,也就是自觉地把知性思维作为辩证思维(理性思维)的一个从属环节。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 K. Smith,Bedford/St. Martin's Boston,1965,p.93.